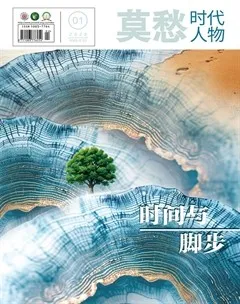来萧寺问年华
常熟虞山下有座庙,名唤兴福寺。萧梁年间,上既有天子以身事佛,下亦不乏刺史舍宅为寺。于是,兴福寺成了“南朝四百八十寺”之一。
大唐天宝,来了一位“竹杖芒鞋”的“背包客”,纵使尘满面、鬓如霜,也难掩眉目间残存的清朗。当他看到寺前涧泉淙淙,林后幽鸟鸣啭,顿然心生欢喜,须臾间,他脑海中灵光一现,随口吟道:“清晨入古寺,初日照高林。曲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山光悦鸟性,潭影空人心。万籁此都寂,但余钟磬音。”
一千两百多年后,同样的一个清晨,我走进了同样的兴福寺,忍不住“按图索骥”。那条石子小道,觉得是当年诗人走过的;“曲径通幽”说的是山坡上那片竹林;再观花木深处,亦是昔日老僧盘腿打坐的禅房;茶馆旁的空心潭,更是当年诗人用来泡茶喝的泉水;救虎阁前,方方正正的白莲池更似一块端砚,蘸池水为墨,以青竹为笔,必能写下“一倡而三叹”的珠玑妙句。镇寺之宝“三绝碑”更是集米芾的手书、常建的诗歌、穆大展的雕工于一身。
千百年后,斯人已逝,而兴福寺依旧是唐诗里的那个兴福寺。正史对这位作者的生平,不过寥寥数语,常建是幸运的,他未及弱冠便进士及第;常建又是不幸的,他官运奇差,蹉跎至中年才混上九品小吏。拿惯了笔的手使不惯刀枪,于是干脆裸辞,寻找心中的诗和远方。
江南的寺院大多如园林般精致典雅,楼阁依山而筑,廊道错落有致,院落次第连绵,花木掩映其间。常建蹲在潭畔,忽然,大殿里传来一阵洪亮梵音:“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原本在入世和出世之间彷徨犹疑的他,身心一振,顿然生悟。此后,遁隐林泉,史书中再无有关他的只言片语。
如果说,常建是尘心里的佛界,那么,翁同龢就是佛界中的尘心。公元1898年,兴福寺来了一位鹤发老者,他佝偻着腰,拄着拐杖,慢悠悠跨过通往寺庙的青石板桥,两扇幽深的大门在他面前打开。当他正欲抬脚跨过山门之际,忽然扭转了头,老人浑浊的老眼漠然打量了一下门外的世界,善男信女们扶老携幼,在曈曈人影中,他看到的是虔诚无比和苦海无涯。“山中藏古寺,门外皆劳人”,一声轻叹,背过身去,从此,廉饮堂成了他生命中最后的驿站。
这位貌不惊人的老者叫翁同龢。他21岁选为拔贡,23岁中举,27岁进士及第,妥妥的“学霸”。可会读书并不见得会做官,尤其在风云诡谲、暗流涌动的18世纪末,中法战争、洋务运动……“子曰诗云”这套早已跟不上时代步伐了。
翁同龢的才干、威望并不足以持国服众,他凭借“帝师”身份,一方面窥伺君意,主动奉迎,积极成为甲午战争首席“主战派”;另一方面,因与李鸿章有私隙,不拨一毛军费,导致经年未添寸舰,一支世界顶级的海军,竟亡于党争。“居心叵测,并及怙权”,老亲王的临终遗言,让小皇帝下了铁心罢黜。一纸“革职,永不叙用”,切断了师徒间所有的情分,“交地方官严加管束”,言辞之间颇有画地为牢的味道。
翁同龢没有纨绔柳永“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的洒脱不羁,便将“一生几许伤心事”销了空门去。他经常找方丈主持谈经论禅、切磋佛理,但更多时候,却是一个人站在殿前那棵五百多年的樟树下,透过萧瑟而固执的枯枝,仰望着水洗般高而湛蓝的天空。
寺庙的大门,在兴与废、毁与建的更迭劫数中开开合合……与别处寺庙不同,这里没有缭绕的香烟,倒是还原了禅佛的本真。除了擦肩而过的缁衣僧侣,几乎不见人影,合了“万籁此俱寂”的本意。老子说归根曰静,意思是,万物之根来自静,回归静,方为回归生命之源。
兴福寺有为那句“曲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来的,也有简单直接奔蕈油面来的。这碗用虞山的野生菌菇为原料熬制的面,最早只是常熟兴福寺和尚和香客食用的一道素食。翁同龢、宋庆龄姐妹等吃过后大加赞赏,一传十十传百,大家趋之若鹜,使蕈油面成为常熟市非物质文化遗产。
深秋时节,兴福寺赏枫正当时。千余株红枫与千年古木、青瓦黄墙交相辉映,是让人无法忽视的存在。每一片红叶都蕴含着禅意,在风中低语,与钟声共鸣。光与影斑驳交错,恍惚间有种不知今夕是何年的错觉。
对比那些装修辉煌的寺庙,兴福寺透出一种历史悠久的文化气息。轻悠空灵的经文声和深沉优雅的檀香,还有那艳丽逼人的红色,带着一种独有的静寂与肃穆。
图片由本文作者提供
编辑 周晓序 2475496811@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