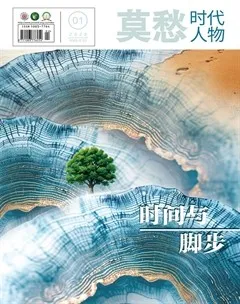冬不再寒
《列子·汤问》中说,凉是冷之始,寒是冷之极。《说文解字》亦言:“寒,冻也,从人在宀下,以茻荐覆之,下有仌。”意思是人蜷缩在室内,以草避寒,外面有冰。可见,冬渐深,寒意浓,岁月染寒,人间已冬。
按理来说,生居北方,理应爱冬,但于我而言,冬的记忆并不那么美好,却是一种刻骨铭心的“寒”。
20世纪80年代,我在鲁西北平原的农村长大,当时生活条件异常艰苦,房屋虽说是砖砌的,但保温性能很差,老式的木头门窗已经严重变形,留着不大不小的缝隙,凛冽的寒风会趁虚而入。那时,取暖设备是蜂窝煤炉子,晚上睡觉的时候还要封死,以免煤气中毒。孩提之时,冬天最不爱干的事,就是早晨从暖暖的被窝里爬出来,因为要穿的衣服都是冰凉的。这时,早起的母亲就会把棉袄、棉裤拿到炉火上先烤一烤,让我趁热穿上。那时,我感觉炉火之暖是世上最惬意的暖。
五年级的时候,我转到镇上的小学读书,距家有四五里路,由于学校没有食堂,只能每天骑着自行车来回跑。冬天尤为艰难,不仅要上早自习,还要上晚自习,每天上下学得骑行四五十里路。寒冬季节,朔风凛冽,逆风行车,犹如刀割,刺痛肌骨,而且那时的冬衣,棉絮为主,臃肿不堪,透风撒气。长期与寒为伍,导致手脚、面颊、耳朵等都生了冻疮,让人不忍直视。最难熬的是,春暖之时,冻疮渐好,奇痒难忍。
20世纪90年代初期,我到县城读高中,学校条件不算好,宿舍是由原来的平房教室改建的,门窗也是木制的,严重变形,就算关着门,寒风也是无孔不入,而且宿舍里没有生炉火。一间教室住着七八十人,异常嘈杂。极寒天气,宿舍里犹如冰窖,晚上睡觉需要盖着两层厚厚的棉被。那时,晚上钻被窝是一件极其考验意志力和忍耐力的事情,脱掉暖暖的衣服猛然钻进冰冷的被窝,顿时像触电一般,痛彻全身。无奈之下,只能穿着袜子和秋衣秋裤,先把被窝焐暖和后,再脱去袜衣,方能安然入睡。如此境况,持续了两年,之后搬到了新盖的宿舍楼,第一晚,室友们兴奋得彻夜未眠。
时光荏苒,进入21世纪以后,无论是上大学还是参加工作,无论是租房还是买房,都有了取暖设施。我对寒冷最深刻的记忆从未再超越儿时和读书时的阈值。如今,家乡的条件早已今非昔比,就算村里的小学也用上了炉火或者空调。仍然居住在农村的父母,也用上了天然气炉取暖,房子经过翻新以后,保暖性能也大为改观,冬寒似乎离我渐行渐远。
一个严寒的冬日,我和女儿去爬山,面对枯山、寒枝、烈风,女儿叫苦不迭,后悔跟我而来。我跟女儿讲起了往事,还有那刻骨铭心的“寒”。女儿听后眼睛飘向远方,我晓得她没有切肤之感是很难理解我所描述的那种“寒”,这或许就是岁月的代沟吧。
追忆过往,世事沧桑。我想说,其实冬寒的温度相差不大,变化的是社会的发展、境遇的改善和能力的提升。如今,岁月安然,冬不再寒,但我依然要珍藏那份“寒”,因为它可以让我搏击梦想、催人奋进。
编辑 马哲 xjjyh_326@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