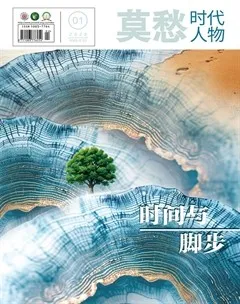我们都记得
一
2006年年末,凭借在大学期间公开发表的近百万字作品,我入职武汉一家当时月发行量近千万份的知名杂志社,做文字编辑。
那年冬天,武汉异常干冷。那天,我提交的选题全部被否。下班后,同事们陆续离开,我独自坐在看似充满书香实则为工业流水线车间的办公室,被一种强烈的绝望感紧紧包围。
在那家杂志社工作的岁月,这种绝望感如影随形。直到我多年后离开时才明白,这是管理者有意为之的管理策略。他们认为,置之死地而后生,釜底抽薪才能重生。确实有许多同事在这种管理方式下爆发出了潜力和创造力。然而,绝望对我来说,只会带来无力感,以及自我怀疑。
次年3月,春寒料峭,我到南京组稿。确切地说,是前往《莫愁》杂志社。当时,经人介绍,我了解到,在《莫愁》杂志社工作的尹伏仓,擅长撰写我所供职的这家杂志所需的稿件。而我之前又“恰好”在《莫愁》发表了多篇文章。
我已经不太记得当时与尹伏仓交流的具体情况,以及我是如何完成组稿任务的。但我清楚地记得,时任《莫愁》总编助理兼“智慧女性”版编辑部主任汪小农老师盛情请我吃饭,吃的是火锅,一起来的还有当时“智慧女性”版编辑陆艾涢。那时的陆艾涢,尽管已是资深编辑,却依旧保持着一种初出茅庐的清新气质。一头长长的乌黑秀发,言谈不多,却总是能细心地关照到每个人。那顿饭,我们谈笑风生,好不畅快,空气里弥漫的都是温暖和青春的气息。
《莫愁》杂志社的盛情款待,是对同行的热忱欢迎,也是对作者的尊重,但归根结底,是对人的尊重。这份热情和尊重,是《莫愁》的底色,也是一份文化产品应有的精神。它让我感受到了温暖和力量,我甚至因此爱上了南京这座城市。后来,有一次,我从温州组稿归来,还特意绕道去了一趟南京。
二
2011年,《莫愁》杂志社在南京举办笔会,已经到苏州生活的我有幸受邀参加。在笔会上,《莫愁》“天下男人”(后更名为“时代人物”)版主编家英宏对我说:“我原以为你不会离开,没想到你竟然辞职了。”当时我并不是家英宏的作者,这也是我与家英宏的初次见面,他却对我表示了如此深切的关注,并说出这样一番话,着实让我感到既意外又深受感动。由此,时至今日,我依然记得他的这番话。
当我摸清了知名杂志发稿套路,并开始稳定地发稿后,我果断地离开了这家杂志社,转而加入另一家杂志社,担任副主编兼编辑部主任。但不久之后,我再次辞职,离开武汉,前往苏州生活,让身边所有人惊讶不已。
说回这次笔会。我见到了自己曾经担任杂志编辑时的作者唐新勇以及同事黄利军等老朋友。原来,大家都是《莫愁》的作者。在笔会交流环节,我自豪地提到一年内在《莫愁》系列刊上发表了16篇文章。唐新勇也不谦虚地表示,他一年内在《莫愁》系列刊上发表了18篇文章。大家虽是朋友,但也暗自较劲在《莫愁》的发稿量。那真是一个写作者以在《莫愁》上发表文章为荣的黄金时代。这就是《莫愁》的魅力所在。
这次笔会上,除了家英宏,我还遇到了《莫愁》许多可爱且风格各异的编辑们。比如钟健,他利用空闲时间自驾游去了许多地方。2023年1月,我的稿件转到了钟健手中。他神通广大地找到了我的微信并添加我为好友,向我索要稿子的照片。钟健竟然还能“对得上号”我,我祝愿他在新的一年里继续畅游祖国的大好河山,他听后哈哈大笑。我们都记得。
笔会结束的那天晚上,我没有返程,而是留在了南京,见到了严培红。严培红负责《莫愁》发行工作,而我是写作者,我已经记不清两个不是同一业务线的人是如何坐到一起的。只记得那天晚上,我们喝了好多好多酒,一瓶接一瓶。饭桌下是一个网兜,方便客人放置随身物品,而我们那张饭桌下塞满了空酒瓶。酒意正浓,我们说了好多好多话。从《莫愁》杂志聊到各自的生活。这是我们第一次见面,但因为《莫愁》,我们像是久别重逢的老友。
三
2021年12月31日,暮色中,我站在刺骨的寒风里与已是《莫愁》总编的陆艾涢通电话,敲定了在“智慧女性”版开设“跟翁炫读红色经典”的专栏。撰写本文,是2024年12月31日。搁在以前,这或许是巧合,但是,今天看来,这一定是天注定。
从2021年12月到2024年12月,一眨眼,三年时间。在这三年里,除了撰写“跟翁炫读红色经典”专栏,我还重新拾起笔杆,陆续为《莫愁》撰写了其他文章。每到年末,我都会不由自主地陷入一种看似矫情实则难以抑制的感伤。我便在微信上,看似客套实则发自肺腑地感谢陆艾涢。如果不是给《莫愁》撰稿,这些日子,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如流水,无留痕。工作无比繁忙的陆艾涢总是耐心地回应我、鼓励我、肯定我,就像那个春寒料峭的3月一样。
又是3月。2023年3月31日,我去南京办事,顺道到《莫愁》杂志社,见到了陆艾涢。这是我们十六年后的重逢。吃饭的时候,我问陆艾涢记不记得那年吃火锅的事,她说不记得。不过,她又提到,当年见到我的时候,我的眼睛又大又明亮,而现在我戴上了眼镜。其实,我们都记得。
前不久,我将《莫愁》杂志上的文章转发到了微信朋友圈。黄冠突然出现,问我是不是到《莫愁》杂志社工作了?我回复说,是不是我们写稿发稿还是昨天的事?其实快过去二十年了,我也快40岁了,40岁怎么可能再折腾去南京呢!黄冠显然才意识到时间的流逝之快。随后,黄冠连续给我发了三个哭泣的表情。黄冠是我在《莫愁》的第一位编辑,也是唯一一位离开《莫愁》编辑岗位后我们仍保持联系的编辑。
是的,2025年,我就40岁了,《莫愁》也迎来它的40周年。家英宏向我约稿,在《莫愁》创刊40周年之际,请我写一篇与《莫愁》的故事。我说,我已经料到2025年《莫愁》会征集40周年纪念稿件;我也想过,如果我来写,该从哪里着笔。但是,我没有想好。可能我还没开始写,情感和思绪就已经泛滥成灾了。实际上,当我写完这篇文章,写到这里的时候,我已经泪流满面泣不成声了。
(作者系《莫愁》杂志长达二十多年的忠实读者和作者。在《莫愁》杂志“智慧女性”版开设专栏“跟翁炫读红色经典”;在《莫愁》杂志系列刊发表文章超过60万字。)
编辑 王冬艳 437408345@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