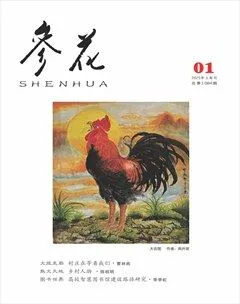乡村人物
牛伯伯
去年国庆节,母亲惦念她的爱孙,把乡下的农活儿留给了父亲,上城里来小住。来时,总忘不了带上几样新鲜蔬菜。在与母亲的闲谈中,她告诉我,原来生产队的牛伯伯去世了。我感到有些惋惜。
牛伯伯的真名叫李宝生。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期,我所在的村庄只有一台拖拉机,就留下了一头耕牛帮助拖拉机完成耕田任务。牛伯伯从小放牛,懂得牛的性子,熟悉牛犁地的一套方法,便成了村里的养牛耕田手,社员们都称他为“牛伯伯”,他默允了。时间一长,人们几乎忘记了他的真名,小辈们更加不知道,都随着大人叫。他的真名就像田地里的陈芝麻烂谷子,成为陈年往事。
为了方便对牛的护理,牛棚便临水而筑,与牛伯伯所住的小瓦房近在咫尺。牛棚的整个架子用杂木组成,顶是稻草盖的,显示着浓郁的乡村气息。河边筑有石驳岸,栽着一排杨柳,杨柳的空隙之间铺着洗衣淘米的石级。河里边,常有捕鱼的网船划过,也有运载农作物的橹船摇过,在水面涌起层层波浪。牛伯伯和一头老牛就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
牛棚内没有一件多余的摆设:碗口粗的槐树棍打了一个地桩用来拴牛,那地桩十分结实,不结实,怎么拴住千把斤的老牛,即使老牛有倒拔杨柳之力,地桩也纹丝不动。棚内的地,被老牛长年累月踩得要多瓷实有多瓷实,整块地如一把巨大的青铜镜泛着古拙的光。一把厚重的铡刀固定在长木凳上,养牛铡草的人可以坐在凳面上铡草。所铡的牛料,是清白稻草,或者是晒干的青草。铡好了,一捧一捧喂牛。放牛料的用具,是一个老石臼,由乡间石匠用金山石凿成,有两百来斤重,怕老牛使性子时撞翻。老牛好像从不挑剔所喂之料,张大着嘴嚼着,享受着田野美味。它知道只有吃饱了喝足了才能完成它的使命,把一块一块换季播种的土地深耕,让土地变得肥沃,让土地的主人有个好收成。我一见到这把铡草的大刀,就想起开封府处决犯人的那几把铡刀,感觉有点恐怖。但此地是乡村牛棚,并不是威名赫赫的开封府,铡刀的用途是铡草而已,就像家里厨房砧板上的菜刀,是一种日常生活用具。
暖和的日子,牛伯伯每天放两次牛,让牛到田野去活动活动筋骨,吃点鲜嫩的青草,把牛喂肥了好长力气。炎热的夏天,牛伯伯常牵着牛,来到小河浅滩上,让牛下水洗澡,牛与人一样也要讲究卫生。年深日久,那滩给牛蹲滑了,人们便称其为“牛窝潭”,成了地名。那牛健壮有力,犁起地来从不偷懒,那犁起的月牙形的土,从本来结实的地里翻滚过来,无声无息,静卧着,等太阳一晒,就变得疏松。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农忙犁地,自然是牛伯伯最辛苦的时候。牛伯伯赶牛犁地,有他自己的一套方法,他懂得不能让牛犁得太久,否则牛会累坏,要让牛适当休息,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特别是扶犁,更是一门学问,要随地形的深浅掌握,不能使拉犁的牛感到不适。
我喜欢看牛伯伯犁地,如行云流水一般。牛走在前,犁拖在牛的后面,牛伯伯扶着犁走在牛后。他弓着身,弯成犁把状。犁地老牛的哞哞长歌,犹如山脚下古寺的晨钟暮鼓,散漫的脚步踏出田野青青的禾苗。老牛低头拉犁的姿势,仿佛是运河上的纤夫,犁起的黄土泛着光亮,像堆积的金黄的稻谷。牛伯伯赶牛犁地是留在我记忆中的一幅农事画。其实,犁地并非舒适悠然,犁地是一种技术性的农活儿,没有经历过犁地的人难以懂得其中的甘苦与奥妙。牛伯伯犁地的辛苦从不写在脸上,他总是那么乐观,扶着犁赶着牛唱他的山歌:大姐嫁了渡船上,摇来摇去好风光;二姐嫁了网船上,鱼腥虾蟹吃不光。那歌声抑扬顿挫,引得孩子们跟在后面哈哈笑。
农闲时,孩子们都喜欢和牛伯伯玩,听他讲故事:“程咬金”“傻女婿”“盗仙草”“江西人识宝”等。让我记忆犹新的是“桃园三结义”的故事。牛伯伯讲起故事来声情并茂:那年,刘关张三人认识后,在张飞家后花园内结拜兄弟。一报年龄,三人同年同月同日同时生,谁是老大,这就难了。张飞要做老大,关公不答应,刘备不说话。张飞说,园内有棵大树,看谁爬得高,谁是老大。张飞从小会爬树,一下子爬到了树顶。关公爬了一半,坐在树杈上。刘备不爬,就在树根上一坐。张飞说,我是老大。关公说,要请个长者来评理。此时,正好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经过这里,就请他来评判。老人说,树高千丈,叶落归根,坐在树根上的最大。这样,刘备就做了大哥,关公第二,张飞做了小弟。有趣的故事吸引着孩子们。
我们几个伙伴常去牛身上拍牛虻。那牛虻是一种专叮牛的虫子,体如蜜蜂,金眼睛特别大,仿佛牛眼。牛伯伯碰见了,就骂我们:“小赤佬!当心老牛发脾气,一脚把你踩死,快走!”那年月,“粪是田中宝,种田少不了”。放学后,父母常叫男孩子到田野去拾粪,有时难拾,就到牛棚内偷牛粪。牛伯伯瞧见了,便破口大骂:“小赤佬,你们瞎眼了!这是集体的粪,谁敢偷?回头告诉你们父母。” 牛伯伯生气地用牛鞭把我们吓跑。现在回想起牛伯伯的骂,其实是对孩子们的关心,是对集体的爱。
到了一九七六年,牛已老态龙钟,不能犁地,村里也准备全部用拖拉机耕田。寒冷的冬天,生产队长叫牛伯伯把牛杀了,分给各家各户。牛伯伯舍不得杀牛,但队长的话他又不得不听。这一夜,牛伯伯没有合眼,在牛棚坐了一夜,足足抽了一包“经济”牌香烟,一个个烟头丢在脚边,陪牛度过了最后一个晚上。黎明时分,牛伯伯开始做杀牛的准备,削了五个树桩准备拴牛,“咔嚓、咔嚓”的磨刀声在河面上飘荡,惊醒了沉睡的村民,大家都到望虞河边看杀牛。
全队的社员几乎都来了。牛伯伯牵着牛迈着沉重的脚步走过来,选好一块空地。生产队长帮忙打桩,一共打了五个,中间一个拴牛绳用,角上四个拴牛脚。一切准备好,牛伯伯最后一次站在牛身边抚摸它,依依不舍。老牛懂事,流泪了,像狗一样忠诚,也像一位风烛残年的老人即将离开他的老伙计。在队长的再三催促下,牛伯伯强忍着泪水,在老牛头上蒙了一块黑布,把牛眼遮住,套在牛脚上的四根绳子一用力,老牛便趴下了,牛伯伯举起雪亮的大刀劈下,血涌如泉……
这天,生产队每家分到了几斤牛肉。傍晚,我到牛伯伯家去,见他坐在房檐下的台阶上抽闷烟,眼泪汪汪,手中抚摸着牛鞭,出神地望着牛棚的方向。我没惊动他,也不愿惊动他,因为这么多年来,他与牛的亲情是难以割舍的。
一晃四十多年过去了,牛伯伯也离开了人间,但他在我心目中留下的印象,如同牛在他心目中一样难以抹去。
厨师潘小连
以前,潘家厨师在村上是比较有名的,潘小连就接受过潘家厨师的传承。
我们村流传着一句歇后语:潘家厨师——大手。
什么意思呢?打个比方吧:东家举办婚宴,一般的厨师分切咸肉时,都是一薄片一薄片装盆;而潘家厨师是一大块一大块分切装盆,厚度超出常规,手面大,实碰实,才落了个不知是讽刺还是赞扬的名声。
老一辈的潘家厨师我没见过,只熟悉潘小连。平民百姓家办事很少请小连,因为生活条件普通,办事用钱精打细算,请的厨师当然也有讲究,不能大手大脚。有一次,一农家当面要求小连把肉切薄点,他一口回绝:“这不是潘家厨师的风格,切在盆里的肉被一阵风刮走,你下次另请高明,别坏了我潘家厨师的名声!”农家怕准备的菜出洋相,急得双手拍大腿:“好你个潘家厨师!你是死要面子,我是活受罪。”富人家有请小连的,办事要面子,但毕竟那年代富人少,所以小连的生意不景气,只逢年过节做几回厨,生活贫困。
我认识小连时,是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他当时已经六十开外,不折不扣一个小老头的模样。鼻子是常年红的“酒糟鼻”,如一颗红提子镶嵌在鼻梁上,不知是他用手多摸多捏所致,还是当厨师时火烤火燎所致。宽宽的嘴巴,牙齿脱落,两边的脸已经凹进去。小连的一双手比常人大,抓菜、抓东西时,感觉他如老鹰抓小鸡般省力。我没有看见小连穿过一件像样、干净的衣服,冬天总是穿一件湖蓝色打补丁的转裙,夏天穿一件灰色的土布衬衫。小连作为一个乡村手艺人,烟没见他抽过,酒没见他喝过,老婆没见他娶过,地没见他种过,房没见他盖过,鸡鸭没见他养过,只当了仓库临时看管员。种种原因,他成了生产队的“五保户”。在当时,五保户没人欺,有困难人人帮一把。
小连住在生产队仓库场边的一间小屋内,小屋傍着仓库,吃喝拉撒睡全在里面,紧是紧了点,但在那年代有屋住已经不错。小屋一分为二,里面睡,外面吃,床底下藏着一担小连年轻时做厨师用的碗盆,长年累月蒙上了厚厚的灰尘。这担碗盆,小连当宝贝似的,好比一担青花瓷,从不外借,也不允许社员看。如果哪个社员悄悄地溜进去翻看,小连就跟他急,别说鼻子红,整个脸、脖子都急红了,骂他偷东西,找队长理论。年纪大一点的人,都说小连的一担“吃饭家伙”是老碗、老盆,祖上传下来的。小连出身富户,父母去世早,没来得及给他成家,后来,房子、田地分给了最贫困的农民,小连只留一间弄堂样的落脚屋。再往后,因落脚屋连着正屋,正屋的新主人翻建房子,把落脚屋半爿墙拆了,小连无处安身,生产队就给他在仓库旁建了一间小屋。
小屋前与仓库山墙有一个转角,是小连冬天晒太阳的地方。队里的社员来陪他,我们小孩子也来凑热闹,和小连一起晒太阳,他从不打骂我们。小连晒太阳时,手里喜欢捧一个黄色的陶钵取暖。陶钵土头土脑的,就像淳朴的农民。陶钵之所以暖和,是钵中加了烧饭时余火未尽的稻草灰,带有星星之火的稻草灰中间夹一两把砻糠,让稻草灰的余热延长。小连手捧陶钵取暖时,样子大都是木讷的,只有我们一帮小孩子和他一起取暖时他才开心,眼睛眯成一条缝,几双冻得红萝卜似的小手轮流伸向暖和的陶钵。有一天,陶钵噼啪一声裂开了一条缝,可能是陶钵经受不起长时间的高温裂开了。小连找来铁丝,把裂了的陶钵上口与下底上了两道箍,继续用。
小孩子喜欢陪小连晒太阳、烘陶钵,其实是想吃他爆的稻谷花。村民们晒稻谷时,总有一些稻谷失落在坑坑洼洼中,小连就把这些失落的稻谷挖出来,等冬天烘陶钵时爆给孩子们吃。他自己不吃,用稻谷花来吸引孩子,陪他度过寂寞孤单的生活。一只温暖的陶钵,给冬天带来了融融暖意,带来了人气;如果离开了陶钵,将会过得漫长而寒冷。如稻谷花般的雪花在冬天总要下几次,覆盖了乡下弯曲又漫长的小路,也把仓库场覆盖,天又冷了几分。下雪天,小连躲在小屋烘陶钵,没有了伴儿,只有几只麻雀在仓库场的柴垛上觅食,叽叽喳喳叫个不停,几条草狗在雪地撒欢儿。小连孤守小屋,倾听雪的絮语。
这一年,小连病了,而且一病不起。病时需要有人照顾,生产队指派某某社员去,可许多社员都不愿意去。小连一身脏兮兮的,又非亲非故。别看平日里许多社员都和小连蛮亲近,一旦有事,就躲得远远的。生产队长后来想到了小连的徒弟——王厨师,他是小连唯一的徒弟,五十多岁,驼背,后颈下面长了一个隆起的包,走路一踮一踮的,样子如一头骆驼,说话声音很低,但爱唠叨。队长把照顾小连的事说了,王厨师二话没说,小连是公认的“五保户”,没亲没眷,徒弟照顾师父理所当然。在旁人眼里,王厨师是想得到小连当宝贝似的碗盆。王厨师不管风言风语,一直照顾到师父安详地离开人间,尽到了做徒弟的一份责任。后来,队长做主,那担碗盆叫王厨师先挑十个,其余分给各家各户一到两个,没见什么特别,是一种粗糙的碗盆。小连之所以藏着,我想他不过是想给自己的生活找一个寄托。
小连死后,生产队在仓库场为他开丧,买树板请木匠做棺材,各家各户推选一个代表参加丧事。我家母亲推选我去,父亲在外地工作,当时我十多岁,妹妹七八岁。我们小男孩去,帮不上什么忙,只是看热闹,最终是想吃一顿丰盛一点的饭菜。那年代好不容易凑了十个菜,如今只记得两个:红烧豆腐、蚬肉炒韭菜。印象中没有猪肉,但也让我饱了一次口福。小连和普通老百姓一样埋在荒草地。小连住的小屋,后来生产队用来烧茶水。
如今,农村的田地都承包给了种田大户,几十年前生产队建造的仓库已破烂不堪,小连住的小屋也是如此。种田大户重建仓库、重铺场地。一日,经历了将近半个世纪风雨的小屋终于被推倒,像割倒田间的一把青草那样毫不费力。在仓库场生活的点点滴滴以及各种活动的场景,如看露天电影、开生产大会等只留在了村民的记忆中。往事历历在目,对比现今与往日,颇有感慨。后来,小屋苍老的风姿被一位写生的画家用油画留住,我在旁边看了很久,深刻地印在记忆中。
我不懂画,只是疑惑家乡这样一处平常的景物为何能够吸引画家。也许是画家拥有独到的眼光、独到的审美,如此苍老的场景随时会消失,再不画下来,以后不会再有。至今,我还依稀记得画面:黛青色的远山朦朦胧胧,山脚下是高低错落、粉墙黛瓦的村舍,一条小河介于村舍与仓库场之间,河上有小石桥,颓垣败壁的小屋露出红砖的本色,小屋墙脚下斑驳的青苔,窗棂东倒西歪深深刻在画上。小屋苍老的风姿入了画,让我遗憾的是当时没有买下这幅画。每当想起画家的画,就会想起画中的小屋,这里曾经住着厨师潘小连。
作者简介:陈祖明,江苏常熟人,系江苏省作协会员,江苏文学院第3期作家研讨班学员。作品散见于《人民日报》《雨花》《散文百家》《太湖》《江苏散文》,出版散文集《六桥烟雨》。
(责任编辑 徐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