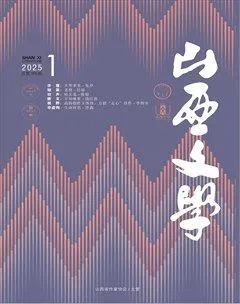不知味集
世家子弟江湖老
晚秋时,同事帮忙买回十斤东北新米。第一顿煮了粥,米香恣意,飞窜家中角角落落。谷物香气如此治愈,大抵会刺激人的大脑分泌多巴胺吧,好生愉悦,像跑了五公里。
多年不曾吃到新米。熬好后的粥,牛奶一般白皙,香糯润喉,筷子挑起,还拉丝。秋燥的天气,大米最是滋润肠胃。差不多每天吃一餐粥,无须佐菜,滔滔迭迭顺喉而去了。
同事好心来问,又到一小批新货,可还要了。我纠结一番,到底拒绝了。苦恼的是,这新米太可口,惧怕长久吃下去,又得胖三斤,好不容易减下来的。
新米,煮粥好,煮饭更佳。新米不太吃水,稍微煮干点,粒粒分明,泛着油光,一忽儿,将半盏饭吞下去,不解馋,情不自禁又去电饭煲挖一勺……刚吃进去,又后悔。这么大个人了,可都是碳水啊,怎么不知节制呢?
吃到好东西,颇为自责,心头惴惴的。做人真难。
十斤新米,很快被吃掉一半。颇舍不得,袋口扎紧,留待以后慢慢煮粥。重新买回另一种所谓的新米,产自江苏。口感高下立判。可能是气候的原因,这种产自长江中下游平原的稻米,一无筋骨,嚼在嘴里,绵软松散,像一个人缺了心气,总归懒洋洋的,黯淡无光。
同样是新米,吃得人苦不堪言。明珠在前,再吃河蚌,当然差点意思。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期,在一北方小城,吃到过一种粳米,煮出的粥,绿意茵茵,香糯挂喉。煮饭呢,香软而有筋道。吃剩下的饭,略微炒一炒,简直赛螃蟹。故,多年不忘。据说产自旱田。彼时,碾米技术不甚发达,更不存在抛光。这米留有大量角质层,甚至胚芽还保留着的。既有营养,口感亦好。如今,确乎享用不到了。
天一冷,便想去内蒙,无论包头、呼和浩特,还是巴彦淖尔。为什么呢?想吃当地羊肉烧麦,必须现包现蒸现食。冷风一起,走在路上的我将领口竖起,无比深刻想念着内蒙,唾液被得不到的美食刺激得翻涌不息。一次,一位呼和浩特读者朋友说要寄点烧麦皮来。
萍水相逢,哪好意思呢?
内蒙的烧麦皮,擀得薄如蝉翼,挖一坨羊肉馅置于其中,拇指食指轻轻一攥,瞬间出现一朵花儿。花边多褶皱,边沿静静垂下,像蓬蓬裙蕾丝。上笼屉,十分钟即成。羊肉馅,要切成小丁,配以一定比例京葱粒,不能用机器绞。一边吃烧麦,一边喝砖茶解腻,窗外北风呼啸,屋内温暖如春。我至少可以吃下六只烧麦吧,然后在寒风里呼呼走上十公里,将热量全部消耗掉。
内蒙的山苍黄苍褐苍青,遍布古意,这里的牛羊美味,没话讲。
生活于遍布牛羊之地,人的幸福指数想必高得多?至今网购到的牛羊肉,一贯差点意思。好肉无须佐料,直接清水煮,撒点盐,大口拥抱肉之本味。
享用不到美味,退而求其次,就读读写食书。
最近读着的,是王世襄公子王敦煌先生的《吃主儿》。一天读几页,舍不得读完。不愧为世家子弟,家底殷厚。王敦煌先生自小跟随祖父生活,家里有个张奶奶和玉爷,一直跟着祖父的。据说是正黄旗,清代官员,有薪酬拿的。大清完了之后,迫不得已,来到他家。
张奶奶可太会做菜了,简直御膳房大厨水准。老太太有耐心,不厌其烦,做出的每道菜,均被王敦煌祖父点赞。清蒸白鳝、清蒸甲鱼之类,皆属简易之菜了。
王敦煌先生自小耳濡目染,张奶奶也乐意教,事无巨细记录下来,一次次令人惊叹。
比如一道红烧肉,到过王府上的客人,无人不爱。隔三差五来做客,屡屡提起。
张奶奶这个人呢,也是奇人,为厨为得精致讲究,是得了神道的了。每日买菜,遇见好食材,便买下。常常呢,又买得超支了。最神奇的是,她在家门口银行,还能借到款。月终,超支部分,但凡讲得出,王敦煌祖父如数增加。
做红烧肉要用到一种柴火。彼时北京没得售卖了。玉爷便帮张奶奶,自己动手。将炭砸碎,佐以米汤搅拌,摊一个个炭饼,晒干。备用。
张奶奶去菜市碰见上好五花肉,买回,切小块,佐以各种香料煸香,盛起,备用。大葱多剥几层皮,切段。另起一口砂锅,一层葱段,一层肉,码放好,盖子边沿封上纸,盖上有一小孔,出气即可。将米汤炭置于一特殊灶中,引燃,上覆一层灰,令其缓慢燃烧。砂锅坐于其上,慢煨,一日一夜,红烧肉成。
还有一道炒芙蓉鸡片,更是震碎我朴素的三观。
一只老母鸡,买回,杀好,褪毛,剪刀自鸡胸剪开,顺着纹理扯下鸡胸肉,再去寻找贴近脊梁骨边沿的一种叫“鸡牙子”的两小块肉。这肉据说最嫩。取出后洗净,以刀背轻剁,成鸡茸。坐一口锅,倒油,将鸡茸一勺一勺溜进去。火候要掌控好,油温不可太高——高了,鸡茸黄了。油温也不可太低——低了,鸡茸散了不成型。要恰当的火候,鸡茸溜进油里成片状。油沥干,锅底少许油,煸炒笋干、香菇等物,差不多熟时,汇入鸡茸,略炒几下,出锅,装盘。这道菜,每次均被王敦煌祖父吃得交口称赞。
张奶奶当真传奇人物。原来,鸡肉中还有一种叫作“鸡牙子”的组织,真是百年未闻。以后炖老母鸡时,我一定要找到,开开眼界。
据传,王世襄先生旧年里冬日深夜,带着王敦煌偷偷溜出家门,去打猎。当带着猎物归来时,大雪纷纷,家人尚未醒来。
世家子弟江湖老。
一啄一饮也是尊严
有一个早晨,在楼道里,忽闻一阵香气……嗅觉迅速在记忆库中搜寻,嗯,不错,谁家正在炝炒扁豆。如此,激发起强烈食欲,速往菜市,买回扁豆半斤。
将七八片五花肉中火煸出油后,改小火慢慢焗至焦黄,汇入扁豆爆炒,中途略激点凉水。扁豆遇水汽,秒熟。起锅前,撒一撮蒜末。
露天蔬菜,被寒霜杀了几夜,口感甚好。当然,也得益于动物油脂的激发。
五花肉是个好东西,可用来炝炒任何蔬菜,平包菜、花菜、四季豆、豇豆、大白菜等。
前几日,凄风苦雨的,人在精神层面愈发颓丧,枯意百出。那次,也是站在厨房,小火慢煎五花肉,动物凝脂在被高温转化为液体的过程中,散发出这股夺人心魄的香气,真是安慰人,闻着闻着,心情渐渐好转,无比慰藉。
咖啡的香气,面包刚出炉的香气,东北大米的香气,热巧克力的香气……无一不治愈人。神奇的气体物质直冲大脑皮层,掀开天灵盖,刺激大脑大肆分泌多巴胺,原本颓废的人瞬间脱胎换骨,又变得正常起来了。
着魔一般,近日,采购回的均是五花肉,分别配以扁豆、四季豆炝炒,配一盏米饭,吃得颇为满足。
一日,逛商超,见青梗花菜比较新鲜,买回佐以五花肉炝炒,酱油上色,一点盐而已,其味不输鲍翅龙涎。甚至,碗底一点菜渣渣,也用筷尖捞起吃下去了,五花肉同样一片不剩。
平包菜到了初冬,被霜气杀过,口感尤佳。五花肉干煸至焦香,丢几颗小米辣,姜片、蒜片若干,汇入平包菜大火炝炒,起锅前,一点盐,少许白醋调味。另,平包菜手撕才好,不要动刀切。
黄昏下班,逢天气晴好,总爱拐去菜市转一圈,说不定可以遇见什么新奇食材?一日,菜市转着转着,灵感忽现,打算翌日午餐做一道简易版徽州一品锅。需提前采购食材若干。
豆腐果半斤,黑猪前胛六七两。不要用机器绞出的肉泥,回家自己动手剁。猪肉温水洗净,切薄片,剁至肉粒黄米大小即可,打一只鸡蛋,拌以酱油、盐、香葱、姜粒,顺时针搅拌、上劲,再塞入豆腐果中。这样的肉馅,吃起来既有颗粒感,又有层次感。
翌日,拎回两只圆白萝卜,滚刀切,焯水祛除辣腥气,备用。五花肉切一寸厚度,小火慢煸出油,加八角、姜片、京葱段炸香,豆腐果逐一铺在五花肉片上,小火慢熏,肉糜定型后,香醋去腥,酱油上色,翻炒片刻,加水焖煮,中途汇入萝卜块,先中火十分钟,后改文火咕嘟咕嘟半小时。
正宗徽州一品锅,食材多样,有笋干、豆角干、蛋饺、黄花菜等。最灵魂的,则是猪骨吊汤。我删繁就简,做了一锅简洁不芜版。萝卜炖得出神入化,入嘴,轻轻一抿,唯余一摊汁水。豆腐果,咬一口,汁水飞溅,内嵌的肉馅同样鲜美多汁,有筋道。
一直寻找过去年代那种原始小炉,红泥陶土烧制,可烧炭那种,上面坐一口小铁锅。炭火卧于炉膛红妍妍,小铁锅咕嘟咕嘟,白汽升腾,将锅盖顶开一毫毫缝隙,肉香、菜香携手溜出,一股脑钻入鼻腔肺腑……坐家里久闻,好像要升仙,一颗心顿时安宁,何惧窗外风雪交加?
吃牛羊肉、鱼虾,一向上火。平素多以猪肉为主。
苏轼突遭大劫贬谪黄州时期,那一点微薄俸禄,不够一大家子开销。能吃得起什么呢,无非猪肉。到这落魄境地了,他仍兴致不减,写一首诙谐的《猪肉颂》:
净洗铛,少著水,柴头罨烟焰不起。待他自熟莫催他,火候足时他自美。黄州好猪肉,价贱如泥土。贵者不肯吃,贫者不解煮,早晨起来打两碗,饱得自家君莫管。
十一假期回小城探望双亲,在饭馆,也吃到一份红烧肉,夹一筷,可拉丝,口感软糯筋道。可以给它打十分。
大白菜炖粉丝,也是一道冬日常做的平凡菜。五花肉切得厚厚的,煸出油脂,倒入同样切得粗朴的大白菜,炝炒出水,小火慢炖,末了,加一把粉丝。当然,若隔夜炖了一只鸡,浇一瓢鸡汤进去,甚好。最平易的菜,最养人。
大白菜吃到末了,剩一颗橙黄透亮菜心,还可用来凉拌。切细丝,用盐腌制五六分钟,挤出多余汁水,佐以香醋、麻油、花生碎,最后撒一撮黑芝麻。这道小菜,是一位河南同行指导的。窗外冰天雪地,室内人夹一箸凉拌白菜心,大嚼,咽下,透心凉,如若一剑穿喉,而你的肉身又为暖气紧紧包裹着,冰火两重天,心上凉凉润润,说不出的舒豁。
同事前阵网购到稻花香2号,是刚碾出的新米。让她帮忙代下一单。许多年不曾吃到新米了。用来煮了一顿粥,糯糯茸茸,扑鼻之香。过几日,同事问,可还要了?
到底推辞掉。这东北大地上被严霜寒霖鞭打过的新米,实在美味。但,太好的东西,也是害人的,不利于减重。用来煮饭更美味,每一顿,还不要多吃几口?
也不知,坚持这般没苦硬吃的自律作风,意义何在?古人云:鸡猪鱼蒜,逢著则吃。生老病死,时至则行。该怎样,还是怎样吧。
也可能潜意识里,嫌这新米价昂?平素吃的东北大米,差不多四五元一斤。况且它只给人类提供碳水,实无营养可言。还是吃肉补充蛋白的好。
不知接下来的冬天,还要消耗掉多少五花肉。
站在灶台前,铁锅已热,五花肉一片片入锅,刺啦一声微响,一霎时,香气杂糅着镬气,久久萦绕,给予身心极大抚慰。
五花肉煸得焦脆点,用生菜卷起,入嘴大嚼,想必齿颊留香?读书写作是尊严,一啄一饮也是尊严。
蒸双臭
有一年,访小城绍兴。从鲁迅故居出来,乘乌篷船到沈园。走走停停间,天色向晚,宴席被安排在一家不起眼的老店。
美味接二连三:清蒸带鱼、醉蟹、河虾。作为一名内地人,实在吃不惯醉蟹,一名当地同行则频频叫好,他孜孜不倦,啜了一匹又一匹,不时抿口黄酒,呷得津津有味……不为所动的我,枯坐静等,总归有那一道菜的。俄顷,果然来了,唤名“蒸双臭”,臭苋菜秆与臭豆腐同蒸。陪同的当地女孩教会我“苋菜梗”的绍兴方言——汉菜光,“光”字不可拖音,如蜻蜓点水般迅速收起。
这道蒸双臭与皖地雪菜炖豆腐同质,食材、做法上略略不同。皖地用炖的方式,豆腐则是新鲜豆腐。绍兴这道菜则是清蒸,用的是臭豆腐。臭苋菜秆被切得整齐,一节节隐身于臭豆腐中。这道菜于视觉上,便夺人眼目,水墨画一样洇开,苋菜秆尚有一点绿意,臭豆腐的白里点染了丝丝缕缕的墨黑。紧接着,一阵臭香时隐时现,直接将嗅觉点燃,唾液横生。夹一根苋菜秆,直接吮吸,果冻一样的芯子飞一般入喉,容不得仔细体味,瞬间化为无形,不太咸,唇齿间袅绕淡淡香气。吃到后来,忽然思念起白米饭,假若来上一盏,浇上蒸双臭汤汁,哗哗刨下去的快感,胜却人间无数……
当晚,我们吃的是面。宴席尾声,不免伤感,真是一颗农业文明培养起来的胃,纵然受过几十年城市文明洗礼,也不改淳朴本质,无视一桌山珍海味,偏偏难舍臭汁淘饭。
食物发酵后的淡淡臭味,何以吃到嘴里却又那么香,惹人成瘾?
芜湖臭干,徽州臭鳜鱼,绍兴臭苋菜秆……这些食物滋味上的无穷奥义,确乎博大精深,当真值得为之写一篇哲学论文——何以闻起来臭,吃起来却又那么香?
凉拌荆芥
商城坐落于大别山中,隶属河南信阳市管辖,这里的炖菜历史悠久,且专门成立了一个炖菜协会。那几日的餐桌上,一道道炖菜,样样滋润可口,老鸭汤尤甚,炉火温着,喝到末了,也是烫的。鸭汤凉了,腥气重,纵然夏日,也要喝热的。鸭汤里有铁棍山药、枸杞,也搁冬瓜、干香菇,或者海带结。久炖致香,汤的鲜美无匹,自不待言。
一次晚宴上,一道凉拌荆芥非常惊艳,滋味殊异,至今不忘。
新鲜荆芥,焯水断生后,烈阳下晒干。吃它时,温水泡发,洗净,碎切,拌之香醋、麻油、蒜粒,撒点儿熟芝麻。这道凉菜随同白切牛肉、油炸花生米等小菜,一起做了头道冷盘。不起眼的白碟里,墨一般乌黑,团成圆锥形。起先,不经意夹一丝丝,入嘴,石破天惊,先是薄荷般的凉润,继而齿颊生香。满桌珍馐,众人纷纷饕餮大菜。圆桌上的转盘来来回回无数次,独我一人,钟情那一碟凉拌荆芥。当夜,所有的美食皆失色。
小小一碟凉菜,简直惊鸿照影。餐后,嘴里一股似淡若浓的香气,久久不散。
每临夏日,我们这座城市的菜场,也能见到荆芥的身影,向来喜欢闻嗅它特有的药香气。我做西红柿鸡蛋面时,放几株荆芥在面汤上作香头。偶尔,也会买二三两,凉拌,吃到嘴的,单纯是一份粗朴的药香,不及商城那次夜宴上吃到的底蕴深厚。
几年后,遇见河南作家冯杰老师。无意中说起商城之旅,当我开始夸赞商城的面食以及炖菜的美味时,冯老师操一口浓重的河南腔,云淡风轻道:商城有一道凉拌荆芥可美……我简直要跳起来,终于遇见一位懂得食物之美的老饕。
凉拌荆芥,何以如此美味?往后再也不曾遇见。
歙县味道
到达歙县,已是暮晚时分。饥肠辘辘,放下行李,直接坐至餐桌上。徽州特色菜品,一字排开。酒精炉里,一小朵蓝妍妍微火,将胡适一品锅温着,热气自陶钵小孔里嘟嘟往外蹿。一条臭鳜鱼,红烧了,被无数笋丁香菇丁包裹着,香气奇崛。平素,最爱这两道菜,可是,当夜望着满桌珍馐,胃里阵阵翻腾,长途颠簸导致的晕车尚未缓解。
危难之际,服务员端上一只巨大陶罐,里面正炖了热粥,由大米、薏米熬成,加了大量肚丝。这罐热粥好比大慈大悲菩萨,真是救了我一条命。在众人的推杯换盏中,我像个坐禅人置身事外,静静吃下四小盏热粥。
五六年往矣,歙县的那罐肚片粥一直留存于味蕾记忆中。肚片粥,真是解人困厄——食盐的咸,正是可以平息体内秽浊之气的独一味,也最止吐。当夜,我一边吃粥,一边瞅着别人自胡适一品锅里频繁搛出蛋饺、肉丸等什物,抑或大啖臭鳜鱼,满眼含恨。临了,散席之际,上来一笼南瓜饺。尝一只,惊为天人。可惜凉了,如若热吃,风味更佳。
这样平凡的南瓜饺,最考验大厨功夫。饺皮里,除了面粉,还掺有煮熟的老南瓜泥。乍入嘴,口腔第一时间捕捉到的,均是老南瓜的甜糯绵软;饺子馅则由嫩南瓜丝及少量豆干丁制成,没有一根肉丝,走的是茹素一途。如此简淡质朴,却让人一吃难忘。
世上的好素斋,皆可将人的味蕾送至仙境。中国的顶尖大厨,犹如深山修道人,深深懂得捕捉食物的自然之味。什么是自然之味?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本味。味道,味道,什么是道?道,即万物的规律。食物的规律,不就是它一直存在的本味吗?一日三餐的烹煮中,我一向排斥味精、鸡精、海鲜酱等调味品的加入。一个好的大厨,是规避这些工业化调料的,他只肯大老实地将食物的本味呈现给你。
这样至简至淡的道理,同样适用于万物。一篇文章,朴素平常的才好,如行云流水,当行则行,当止则止,气韵自成——纵然底子里一派阔气,也是冲淡的阔气。
自酒店出来,夜气已深。群山嵯峨间,悬一轮薄月。山风徐徐,颇有凉意。
翌日,早早醒来,沿县城古街闲走,不觉到了中饭时间。午宴设在歙县西街一号大礼堂食堂。
西街一号,白苍苍耸立于烈日下,有一种历史的沧桑感,予人时光倒流的恍惚。人往建筑面前一站,旧气扑面,似被送至另一时间轴上。该建筑一望可知,建造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于西街一号门前伫立久之,有种说不清的情绪——建筑同样会说话,它的语言是凝固着的历史。
歙县,既有着古气,也不乏旧气——古城墙尚存,古桥犹在,群山间难得的一座古城,始终静静的。沿途窄溪无数,一直流啊流,到底将徽文化的气脉保存下来。歙县这座小城,总归是幽静的,沉寂的,又不失雍容。
土鸡汤,透鲜至顶。卤鸡蛋的咸香,勾人心魄。皖南鸡种,骨架小,清瘦,灵动。一只老母鸡,两斤来重,产下的蛋也小,比鸽子蛋大一点点。
一道红烧土鸭,人间至味。皖南鸭子同样体格小,毛重三两斤。这鸭子,是饮着天然溪水,享用着新安江螺蛳长大的。拿它来烹了,滋味殊异。
葛粉圆子,也是一绝,掺了少许豆干、肉丁,隔水干蒸,趁热吃,弹牙软糯。盛名远扬的徽州名菜刀板香,透着颤巍巍的油光,夹一片放眼前,可照见对面人影,堪比四川的灯影牛肉。将咸肉放置竹质砧板上蒸透,渍出的肥油被砧板吸尽。这样的肉,吃起来则不腻口。绩溪炒粉丝,自不待言。
情绪放松下来,胃口也开了,一轮一轮吃起来,佐以酸梅汤,酸酸凉凉,予人前世今生同在之感。
歙县原本是古徽州政府所在地,依旧残存一份政治文化中心的稳重妥帖。虽只认识五六位徽州人,但他们骨子里的那种优雅、温和、体贴、知礼,随时洋溢着,总带给人舒豁之感,难怪民国人士喜爱结交徽州人胡适之先生,他始终笑眯眯的,不给人压力。就连生性怯懦、敏感、害羞的张爱玲去国他乡以后,栖身于美国青年救济会提供的陋室,第一个想起拜访的,也是胡适之先生。这里面一定有着渊源的。自民国到当下,徽州人永远这么可信,可托。
临别,一位不认识的长辈特地跑来告知:你如果在这里住上几天,一定不想走的。是的,一直想结伴几个合宜的人,带着干粮,拄着棍子,走一走徽杭古道。总是缺乏机缘,不能如愿。
我自小生长于安庆地区。安庆与徽州始终是一脉的——于文化底蕴上,可以更好地代表安徽的,只能是安庆与徽州——不论是身处皖南的特殊地理位置,抑或人文传承,都是纷繁万千首屈一指的。新文化运动的两位杰出代表——胡适,陈独秀,分别来自徽州与安庆,就不提稍远些的赫赫有名的桐城派,以及源远流长的徽学了。
当年,石涛第一次来徽州,无法驾驭黄山的雄宏庄严巍峨肃穆。手拿画笔的他非常自卑。但他也未气馁、沮丧或者一蹶不振,只默默下得山来,退至宣州,费纸泼墨,苦练内功。几年后,再上黄山,笔下山水,自然而成。这就是一个人临山川而不乱的定力,也是我们这个日新月异的时代最缺乏的工匠精神。
回庐途中,过黄山脚下太平湖,我们歇憩了一小会儿。带一颗闲心,徜徉于徽州的山水之间,算悟过一回道了。
陶潜诗云:人生似幻化,终当归空无。
人活着,本该与山水自然同声共气,品尝本味食物,书写朴素文章。
度夏
每年入夏,总要泡一罐豇豆,底下垫一层新蒜瓣、小米辣,上头压一块石头。
这石头,用了七八年,渐起包浆,遍布幽光,弥漫一股蔬菜与盐的家常气。
一周后,豇豆准时回味,由青泛黄,一股奇异的酸气自密缝的罐盖处旁逸而出,惹人垂涎。可以食用了。取一小把,顺带几只小米辣几颗蒜瓣,碎切。热锅滚油,炝炒,激点儿凉水,取其脆口,迅速起锅,一道佐粥佳品。入嘴,酸辣脆。
腌制咸菜,是认手的。我母亲腌出的菜不比我的可口。故,小时候,无论腌制萝卜,还是雪里蕻,她都差遣我揉制,装坛。
吾乡栽南瓜,亦如是。有人栽下的南瓜全开谎花,一个南瓜也不愿结。有人栽下的南瓜,特别肯结。真是神秘的事情呢。
早餐时,一碗小米粥就腌豇豆,简直金不换,为夏季佐粥佳品首选,其次才是咸鸭蛋。午餐虽说有三菜一汤,但,偶尔搛一点腌豇豆搭搭嘴,也能将剩在碗底的那口米饭送下去了。
隔六七日炒一碟,一罐豇豆倏忽见底。转眼入伏,这罐底汤千万不能倒掉,它宛如一道药引子——正好用它来泡籽姜、红白萝卜等。
入伏当日,籽姜、红白萝卜悉数买回,洗净控水。籽姜切薄片,放最底层。红白萝卜切长条,位居中层。小米辣少不了,盖在上头。最末施以一块压仓石。所有食材没入汤水中,阻隔着空气,以防腐烂。黄灿灿的汤水掩映着各样红黄白的蔬菜,异常悦目,艺术品一样静置于冰箱冷藏室涅槃……
大约一周后,所有食材俱回味。那么,可以炖酸汤鸭了。
老鸭半只,洗净血水,滚水焯烫一下,斩成块,备用。抓一撮泡姜,几根白萝卜,入锅炝出香气,入鸭块爆炒,再移入砂煲,加水,猛火攻开,中小火慢炖。
伏天闷热潮湿,一向乏胃口。酸,作为独一味,最能提振食欲。鸭汤的腻恰好被萝卜的酸解掉了,喝起来止渴生津,又补了虚弱,健了心脾。
鸭汤里放山药、海带,皆不及泡姜、白萝卜可口。后者才是驯服酷夏味蕾的神品。
平素炒藕片f9gDPCoO0IwsFnwwU0iWaj9ghEuC4nYYF0kWcPv8Ms4=、仔鸡,熘肉片肉丝,清蒸鲈鱼等,都会用到泡姜。那一味酸,若隐若现,丝丝入扣,最是勾人心魄。早餐喝粥,亦可直接食用,尤其红白萝卜,酸咸适中,刺激味蕾大肆分泌唾液……一碗粥食毕,神清气爽。
作为一个贫乏年月过来的人,早餐习惯喝粥,味蕾形成惯性无法更改。偶尔改食西餐,诸如一块牛排,鸡蛋煎至半生,撒什么胡麻籽,配一杯牛奶……吃起来,非常不快乐,总归没有一碗粥来得舒豁安适。
胃肠是有记忆的,颇为念旧。
养生的最高境界,是不养生。我奶奶一辈子早餐喝粥,喝了八十多年。小孩爷爷奶奶亦如是,一位九十二,一位九十岁,照样天天早餐喝粥。
吃得顺口舒泰,吃得快乐,便是最好的养生。
一日,去市里办事,午餐顺便外面解决。在一家名曰“南京大排档”小食店,喝到名闻遐迩的美龄粥,也就那么回事。粥是牛奶熬出的,点缀若干新鲜百合、几粒山药。不难,我也会做。奈何它是甜的,我的味蕾不喜欢。这款粥确实有营养,但一旦不喜欢,未必适合我的体质了。还是热衷熬得出油的小米粥,配一两只鸡蛋,或煮或煎,搭配一两根天目山小红薯。倘奢侈点,煎一块三文鱼也好。
有了一罐酸汤水。午餐,亦可做酸汤鱼。
野生乌鳢一条,斜切薄片,裹上薄芡,备用。鱼骨及头尾,薄油煎一下去腥,抓一把泡姜、小米辣,白萝卜若干炝炒,加水,一起炖至牛乳状,再舀一小勺酸汤泼进去,这才是灵魂佐料。下鱼片,略微汆一下,熄火,撒一把紫苏或荆芥,也是一道下饭菜。
酸甜苦辣咸——酸,居位首。尤其伏天里,这一味酸,简直是对人类的一种救赎。倘少了这一味酸,简直茶饭不思了。
有一年秋,去柳州乡下。侗族的寨子里,几乎家家备有一坛酸肉。两广地区比起内地,更加湿热。酸,不仅开胃,也具祛湿功能吧。由糯米制成的醪糟,与新鲜猪肉一起发酵,长达数月。或清蒸,或与蔬菜炝炒,形同腊肉。用的是茶油,酸香扑鼻。
那个侗族寨子里的人们非常享受生活的。我住的是民宿,一大早下楼来,屋外微雨,灶堂已熄,一家人围坐桌前,尽享两菜一汤。酸肉的鲜香味与柴火气紧紧纠缠,经久不散——我不曾在别处闻见过如此奇崛的酸香气。莫非几片酸肉炝炒出的苦菜,再舀几瓢水,一起炖开,苦菜叶子早已浑黄,汤面上漂一点茶油星子,一家人吃得呀,叫天地都动了颜色。我撑一把伞,门口伫立久之,眼前青山流云飞岚,耳畔溪水潺潺,岸畔茂密高耸的凤尾竹难敌雨水,就也一齐倾倒于溪流之上了。
贵州有著名的酸汤鱼,云南的傣族还有撒撇。尤其后者,简直奇异。所谓撒撇,则是残留于牛盲肠中的不曾消化掉的草汁,是傣族人的心水之物。杀牛后,取出盲肠中的绿汁,烧滚消毒,过滤掉草渣,调以醋、小米辣、紫苏、折耳根等,当蘸水。取新鲜生牛肉一块,剁碎,蘸着撒撇吃,颇有日料风格。
撒撇是苦的,调以醋的酸,也不知入嘴,是怎样的天翻地覆。
一年一年,人们在这酸酸苦苦中,将日子一天一天过下来了。
中国有羊之地,皆信奉伏天吃羊。据说皖北萧县,每年伏天,都要举办一场大型伏羊节,该是何等盛况呢?
有一年夏,去宿州采访。乡下的一个雨夜,吃到椒盐羊排,最后收尾的自是羊肉馅饺子,不膻不腻,鲜美多汁。那些饺子,皆是那位讷言的主妇一个一个捏出的。酒席上,我频频打量着上菜的她,衣着朴素的她,如此心灵手巧。她的椒盐羊排并不逊色于城市酒店大厨,羊肉饺子自是不遑多让。
我所在的这座城市,若想外食,根本喝不到正宗羊汤。街头每家经营羊肉的小食店,无一例外均沦陷于一种叫作羊肉精的黑科技之中了。
羊汤祛除胃寒。到了伏天,唯有自己来炖。
羊棒骨三两,拦中敲一裂隙,骨髓微露,焯水,清水熬汤。羊后腿肉,切小块,浸出血水,以京葱段、姜片,薄油炝炒至香,一并汇入羊汤中,小火久炖,中途切一根胡萝卜。吃肉喝汤,最是美味。
羊后腿,亦可大块烀熟,再切薄片,汇入炖好的羊汤中。倘做点油辣子,更完美。二荆条、子弹头、小米辣焙香,石臼中捣碎,盛入碗中备用。问店家要一块羊油,小火熬毕,趁热倒入辣椒碎中……羊油的一点膻气,随着刺啦一声,瞬间化为乌有,高温烈油反而将辣椒的香气更大程度地激发出来,和盘而出的才是油香椒香杂糅的至香。
盛一碗羊汤,挑一点儿油辣子,沁出一头汗。
【作者简介】钱红莉,又名钱红丽,安徽枞阳人,出版有散文随笔集《低眉》《风吹浮世》《诗经别意》《读画记》《一辈子历历在》《四季书》《一人食一粟米》《植物记》《等信来》《以爱之名》《河山册页》《小食谭记》等二十余部,曾获百花文学奖、刘勰散文奖等,现居合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