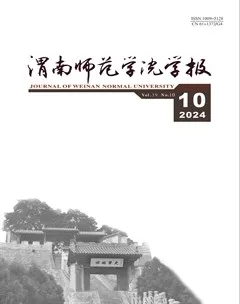在中西隔空对话中理解司马迁的历史哲学
摘" " 要:“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是鲁迅先生对《史记》历史性与文学性完美融合的高度概括与总结,也是对司马迁历史哲学的形象化表述。如果联系20世纪以来西方历史观念对研究方法的影响,大体经历了客观的重建论、主观的建构论和语言的解构论三种不同方法论的交替转变。司马迁通过《史记》创作体现的历史哲学观念接近主观的建构论,但它却以早熟的叙事策略,独领风骚两千年。这样一来,人们自然而然地联想到,司马迁“无韵之离骚”的美学追求与美国哲学家海登·怀特构建的后现代历史叙事学的基本理念极其相似。即便如此,我们只能将其看作后现代主义与古典主义的隔空对话,而各自的观念和指涉终究不同。
关键词:司马迁;重建理论;建构理论;叙事哲学;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中图分类号:K207" " " " "文献标志码:A" " " " "文章编号:1009-5128(2024)10-0038-06
收稿日期:2024-06-28
作者简介:齐效斌,男,陕西泾阳人,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主要从事文艺符号学、语言符号学的理论和应用研究。
虽然叙事的转向,是历史哲学变革的标志,但《史记》的叙事策略绝不是新历史主义哲学文学化、审美化的一个注脚。倒不妨说,它是一个没有任何羁绊、空前绝后的高级的历史哲学范本。原因在于司马迁不仅有立德立功立言的志向,也有“成一家之言”的抱负,“原始察终,见盛观衰”的历史意识,和“寓叙事于论断”的思维逻辑。所以,即使西方的历史写作有重视叙事的渊源,却断然没有这样自觉超前的历史意识。
一、从重建到建构理路的变化,确认
司马迁叙事哲学的历史地位
实际上,司马迁的哲学创见早有定评。国内著名哲学家、燕京大学常乃德教授曾经著文说:“司马迁的《史记》在中国学术界曾备受崇拜,但是推尊他的,不是鉴赏他的文辞,便是夸赞他的史料,还有些莫名其妙的考据家,认为他的《史记》的记述自相抵牾处甚多,颇欠正确,照他们的看法,还不如班固的《汉书》。其实太史公根本不是在写历史,他是在写哲学,他著《史记》的动机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言’。……明白了这个,才知道为什么《史记》在中国历史著述中占独一无二的位置,不但远非班固、范晔之流所敢望,就是司马温公的《资治通鉴》也逊之甚远。因为这些人的著作只是抄袭式的断烂朝报,而太史公的《史记》却是一部‘穷天人之故,达古今之变’的‘一家言’。”[1]2常乃德教授这段话,高度概括了司马迁作为一个史学家的抱负和社会担当,尤其是“他是在写哲学”这一真知灼见,又点出了司马迁的学者身份,因而成为区分《史记》学术类别的一个界标。
那么,司马迁究竟是如何概念化自己的叙事哲学呢?我们又是如何为其定位呢?在此,我们首先回顾一下20世纪以来西方史学理论家和实践的史学家重构论、建构论和解构论三种不同的研究方略,从比较中见出司马迁叙事哲学的超前性。
重构论的观点认为,历史学的任务,就是还原过去事件的本来面目,找出历史中已有的情节、节奏和模式。如扬雄所说的实录。或如德国著名哲学家兰克所云,“据实直书”。在重构论的史学家看来,过去的历史真相就隐匿在纷繁复杂的史料之中,只要学者们排除偏见,剔除杂念,不偏不倚而又能科学地厘清与整合史料中的某些片段、某些细节,其价值就会被我们所发现。不仅小的事件敢于断定,即使大的政治事件我们亦可以在史料中通过蛛丝马迹识别它的微言大义。前提是,这些史料必须是真实可靠的过去,经得起推敲的历史遗迹,而且史学家也像一个考古学专家那样具备相应的技能技巧,能够辨别史料本身的暧昧性、复杂性。如此一来,历史学家就可以心满意足地将历史的记忆变成历史的表现了。这种坚持实事求是的精神,固然可嘉,然而,实际上要真正搞清楚事实的真相,谈何容易!这不仅牵涉学者的素养,也牵涉事实攻坚的难度,而这一点又必然影响历史学家的心理。苏格兰哲学家托马斯·卡莱尔在《论历史》中就讲过史学家在史料鉴别中的一些困惑:“最有天分的人也能观察到更可以记录到自己头脑中的连续的印象序列,因此,……他的观察也必然是连续的,而事件常常会同时发生——并不像历史书中所写的那样:实际事件之间绝不像父母与后代的关系那么简单;每个事件都不单单是某一事件的后果,而是源自在它之前或与它同时发生的全部事件共同的作用,随后又反过来与其它事件一起产生新的事件——这是一场永不停歇的混乱,事物在无数的因素作用下不断地塑造自身,这种混乱——正是历史学家所要描述或者说科学地估算的东西,这种描述只能通过有限的几条线索彼此穿插交织来进行!从本质上讲,人们认为所有行为都可以在宽度、深度和长度上延展——一切叙事因此本质上都只有一个纬度——故事是线性的,而行为是立体的,唉!我们所谓的‘因果链’亦是线性的——但一切事情都处于广阔深邃的无限之中,每个原子都是与所有的原子交织联结在一起的!”[2]39看来,重构论的主张,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如果要获得历史事实的真谛,必须另辟蹊径。
持建构论观点的学者则认为,如果完全依赖重构论者仅有的那一点朴素的历史经验,并不能彻底揭示历史事实的全貌,至多仅得皮毛而已。假使偏听偏信,一叶障目不见泰山,反而妨碍了历史真相的呈" " "现。例如,发生在唐代初年震惊朝野的皇位争夺战。这场战争的双方是当时作为太子的李建成和后来僭越皇位的唐太宗李世民。这场变故,就是有名的“玄武门之变”。一千多年过去了,一场腥风血雨早已化为过眼烟云,虽然关于李世民继位而谋杀李建成的合法性,始终受到质疑,而李世民的形象却在《隋唐演义》等野史小说中,不断得到丰富和完善。孰是孰非,历史的真相究竟是什么?仍然难以定夺,或者根本不需要定夺。相反汉武帝时期的太子刘据谋反案,却有幸终见天日,因而另当别论。由于权力和暴力的打压,太子刘据左冲右突,难以找到真相,也难以洗刷罪名,以至牵连许多无辜。要不是一位令狐茂小官吏的来信惊醒了汉武帝,另一位掌管刘邦陵寝的官员田千秋替太子叫屈,所谓蛊惑之祸衍生的太子谋反一案,绝不可能峰回路转,而汉武帝也不可能为太子平反昭雪,那么在司马迁的《史记》中,这个事件或许永远成为一桩无法申辩的冤假错案。
看来,纯客观的还原难度的确很大。所以建构论认为,重新回到事件之中,重新再现已经作古的历史作家的思想意识,仅仅是一种良好的愿望,因为此中消息已被各种意识沾染了无数遍,以至蛛丝马迹都难以存在,那里谈得上原原本本的事实真相。由于所有的事实,已经缺场,难以复活。如果硬性恢复,只恐怕“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因而历史学家关心的并不是预测未来,而是理解过去。况且,任何学者对史料的取舍和甄别,皆有自己的价值观念、政治立场以及自己的气质和爱好。他们不可能非常客气地还原历史真相而对自己利益、好恶无动于衷。因此这种重建论自然而然地被建构论所否定,而且严格地说,重建论并不是重建,而是重现,或者重新恢复。
那么什么样的理论和实践才是真正意义上的重建呢?就是对重建论反其道而行之的建构论。
克罗齐有言: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柯林伍德则进一步指出: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也就是说,史学家的责任和义务就是把史料或别人的思想改造成自己的思想,把历史符号域中的历史意识变作为自我的历史意识。正如司马迁所言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言”。“成一家言”就是公众意识自我化与自我意识公众化的过程。柯林伍德同样认为:“它是思想的一种活动,这种活动只有在认识者的心灵重演它并且在这样做之中认识它的时候,才能被人认识。对于历史学家来说,他所正在研究其历史的那些活动并不是观看的对象,而是要通过他自己的心灵去生活的那些经验;它们是客观的,或者说为他所认识的,仅仅因为它们也是主观的,或者说也是他自己的活动。”[3]247–248国内学者韩震教授主编的《历史的观念》认为,柯林伍德关于历史是一种积极的批判活动,因而特别注重历史书写在重演过去中的主观能动性,是值得肯定的。但是,却又不自觉地走向个性化的极端,从而给人以主观认识代替客观事实的印象。[4]543而我却不能苟同这一观点。原因是司马迁对历史与个人心灵关系的体验比柯林伍德更早。这一点恰恰被著名学者李长之先生所看破:“在历史科学的方法上,司马迁的贡献尤其大,体裁的创制已由前人说过,我们不必多说。我觉得最难得的是,司马迁的历史实在已由广度而更走入深度。正像德国史学家考尔夫(Korff)那般人的所谓,历史的意义,不在探求外延,而更在探求内包。司马迁的历史已经能够探求到人类的心灵。所以他的历史,乃不惟超过了政治史,而且更超过了文化史,乃是一种精神史,心灵史了。”[5]265–266所以,我们可以肯定地说,《史记》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科学文本,也不是单纯的精神文本,而是科学理性与精神个性相结合的历史文本。这也是《史记》倾向于建构性的哲学理念、并取得成功的原因。
总之,要想真正地重建新的历史哲学,就应当像司马迁那样“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言”。而要“成一家言”,就必须用新的理论武装自己。这种新的理论,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社会学,以及后现代主义思潮影响下史学领域的解释学理论。
二、在解构历史哲学向叙事历史哲学
转化中理解《史记》的叙事策略
客观上讲,对重构论进行颠覆的是解构主义。重构论之所以被颠覆,就是在卡莱尔他们看来,浩如烟海的过去,本身就是一种“存在的混沌”。历史研究不在于过去究竟是什么,而在于历史学者究竟需要什么,过去的历史资料究竟可以为我们提供什么。他们不相信有什么历史的事实,重建历史的过去完全是一种乌托邦式的幻影。所以与其寄希望于过去,还不如设身处地设想现在;与其迷信一成不变的史料,还不如充实历史学者的胸次和技能。关心文本,关心历史文本化的工作,才是最为重要的。语言的转向,或者叙事的转向,提供了历史文本化的可能,故而历史的修撰,注重的不是文本的内容,而是文本的形式。由是,历史的书写,也可以理直气壮地把历史当作小说来创造。就是说,历史文本既可以是历史的,也可以是文学的。既可以当作思想来接受,也可以作为文学制品来享受。这样一来,《史记》“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叙事策略岂不正好与海登·怀特和安克斯特密代表的叙事主义历史哲学不谋而合?!然而这一隔空对话的语境形成,并不能代表司马迁固定地属于哪一种哲学体系,而只能说属于他自己独创的“一家之言”。因为司马迁的叙事策略与新历史主义恢复历史叙事的要义并不是无缝衔接,创作的志趣和理论归宿也不尽一致。其中,一个最大的区别是司马迁有意识地将神话哲学与政治哲学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使其既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又具有永久的理论魅力。这种思想就被“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经典性概括和总结,而西方当代历史哲学尤其是新历史主义的历史意识并不以此为旨归。
所谓“史家之绝唱”,就是历代史学家、批评家十分赞赏司马迁的不虚美不隐恶的实录精神。为了求得事实的确凿无误,他的视角和足迹几乎遍布大半个九州。因而才成就了秦始皇、汉武帝、刘邦、项羽、吕雉、孔子和司马相如等许许多多的英雄豪杰、文人骚客。吕雉是一个内心和外表丑恶到极点的人物,太史公依然实事求是地论述了她“佐高祖而定天下”的历史功绩。不过司马迁为了实现他的抱负,又不可能事无巨细,有闻必录。而是有所选择、有所增删。例如舜,最感人的事迹莫过于和娥皇、女英凄凄惨惨戚戚的爱情传说,但司马迁并没有采纳这一深入人心的掌故。只择取了舜陷于后母和弟弟的虐待和迫害的圈套,从不计较,更不去报复,始终坚持人子之道,尽显孝悌人性光辉的一面。这种精神和品质,更适合于体现《史记》的人伦道德和政治哲学指义。对于汉高祖刘邦,司马迁虽然见不得他那流氓气,但是抱着为刘邦本人负责,更为历史负责的态度,仍然心悦诚服地称道他“汉承秦制”,实现大一统的功绩。赞赏那杀马为盟,“非刘氏而王者,若无功上所不置而侯者,天下共诛之”[6]801的誓言。黄帝同样如此。司马迁在写作五帝本纪之前,涉猎了许多史料,但都觉得“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6]46,于是他“择其言尤雅者,故著为本纪书首”[6]46,简而雅,质而不夸。叙事,更详略得宜,变化尽致。然而,司马迁为历史负责的精神,不仅表现在不虚美的描写之中,更多的也许还表现在不隐恶的批判中。《孝武本纪》颇多微词,其初稿因借机针砭时事,就引起汉武帝的强烈不满,以至于毁之一炬。而《封禅书》则通过方士们四处求仙而不得,讥讽封建帝王追求长生不老的荒诞无稽。“故《史记》一书,《封禅》为大。”[7]292“此书妙在将黄虞历代祀典与封禅牵合为一,将封禅与神仙牵合为一,又将河决、匈奴诸事与求仙牵合为一,似涉傅会而其中格格不相蒙处,读之自见。累累万余言,无一着实语,每用虚字诞语翻弄,其褒贬即在其中。”[8]83“初看叙事平直,再看则各有关合。细心读之,则一句一字之中,嘻笑怒骂无所不有。”[7]292可谓一唱三叹,韵味不绝。于此有了更清晰的洞见:司马迁“见盛观衰““通古今之变”的觉悟,并不以为越是尽可能多地收集与表现对象相关的信息资料,就越具有更大的意义空间。相反,有时候很可能是别人未必关注的神话信息,却是他发掘和整合神话哲学的对象。法国哲学家利科曾经自信地断言,我选择了意义,剩下的都是无意义。司马迁同样如此。原因在于这一神话传说,经过他的点染,具有了推动意识运动的力量,具有了创造现实的潜能。可见,司马迁既尊重历史,反对话语之外无事实;但又不迷信历史,而是正确地认识历史,注意话语表达的言外之意,以便让人们从中发现需要解释的诸多因素从而予以再解释。这种理直气壮的建构神话哲学、进而把神话哲学作为历史哲学发生学的起始点,正显示了司马迁历史哲学的超前性和科学性。
所谓“无韵之离骚”,在逻辑上也应当作如是观。表面上看,“史家之绝唱”指涉的是《史记》文本的历史精神和历史意识,而“无韵之离骚”指涉的是《史记》的审美精神和审美特征。实际上,它们都是通过叙事的策略表达“原始察终,见盛观衰”的超前意识。只不过,“无韵之离骚”更注重以情抒史或者以情写史,这也与《离骚》这一独立奇特的作品样式有关。楚地本来就充满着浪漫神秘的文化色彩,《离骚》辞采瑰丽、想象丰富的神话传说正好体现了这种得天独厚的优越感。在我们看来,这些神话传说不仅仅是诗,是一篇篇性格独立不移的生命赞歌;同时又是历史,或者间接地书写着一代爱国志士的孤独与悲愤。一首《天问》更是将屈原炽热的情感和科学的幻想升至天花板。这些神话歌谣与代表中原文化的《诗经》有着不同的审美取向和不同的情感表达方式。其中,在叙事方式上就大胆地运用了具有想象力的比兴手法,“《离骚》之文,依《诗》取兴,引类譬喻。故善鸟香草,以配忠奸;恶禽臭物,以比谗佞;灵修美人,以媲于君;宓妃佚女,以譬贤臣;虬龙鸾凤,以托君子;飘风云霓,以为小人”[9],司马迁正是看中这一点,才把它收录到《屈原列传》中来,又把比兴以及更为广义的想象符号推衍到《项羽本纪》等作品中去。这样,当我们看到垓下之围的激烈厮杀,就不再纠缠项羽无以名状的抗暴勇气,和四面楚歌构成的超长压力是否真实。而是把全部同情和理解播洒在残酷的命运旋涡里,投放在人间至爱的生死之恋中。离骚者,犹离忧也,正是这个意思。所以,我认为,《史记》之所以改变编年史的传统书写模式,可堪为“成一家言”的高级范本,就是因为它体验并再现了历史人物的内心世界。这是《史记》文本的叙事特色。
巴尔扎克说过,文学是人心的历史。在某种意义上,历史更应该是一部人心的历史。事件是人心的事件,事实也是人心的事实。可是当我们一旦讨论起历史的本质时,往往忽略了这一点。以上论述的几种研究历史的模式或者理论流派,几乎都顾左右而言纯而又纯的历史哲学,轻视活跃在历史长河里充满传奇色彩的人物形象。后现代历史叙事学口口声声说要将文学的要素引入历史的书写和研究,可是他们如果忽略了对人物的描写和刻画,尤其忽视对人物内心世界的精雕细刻,即使再离奇曲折的情节模式,义正词严的论证模式,准确无误的意识形态模式,其理论仍然是灰色的。而不入任何一种流派的司马迁却在通过书写《史记》实践人心的历史这个重大课题。事实说明,司马迁的《史记》之所以历久不衰,原因就在于作者以自己的心灵体验历史本身,体验许许多多历史人物的内心欢乐和痛楚,体验过人物命运的悲欢离合。叙事哲学的转向得以成功,关键就在于丰富复杂的人物精神世界深化了历史的哲学意蕴。
三、从司马迁与怀特历史话语的比较中
认识《史记》话语的独特性
话语的功能是什么?怀特认为:“话语是一种文类,其中最主要的是要赢得这种表达的权力,相信事物完全可以用其他方式来表达的。转义行为是话语的灵魂,没有转义的机制,话语就不能履行其作用,就不能达到其目的。”[10]3巴尔特则认为,话语是超越了句子层次的词语系统,即比语句更大的语言单位。他还揭示,历史学家都是“不诚实的”。他们在撰写历史文本的时候,往往隐瞒历史话语与自己主观倾向性之间的关系,以便创造出客观实在性的幻象,模糊读者关于历史的叙述与虚构的叙述的界限。更进一步说,历史话语表面上只是操作“能指”和“指称”两个术语,实际上,是以指称——所谓“真实发生的事”——掩饰历史学家论点的“所指”。进而巴尔特指出:“历史的话语,不按内容只按结构来看,本质上是意识形态的产物,或更准确些说,是想象的产物。”[11]59–60所以没有话语,就没有叙述主义的历史哲学。这样一来,历史事实对于历史写作似乎是可有可无的了。
然而,在司马迁的哲学里,“成一家言”之“言”却承担了历史话语两个方面的功能。亦即“言什么”和“如何言”。“言什么”是符号的所指,“如何言”是符号的能指。作为符号的所指,“言”指涉的是司马迁历史哲学的基本观念、理论思想体系及其内涵。而作为符号能指的“言”,则是如何表达“言”的内容的方法。虽然“怎么言”比“言什么”更为重要,但如何“言”,并不等于完全离开“言什么”的核心内容,天马行空,无迹可寻。也就是说,如何体现表达的创造性,在熟悉的符号域生成一种独特的叙事方法,并不是以小说的叙事之法代替历史的叙事。相反,必须以历史事实为依据,坚信以回归历史理性为目的,以此凸显自己的话语权。所谓想象、虚构和抒情,都应围绕着“原始察终,见盛观衰”“寓论断于叙事”的理性原则去操作。这种话语既昭明了一定的意识形态涵义,又表达了司马迁独特的理想和愿望。而且,在历史文本艺术化的共同呼声中,“怎么写”在后现代历史叙事一派那里,主张的是转义——隐喻、换喻、提喻和反讽的理论建构。在怀特看来,隐喻实质上是再现的,换喻是还原的,提喻是综合的,而反讽则是否定的。这四种转义方式构成了历史意识的深层结构,成为历史学家描述过去历史事实的写作类型。就是说,这四种转义形式预示了论证、情节编排及意识形态模式的描述方式,而且最终决定了历史写作的主观选择。历史学者正是在修辞转义形式的暗示下,自觉地将部分与部分,部分与整体互相链接,从而使事物之间产生了有意义的关系。
然而,如果忽视历史话语归根结底是活生生的诗语创造,刻意地套用四种转义形式进行模仿,哪怕是其中的一种,就有可能陷入一种对号入座的机械主义泥沼,从而给人一种印象:这种转义形式,不是历史学者在历史事件中被发现的,而是由按图索骥的形式需要强行加上去的。而在司马迁的创造实践中,历史话语则是通过张扬传统比兴手法的辉煌成就,形象地再现了“怎么写”的伦理道德观念和汉民族的审美习俗。可见,这两种话语的创造皆有不同的方法论和具体的方法追求,其间只能相互发明而不可能相互通约。
参考文献:
[1]" 常乃德.历史哲学论丛:历史与哲学[M].上海:商务印书馆,1947.
[2]" 弗格森.虚拟的历史[M].颜筝,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2.
[3]" 柯林伍德.历史的观念[M].何兆武,张文杰,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
[4]" 韩震.历史的观念[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
[5]" 李长之.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
[6]" 司马迁.史记[M].裴骃,集解.司马贞,索隐.张守节,正义.北京:中华书局,1959.
[7]" 吴见思.史记论文:上册[M].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2024.
[8]" 钟惺.钟惺评《史记》二种[M].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2022.
[9]" 王逸.楚辞:卷一:离骚经序[M].四部丛刊影印宋刻本.
[10]" 怀特.后现代历史叙事学[M].陈永国,张万娟,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
[11]" 巴尔特.符号学原理:结构主义文学理论文选[M].李幼蒸,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
【责任编辑" " 朱正平】
On the Understanding of Sima Qian’s Historical Philosophy in a Cross-Time Dialogue between Chinese and Western Context
QI Xiaobin
(School of Literary Arts, 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 Xi’an 710100,China)
Abstract:Lu Xun renders a high praise and summary of the perfect fusion of historicity and literary quality in Historical Records by employing “the pinnacle of historiography, the unrhymed Lament”, which is also a vivid expression of Sima Qian’s historical philosophy. Considering the influence of Western historical perspectives on research methods since the 20th century, there have been three main methodological shifts: objective reconstructionism, subjective constructivism, and linguistic deconstructionism. This paper holds that Sima Qian’s historical philosophy reflected in Historical Records is related closely to subjective constructivism, yet it stands out for two millennia with its precocious narrative strategy. This naturally leads one to think of the aesthetic pursuit of Sima Qian’s “unrhymed Lament” as being remarkably similar to the fundamental concepts of postmodern historical narratology constructed by American philosopher Hayden White. Even so, we can only regard this as a dialogue across time between postmodernism and classicism, with their respective ideas and references ultimately different.
Key words:Sima Qian; the theory of reconstruction; constructive theory; narrative philosophy; the pinnacle of historiography, the unrhymed Lament
——兼答张大可先生《司马迁生年述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