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明士大夫的困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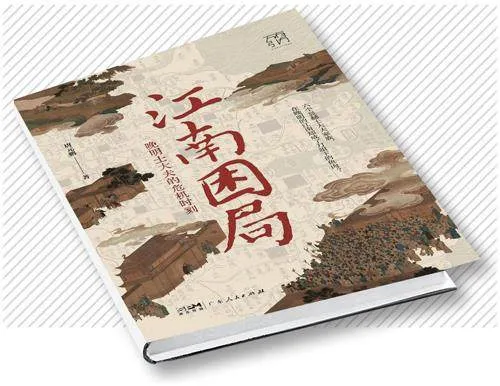
1948年,吴晗与费孝通在《皇权与绅权》里提出,所谓“绅权”,就是“绅士”之权。“绅士是退任的官僚或是官僚的亲亲戚戚。他们在野,可是朝廷内有人,他们没有政权,可是有势力。”“官僚是和绅士共治地方的……往上更推一层,绅士也和皇权共治天下。”费孝通在书中提出:“政治愈可怕,苛政猛于虎的时候,绅士们免疫性和掩护作用的价值也愈大,托庇豪门才有命。”
在唐元鹏的新著《江南困局:晚明士大夫的危机时刻》里,读者同样能够发现,即便在危急时刻,晚明年间士大夫的“绅权”也引人注目。比如,书中提到宜兴(今属无锡市)缙绅陈一教的两个家奴竟也能称霸乡里。他们看上他人家财妻子,就能凭空诬陷他人,随后将其家财席卷而空。区区家奴威风如此,何况家主!
而这与明代的“制度安排”大有关系。明朝开国之初,太祖朱元璋就下令,“自今百司见任官员之家,有田土者输租税外,悉免其徭役”。发展到明代中后期,嘉靖二十四年(1545)规定,京官一品免三十丁,二品二十四丁,至九品兔六丁,外官各减一半,不但见任或退休官员,连学校生员除本身外,也免户内差徭二丁。这就使得士绅家族得以逃避沉重的徭役负担。
不仅如此,嘉靖二十四年还规定京官一品免粮三十石,二品二十四石,到九品免粮六石,外官减半。甚至生员无力完粮时也可以奏销豁免。而且,官员退休,身份特权仍在,“致仕官居乡里……庶民则以官礼谒见,敢有凌侮者论如律”。这实际上就是皇权对绅权的有意宽容放纵。
就像《江南困局》里提到的那样,“当时的缙绅家族,不一定非要贪腐才能发家致富”。只要科考场上发挥出色步入仕途,自然就能“学而仕则富”。书中就提到了几个缙绅家族白手起家的故事。譬如湖州南浔人董份,“原本还是普通人家”,但考取进士后“仅仅用了20年,就成为当地数一数二的富家大户”。
个中奥妙,就在于不少人会主动带田产、房产投献到董家。“如此一来,平民百姓可以免除赋税徭役,或打折缴税,还能得到大户荫庇,不受别人欺负。”这种情况,实在令人联想起传世名篇《范进中举》:“自此以后,果然有许多人来奉承他:有送田产的;有人送店房的;还有那些破落户,两口子来投身为仆,图荫庇的。到两三个月,范进家奴仆、丫鬟都有了,钱、米是不消说了。”
无怪乎《江南困局》书中的描述:“在大明270多年历史中,科举出身的孔孟弟子组成了这个国家最有权势的阶层。”当然,从《江南困局》提到了不止一个“鲤鱼跃龙门”的例子来看,明代的科举制度在成就寒门子弟的上升通道这方面,仍然起着一定的正面作用。
至于书名中的所谓“江南”,指的是以苏州府、松江府为核心,今天分属江浙沪的环太湖流域,而这一带真是大明朝廷的“人文渊薮”。一县所出进士、状元,甚至可能胜过别处一省。士绅之盛,自不待言。功名之士除进入朝廷为官之外,更多的则是滞留乡里,形成庞大的士绅阶层。他们通过各种师生、同年、亲缘、地缘等关系网络,以及官府赋予的特权,广泛地干预地方事务。刘宗周就因此感叹:“江南冠盖辐辏之地,无一事无绅衿孝廉把持,无一时无绅衿孝廉嘱托。”
尽管如此,如此显赫的江南士大夫们还是遇到自己的“至暗时刻”。《江南困局》里描述了万历、天启、崇祯三朝的六件士大夫家族的祸事,即“董范之变”“荆熊分袒”“火烧董家楼”“郑鄤凌迟”“扒宰相坟”“王氏复仇记”。
其中,“王氏复仇记”里的苦主,常熟人祝化雍,也不是泛泛之辈,他在天启元年(1621)考取举人。须知,常熟所在的南直隶,是整个明朝举人录取率最低的地方(2.3%),连举人考进士的难度都只能瞠乎其后(6%)。但跻身士绅之列的祝化雍,还是被谋夺自家房产的恶邻逼死了,原因无他,邻居也是士绅,而且是一门四进士的赵氏。其势自然不是区区一个举人所能抵挡得了的。而武进(今属常州市)人郑鄤以二甲第30名进士出身金榜题名,中庶吉士入翰林院,最后却以“杖母”忤逆大罪遭崇祯皇帝亲自下令凌迟极刑—有明一代,“凌迟而死的文官不过三五人尔”。在皇权面前,绅权显得脆弱无比。
至于前面提到的董份,虽然有过兴建义仓、购置义田的善举,也难免民众蜂起,成百上千地上门纠缠,要求还钱退田,甚至劫掠粮米。经此一遭“斗地主”,董家家道中落,一蹶不振。以吏部尚书、翰林学士“致仕”(退休的)董份去世不过十年,董家“家中房屋已被奴仆侵占,却无力讨回”。无怪乎归有光有言,“吾吴中,无百年之家久矣”。
士大夫何以落到如此地步?用列夫·托尔斯泰在《安娜·卡列尼娜》里的名言来说,就是“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祝化雍死于士绅倾轧这一点,倒是恰恰说明,“江南士大夫”这一群体,绝非铁板一块。
大名鼎鼎的“东林党”虽以无锡东林书院为名,其实“东林三君”,即顾宪成、赵南星、邹元标里,倒是只有顾宪成一位是江南人,反而作为“东林党”敌手的“浙党”里,像嘉兴平湖人刘廷元之类,出生地距离无锡不过二百里,却未以地缘关系投身东林。
至于类似董份的噩运,《江南困局》里分析,明代中后期,“除了正税,还有各种苛捐杂税,以及看不到的各级官吏的中饱私囊,所有这些搜刮与人民生存之间的平衡点”,也就是书中所言的“胥吏平衡”状态,被打破了。一旦超过临界点,民众就会奋力反抗,酿成一次次的“民变”。
耐人寻味的是,在这些民变中,也有万历年间的“民抄董宦”一案。著名的书画家董其昌平素放纵家奴鱼肉乡里(华亭县即今上海市松江区),终于引来民众围攻,火烧董家楼。恰恰是生员在这一事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以至于董其昌事后坚持,松江民众是被秀才煽动,所以“民抄董宦”根本就是“士抄董宦”。
书中认为,这是因为江南的科举难度过高。渴望走上仕途,挤进上层社会的生员队伍是如此庞大,而取士名额又极其有限,屡试屡败,老死场屋便成寻常之事;失望、愤懑之余,便成为“蓝袍大王”,在城际乡间掀起波澜了。
除了这些原因之外,作者也将社会巨变的原因归结于“隆庆开海”(1567)之后海外白银涌入明朝,“白银资本以无与伦比的威力,冲击着以土地产出为命脉的农业社会”,“这次冲击直接导致官员与在野缙绅集团共治地方的秩序开始崩溃”。海外白银促使明朝货币彻底转变为“银本位”自是事实,但遗憾的是,全书对其影响并未详加辨析,语焉不详之下,论点未免显得有些单薄了。
另外,《江南困局》未及展开阐述,但同样值得一提的是,明代中后期江南的“民风尚奢”固然成为世人瞩目的现象,所谓“人情以放荡为快,世风以侈靡相高,虽逾制犯禁,不知忌也”,而这是否也与当地士绅家族富贵难以长久延续互为因果呢?
世事难测,人生无奈,“缙绅家非奕叶科第,富贵难于长守”,达官显贵之家也罕能保其永久富贵。既然门祚盛衰无常,荣华富贵不知哪日就会像《红楼梦》里的贾家一样落得“白茫茫一片大地真干净”的下场,那么及时行乐,将较多的金钱用于奢侈性的消费,恐怕也就顺理成章了。
最后,延续晚明三朝的“江南困局”的终局又是如何呢?甲申之变,明廷灭亡。不多久后,清军入关,终于一统天下。在明清鼎革的社会激荡过程中,江南士绅做出了各自的抉择。
同为董其昌的孙子,董庭在河南归德知府任上投降清军,回乡后为反清志士所杀。董建中一直以变卖祖上留下的字画为生,最后以向康熙帝献上董其昌字画赢得“圣心”,谋得一份官职。而董康则毅然投身反清事业,随后事败遇难。
随大明一起灭亡的,还有士绅在江南社会的显赫地位。清政府先后兴起丁酉科场案、通海案、哭庙案、奏销案。在朝廷连续不断的无情打击下,江南“士大夫日贱,官长日尊,于是曲意承奉,备极卑污,甚至生子逍女,厚礼献媚,立碑造祠,仆仆跪拜,此辈风气愈盛,视为当然,彼此效尤,恬不为怪”。
清代前期,一如《皇权与绅权》所言,“新绅士是从奴化教育里成长的,不提反抗,连挨了打都是‘恩谴’,削职充军,只要留住脑袋便感谢圣恩不尽,服服帖帖,比狗还听话”。就这样的不堪处境而言,晚明士大夫在进入清代之后,其实并未走出“危急时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