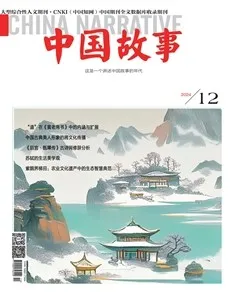白先勇小说影像化叙事的独特魅力
【导读】白先勇的小说受中国传统文学的影响,具有浓厚的人文色彩。同时,他的小说呈现出强烈的画面感,这使得小说具有影像化特质。本文从叙述画面的影像化、时空结构的影像化两方面入手,对白先勇小说中的影像化特质进行深入分析。
白先勇是当代著名作家,他的小说作品主要有《寂寞的十七岁》《台北人》《纽约客》和《孽子》等。小说中高超的语言艺术、娴熟的写作技巧和崇高的文学素养历来为人称道,使其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白先勇本人深受中国传统文学的影响,其小说的影像化特质也受到了中国传统文学的影响。他本人曾经说过:“我受中国诗的影响很大。我从小爱好唐诗宋词元曲,它们不但给我感性的影响,具体的意象表达手法也启发了我。我从小就看红楼水浒这些传统小说。”在其小说《满天里亮晶晶的星》中,便出现了中国传统诗歌中出现的“暖烟”“荷花”“月亮”等意象的组合,它们犹如电影中一个个切换而过的特写镜头,为小说文本增添了画面感。
另外,他的很多小说也被改编成了影视作品和戏剧作品。例如,《金大班的最后一夜》《玉卿嫂》《花桥荣记》《一把青》等都被改编为了影视作品。白先勇的小说之所以能够受到诸多知名导演的青睐,不仅是因为小说中生动饱满的人物形象、曲折生动的故事情节,也是因为其文本创作中含有影像化特质,便于改编为影视作品。在白先勇的小说中,影像化特质主要表现在小说文本讲究叙述画面,具有强烈的视觉画面感以及音画结合的视听性。同时,小说文本讲究时间的碎片化和空间的重构化。
一、叙述画面的影像化
小说是一种以刻画人物形象为中心,通过故事情节和环境描绘来反映社会生活的文学体裁。小说中的事物和场景都是高度中介化的,显得略微抽象。反观电影、电视剧,它们具有强烈的画面感和直接性。
(一)强烈的视觉画面感
白先勇的小说在对某一景物、人物进行刻画,或对某一情节事件进行讲述时,往往会使用富有动感的形象化文字,使得小说内容具有强烈的画面感。这种画面感主要是通过色彩词来呈现。
在电影美学理论中,色彩被当作一种极具表现力的艺术手段,起到渲染氛围、表现张力的作用。在文学领域中,色彩也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运用色彩词是白先勇小说中的一项显著特征。“可以这样说,一个对色调敏感的人一定程度上也是内心丰富而又和外界有距离感的人,而白先勇正是这样一个对色调敏感的学生。”翻开白先勇的文学作品,色彩词比比皆是,很多篇小说的题目直接与色彩相关,例如《那片血一般红的杜鹃花》《一把青》和《黑虹》。
在长篇小说《孽子》中,白先勇用生动的笔触描绘了新公园的景象:
“公园里的树木,热得都在冒烟。那些棕榈、绿珊瑚、大王椰,一丛丛郁郁蒸蒸,顶上罩着一层热雾……天上黑沉沉,云层低得压到了地面一般。夜空的一角,一团肥圆的大月亮,低低浮在椰树顶上,昏红昏红的,好像一只发着猩红热的大肉球,带着血丝。”
在这段描写中,作者运用了大量色彩词,如:绿、黑沉沉。昏红,这些色彩词使得此处的环境描写更为鲜活,仿佛一幅生动的画卷。白先勇为读者描绘了一个气氛压抑的王国,在这里,有罩着热雾的绿珊瑚,有黑沉沉的云朵,还有昏红肥圆的月亮。这些被赋予色彩的景物给读者以强烈的视觉冲击力和画面感,令读者仿佛身处于这个压抑昏暗的新公园之中。将昏红色的月亮放置于黑色的背景之中,具有强烈的对比效果。而且在此处,形容月亮的红色并非正红,而是昏红,就更显示出月亮的肥腻、硕大。
在白先勇的小说中,色彩词使得文本带有视觉冲击力,读者在阅读时就像身处于小说场景之中,这与影视作品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二)音画结合的视听性
在影视作品中,丰富的声音是必不可少的要素,它为电影和电视剧讲述故事、塑造人物、营造环境、渲染氛围,都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在小说中,将声音和画面结合起来能够增强文本的视听性,创造出非同寻常的视觉空间,使得叙述画面更具影像特点。
在小说《闷雷》中,白先勇也采用了音画结合的手法来体现叙述画面的影像化。文中写道:
“客堂里又热又闷,空气浊重得很,纱窗上不断发出‘噗咚’、‘噗咚’蛾子撞闯的声音,窗外一阵连一阵呜着隆隆隆沙哑的闷雷,福生嫂的额头一直不停的沁汗,她觉得快闷得透不过气来了。”
在这段描写中,白先勇先描绘了在一个闷热的客堂中,福生嫂沁汗,以及蛾子撞纱窗的画面。接着,作者描写了蛾子撞纱窗的声音和闷雷的声音。此处,音、画被巧妙地融合,文本也因此具有强烈的视听性,使得读者能够真切地感受到福生嫂内心被压抑的情欲,体会到她的痛苦与无奈。由此可见,音画融合不仅能够渲染氛围,也能够反映人物的心理,使文章具有画面感。
二、时空结构的影像化
通常而言,小说是时间的艺术,按照时间顺序讲述故事是其基本特征,但往往会忽略空间构建。随着影视艺术对小说文本的不断渗透,现代小说会借鉴现代影视作品的各种叙事技巧,运用时间倒置或交叉的手法,打破传统小说中单线条的时间顺序,进而从多个角度切入故事、塑造人物、表达情感。
白先勇在创作小说时,兼顾了时间结构和空间结构的双重变化。在选择叙事手法时,他常常采用意识流的叙事方法,让具体的事件随着人物的心理活动随意展开,没有明确的时间线索,这在很大程度上超越了传统的叙事方法,具有鲜明的现代主义特点。
(一)时间的碎片化
一般而言,小说叙事多以时间的连续性为基础,故事发展顺序比较清晰。然而,当小说吸取影视作品的优势,打碎时间顺序,用场景转换替代传统叙事顺序,使场景显现出非连续性,这就形成了空间小说。
这类小说多利用“闪回”技巧,“将回忆的往事转化为不同的场景,以形象直观的方式呈现出那时彼地,借此来附和比衬此时的现场景。”“闪回”技巧将时间碎片化,小说在时间的转换中,表现人物的心理活动以及历史沧桑感。
例如,在白先勇的小说《游园惊梦》中,主人公蓝田玉身处富丽堂皇的窦公馆,看着此情此景,想着昔日的荣光和如今的落魄,她喝醉了酒,也陷入了回忆与现实交杂的泥潭之中。作者在文中使用了“闪回”技巧,让叙述场景不断地在往事与现实之间来回切换,将不同时间段发生的事情交叉剪辑在一起,使得读者在蓝田玉断断续续的回忆中,体会到了她凄凉落魄的处境,由此加深了人物的悲剧色彩。
又如,在小说《金大班的最后一夜》中,小说通过金大班个人意识的流动,将故事的叙述点自如地切换于现实与回忆之间,时间在现在和过去之间来回游走,逐渐地将读者带入这个历经几十年沧桑的悲剧故事中。
(二)空间的重构化
在影视制作中,电影镜头的剪辑是一个重要环节。剪辑师会把一系列相关或不相关场景的镜头组织在一起。有时,叙事时间会被打断,一些看似无关的意义单位组合,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影片叙事和主题表达。小说运用这一技巧,将不同时空的故事并置在一起,便会与传统小说讲述一个完整的故事不同,会产生层层相生的意义,小说的内涵更为丰富。
这类技巧与影视作品中的“蒙太奇”手法相关联,即“打破叙述情节的时间流程,将不同的空间场景按照一定的艺术构思逻辑交叉衔接组合,力求从多重空间叠合并置的角度来讲述故事、刻画形象。”这种“蒙太奇”手法,常见于白先勇的小说中。
在《金大班的最后一夜》中,小说除了叙写金大班当晚真实发生的事件,还在其中穿插了金大班脑海中出现的几次回忆。例如,金大班曾经在上海“百乐门”当台柱子时风光的场景;金大班曾经收了被童得怀赶出门的朱凤为徒,并把她调教成了一位红舞女的过程;金大班与一位纯情标致的大学生相恋,并为其堕胎的悲剧爱情故事……这些片段式的描写,把不同时空发生的故事组合拼接在一起,带读者领略了上海与台北两个不同空间发生的故事,也将一个常年在风月场混迹的舞女形象展现在读者眼前,加深了金大班这个人物的悲剧意蕴,也突出了她粗俗泼辣、善良的性格。
小说《谪仙记》主要描绘了孤傲的贵族千金李彤,在家庭遭遇变故后自我放逐的故事。她在家国深陷变故时来到美国留学,并在这里遇到了满怀激情的朋友。他们相继恋爱、结婚,而李彤也日益失去了曾经的光芒,最后走向了悲剧。白先勇运用影像化的手法将不同人物的命运并置在同一时间的不同场景中,在讲述李彤悲惨命运的同时,将好友们的婚恋活动穿插其中。这些来回切换、迅速跳转的场面,使得小说情节与影视作品中来回切换的分镜头有着极大的相似性,也加深了李彤的悲剧色彩。
由此可见,小说的叙事若突破空间顺序,则能够更加灵活自如地展示小说人物的命运遭际和人生沉浮。这种充满影像可视性的艺术手法使得小说更富画面感,也烘托了小说的主题,具有独特的艺术审美价值。
三、结语
白先勇的小说对当今文坛仍然有借鉴意义。他在继承中国传统文学人文性的基础上,对小说的叙事技巧进行了创新,取得了一定意义的突破。白先勇的小说受到了读者的追捧和喜爱,也受到影视剧导演的青睐。
参考文献
[1]白先勇.白先勇与《游园惊梦》[M].广州:花城出版社,2000.
[2]王玲玲,沈浮明.最后的贵族——白先勇传[M].北京:团结出版社,2001.
[3]方静杰.白先勇小说的“电影化想象”[D].河南:河南师范大学,2015.
[4]牟文烨.论王安忆小说的影像化叙事[D].青岛:中国海洋大学,2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