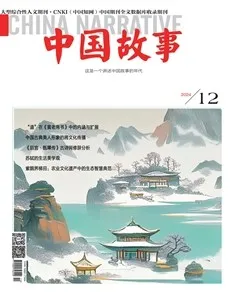刘禹锡对“桃源”理想的追逐与超越
【导读】刘禹锡继承并发扬了魏晋陶渊明所创的桃源情结,在地域空间中对“桃源”理想进行了实践,更加仙化了原本存在于文本想象中的“世外桃源”。刘禹锡励精图治,却被迫远离政治权力中心,又因玄都观题诗这一导火索,被守旧派抨击的他再次遭贬。刘禹锡在面对政治上的失意时,在秉持传统儒教思想的基础上,自觉靠拢宗教,以期实现“桃源”理想。刘禹锡在“巴山楚水凄凉地”的二十余年中,主动将少数民族的风俗人情融入诗歌,丰盈自身的精神世界。
匡扶社稷,挽大厦之将倾,重现大唐盛世,是刘禹锡毕生的“桃源”理想。但永贞革新的失败以及长达二十四年的贬谪生涯,让他逐渐意识到现实与理想的巨大差距。刘禹锡重游玄都观之际,深刻洞察了世间万物的沧桑变化。而之前长达十年的朗州贬谪岁月,让他内心深处对武陵桃源的向往被唤醒,更促使他深入探索桃源仙境与现实世界的种种纠葛。
刘禹锡的官场仕途是坎坷多舛的,但他的抱负始终如初,坚信“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一路追逐理想的“桃源”,最终达成对自我的超越。
一、中唐变迁下的刘禹锡诗歌创作
随着一声声“渔阳鼙鼓”,安史之乱让盛唐气象匆匆降下帷幕。恰如六朝时繁华的“朱雀桥边”“乌衣巷口”,随着岁月轮转,最终归于荒凉。“诗到元和体变新”,中唐政治格局与社会生活的变迁,极大影响了诗人的创作心态与思想风格。贞元以后,贪婪无度的宦官“威权日炽”,不思进取的官吏“剥下媚上”。在这些蠹虫的侵蚀啮咬下,大唐已是千疮百孔,如同桃树受了虫害,长出脓包,得了流胶病。
(一)咏史言志
处于国家由盛转衰节点上的中唐诗人,一边回味着盛唐风骨的浪漫与傲气,一边在时过境迁的失落里煎熬。面对唐朝这棵曾经“灼灼其华”,而今“痈疽疔疖”的桃树,刘禹锡从未放弃,始终怀着一颗诚挚的“报国松筠心”。为了重整朝政秩序,永贞元年,刘禹锡参与了以“内抑宦官,外制方镇,摄天下财赋兵力而尽归之朝廷”为目标的王叔文政治革新集团。由于触犯了“阉宦”“强藩”的利益,改革受到阻挠,难以推行。革新失败后,刘禹锡亦难逃被贬的悲剧命运。
《容斋随笔》载:“唐人歌诗,其于先世及当时事,直辞咏寄,略无避隐。”洪迈枚举了杜甫、白居易、元稹和李商隐的部分诗作,阐述了唐人作诗无避讳的特点。而作为元白好友的刘禹锡,其作诗亦具有很强的现实性。刘禹锡常常借古讽今,针砭时弊,在咏史中抒发报国志向。譬如在《咏史二首》中,他借任少卿不愿弃旧主卫青而改投霍去病的典故,来表达虽然“世道剧颓波”,但是“我心如砥柱”的坚定情操。他还将汉朝“明王道”的贾谊与“工车戏”的卫绾相对比,以讽刺当权者识人不清、小人投机取巧。刘禹锡多次遭遇流贬,光阴流转,“衰节”已至,但仍存“老骥伏枥”之志。他辛辣嘲讽了唯利是图、无耻窃国的王侯,以“昔贤”为榜样,坚守节操,为国而忧。
(二)桃花讽喻
玄都观坐落于长安城内,是一座闻名遐迩的道教庙宇,“汇聚了来自全国各地的高道大德,参与了唐代宫廷的道教活动和文化事业,在唐代道教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玄都观具体的始建时间已经难以考证,北周时已有相关记录,隋初至唐玄宗时代是其辉煌时期,后来在唐昭宗天祐元年(904年),因四镇节度使朱全忠的叛变而毁于一旦。玄都观本是十分清净的宗教场所,但后来却种植了百亩碧桃,染上了世俗色彩。玄都观从繁华逐渐走向衰亡的进程,“可以间接地观察到唐代道教的升降和变迁”,也能窥见唐王朝由盛而衰的历程。
刘禹锡曾在玄都观几度题诗,玄都观见证了刘禹锡的宦海浮沉。一首《元和十年自朗州承召至京戏赠看花诸君子》,狠狠戳痛了朝中趋炎附势的守旧派。这首诗表面上看,是记叙玄都观赏桃花一事,实际以桃花喻权贵,讥刺之意尽显,惹得“执政不悦”。刘禹锡因“语涉讥刺”被贬为连州刺史,而这一贬足有十四年,其间“连刺数郡”,先后任夔州、和州刺史等职。《鹤林玉露》记载:“刘禹锡种桃之句,不过感叹之词耳,非甚有所讥刺也,然亦不免于迁谪。”罗大经认为,刘禹锡遭遇贬谪是政治斗争的必然,与诗人在玄都观的题诗关系甚微。如果说政治斗争的失败是诗人遭遇贬谪的根本原因,那么这首玄都观桃花诗是诗人再次遭贬的直接导火索。故玄都观可抽象为刘禹锡人生轨迹中一个重要的地标。
二、真实与虚构:武陵“桃源”的流变
当社会秩序逐步瓦解,个体身处艰难的境遇时,文人往往会在自己的想象中构建一个“桃源”世界,以此作为心灵的栖息之所。
(一)桃源流变
“桃源”情结可以上溯至陶渊明的《桃花源记》。清人王先谦亦认为:“桃花源,章自陶靖节之记,至唐乃仙之。”陶渊明虚构的世外桃源,其入口处便已是不同寻常的曼妙之景。它被武陵的一位渔人偶然发现,在这片桃源里,时间仿佛静息,桃源中人“不知有汉,无论魏晋”,隐逸意味浓厚,折射出创作者的避世之心。
桃源社会具有天下大同的性质。“桃源”里有“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的理想生活,但“桃源”可遇不可求。武陵渔人在无意中进入了桃源,但他一旦离开,回到尘世,便再也寻不到了,只能“遂迷不复得路”,空余叹惋。《隋书》记载:“武陵郡梁至武州,后改曰为沅州。平陈,为朗州。”文学地理具有虚构性,但陶渊明笔下的“武陵”并非全然幻构,亦有实地为载体,有迹可循,从而为后世文人提供了理想依托。
《旧唐书》描述朗州是“地居西南夷,土风僻陋”,但是文学却赋予了“武陵”独特的“桃源”气质。“诗佛”王维对武陵桃源非常渴慕,写下多首相关的诗歌,有“渔舟逐水爱山春,两岸桃花夹去津”“春来遍是桃花水,不辨仙源何处寻”等句。王维《桃源行》是对陶渊明《桃花源记》的艺术再创造,其中提及的“灵境”“尘心”,借用佛语表达了他的出世之心。刘禹锡在被贬朗州之前,也曾写下一首《桃源行》。这首诗与陶渊明的《桃花源记》在叙事结构上,几乎完全一致,都是渔人无意间误入桃源,然后离开桃源,最后难寻桃源。但刘禹锡诗中提到的“石髓”“松脂”,都属于道教炼丹的素材,构筑了一个与王维笔下佛教仙境截然不同的道教式仙境。
(二)精神寄寓
刘禹锡因革新被贬,曾担任朗州司马几近十年,在真实的地理上与武陵桃源发生了关联。在朗州这样的“凄凉地”,他并没有一味地沉浸在贬谪的失意中,而是以“我言秋日胜春朝”的旷达豪情,亲往武陵桃源,一探究竟。“渊明著前志,子骥思远蹠”,身处实际的武陵,刘禹锡联想到陶渊明诗文中的桃源,也在心中有了一处静谧的安慰之所。
身处“凄凉地”,刘禹锡依旧拥有乐观的态度和高雅的情调,在中秋之夜,前往桃源“玩月”。刘禹锡在《八月十五日夜桃源玩月》一诗中直接把桃源称为“仙府”,佳节美景,清静宜人。其中“凝光悠悠寒露坠,此时立在最高山”一句,与《游桃源一百韵》中的“遂登最高顶,纵目还楚泽”有异曲同工之妙。诗人登顶桃源的最高处,俯仰之间,将风云山水、天地群山尽收眼底。圆月高悬的苍穹之下,“少君”为诗人引路,得以远远地与“仙官”相见。斗转星移之间,诗人飘飘欲仙,但一声“天乐”,将诗人拉回寒风刺骨的人间。日出东方,月亮西斜,引起诗人无限遐想与美感的桃源仙境即将消失,赏月的闲情逸致已化为悲凉落寞。此后一别,“绝景良时”再难相会,故诗人万分不舍,频频回望。
不过,刘禹锡笔下的桃源并不是全然地单纯美好,在《游桃源一百韵》中,诗人自抒心志:“巧言忽成锦,苦志徒食蘖。平地生峰峦,深心有矛戟。层波一震荡,弱植忽沦溺。北渚吊灵均,长岑思亭伯。”桃源之景虽然美丽可爱,但诗人却在现实生活中饱受贬谪之苦,也为国家朝纲痛心疾首,由此联想到与自己境遇相似的屈原与崔驷,不禁心神震荡。如果说“凄凉地”是诗人刘禹锡肉体的生活空间,那么“桃源乡”则成了诗人精神的安放空间。
桃源意象附丽着宁静安逸,脱离俗世纷扰,甚至远离生死病老之苦,这使得桃源具有了仙化的潜质。唐朝对儒释道三教采取了调和并用的政策,这也促使桃源意象有了宗教化的意味。
三、闻唱竹枝歌:巴蜀风俗人情再现
朗州虽然是“凄凉地”,但是既有宁静的武陵桃源,亦有质朴的乡土民歌。“禹锡在朗州十年,唯以文章吟咏,陶冶情性。蛮俗好巫,每淫词鼓舞,必歌俚辞。禹锡或从事于其间,乃依骚人之作,为新辞以教巫祝。故武陵溪洞间夷歌,率多禹锡之辞也。”刘禹锡在朗州任职期间,秉持“虽甿谣俚音,可俪风什”的创作思想,不仅欣赏民歌民舞,了解到当地百姓有频繁祭祀的传统,还对民歌进行了艺术加工与形式创新,创作了“含思宛转”的新辞,在竹枝词中再现了巴蜀地区的风俗人情。
(一)民俗入诗
刘禹锡对巴蜀民俗的描绘是“其他唐代诗人笔墨未至、锄犁罕及的”。荆楚之地常有祭祀,崇神信巫,刘禹锡以诗记之。
《阳山庙观赛神》诗云:“荆巫脉脉传神语,野老娑娑起醉颜。日落风生庙门外,几人连蹋竹歌还。”朗州有祭神的风俗,所谓“赛神”,就是当地人迎神的集会。此处的“神”,源于历史上真实存在的人物。刘禹锡亦自注云:“梁松南征至此,遂为其神,在朗州。”百姓有感梁松因征战而死,逐渐将其神化,令其得享供奉。“赛神”一系列的箫鼓、杂戏等仪仗活动完毕后,众人翩翩起舞,吟唱“竹歌”而还。与梁松庙的人声鼎沸不同,子胥庙尤为荒凉。《汉寿城春望》诗云:“汉寿城边野草春,荒祠古墓对荆榛。田中牧竖烧刍狗,陌上行人看石麟。”“荒祠古墓”指的是诗人在朗州登汉寿城所望见的子胥庙和楚王坟。世事沧桑,曾经历史上的风流人物,如今也只有牧童焚烧草扎成的狗来祭祀。
除了采菱、竞渡等日常习俗外,荆楚之地亦有独特的民族节日。刘禹锡登临武陵城时,忆起俚人庆祝的“祠竹节”,并以“仙洞闭桃花”之句抒发感慨。《后汉书》中的《南蛮西南夷传》对“祠竹节”的来源有较为详细的记载:浣衣女于水中流竹发现男婴,便以竹为姓,抚养长大,男子死后亦逐渐被神化为竹王神。此神话源于夜郎地区,后流传到朗州,遂演化为“祠竹节”。
(二)文体创造
竹枝词源于民间的祭祀习俗,既浸透了奇诡的宗教色彩,又氤氲着浓郁的乡土气息。“竹枝”一词,最早由杜甫提出,刘禹锡则使“竹枝”由乡野民歌转为文人诗词。因此,刘禹锡对“文人竹枝词”有文体创造之功。
刘禹锡二度被贬,任夔州刺史时,曾作多首《竹枝词》。“他入峡任夔州刺史的三年,便是学习民歌取得创作大丰收的时期。”刘禹锡的《竹枝词》展现了巴蜀地区的风俗习惯与民歌风味,开拓了中唐的通俗诗风。竹枝声里不仅流露了夔州当地的山川节物与“赛神”传统,还传达了巴蜀男女相悦的缱绻情意,更融入了诗人自身的诙谐嘲谑。《竹枝词二首》云:“楚水巴山江雨多,巴人能唱本乡歌。今朝北客思归去,回入纥那披绿罗。”诗人久受贬谪远任之苦,又听到巴人吟唱本乡之歌,思归之意愈浓,亦回忆起故乡之曲《纥那》。白居易在《忆梦得》诗中云:“几时红烛下,闻唱竹枝歌。”并自注云:“梦得能唱《竹枝》,听者愁绝。”刘禹锡在夔州谪居期间,亦将自己几度从中央被贬谪到地方的经历,写成《浪淘沙词九首》。钱塘江水奔腾汹涌,虽然因为撞到岸边山石而回,但它并非什么都没能改变,尚可“卷起沙堆似雪堆”。
刘禹锡生活在政治昏暗、民生凋敝的中唐时期,他参与永贞改革,成为核心人员之一,以期能够除蛀革新,却惨遭贬谪。他左迁朗州,虽无实权,但得以亲往武陵桃源。桃源这一概念,在历经众多诗文的再次想象与描绘后,逐渐被赋予了超凡脱俗、近乎仙界的特质,为失意的文人士子提供了精神慰藉。在巴山楚水的二十余年里,刘禹锡并未浑噩度日,而是努力汲取儒释道中的积极思想。
大和二年(828年),刘禹锡得返长安,此时玄都观的桃花已经凋零殆尽,种桃道士不见踪影。诗人一扫心中块垒,而朗州的桃源与巴蜀的民歌将永远存在于他的诗歌中,支撑他走过坎坷的仕途,实现对自我的超越。
参考文献
[1]刘禹锡.刘禹锡集笺证[M].瞿蜕园,笺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
[2]白居易.白居易诗集校注[M].谢思炜,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06.
[3]刘昫.旧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4]刘康乐.唐代长安玄都观考[J].中国本土宗教研究,2022.
[5]张思齐.从刘禹锡诗看中唐道教的升降变迁[J].宗教学研究,2000(1).
[6]陶渊明.陶渊明集[M].逯钦立,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18.
[7]王维.王维诗集[M].赵殿成,笺注,白鹤,校点.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
[8]刘禹锡.刘禹锡集[M].卞孝萱,校订.北京:中华书局,1990.
[9]肖瑞峰.论刘禹锡诗的历史地位[J].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5(5).
[10]杨世明.巴蜀文学史[M].成都:巴蜀书社,2003.
[11]王鸣盛.十七史商榷[M].黄曙辉,点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12]洪迈.容斋随笔[M].孔凡礼,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15.
[13]罗大经.鹤林玉露[M].刘友智,校注.济南:齐鲁书社,2017.
[14]王先谦.葵园四种[M].梅季,标点.长沙:岳麓书社,1986.
[15]老子.老子[M].汤漳平,王朝华,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14.
[16]魏征.隋书[M].北京:中华书局,20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