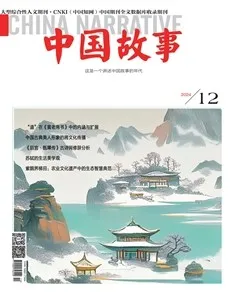浅谈古代朝鲜、日本对汉字受容的共同点
【导读】古代中国对周边国家和地区在政治、文化、经济等多个领域均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形成了以汉文化为导向、以汉字为核心的文化共同体,学界称之为“汉字文化圈”。汉字作为其中的纽带,起着无可替代的作用。今天,我们应该深化东亚地区文化史研究,促进东亚文明之间的对话交流,让汉字在全球舞台上展现魅力。
汉字文化圈是世界五大文化圈之一,指曾用汉字书写历史,曾共同使用文言文作为书面语,并受中华法系影响的东亚国家和地区。从地理划分的角度称之为东亚文化圈,从思想的角度可称为儒家文化圈。因所属国家和地区的人民都使用筷子进餐,也有人戏称为“筷子文化圈”。其中汉化最深的,当属朝鲜半岛和日本。汉字和汉文是汉字文化圈形成的先决条件,古代朝鲜和日本没有自己的文字,他们学习使用汉字,并以此为媒介,接受了中国文化在律令、宗教思想、教育制度、技术文化等各方面的影响,引起了一系列相似的文化现象,从而构成了文化共同体。由此可见,汉字传播带来的意义远远超过文字本身。但这种文化流向是单边的,是两国基于文化需求,单方面接受中国文化。本文将从古代朝鲜和日本对汉字受容的共同点进行探讨。
一、汉字的东传和影响
在古代东亚社会,识汉字、通汉文是身份的象征,王公贵族学的都是汉字,国家考试也用汉文,公私文书都用汉字编写。直到19世纪以前,汉文仍然是整个东亚地区最权威的书写文字。日本明治维新前的最后一部图书目录显示,日本的幕府文库(相当于国家图书馆)里仍然有65%为汉文书籍;而在朝鲜,直至1895年甲午战争中国战败为止,汉文一直是其官方文字。如今朝鲜和日本的常用汉字限定在1800字左右,因此现代日、朝/韩学者如果没有经过正规的汉文训练,甚至无法阅读本国的古典文献资料。
汉字东传的说法众多,最初何时传入朝、日至今学界尚无定论。汉文典籍系统地传入朝鲜时,正值半岛的三国时代(约公元300年),高句丽最早,百济次之,新罗最迟。早期传入的主要是《论语》等一批儒家经传,大约从6世纪开始,朝鲜半岛的史书记载开始广泛使用汉字;日本在4世纪后半叶,由百济博士王仁携《论语》及《千字文》东渡日本,初传汉籍,至8世纪时日本开始普遍使用汉字。日本最早的史书《古事记》和《日本书纪》就是以汉字记录的。
隋唐时期,朝鲜半岛和日本各自的中央集权初步建立,两国都向中国派遣了大量使节和留学生,学习先进科技文化及律令典章制度,带回了包括史书、儒家经典及佛教经文在内的大量汉文典籍。这给朝鲜和日本的史学、教育、文学、政治和宗教等多个领域带来影响,大大促进了两国的发展。
在史学方面,史书随汉字传入,朝鲜和日本模仿中国史书的体例,以汉字置国史。比如,日本的《日本书纪》、朝鲜的《三国史记》等。在教育方面,朝鲜和日本建各类学堂教授汉字汉文,皆设太学、科举,置博士、助教等。国家考试亦以经传为主要科目。在文学方面,朝鲜和日本的文学作品,无论形式还是内容都是模仿中国文学。以东亚文学形式之首的汉诗为例,一些优秀的朝鲜和日本汉诗,若抹去作者姓名及诗中所涉地名,与中国本土汉诗放在一起,甚至难辨国别。汉诗对朝鲜和日本的母语诗歌也有着不容忽视的影响,比如朝鲜诗歌流行的四四、三四调,是模仿《诗经》中的四言诗;日本和歌的五七五调,则受到五言及七言诗的影响。
二、早期汉字的使用
汉字传入之后,朝鲜和日本皆兴起了“文言二途”之制,即口语使用本土语言,但书写使用汉文。因此朝、日最初的文学作品,皆是以汉字标记母语文学的作品,比如朝、日两国上古时代的原始母语歌谣。汉字作为唯一的记录工具,朝、日两国的使用方法基本相同,都分为三种方式:
第一种是将汉字作为音标,以汉字的发音记录母语的发音,汉字本身不表达任何含义。比如日本最早的史书之一《古事记》,收录了若干全部用汉字标记日语发音的上古歌谣。
第二种是用汉字词记录母语的词义。相当于用汉字翻译并传达原本的含义。
第三种是结合以上两种方法,即汉字标音和标义混用,既能一定程度上保持母语原文形态,又能较为准确地传达文字本身的含义。日本第一部诗歌总集《万叶集》就是用此法写成,这种文字也被称为万叶假名。朝鲜的新罗乡歌也是采用此种方式,被称为“吏读”,即以汉字标记朝鲜语发音和意义,用朝鲜语发音读汉字。古代朝鲜和日本用汉字成功记录了母语文化的口传文学,由此开创了各自的母语文学时代。
三、汉字的音读与训读
现代人阅读的外国文学作品通常都已经翻译过,一些畅销书籍甚至能被翻译成上百种语言,方便世界各国人民阅读。但是在古代,东亚文人交流靠的并非翻译,而是直读中国文学。其实汉语与朝鲜语、日本语属于完全不同的语系。汉语属于汉藏语系,为孤立语,语法顺序是主语+谓语+宾语;朝鲜语和日语属于阿尔泰语系,为黏着语,语法顺序是主语+宾语+谓语,动词在最后,而且需要添加助词表明名词、动词的状态。句子的语法关系,通过实词后面的黏着部分实现,与汉语存在巨大差异。但是基于当时对中国文化的迫切渴望,朝鲜和日本可谓费尽心力,创造了一种巧妙且独特的阅读方式,使他们的文人能够直接阅读中国文学,甚至能以汉文创作文学作品,这便是汉字的音读和训读。在古代,朝、日两国都出现过音读和训读现象,但朝鲜训读到吏读后就逐渐没落了。
词汇是语言之间建立对应关系的基本条件。古代朝鲜人和日本人在母语与汉语之间建立了直接对应关系,即与汉字形同、义同,音可不同。因此同样一个汉字,在朝鲜语和日语中可能存在多个发音,其中包括音读发音和训读发音。另外,上面提到过,汉语与二者在语法方面也存在巨大差异,因此除了词汇的训读方式外,也产生了语法的训读方式。
(一)词汇的音读
音读指模仿汉字的读音,选择尽量接近汉语发音的识读法,一般按照这个汉字从中国传入朝、日的读音来发音。根据汉字传入的时代和来源地的不同,日本的音读分为“吴音”(7世纪通过朝鲜半岛的百济传来的江南音)、“汉音”(8世纪以后的唐代长安音)、“唐音”(宋元以后主要由禅宗的传播带来的福建等南方地区的特殊发音)三种。朝鲜则保留唐宋时期的中原发音。所以两国汉字词的音读,听起来与中国汉语的方言极为相似。以“汉字”这两个字举例,中、朝、日三国的写法完全相同,但发音上有些微区别,汉语拼音为“hànzì”,日语罗马音为“KanJi(かんじ)”,朝鲜/韩语罗马音为“HanJa(한자)”,后两者读起来与汉语方言无异。音读方法使得每一个汉字有了对应的朝鲜语与日语发音,构成了一套音读系统。
(二)词汇的训读
词汇训读是只借用汉字的形和义,读音还是按照母语来发音。即给朝鲜语和日语的固有词汇配上意义相同的汉字词。比如最早东传的汉文典籍《千字文》,两国在现代的标准阅读方法都是音训结合,即音读和训读两种方式都读一遍,只不过朝鲜/韩国是先训后音,而日本是先音后训。
以第一句“天地玄黄”为例,朝/韩语读法为:하늘(天)천(天)따(地)지(地)감을(玄)현(玄)누를(黄)황(黄);日语读法为:てん(天)ち(地)のあめつ(天)ち(地)はげん(玄)こう(黄)とくろく(玄)きなり(黄)。其中하늘和あめつち分别是“天”的朝/韩语及日语固有词发音,即训读,而천和てん则是音读,以此类推。另外日语中还加入了の、は、と这样的介词、助词和连词帮助理解,他们把这种音训结合的读法称为文选读。这种现象也存在于汉语方言当中,此处举一个汉语语境中的训读例子,比如四川话把手肘称为“倒拐子”,那么“倒拐子”可视为手肘的四川话训读。
(三)语法的训读
语法训读是根据不同的语法顺序,颠倒谓语和宾语的次序来阅读汉文的方法。例如,给汉文标注该词在日文或朝鲜/韩文语法上应在的位置和顺序,以符合后者的语法习惯,再添加上相应的日文或朝鲜/韩文的助词,这样在阅读时无需翻译也能看懂。
四、母语文字出现——日本假名与朝鲜谚文
日本和朝鲜半岛接受并使用汉字、汉文到一定阶段之后,也都逐渐发展出了自己的母语文字,分别被称为“假名”和“谚文”。母语文字的创制初衷其实都是为了能更高效地阅读、记录汉文。因为汉字笔画较多、书写复杂,写起来较为费时,在民间难以推广。为了提高书写速度,促进教育普及,作为简化文字的假名和谚文就诞生了。
日本假名文字最早出现在公元8至9世纪,由汉字草书衍化而来,经历了从万叶假名过渡到平假名的阶段,初期也被称为“草假名”。另外,也有取汉字楷书的偏旁部首创制的片假名。由于这些文字都是由汉字字形假借得来,因此被称为“假名”,对应的是汉字的“真名”。平假名和片假名都是五十个音,但中世纪以前的五十音排列法与现代不同,现在通行的方法是室町时代以后才定型的。
朝鲜则是在公元15世纪由朝鲜王朝第四代王世宗大王,召集语言学者创制的“训民正音”,也就是谚文。最初由28个字母组成(现代韩文有40个),主要参照物还是汉字及汉字音韵。“谚”本身有“俗语”“方言”的含义,对应的正是汉文的“雅”和“正”。本质上假名和谚文都是表音符号,跟汉语拼音类似,用于标记汉字的读音,单独出现时不具备任何含义。
一方面,长久以来古代朝鲜和日本上流社会,都将汉字作为中华文化象征的“高级”文字崇尚,因此母语文字在创制之初都遭到了知识分子阶层的强烈反对,认为其破坏了汉字的“纯洁性”,实属“夷狄”之事,不仅被贵族文人抵制,在官方及正式场合也不得使用;另一方面,受古代中国“女子无才便是德”的思想影响,古代东亚社会只有男性才能学习汉字汉文,而不能接受正统教育的女性才会退而求其次,学习母语文字,因此假名和谚文都一度流为女性文字。
比如有日版红楼梦之称的《源氏物语》,就是由平安时期宫廷女官紫式部用平假名文字书写而成。同时期的女官清少纳言,日本随笔文学鼻祖《枕草子》的作者,在宫里写汉诗时还被紫式部嘲讽为装模作样,“她那样自以为是地书写汉字,其实,仔细看来,有很多地方倒未必是妥善的”。因为在平安时代的日本,汉学乃严肃、高深的“治世之学”,汉字并不适合女流之辈作吟风弄月之用。平假名,除了和歌外,主要用于私人书信及女流文学。所以平假名,别名女文字(女手),汉字则是男文字。
朝鲜谚文也一样,除了用于翻译汉文书籍的“谚解”之外,主要用于家人、妇女间的书信往来、日记、诗歌等。其中最大的用处就是写信,绝大多数为女性所写,这也是男子为数不多会使用谚文的情况,目的是方便家中女眷阅读。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古代朝、日两国对于汉字的一种近乎偏执的推崇。不过两国也因此涌现出了一批女性作者以母语文字创作的优秀文学作品。作者群体均为宫廷女性,她们以自我人生经历为蓝本创作,记录了不为人知的宫中生活细节,因此被称为宫廷女性文学,也被称为女性日记文学。比如上面提到过的日本的《枕草子》《紫式部日记》等,以及朝鲜的《癸丑日记》《仁显皇后传》等。这些贵族女性以书写自我人生的方式,描绘出千百年前的宫廷画卷,展现了乱世中女性强韧的精神力量,朝鲜和日本至此也迎来了各自女性文学史上的高峰。
五、结语
汉字作为世界上唯一沿用至今的古老文字系统,方寸间蕴含着中国五千年的历史文化、哲学思想、伦理道德和审美情趣,是中华民族的骄傲,更是中国文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历史上东亚曾经是汉字的世界,东亚汉字文化圈是以古代中国王朝为中心的东亚文化系统。21世纪以来,中国综合国力持续增强,国际地位不断提升,我们应坚定文化自信,进一步推动汉字在东亚乃至其他国家的影响力,让中国汉字和汉文化的魅力在全世界大放光彩。
参考文献
[1]张哲俊.东亚比较文学导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2]朱云影.中国文化对日韩越的影响[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3]冯立君.唐朝与东亚[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1.
[4]聂友君,陈小法,刘阳,等.东亚语言与文化[M].杭州: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2018.
[5]金文京.汉文与东亚世界[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