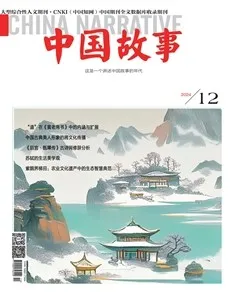以忠恕为道:《中庸》“道不远人”的哲学解读
【导读】“道不远人”出自《中庸》第十三章首句。“子曰:‘道不远人。人之为道而远人,不可以为道。’”由此衍生出两个核心问题:道和人为什么分离?道和人又如何合一?围绕这两个问题,本文采用以经解经、以庸释庸的方法,深入探究。“道不远人”的思想内涵至少包括三个方面:第一,人道相依。道为遵循本性行事,同时中庸之道是人至高的追求。二者不可分离,相互依存。第二,人为规矱。中庸之道为标杆,但做任何事情的最终动机和出发点都要落到人自身上来。第三,推己及人以求道。
一、引言
《中庸》开篇即是:“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天生的叫作“性”,顺着“性”发展就叫作“道”。由此可见道与人的关系本应十分紧密,然而下文中的“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子曰:‘道其不行矣夫!’”等句却一直强调人与道之间的距离。至此,关于道与人关系的第一个问题出现:“道和人为什么分离?”
在明确道与人之间的距离之后,后文又说“君子之道,费而隐。夫妇之愚,可以与知焉”。可见道与人不是完全没有交集的,甚至道与人的关系十分紧密,连愚昧的老百姓都可以知道。这便引出了道与人关系的第二个问题:“道和人如何合一?”要解决这两个问题,重点在于对“行道”的理解。而“道不远人”主要阐释了怎样行道的问题,因此是解决“人”“道”关系问题的突破口。
二、人道相依
“子曰:‘道不远人,人之为道而远人,不可以为道。’”此句既总领全章,点明了“道不远人”的主题。又引出了“道不远人”中“人道相依”的思想内涵,解决了行道之前如何选择正确道路和在理论上如何执行的问题。郑玄注、孔颖达疏的《礼记正义》对此句解释道:
“‘道不远人’者,言中庸之道不远离于人身,但人能行之于己,则中庸也。‘人之为道而远人,不可以为道’,言人为中庸之道,当附近于人,谓人所能行,则己所行可以为道。若违理离远,则不可施于己,又不可行于人,则非道也。”
这里强调了“为道”的方法。行中庸之道的重点是“行之于己”和“人所能行”,反之则非道。朱熹在《四书集注》中对此句解释为:
“道者,率性而已,固众人之所能知能行者也,故常不远于人。若为道者厌其卑近,以为不足为,而反务为高远难行之事,则非所以为道矣。”
朱子在这里点明了道“庸”的特点,朱子认为行道就是行平常事,“人莫不有是形,故虽上智不能无人心;亦莫不有是性,故虽下愚不能无道心”。因此,人与道天生就有着紧密的联系。但是因为道心惟微,人们又不满足行平常事的迫近,反而误入了高远难行的歧途,自然和道越离越远。
戴震在《中庸补注》中也对此做出了解释:
“而如若,语之转。以为,与下文‘以为’同。上所谓‘费’,遍及事物言之,皆不远人者也。人之为道若远人,不可以谓之道。素隐行怪之非道,明矣。”
“费”即“君子之道费而隐”,强调的是道的广泛性。人本身是道的一部分,因此“夫妇之愚,可以与知焉”。“素隐行怪”出自《中庸》第十一章:“子曰:‘素隐行怪,后世有述焉,吾弗为之矣。’”戴震在郑注的基础上补注道:“舍常行之道而专乡隐僻,以矫奇于众也。”由此可见“素隐行怪”存在着“舍常行之道”和“矫奇于众”两个问题,违背了行平常事和执其两端取其中的中庸要求,所以素隐行怪是非道的行为。
通过以上梳理可以得知,“人道相依”之中又包含着“道不离人”和“道不可离”这两种思想。“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说明了道与人的关系,即道为遵循本性行事,道是无法与人分离的。因此“道不远人”章指出“为道”时,行的是人所能行的平常事。“道不离人”强调的是“为道”的可行性与选择正确的道路,“道不可离”则点明“为道”的执行方法。“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这里指出“为道”需坚持不懈。“夫妇之愚,可以与知焉,及其至也,虽圣人亦有所不知焉。夫妇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虽圣人亦有所不能焉。”这里探讨的是道的“知”与“行”问题,道的广泛性使“夫妇之愚”也能知道和实行,但是论及细微处,则圣人也难以“知行”。
三、人为规矱
在明晰“为道”的正确路径和理论方法之后,本章接着引用《豳风·伐柯》中的句子:“伐柯,伐柯,其则不远。”用来解决“为道”实践中遇到的尺度问题。
“柯,斧柄也”,“则,法也”,这里借用拿着斧头砍树做斧柄,来比喻君子“为道”以“求道”的过程。其后补充道:“执柯以伐柯,睨而视之,犹以为远。”拿着斧头砍树做斧柄的结果是“犹以为远”。章学诚在《文史通义》中提道:“学于圣人,斯为贤人;学于贤人,斯为君子;学于众人,斯为圣人。非众可学也,求道必于一阴一阳之迹也。”拿着斧头砍树做斧柄,犹如学于圣人、贤人,可为贤人、君子,而不可为圣人。此时便触及了本句的核心问题:“何为尺矱?”紧接着提出了正确的解决方法:“故君子以人治人,改而止。”尺矱应该是“人”。郑玄在这里注解道:“君子以人道治之。”孔颖达继而解释道:“君子当以人道治此有过之人。”这里的“人”皆指“人道”。而“人道”——“即所不愿于上,无以交于下,所不愿于下,无以事上,况是在身外,于他人之处,欲以为道,何可得乎?明行道在于身而求道也。”应求于己身,而不是求于类似斧头之类的外物。
朱熹在这里对“人道”进行了更加深入的解读:“则所以为人之道,各在当人之身,初无彼此之别……责之以其所能知能行。”又引用张载的“以众人望人则易从”。“人道”不被圣人、贤人和君子所独有,而是人人都可以求诸于己。由此“人”“人道”“己”“他人”“众人”成为了一个有机的整体。
四、推己及人
明确了“人”是“为道”的尺度,接下来如何通过“己”找到“人”以求“道”的问题应运而生。“忠恕违道不远,施诸己而不愿,亦勿施于人。”此句提出了解决路径。
“忠”在《说文解字》中被解释为:“忠,敬也。从心中声。”《礼记正义》:“忠者,内尽于心。”《四书章句集注》:“尽己之心为忠。”由此可见“忠”蕴含着坚定、忠实、顽强、永不言败的意蕴。
“忠”包含着对自己内心的坚定。在《中庸》第八章中孔子称赞颜回:“回之为人也,择乎中庸,得一善,则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颜回择乎正道,从乎正道,小心谨慎忠实于中庸之道,宁死不变,是对自己内心追求之事的坚守。“忠”同时也表达了对他人的忠诚。《论语·雍也》:“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忠”不但要忠心于自己的内心,同时也要推己及人,忠心于他人。曾子三省吾身时对“与人谋而不忠乎”进行了反省,孔子在《中庸》中也对自己的“忠”进行了反省:“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也;所求乎弟以事兄,未能也;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未能也。”故而儒家所讲究父子、君臣、兄弟、朋友的人伦关系都需要以“忠”相对。
“恕”在说文解字中被解释为:“恕,仁也。从心如声。”《礼记正义》:“恕者,外不欺物。恕,忖也。忖度其义于人。”《四书集注》:“推己及人为恕。”“恕”有宽容、宽恕、体谅、包容之意。
“恕”的重点在于以己之心,将心比心,仔细考量他人之心,自己不愿意的事情不要施加给别人。“勿施于人”一词多次出现于儒家经典之中。《论语·颜渊》仲弓问仁,孔子回答:“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邦无怨,在家无怨。”《论语·卫灵公》中子贡问人生修养的道理,孔子答道:“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中庸》“道不远人”章中同样也提道:“施诸己而不愿,亦勿施于人。”这体现了儒家的仁爱之心,同时也体现了中庸之道。自己都不愿意的事情,却施加在别人的身上,这违背了中庸之道,自然就是违道已远。
“恕”更是一种温柔的力量。子路问强,孔子回道:“宽柔以教,不报无道,南方之强也,君子居之。”南方之强与北方之强不同,它更多强调的是一种带有柔性的刚强。而在孔子看来,南方的强才是真正的强。“恕”和南方之强都同样带有宽容和温柔的特点。“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推己及人,站在别人的角度来思考问题,收起自己的锋芒,用温柔来面对别人的误解,心怀善意和宽容正是“恕”的力量所在。
“忠”与“恕”一个由内到外,一个从外及里。《中庸补注》:“不怨者,人之常情,发乎自然者也。己不愿受,知人亦不愿受。于施道务在无憾,相去不远矣。”推己及人,将忠与恕彼此相连,相互贯通。“忠”强调对自己和他人的忠诚,“恕”强调自己不愿意的事情不要强加给别人。“尽己之谓忠,推己及人之谓恕。忠恕既尽,己私乃克,此理所在,斯能贯通。”尽己之心,尽己诚心,自然毫无遗憾。抛弃自己的私心,既为自己考虑,也为他人考虑,“己”通过“忠”与“恕”超脱为了“人”,此时“道”“人”“己”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符合了中庸之道的内在要求,“人”和“道”因此相去不远。
五、结语
“道不远人”章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解答了如何“为道”的问题。人在追求“道”的过程中常常将外物作为“为道”的标杆,但实际上“为道”的方法应该从自己身上去寻找。天命之性将“人”与“道”牢牢绑定。“他人”则是“人”与“己”的媒介。“己”在行平常事时,通过推己及人的“忠恕”之道去除私念,以达到“人”的境界,由此人道合一。
参考文献
[1]王国轩.大学·中庸[M].北京:中华书局,2019.
[2]孔颖达.礼记正义[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9.
[3]朱熹.四书章句集注[M].长沙:岳麓书社,2004.
[4]戴震.戴震全书:第2册[M].合肥:黄山书社,1994.
[5]章学诚.文史通义[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1.
[6]张载.张子正蒙[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
[7]许慎.说文解字[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6.
[8]孔丘.论语[M].杨伯峻,杨逢彬,注译.长沙:岳麓书社,2000.
[9]顾炎武.日知录[M].长春: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