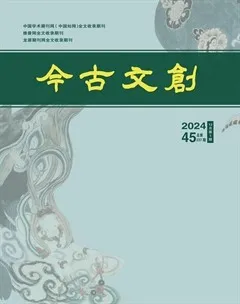翻译美学视角下小说《长恨歌》英译研究
【摘要】王安忆的小说《长恨歌》里包含大量具有鲜明时代特征和地域文化特色的描写,给人以美的体验。本文以翻译美学理论为指导,探讨《长恨歌》英译本如何再现小说中的审美信息。翻译美学要求译者理解、转化、加工审美客体中的审美信息,再现美感,使译文读者产生与原文读者相同的审美体验。本文从音、字、词、句四个层面分析了原文形式系统翻译中的审美再现,并对原文非形式系统中的情、意、象等方面的英译进行了考察。研究发现,《长恨歌》的英译极大限度地保留了原作内容和文化特色,译者注重汉英双语和文化差异,运用了直译、意译、加注、省略等多种翻译方法,尽量传达了原作的文化特色,将原语的美展示给读者。《长恨歌》的英译成功再现了原作的真和美,该理论对于中国当代小说英译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关键词】《长恨歌》;翻译美学;审美再现;小说英译
【中图分类号】H3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4)45-0106-04
【DOI】10.20024/j.cnki.CN42-1911/I.2024.45.026
一、引言
王安忆的《长恨歌》是20世纪90年代最有影响力的中国作品之一。小说以20世纪40年代的上海为背景,讲述了主人公王琦瑶在之后的40年间饱经沧桑的生活和跌宕起伏的感情经历。王琦瑶成长于上海弄堂,成为“上海小姐”后做了某政要的情人。战乱结束回到上海后又结识了新的朋友,独自抚养女儿长大。在某个夜晚被人谋财害命,故事戛然而止。2008年,《长恨歌》的英译本The Song of Everlasting Sorrow:A Novel of Shanghai由汉学家白睿文(Michael Berry)、陈毓贤(Susan Chan Egan)合译,经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出版。译作引起美国多家主流媒体的关注,好评如潮。小说英译本获2009年美国现代语言协会最佳文学翻译作品奖荣誉提名、2011年“布克国际文学奖”提名奖,及2017年的“纽曼华语文学奖”。这些奖项体现了小说获得的成就和影响力,其文学价值得到了广泛认可。
自《长恨歌》英译本面世,对《长恨歌》翻译的研究越来越多。当前对《长恨歌》英译的研究视角、方法和内容多样化,有语言学视角、文化视角和社会翻译学视角,方法有语料库方法,研究内容包括译本传播与接受、女性服饰和女性形象等。《长恨歌》是一部写实作品。作者注重细节描写,笔触细致绵密,大段评论性叙述语言也独具特色。文中重复出现的文化元素为读者展示了20世纪上海40年间的独特风貌,体现了特定时代和文化变迁。小说具有很高的审美价值,翻译美学对《长恨歌》翻译研究较为适用。本文以翻译美学为理论指导,对小说《长恨歌》的英译本从形式系统和非形式系统两个层面进行了文本分析,探讨了《长恨歌》的英译如何再现了原文中的审美信息,以期拓宽《长恨歌》英译研究视角,研究《长恨歌》英译中的审美再现也为小说英译实践提供了一定的借鉴与参考。
二、翻译美学
对美的研究在中西方已渊源久远。将美学应用到翻译学中,形成了翻译美学。其任务就是运用美学来分析、阐释和解决在语际转换中出现的美学问题。包括对翻译中的审美客体(即原文)、审美主体(即译者)和审美关系的研究,也包括翻译中审美再现手段。在翻译审美客体中,一切存在的美都是审美对象,可以将这些对象分为形式系统和非形式系统这两个系统。具体来说,形式系统关注内容的物态形式、外象形式,研究语音、文字、词汇及句段四个层级所呈现的审美形式信息,对审美符号进行解码。非形式系统,也叫作内在形式系统,包括情、志、意、象四个方面,从整体把握审美模糊集。
文学翻译作为翻译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本质也是一种审美活动,需要译者分解原文及其文学美,通过观览、品味、领悟、再现这一文学翻译审美图式对原作进行艺术再创造,并传达原文的艺术审美信息。文学翻译的审美目的就是要再现原语中的美。这就要求译者不仅要达意、传情,还要在表现法上符合目的语审美传感的最佳效果,择优而从,力求臻于完美。翻译美学尤其适用于文学翻译的研究,给文学作品中的审美信息再现提供了理论依据,分析、探讨其中审美信息和审美价值的再现对文学翻译实践具有指导作用。
三、实现文学翻译审美再现的两大系统
(一)形式系统
语言承载了作品的审美信息,文学作品的美学价值也体现在语言中。形式系统中,在语音、文字、词汇、句段四个层面承载审美信息、传达审美意义。译者需具备对语言审美的感知和转换能力,运用其情、知、才、志,来实现语言各个层面的审美再现。
1.语音层面
作为语言的要素之一,语音承载了语言的审美信息,要求SL与TL在语音美上呈现形式对应或效果对应。语音层审美构成包括音位、音律、音韵等要素,其中音位是承载审美意义、传递审美信息的基本单位。音律和音韵对于审美价值的表现也具有重要意义。此外,语言中的叠字、头尾韵和拟声词等,都能保留描绘声音的审美视听信息。成功的审美再现能够使读者沉浸在文章中,与译者、甚至是作者产生感应和共鸣。《长恨歌》中含有不少叠音词、拟声词和押尾韵的句式,如何再现其中蕴含的音美考察译者的双语功力。
梅兰芳是我国京剧表演大师,擅旦角。欧阳予倩形容梅先生是美的创造者。原文用叠音词“咿咿哦哦”形容留声机中梅兰芳柔曼婉转的唱腔,展现了京剧的魅力。译者运用了异化的手法,译为“Yi yi eh eh”,直接以拼音的形式将原文的音美再现了出来,同时保留了四字的形式,读之朗朗上口、简单易懂,不影响理解其为梅先生的嗓音。同时,相比于将“百折千回”直译为百次曲折和千次迂回,译者将其意译为“round and round, over and over”,用变通的方法实现了对应,体现了艺术家极尽婉转、余音绕梁的歌声,也与前文拼音搭配得宜。
王琦瑶意外怀孕,面临艰难抉择,内心焦灼难安。她打算去医院流产的那天,是个阴雨天。细小的雨点打在三轮车篷上,噼噼啪啪地响,仿佛震耳欲聋,其实是王琦瑶的心在咚咚作响,她突然想留下这个孩子。原文用叠音词“噼噼啪啪”来形容雨打在车篷上的声音,译者将汉语的双声叠音转化为英语的谐音词“titter-tattered”。其中, “titter”原义为“咯咯笑”,而“tatter”有“扯烂、撕碎”之意。译文将副词转换成动词既生动再现了雨落下来的声音,又突出了雨的气势和威力,突出了人物焦急不安的情绪,完美地描摹了“噼噼啪啪”带来的审美视听信息。
2.文字层面
作为语言的浅表层结构之一,文字具有形体特征。在中译英的过程中,如何传递原作者笔下的汉字带来的意趣和意味,对译者来说,有一定的难度,可以灵活运用各种翻译方法来传递审美信息。
汉字具有图像性,承载审美信息,翻译时可以适当地给出汉字来进行补充说明,再现原文的内涵。比如,毛毛娘舅给王琦瑶算命测字,严家师母代王琦瑶给了“天”,毛毛娘舅加了一竖变为“夫”,解释为王小姐命里有贵夫。王琦瑶给了“地”字,毛毛娘舅将之一分为二,在“也”的左边加了“人”字旁,变成“他”,还指贵夫。王琦瑶指着右边,脱口而出:“这不是入土了吗?”她想起了因飞机失事身亡的前政要情人,不禁黯然失色。此段情节深刻体现了汉字的魅力和艺术。译者在英文中不光给出了拼音和汉字的含义,同时穿插了相关汉字,对原文内容做出了详细的解释、说明与恰当的补充,完整地再现了原文中的审美信息。比如将“天”翻译成“tian,or sky”,并给出了汉字“天”;又比如将“夫”翻译成“the character for ‘husband’,夫”。这样,随后将“贵夫”译为“a wealthy husband”就方便读者了解原委,且不显突兀。再比如,译者将“地”译为“di,or ‘earth’”,并给出了“地”的汉字。除此以外,“也”“他”“土”也在恰当位置给出,在不影响原文流畅性的同时,传递了原作的异质文化,使不懂中文的英语读者也能理解此段的含义,感受到原作的文艺性,甚至汉字和中国文化的魅力。
在汉语中,人们喜欢利用文字的形与音结合起来的双关语带来巧妙动人的视听美感。如何译出双关语的双层含义,也需要译者的才智。在一次平安里四人间的下午茶时,萨沙带来了一个正宗的苏联大圆面包,由他的一个苏联女性朋友烘烤。后来,在下午茶的时候,大家开萨沙的玩笑,用苏联面包指代那个做面包的苏联女人。萨沙说的“苏联面包还可以,苏联的洋葱土豆却吃不消”。译者直译为“‘foreign’ onions and ‘earthly’ potatoes”,忠实、流畅,既不改变原文词语形式,又巧妙突出了萨沙话里的暗示。
3.词汇层面
在词汇层面,审美信息体现在原语用词和利用词语的各种修辞手段中。用词包括常规的与非常规的词语搭配,也包括成语、俗语、四字词语等,都包含大量内涵。而修辞则包括更多承载审美信息的手段,如排比、比喻、反衬等。为再现原文词汇中包含的审美信息,译者可以借用多种翻译方法和技巧,灵活翻译文学作品中的审美对象。比如,原文描述弄堂里的流言遇风则起、见缝就钻,而散播流言的人的想象力能跳龙门、能钻狗洞,毫无“清规戒律”。四字词语“清规戒律”是佛教徒所严格遵守的规则和戒条,比喻束缚人的规章制度。戒律和清规词意相近,译者合并意译为“fetters”,即脚镣、束缚。又将“一无清规戒律”译为“free from all fetters”,译者用首韵法灵活对应了原文重复的审美信息,同时具有音韵美。再比如,李主任迷上了京剧里的男旦,认为男人比女人更懂得演好女人,“这也是身在此山中不识真面目,也是局外人清的道理”。“身在此山中不识真面目”化自于苏轼的诗“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指的是之所以认不清庐山的真面目,是因人身处在庐山之中。这与“局外人清”是一个意思。译者直接合并两个表达的意思,意译为“a simple case of an onlooker being able to form a clearer picture of what goes on than the parties involved”,译文再现了原文的内容、涵义,流畅自然、简洁明快。
4.句法层面
在句、段层面,审美信息分三类。第一类是“句法变异”,即利用语法的模糊性来创造美感;第二类是“频度”,即借助形式反复的力度来产生美感;第三类是指宏观上的形式美,即利用整体风格体现美。
在原文里,“虚浮就虚浮,短暂就短暂,哪怕过后做它百年的爬墙虎”一句中重复出现虚浮、短暂二词,同时利用句式重复的力度和虚浮与爬墙虎相押韵来产生美感,因此,原文同时具有形式美和音韵美。译文为“So what if time is transitory,so what if it is illusory,so what if the clouds should transform into ivy,to crawl through the cracks and walls to wait for the next century?”可以看出,译者用三个“so what if”作句首的排比句,叠浪式地再现了原文形式的美感,又选取了“transitory”“illusory”“ivy”“century”这四个押尾韵的词作尾,使译文在不改变原文内容的基础上,读起来朗朗上口,再现了原作的文学性和审美情趣。
再比如,在王琦瑶看来,女儿薇薇时代的上海是走样的、粗鲁的、不忍卒读的。霓虹灯亮起,“夜晚却不是那夜晚”;老字号挂起,“店也不是那店”;路名改回,路上走着的人就“更这人不是那人了”。三连“不是”:却不是、也不是、更不是,铺排的语言具有形式美和感染力,具体说明了回来的不是原先的旧上海辉煌的景象,体现了新上海街景也是走样的、让人不忍看的。译文用了三个“but”和三个分句,体现了转折的语气,在句式上大体对称的同时,保留了原文的审美特色,再现了霓虹灯、老字号、路名的改变,体现了新与旧的不同。
(二)非形式系统
原文审美中除了形式系统里的成分外,还有非物质、非自然感性、非外象成分等组成非形式系统,亦即审美的模糊集,由情、志、意、象构成。译者需把握原文中的情感和意志,来确定译文总体风格的再现;意象是物和情的交融,蕴含审美信息,指涉较宽,是一种模糊存在。本文选取以下译例来考察非形式系统的审美再现。
1.情志
小说名为《长恨歌》,其整体基调是恨、是哀、是痛。小说英译名为The Song of Everlasting Sorrow, 突出一个“sorrow”,可见小说情感基调。译者将原文多次出现的“哀”“哀意”“哀情”“哀伤”,连同“感伤”,也一同译为“sorrow”,保持行文一致,让人联想到题目,同时突显了小说主题。小说中的哀意是沉底的“积淀物,不是水面上的风花雪月”。原文将哀情实体化,与轻灵的“风花雪月”形成对比。译者如实地将“不是水面上的风花雪月”这一诗词中常见的描述译为“...has nothing of the airy-fairy—the wind, flowers, snow,and the moon dancing on the water”,
勾勒出了一副轻快的、如仙境般的美丽景象,再现了原文中的审美信息。
王琦瑶意外怀孕,因毛毛娘舅家庭原因,二人为能否结婚和是否该留下孩子而焦虑、苦恼。恰逢严冬时节,万物凋零。二人到人烟稀少的公园商讨对策,公园里草木凋零,“麻雀在枯草地上作并脚的跳远,太阳移着淡薄的影子,告诉他们时间流淌,刻不容缓”,这凄凉的景象也烘托出了二人内心的焦急。译者在译文“the sparrows hopping on the yellow grass seemed to be the only signs of life”中补充了一句麻雀“似乎是唯一的生命迹象”,在译文“The light of the sun as it shifted gradually through the bare trees...”中也补充了阳光移过“光秃秃的树”。这样的补充体现了景色的同时也衬托了二人绝望的心情。
2.意象
小说中充满了关于上海这座城市的种种描述,尤其是弄堂里的人和物,读起来让人脑中充满了对20世纪旧上海的丰富想象和对新上海的整体印象。上海弄堂的夜晚,是城市的阴暗面,与白天相对。在小说中,麻雀和鸽子相对。鸽子(Pigeons)是自由的象征,它们白天在城市上空飞,将一切秘密尽收眼底。而麻雀是媚俗的,它们飞不高,靠啄食人类的残羹剩饭生存,是自轻自贱、同流合污的象征。弄堂的夜晚有行动的老鼠和小虫、爬行的蟑螂和飞来的麻雀,分别译为“mice”“cockroaches”“insects”和“sparrows”。这些意象是寻常的,一年四季都有。夜幕降临,和人类为了生计、吃饭一样,表面上一切如常,背地里各种夜间活动的生物登场,做“静夜的主人”,发出“窸窸窣窣地响”,而对声音的描写侧面突显了夜的安静。对于“小虫都在动作,麻雀正朝着这边飞行”,译者用现在分词短语作状语,处理为“A myriad insects were astir, drawing the sparrows’attention”,将小虫与麻雀联系了起来,使行文更有逻辑。译文完整再现了弄堂里夜间生物活动的场景。
上海是一座不夜城,霓虹灯和晚会、风情和艳充斥其中,极尽繁华和热闹,否则,就是寂寞加寂寞。尽管如此,在王琦瑶看来,新不如旧,新上海的一切都比不上曾经的繁华。译者将多次出现的“不夜城”翻译为“sleepless city”“this city that never sleeps”。而到了新时代,不夜城也走了样,变成了“the city that used to never sleep”。原文中形容新上海的夜景时,运用了排比的手法,依次展现梧桐树影、候车人的脸、电车的铃声、路灯霓虹灯这些上海夜晚街景的经典元素,包含了人、事、物、色、音和光影,充满了夜晚的视听审美信息。译者提取了四个典型意象,进行了合并翻译,巧妙地将“夜色”“夜声”“夜的眼”统一转化为时间上的“晚”,即”lateness”。译文简洁明了,流畅自然,译者很好地把握了上海夜晚的特色,再现了原文对上海夜晚的描写。
王琦瑶作为曾经的上海小姐,仍然维系着旧时代的体面。其衣箱里充满了各种旧物件,如“缀了珠子的手提包”“散了串的珍珠项链”“掉了水钻的胸针”“蛀了洞的法兰绒贝蕾帽”等。这些物件都是来自几十年前的旧上海,曾经也是崭新华丽的,随着时光的流逝,城市风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物品也藏不住岁月的痕迹。译文中用“beaded handbag”“broken pearl necklace”“the brooch with a missing diamond ”“moth-eaten flannel beret”再现了带有岁月痕迹的老物件。译者形容箱中“奇光异彩的图画”为“colorful”“exotic”“of another time”,这个“another”真正点出了时代的变化,使读者感受到了时代的变化,也隐隐约约从旧物中看到过去的繁华和荣光。
四、结语
本文以翻译美学为理论视角,从语音、文字、词汇、句法这四个形式层面和情志、意象等非形式层面,对王安忆的小说《长恨歌》的英译进行了分析与讨论,考察了译者在小说英译过程中对审美信息的再现。研究发现,《长恨歌》的英译极大限度地保留了原作内容和文化特色,译者注重汉英双语和文化差异,运用了多种翻译方法,对原文进行了适当、恰当的调整,尽量传达了原作的文化特色,成功地将原语中的美本真地展示给读者。
参考文献:
[1]Berry,M.&S.C.Egan.The Song of Everlasting Sorrow: A Novel of Shanghai[M].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08.
[2]百名评论家推荐90年代最有影响的作家作品[J]. 出版参考,2000,(19):8.
[3]岑群霞.场域理论视域下王安忆《长恨歌》上海书写的英译传播探析[J].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2019, (04):48-62.
[4]傅瑜.王安忆《长恨歌》英译本中海派文化的重现[D].复旦大学,2012.
[5]李莹,孙会军.《长恨歌》在海外的译介与接受研究[J].外语导刊,2021,(02):66-73.
[6]刘李银.论小说《长恨歌》中女性服饰的英译[J]. 外语教育,2019,(00):251-260.
[7]刘宓庆.翻译美学导论[M].台北:书林出版社,1995.
[8]刘宓庆.翻译美学基本理论构想[J].中国翻译,1986,(04):19-24.
[9]屈惠宇.从女性主义角度分析王安忆《长恨歌》英译本中的女性与时空[D].北京外国语大学,2015.
[10]汪晓莉,李娇娇.基于语料库的《长恨歌》英译本中程度副词的强化研究[J].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学报,2015,(05):81-89.
[11]王安忆.长恨歌[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
[12]吴赟.上海书写的海外叙述—— 《长恨歌》英译本的传播和接受[J].社会科学,2012,(09):185-192.
[13]张乐金.评价理论视角下《长恨歌》女性形象英译研究[J].外文研究,2021,(03):83-92+109-1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