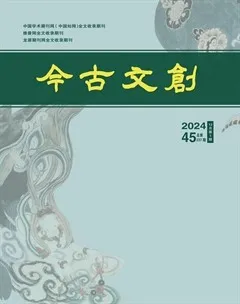女性主义视域下探析沟口健二的叙事特征
【摘要】日本昭和时期的电影大师沟口健二以其独特的镜头语言和叙事特征深刻地对女性角色进行了描绘,成为世界电影史上的重要导演。他在《西鹤一代女》(1952)和《雨月物语》(1953)等代表作品中,通过悲剧的女性形象符号、闭锁的女性空间叙事和先锋的女性意识叙事构建,不仅表达了对旧社会的父权制反思,也呈现出了女性的主体性与复杂性。研究叙事特征不仅在内容层面更好地理解沟口健二的电影创作风格,也为女性主义电影的创作及研究提供参考。
【关键词】女性主义;沟口健二;电影叙事;女性形象;日本电影
【中图分类号】J9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4)45-0090-04
【DOI】10.20024/j.cnki.CN42-1911/I.2024.45.022
经济与社会的发展以及文化教育的进步,让女性地位得以不断提升。在“女性主义”或“女性主体性意识”在学术以外的范围中被广泛提及的当下,其实过去许多文艺作品中早就有不同程度的体现。而20世纪中期,日本电影就已经展现了初步的女性主义思想。日本昭和时期的电影大师沟口健二的作品以刻画女性形象而受到国际的瞩目,日本著名的电影评论家岩崎昶曾评价过沟口健二的作品:“日本的电影作家描写女性的内容虽然不少,但是至今为止,未曾有人超越沟口。”[1]足以可见沟口健二在电影中展现的女性主体性意识以及他塑造的女性形象给当时观众带来的思想冲击性与其社会影响的先锋性。本文将从女性主义的角度,以沟口健二1950年前后的《西鹤一代女》及《雨月物语》等著名作品为例,分析其塑造的人物形象符号及闭锁的电影的空间叙事的特征,再从女性意识的角度进行分析,从这三个方面总结出沟口健二在女性主义视域下的主要的叙事特征。
一、悲剧的女性形象符号
沟口健二从1924年就已经开始专注于女性形象在电影中的刻画,而他后期作品中的女性形象逐渐产生了共通性,正如电影评论家佐藤忠男在评论沟口健二时所说:“经过苦难的磨炼成为圣善的女人,忘掉过去的一切对男人给予宽恕。”[2]沟口健二一直在构建一种符合自己理想的悲剧且崇高的女性形象符号,从女性主义的角度来看,虽然也是一种“凝视”,但其中的怜悯与对社会的讽刺,从电影史甚至从女性主义理论的角度来看也可以说是对于女性符号的一种全新的视角的展现。
(一)情感与欲望的接受者
不可否认在现代社会中的文明中一般会将情欲进行罪恶化,以此规训人们对情感与欲望的羞耻心,从而维持社会稳定。弗洛伊德在谈及情欲时曾认为“文化要求不断地升华,从而削弱了爱欲这个文化的建设者。由于爱欲的削弱而导致的非性欲化解放了破坏性冲动”。[3]虽然在弗洛伊德的眼中文明在压抑人类的爱欲,且这两者之间的矛盾不可调和,但在文艺作品中创作者依然渴求达成一种文明与爱欲之间的平衡,或者实现情感与欲望的自由。而女性在很长的一段时间作为男性中心主义社会的边缘存在,成了禁忌的“情感与欲望”的象征,由于男权社会中只有男性的情感具备正当性,她们多数情况在被动的位置。如果这是一种社会与文化的不公允,那么沟口健二在自己的作品中刻画一种拥抱自己情感与欲望的女性主人公,可以说从另一条道路突破了当时的文化偏见。
沟口健二的女性角色具有高度的主体性,她们通过情欲的表达,彰显出内心的渴望和挣扎。情欲在他的电影中不仅是个人情感的流露,更是对社会压迫的反抗和自我认同的追求。田中娟代饰演的女主春子在《西鹤一代女》(1952)中就是情欲的追随者,她的一生充满了对爱情的追求和对命运的抗争。沟口健二在塑造春子时有别于原作井原西鹤的长篇小说《好色一代女》,原作中的主人公更多是被性欲所驱使,而电影在改编的时候让春子成了追求爱情的女人。她的情欲表达不仅是个人情感的体现,更是对封建社会压迫的一种无声反抗,春子通过与不同男性的情感经历,展现了她对幸福的渴望或是对于真爱的渴求,同时也是对社会束缚的挣扎。春子在这个作品中表达的情欲不仅是个体的情感需求,更是她在封建社会中寻求自我认同和价值的方式。
《雨月物语》(1953)则更加激进,若狭化身为鬼的原因就是死前没有体会到爱情,而她骗主人公原十郎只是因为她想体验情欲的快乐。若狭的情欲不仅是对个人幸福的渴望,更是对战乱和社会动荡的逃避。她的情感表现出一种强烈的主体性,揭示了她内心深处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对压迫现实的反抗。若狭不仅在情感上深深吸引着观众,也通过她的情欲表达,展示了女性在动荡时代中的主体性和自我价值,足以见得情欲在沟口健二作品中的女性形象的重要性。
(二)社会悲剧的牺牲者
谈及社会时不得不提沟口健二在20世纪50年代创作的时代背景。二战后的日本在经济上面临崩溃,想利用西方的现代化快速恢复本国经济。东西方思想产生冲撞之外,电影行业也出现了规制的要素。如此情形下为了不让日本丧失民族主体性,沟口健二做出了自己的选择。他的电影题材虽然多为古代,但其现实主义的内容也成了一种反抗的工具,除了强调艰难处境之外,也通过塑造悲剧的女性形象重新让观众反思自己的选择。
沟口健二电影中的女性角色常常承受着极大的社会压迫,她们的命运充满了悲剧性。这些角色通过她们的经历,揭示了社会结构中的种种问题和压迫机制。上文中提及的《雨月物语》的若狭就是典型的悲剧角色,她原是一名贵族,但因战乱而沦落为野鬼。她的命运是社会动荡和战乱的产物,揭示了战争会让社会结构崩溃,这样的灾难是不分性别和阶级的无差别的悲剧。《西鹤一代女》的春子也是这样一个充满悲剧的人物,女主春子所经历的苦难并不是她本身造成,她更多是被动地受到社会中男性的抛弃和背叛。女主无能为力的悲剧经历让她不得不把希望放在佛教上,使得作品的现实主义特性得到了加强。《近松物语》(1954)从结尾来看虽然歌颂了封建时代的自由恋爱,但是女主人公阿珊依然是无法反抗封建社会毒害的女性形象,以至视死如归的阿珊反而更加突出一种无力的悲凉感。
20世纪50年代正是日本战后重建的关键时刻,也是日本电影刚刚步入黄金时期的年代,沟口的《西鹤一代女》等作品以女性人物作为重点的影像符号,并不是单纯从性别出发,而是以一种文化符号反思了社会的毒害,她们抗争的态度与爱情的追求,给世界电影史带来了东方韵味的悲剧女性形象符号,成为世界电影史中女性银幕形象的经典之一。
(三)自我意识的和谐者
虽然沟口健二构建了在当时来看非常典型且发人深省的女性形象,但是从如今的女性主义的角度来看,沟口健二的作品还是有一部分局限。他的作品中的女性人物与如今的后现代新女性最大的不同是她们依然是自我意识的和谐者,她们的生活驱动一直是围绕男性的,展现出了一种男性的不可缺席性。值得一提的是,在沟口健二笔下的女性人物确实表现了自己的情欲,但是正如法国女性主义理论家露西·伊利格瑞女性在阐述“非一女性”时提到的观点,女性的“非一”的情感表现着实威胁到了男性话语中欲望的固有概念,至此,女性的欲望无法真正被男权世界所认同,因此由男性所建构的欲望表达系统当中,女性依然还是依附着男性。正如电影《雨月物语》的若狭虽然表达了欲望,但依然需要一位男性伴侣才能达成自我完整。《近松物语》也依然是以两性关系贯穿了整部电影的叙事。沟口健二虽借助女性形象来表达人在面对世俗的无力,但他依然保有着男性视点,将女性的情欲放在男性逻辑之下,将性别成为性别的绑定关系的筹码,但在19世纪50年代还没有女性理论出现,所以这样的局限同时也是时代的局限,也在未来女性电影创作时能够脱离男性视点的一种启示。
二、闭锁的女性空间叙事
在文字叙事空间与写真摄影理论的结合发展中,电影的空间研究得以进入到电影研究的视野。与文学不同的是,电影最基本的表现形式是镜头,导演与剪辑师通过镜头排列组合,由二维画面构建出了电影空间。电影叙事的空间除了有书面叙事的空间之外,还要由场景、摄影的运动方式构建。而作为观众在蒙太奇的影响下不仅接受了故事,也在脑中构建了想象的空间。沟口健二的女性主人公通常是处于闭锁的表现空间内,这样特别的空间叙事,从女性主义视角来看在当时具有开创性。1979年,女性文学研究《阁楼上的疯女人:女性作家与十九世纪文学想象》出版,其中作者桑德拉和苏珊就女性与闭锁空间的关系做出了解释:“女性文学被闭锁于男性的文本之中,她们要逃脱这些文本的控制,只有通过智谋和间接的方式。”[4]所以在电影的空间叙事中,不同的空间给予了人物不同情感表现,这样的心绪也通过银幕传达到观众的心中。从女性角度来说,在社会这样的公共空间内大部分是闭锁的或是被压迫的,在面对这样的社会困境之时,女性如何抗争,其人性光辉应当如何展现,成了沟口健二在电影中不断探索的主题之一。
(一)“不存在”的私人空间
私人空间通常令人感到的是安全与放松。这里的私人空间通常为单独存在或者处于家庭中,但是提及家庭的建立时,不得不从时代的角度分析。很明显,封建时期家庭概念依旧是在以男性为中心之下得到完成的,女性在家庭中兼具着不同职责:妻子、母亲、女儿。女性的权利和地位逐渐被剥夺,甚至到了极端的地步。如果理想中的私人空间“家庭”对女性而言是夫妻两人平等,但是实际的封建时期的情况是家是以男性(丈夫或儿子)为中心建立的。从历史话语的角度来看,男性是家庭的绝对持权者,也代表着话语权,而女性通常是作为依附而存在。从生产力的角度来看,和如今的现代社会不同,生产力没有得到发展的封建社会或者其他的社会形态,男性因为生理上比女性更加适合进行长时间的体力劳动成为主要的生产力,当男性是生产力时,他们便可以决定生产关系,以至于如何分配资源或者各种制度。封建时期传统的家庭对于女性的封闭属性本就存在,只是被意识形态所掩盖,让女性无法察觉,也因生产力的原因,她们也无法反抗。
从社会分工的角度来看,在封建的男权社会中,男性外出工作挣钱,独留女性在家打理家务或者照顾老人与孩子。再从家庭的构成方式出发,大部分封建家庭都是以未成年女儿“寄养”在家,成年之后就想要女儿嫁到丈夫家,女性的“家庭”的变动性普遍高于男性。而如果抛开“家庭”的私人空间,则是“完全独处”,与现在社会不同,在封建社会中的独处则是抛弃社会资源的不被认同的存在。所以在这两个社会的现实基础上,沟口健二在作品中构建了一种“不存在”的私人空间,以表示对女性生存空间的叹息和讽刺。
影片《西鹤一代女》表现的场景就符合了一种女主的私人空间逐渐消失,向公共空间融合的趋势。在影片开头,田中绢代所演的主人公春子穿着和服在夜晚踱步,躲避着周围的行人,慢慢走到残垣之间。从影片开头,暴露在公共空间中的春子,与周围的街道格格不入,直到她回忆起过去还在当侍女的经历时,春子的近景增加逐渐成为镜头的主题,而关于她的悲剧才真正开始。在故事后面,无论街头卖艺,还是被买去作妾,又或者是当高级艺妓,这些本应该是私人场景,春子都没有很好地融入其中,始终是男性在占据主体地位,而春子的归属感只有在重回寺庙时获得了一些。而私人空间的消失其实从电影的开头一直贯穿到结尾。例如春子其实是为领主生了一个儿子,但是作为妻子的她却从影片开头就没有得到过对方的接受,反而在后面被认为是破坏了家族的声望。在结尾春子虽然远远地见到了自己朝思暮想的心上人,但是也只能见着最后一面。所谓她心心念念的幸福的私人空间其实从一开始就不存在,而这有很多原因是封建社会所造成的。
(二)闭锁的社会空间
首先,社会公共空间对于私人空间而言,它的特性是开放且自由的,有比私人空间更多的资源。但当主体不是被社会认可的群体时,社会空间的开放性会消失不见,反而是更加闭锁的存在,这样的边缘群体时刻都在受到禁锢。波德莱尔对于边缘群体有着分析:“这些局外人或观察者还包括了诗人、拾荒者、女同性恋、老人和寡妇(一般假定这群人可以躲过令人讨厌的异性恋审视),以及娼妓和流莺,她们在发展中的大都市里全都仰赖机智过活。”[5]而沟口健二的作品中的女性主人公大部分在上述的群体之中。而从电影内容出发,主人公处在的环境旋即形成了对于社会的批判,正如上一节沟口健二对于旧社会中女性私人空间的困境的展现,也从另一方面说明社会空间也未必会对女性有所怜悯。
例如《祇园姐妹》 (1936)和《祇园囃子》 (1953),两部作品在中心立意虽然有不同,但是都展现了当时艺伎作为女性的边缘群体的种种辛酸遭遇,他们虽然在京都祇园这个开放的社会空间之内,依然不被身边的人理解,被自己的客户欺骗,并且她们没有可以逃离的选项,只能不断忍受。而《阿游小姐》(1951)又与上述两部不太一样。如果说祇园姐妹和祇园囃子的女主的身份已经确定好了,这部作品中田中绢代饰演的阿游和乙羽信子饰演的阿静都是因情所困,她们都有着自己想要追求的爱情,但是阴差阳错让他们的角色处于换位的情况,这让他们三个人生活的场所宛如炼狱,而影片的结尾也由阿游退出阿静难产死亡作为一种情感的启示,但是无一例外影片中的女性大多都在无形的闭锁中,难以自拔。
《进松物语》中的女主人公阿春虽然已经结婚,但是她的丈夫只是想挣钱,也对阿春有了误解。这个家庭虽然构成,但是从阿春的视角来说并不幸福,因为其结婚的动机只是阿春的家人让她去结婚。她的姿色与丈夫的财富形成了一种交易,但并没有形成真正的爱情,这也是封建时代常有的情况。而影片开头因为通奸而游街示众的画面,为这部电影奠定了基调,也就是女性无时无刻不被妇道礼教约束,这是一种社会潜规则,这种社会空间成为这部电影一直贯穿且无法消散的存在。起初被误解的阿春也在故事的发展中逐渐喜欢了古川,在结尾,阿春和古川也与开头的游街示众一样,只不过这次在马上的是他们俩。影片最后以众人的指点以及阿春在马上的微笑和古川痛苦的表情,这三个立场及象征意义不同的镜头做结尾。如果恋爱是私人的,那么在面对社会的礼教时,便从私人空间叙事成了公共的空间叙事。通过对于深陷困扰且无奈的阿春的刻画,有力地批判了封建礼教对于女性的压迫。
无论是不存在的私人空间还是步步紧逼的社会空间,沟口健二的作品中,他的女主人公都没有放弃生活的希望,依然在为自己期盼的美好未来去活着,这反而又成了一种讽刺。《雨月物语》《西鹤一代女》等作品中,女性最后的结局都无依无靠并且被社会所谴责。这种电影叙事的空间充斥着的是封建社会吃人的悲凉气氛,但也形成了他的独特的闭锁叙事风格。
三、先锋的女性意识叙事构建
对于女性意识的概念认定学界有不同的说法,这里采用张阿娇的硕士毕业论文《岩井俊二电影中的女性意识研究》中的综合判断作为本次研究的参考:一种女性主义电影中的精神状态,创作者无关性别,有意对女性的处境加以照拂,并且从女性的立场出发对自身以外的世界加以注视。[6]沟口健二的作品无疑是体现了女性意识的,但是从年代来看他的作品从30年到50年时就有了女性意识的创作风格,无疑在电影史上有着一定先锋地位。
沟口健二在创作的时候有意将自己作品中的女性人物进行特别化处理,正如日本电影学者斉藤绫子所说,沟口作品中的女性共有两种,一种是帮助男人出人头地而甘心奉献、自我牺牲的女性,另一种同样会成为社会和男性的牺牲品,却是拼命抵抗这样的社会和命运的女性。[7]这两种女性都是经历了在男权社会的背景下被迫成为牺牲品的处境,而不论女主人公如何面对困境,其结局大多都是悲剧告终。这符合了大部分男权社会中女性的缩影,有着极强的现实主义与社会批评力度。虽然导演作为男性依然存在一些男性凝视的内容,但对于真实人性的挖掘和对于社会剥削女性的现象的揭露依然是沟口健二创作的初衷。
面对女性的困境,雪儿·海蒂提出这种困境产生的原因;“女性缺少的并不是知识,而是权力——社会权、经济权、身体权等等。”[8]也就是说,她认为女性想要冲破枷锁,不应该继续学习社会的规范,也不应该让自己适应这个社会,而是要让自己争取权利。所以雪儿·海蒂在内的女性主义者们认为女性应该争取自己身体的主权,对爱欲的有效释放,也是女性走向自由之路的起点。所以在沟口健二的作品中,基本上出现的女性角色都是包含情感的,她们或是为了追求情感上的自由而深陷旋涡,或是在苦难中依然坚持着自己的爱。在这种极端环境之下,人的本能却闪闪发光让人动容,就连沟口健二选择改编中国的《杨贵妃》中,杨玉环最后也不是为了政权自杀,而是为了自己的爱牺牲,悲剧性的结局让人更痛心和惋惜,也让人反思和觉悟。
在男性中心主义为主的封建社会中,女性的意识一直被礼教严苛地束缚着。在沟口健二的电影中看到大部分的女性主人公都有着被迫流亡或者无依无靠的场景,例如《西鹤一代女》《雨月物语》《进松物语》等等,她们的生活都需要一个男人。而不论她们一开始的处境如何,从影片的故事开头到结尾,她们都被当成男性的附属品,她们知道自己的痛苦,但是她们认为这是自己的命运,根本没有对于封建社会的反抗,这才是当时旧社会的悲哀。当一个本应该有着独立的个人意志却需要社会认同或者男性认同的时候,旧社会的黑暗和悲哀正是沟口健二想表达的。他通过塑造优秀且让观众共情的女性形象表达了对于旧社会的批判。但通过他的作品,观众也自然反思女性在旧社会面对的社会困境在如今有何变化。值得一提的是,沟口健二在创作这些作品的时候,女性主义理论还尚未得到长远发展。从现在的女性主义的视角来看,沟口健二满足了“女性书写”的视角,也让东方女性在旧社会的处境得到了国际的关注,从电影史的角度来看也不失为是一种对女性电影的参考。
四、结语
从女性主义的角度来看,沟口健二的电影在叙事方面通过表现女性角色的情感和命运,构建了具有在当时独特作者风格的女性人物符号,对东方女性在封建社会的悲剧进行着重刻画。而从电影本身,他的作品也自然而然构建了女性人物特有的电影叙事空间。而女性角色作为封建社会的牺牲者,导演通过细腻的视觉符号和独特的叙事手法,批判了父权制社会对女性的种种压迫和不公。基于以上分析,沟口健二在20世纪50年代这个时间点来看,他的作品表现出了当时少有的先锋的女性思想,还对于当时的电影创作有极大的参考意义。不可否认的是女性意识会一直进化发展,现在女性创作与女性电影也需要脱离过去经典作品的框架才能得到长久发展。诚然,仅依靠影视作品并不能解决当下全球要面临的诸多问题,但是通过不断创作与研究,让这些作品进入大众视野,也能够吸引一些大众对性别现状的关注,从而真正构建起平等友善的和谐社会。
参考文献:
[1]岩崎昶.溝口健二[J].フィルムセンターFC溝口健二監督特集(48),1978.7.
[2]佐藤忠男.只为女人拍电影:沟口健二的世界[M].陈梅,陈笃忱译.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9:137.
[3]马尔库塞.爱欲与文明[M].黄勇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59.
[4]桑德拉·吉尔伯特.苏珊·古芭.阁楼上的疯女人:女性作家与19世纪文学想象(上)[M].杨莉馨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107.
[5]琳达·麦道威尔.性别、认同与地方——女性主义地理学概说[M].徐苔玲等译.台北:群学出版有限公司,2006:210.
[6]张阿娇.岩井俊二电影中的女性意识研究[D].陕西科技大学,2000.
[7]斉藤綾子.聖と性 溝口をめぐる二つの女[A]//映画監督 溝口健二[M].东京:新曜社,1999:281.
[8]雪儿·海蒂.海蒂性学报告女人篇[M].林淑贞译.海南:海南出版社,2002:276.
作者简介:
李佩霖,男,汉族,山西太原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传媒学(电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