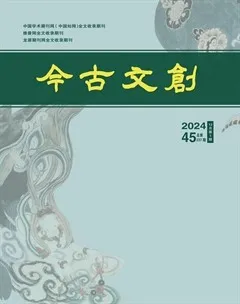《太和正音谱》研究综述
【摘要】朱权《太和正音谱》是一部以指导戏曲创作为目的创作的工具书,由于戏曲创作与语音密切相关,故其对明代语音史的研究具有重要价值。该书研究成果颇多,主要围绕着成书年代、版本情况、戏曲理论、曲史成就、语言学价值、特殊语考订几个方面展开。本文归纳这些研究成果进行综述,希望能够为研究《太和正音谱》的学者们提供资料参考和查询,为其研究工作提供帮助。
【关键词】《太和正音谱》;朱权;研究综述
【中图分类号】J8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4)45-0086-04
【DOI】10.20024/j.cnki.CN42-1911/I.2024.45.021
朱权于明洪武十一年(1378)出生于南京宫中,卒于明正统十三年(1448),号臞仙、涵虚子、丹丘先生,是明太祖朱元璋第十七子,洪武二十四年(1391)受封宁王,都大宁,洪武二十六年(1393)就藩。因其神姿秀朗、天资聪慧,谥为“献”,后人称其为“宁献王”。朱权在曲学、琴乐、文史、道教、戏曲、医家、兵家等方面有着诸多贡献,其中有流传于今的经典著作,如《太和正音谱》 《琼林雅韵》 《神奇秘谱》等。
《太和正音谱》是一本文论韵谱类的著作,共有八个部分,排列井然有序,分别为乐府体式、古今英贤乐府格势、杂剧十二科、群英所编杂剧、善歌之士、音律宫调、词林须知、乐府,前七部分内容为北曲史料以及曲论,第八部分为曲谱。“太和”出自《周易·乾卦·彖》,“干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大和,乃利贞。”“大和”即“太和”,意谓太平正和。朱权《太和正音谱·序》曰:“夫礼乐虽出于人心,非人心之和,无以显礼乐之和;礼乐之和,自非太平之盛,无以致人心之和也。故曰: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依声定调,按名分谱”“譬之良匠,虽能运于斤斧而未尝不由于绳墨也”[1]。由上引可知,朱权将此书命名为“太和正音谱”,意谓该书是盛世曲乐创作的轨范和楷式,为戏曲创作者提供指导。
《太和正音谱》问世后,对后世曲谱的制作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王骥德《曲律·自序》曰:“惟是元周高安氏有《中原音韵》之创,明涵虚子有《太和词谱》之编,北士恃为指南,北词禀为令甲,厥功伟矣。”涵虚子即朱权,《太和词谱》即《太和正音谱》。王骥德是明代后期著名的曲论家,其对朱权《太和正音谱》评价这么高,足见此书的价值。[2]后世学者对此书多有研究,成果丰硕。今试从成书年代、版本情况、戏曲理论、曲史成就、语言学价值五个方面对这些研究成果加以述评。
一、关于成书时间的考察
关于《太和正音谱》的成书年份,因正文前有朱权自序,署题“时岁龙集戊寅序”,并且还盖上刻有“洪武戊寅”字样的葫芦印章,所以历来被认为成书于洪武三十一年(1398)。学者们通过考证,对成书时间有永乐元年(1403)间、永乐七年(1409)前后、永乐四年、永乐五年(1407)或稍前四种不同意见。
夏写时《朱权评传》 (1988)认为《太和正音谱》有两个版本,分别是成书于洪武三十一年的洪武本和完成于永乐末的增订本,即传世本。夏写时分析“知音善歌者三十六人”下记载的内容,又根据《太和正音谱》小令《出队子》所描绘的景色判断此为朱权入庐山之后的作品。此外,夏写时比较其与《录鬼簿续编》中有关明初杂剧作家的作品目录,其中后者收录作品更多,所以断定《太和正音谱》早于《录鬼簿续编》的成书时间(1426)。[3]
洛地《〈太和正音谱〉著作年代疑》(1989)主要根据名下注叙、作者自序、《太和正音谱》与《录鬼簿续编》两书比较以及朱权身世这四个方面,判断朱权《太和正音谱》当作于永乐年间(1403—1425)或永乐七年(1409)前后或以后。洛地指出:“《太和正音谱》‘知音善歌者三十六人’一章所云‘癸未春,渡南康、泊彭蠡’,正合朱权离京赴南昌时情景。”[4]由此认为《太和正音谱》并非写于洪武三十一年(1398),而应该写于永乐元年(1403)之后。因《永乐大典》成书于永乐六年(1408)且未收录朱权之作,洛地认为《太和正音谱》应成书于永乐七年前后或以后,这些结论都是较为合理的。
黄文实《〈太和正音谱〉曲论部分与曲谱非作于同时》(1989)分析谱中乐府体式、古今英贤乐府格势、群英所编杂剧、善歌之士四个部分的内容并结合朱权人生经历,认为曲论部分的撰写晚于洪武三十一年,应该作于朱权的晚年。黄文实指出:“《太和正音谱·善歌之士》云:‘予初入关时,寓遵化,闻于军中。’据《明史》朱权本传,建文元年(1399)九月朱权被燕王朱棣挟持,随同入关。”[5]这是朱权就藩后第一次入关,距洪武三十一年(1398)已经有一年多,确实是晚于洪武三十一年。黄文实仅以朱权波折的人生经历与曲论表现的思想认为曲论写于晚年时期,这缺乏充分的论据支撑。
周维培《〈太和正音谱〉成书考论》 (1990)对朱权《太和正音谱》成书于洪武三十一年的说法提出质疑,认为《太和正音谱》有朱权封藩大宁时的初刻本和改封南昌后的增补本,其中除了“词林须知”“乐府”谱式两部分内容,其他内容都是朱权后来增补的,且增补时间为永乐六年以后。[6]周维培结合朱权杂剧《独步大罗》冲漠子之语:“愚自幼惧生死之苦……至今三十余年矣。”与朱权生年,确定了朱权增补《太和正音谱》有关北曲资料是在永乐六年以后。但由于没有现存的洪武三十一年《太和正音谱》的初刻本,所以这一考论是一种猜想,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新思路。
姚品文《〈太和正音谱〉写作年代及“影写洪武刻本”问题》 (1994)认为《太和正音谱》约完成于永乐四、五年。姚品文从曲谱、曲论、序言、序尾两枚印章四个方面分析证明《太和正音谱》并非作于洪武三十一年。姚品文指出“曲谱收朱权自作的散曲四支,署名‘丹邱’,使用这个别号是朱权学道之后的事”,由此可知曲谱作于洪武以后。[7]这值得我们参考和继续研究。
冯燕群(2006)就朱权鄙弃佛家和《太和正音谱》未提及朱有燉两个方面进行探讨,从而支持姚品文的观点,认为《太和正音谱》写作年份应为永乐四、五年。[8]冯燕群分析了朱权《太和正音谱》未收录朱有燉作品的原因,并由此推测《太和正音谱》的成书时间,也是前人未涉及的地方,值得参考。
笔者认为姚品文的观点更加合理,《太和正音谱》应当成书于永乐四、五年。因《录鬼簿续编》录曲家数量多于《太和正音谱》,所以《太和正音谱》成书时间应当在永乐元年(1403)之后。根据《太和正音谱》中记录的朱权杂剧以及曲学著作的数量,若是在永乐初年至三年内完成,时间较短,所以《太和正音谱》成书时间应当在永乐四、五年甚至靠后的时间里。
二、关于版本情况的考察
由于《太和正音谱》有着众多版本,所以近年有许多学者对其年份、真假进行梳理考证,其中成就较高的有李健和杜雪等学者。
李健《〈太和正音谱〉版本源流考》 (2019)中对《太和正音谱》版本源流做了详细的考证。李健认为《太和正音谱》现存十一种版本,在比较分析的过程中将其分为三组,分别是二卷本、三卷本和十二卷本。[9]文章结尾绘制出了《太和正音谱》的版本源流图,使我们能够一目了然,直观地了解版本的发展情况。李健《〈太和正音谱〉现存版本叙録》(2020)是对上一篇文章的补充,也更加详细地说明了不同版本《太和正音谱》的刻印、题署、行款、印章的情况,并且移录其序跋,略考其刊者、序跋作者及收藏者的情况,简述各版本的特色及其相互关系[10]。这能够让我们概见现存所有版本的面貌,具有很大的数据价值。李健《美国国会图书馆藏抄本〈太和正音谱〉系书贾伪造考》(2020)中认为美国国会图书馆藏抄本是书贾根据《涵芬楼秘籍》本伪造而成,应当将其移出善本古籍行列。[11]
杜雪《盐谷温〈太和正音谱〉排印本研究》(2018)分析了盐谷温排印本的相关问题,使得我们可以略见《太和正音谱》在流传过程中的诸多现象和相关学术史的发展脉络。例如通过《元曲选》和《词品》两节本中所录《太和正音谱》的内容以及版本来源,可知《太和正音谱》的原貌及其流传情况。[12]同年发表的《日本内阁文库藏明刊〈太和正音谱〉考》(2019)开篇就指出了阁本为《太和正音谱》三卷本的祖本,对后出刊本颇有影响,具有校勘价值。例如杜雪主要从题名、龙集戊寅叙、分卷方式和曲谱样式的衍变四个方面去考察阁本在此谱版本变迁过程中的地位。此外还通过与其他版本比较,一一列出阁本对原谱的改动部分,得知阁本对原书的改动不大,从而体现了这一时期重刊者认识的变化。[13]这对于我们研究《太和正音谱》是很有价值的。发表于2020年的《长泽规矩也〈太和正音谱〉手校本研究》主要介绍了日本学者长泽规矩也利用《涵芬楼秘籍》本与内阁文库藏明刊本、《北雅》本进行详细的全书校对工作而得出的《太和正音谱》手校本。此校本不仅关注异文,亦关注分卷方式、行款格式以及异体字、异写字情况,对于研究《太和正音谱》是很有意义的。[14]
此外还有郑嘉靖《鸣野山房抄本〈太和正音谱〉系陈乃干伪造考》[15]、李万营《姚燮旧藏明钞本〈中原音韵〉〈太和正音谱〉考》[16]、龙赛州《康海刻本〈太和正音谱〉及其戏曲史意义》[17]等文章对《太和正音谱》不同版本真伪的考证以及对其戏曲史意义的讨论,都值得我们阅读和参考。
关于《太和正音谱》的版本问题,我们需要尽可能地去接触这些不同本子,进行比较,同时结合现有的研究成果,对《太和正音谱》的版本进行更加详细的分析讨论。
三、关于戏曲理论的研究
陶晶的《朱权〈太和正音谱〉中唱论及其古代歌者史研究》 (2012),从音乐的方向研究《太和正音谱》,着重于对前七章的研究,且将书中声乐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如从演唱者的角度对“偷气”“取气”“换气”“歇气”“就气”“爱者有一口气”等概念的解释,以及各类谱例的展示,是很有新意的。[18]虽然有创新,但更多的是作者自身对于概念的理解,缺乏充分的论据支撑观点。
石富林《北曲格律的形成——〈中原音韵〉与〈太和正音谱〉的比较》(2021)比较《中原音韵》与《太和正音谱》四十定格内曲牌,分析其曲谱特点、类型、作者代群及曲文变化,认为曲牌的格律是由约定俗成的标准渐渐形成了严格的规范。这为探讨格律的发展演变提供了帮助。[19]
四、关于曲史成就的研究
周维培《〈太和正音谱〉及其裔派北曲谱》 (1993)主要介绍了《太和正音谱》在曲谱制作史上的贡献以及以此谱为蓝本形成的三个北曲曲谱裔派,其中以《啸余谱·北曲谱》和《钦定曲谱》成就较高。周维培通过比较分析三个曲谱裔派之间的异同,例如在闭口字上加圈记认、乐字旁注平仄等等,由《啸余谱·北曲谱》创制,一直到《钦定曲谱》都在沿用,因此周维培认为“曲谱编纂,往往是继承性多于独创性”[20]。
宋海容《〈太和正音谱〉的“曲品”及“曲史”研究》 (2014)以史学价值为切入点,采用纵向研究与横向研究交叉并用的方式,发掘《太和正音谱》的史料价值,为研究《太和正音谱》提供了新思路、新角度。[21]其中将《太和正音谱》与不同版本的《录鬼簿》进行比较,来发掘朱权在文献数据记载方面上的价值与贡献,以表格的形式展现出来,从而给研究者们提供一种较为直观的观察方式,是其突出之处。
俞为民《朱权〈太和正音谱〉研究》从朱权生平、戏曲功能、戏曲风格、杂剧题材、戏曲史料、音律论与北曲谱及朱权的其他戏曲论著七个方面对《太和正音谱》进行了论述,着重强调了朱权《太和正音谱》中提出的戏曲风格与杂剧十二科对后世的戏曲理论产生的重要影响。其中结合了刘熙载、王国维、李开先等人对《太和正音谱》的评价,详细讨论了《太和正音谱》的各个部分,给研究者提供了参考。[22]
五、语言学的研究
施向东、高航《〈太和正音谱〉北曲谱考察——兼论周德清“入派三声”问题》 (2006)将《太和正音谱》北曲谱与《中原音韵》和普通话进行各声调乐字对比考究,对声调乐字进行了统计数据化的研究。例如有关北曲谱平声乐字,通过表格之间的数据对比,认为“北曲谱中的平声乐字在《中原音韵》基本被归于平声,在普通话中也大多读平声,也就是平声从元明时期到现代,没有发生太大变化”[23]。其中对去声乐字和入声乐字的分析也是以列表和数据这种直观的方式。此篇文章可以说是研究《太和正音谱》曲谱音韵首篇,是很有意义的,但是仅限于对声调的研究。
庄红梅《〈太和正音谱〉用韵研究》 (2009)从音韵学角度出发,对《太和正音谱》的335篇曲子的用韵情况、闭口韵的用字、各声调乐字的情况进行全面考察。例如通过对《太和正音谱》343章曲子用韵情况的归纳分析,总结出其用韵韵部为18个,包括冬钟、江阳、支思、齐微、鱼模、皆来、真文、寒山、桓欢、先天、萧豪、歌戈、家麻、车遮、庚青、尤侯、监咸、廉纤等韵部等结论,此处不再赘述。这对了解元明两代北方话的语音,以及现代标准音的历史演变,均可提供重要的依据。通过与《中原音韵》的比较研究,也将对从中古音至近代音的转变有更明晰的了解,由此进一步推动《中原音韵》研究朝着更加深入的方向发展。[24]
周一依《元明时期古入声字声调归派研究——以〈太和正音谱〉为立足点》 (2023)通过共时性与历时性相结合的方法,分析《太和正音谱》入声字归调问题。周一依从入声字的清浊入手归派《太和正音谱》《中原音韵》《琼林雅韵》以及《合并字学集韵》中的入声字,再分析《太和正音谱》与另外三者的异同点,从而对元明时期入声字声调归派进行总体考察。周一依认为《太和正音谱》总体上与元末入声声调归派情况一致,但蕴含着新变的可能。这对于元明时期入声字的归派问题提供了具体的依据,也为《太和正音谱》的入声字研究提供了较高的参考价值。[25]但是论文也有一些错误,比如“抹”的声调归派,《太和正音谱》原文有“作上聲”和“作去聲”两读,周一依仅记录了“抹”归去声明母,这说明了在归派过程中有遗漏。又如“嗏”周一依认为此字是清母字,但《字汇》注“嗏,初加切”,该字应为穿母。这些问题会影响研究的结果,需要我们仔细地去发现并改正。
六、关于“二本”含义的研究
《太和正音谱》卷首著录了杂剧作家作品,但是各家版本颇有不同,这一不同在近年来引起了注意,也有部分学者对其进行详细研究分析。叶天山《〈太和正音谱〉考异二题》(2015)认同赵景深对“二本”的理解,即“同题材的戏曲有两本,是两个人所写”。通过举例分析“国朝三十三本(内无名氏三本)”和计算“元五百三十五”标目之下的杂剧数量,论证了“二本”的含义不是一人写有二本,而是“别人写有同名(题材)之作”[26]。
此后有李健《〈太和正音谱〉版本源流考》 (2019)在对此谱进行版本梳理的过程中发现阁本、姚藏本、《北雅》均将“二本”作“2本”,从而导致数目大变,只有宁府本、何钫本、《啸余谱》对“二本”的理解是正确的。但李健并没有做详细的分析,只是发现了这一问题。[9]同年陈艳林发表的《〈太和正音谱〉所载杂剧数目与“二本”考》 (2019),对“二本”含义进行了详细的考证。《太和正音谱》不同版本的“群英所编杂剧”所注“本数”之比较、明末臧懋循《元曲选》中对“二本”的定义,即“二本”已被视为突破杂剧“一本四折”体制的“二本(八折)”、不同版本《录鬼簿》所录“二本”“次本”情况分析,通过这三个方面,详尽地论述了“二本”概念的发展和后人对它的误解情况。[27]
七、结语
上述几个方面的研究,由刚开始对序言研究而产生对著作年代的疑问,到后来对不同版本的研究,展开对《太和正音谱》内容的关注和深入探讨,再对此谱中一些细节的讨论,可以看出学者们对于《太和正音谱》的研究是不断深入的。通过众多学者的共同努力,使得我们对于此谱的著作年代和版本问题有了清晰的认识,研究成果颇丰。但是对于其他内容,诸如对曲谱中的韵部和曲论知识的研究,将其与《中原音韵》等韵书的比较研究,综合朱权曲学著作及其杂剧的研究等等,还没有全面系统地挖掘讨论,这些待将补足的部分仍需要学者们共同努力,作进一步的探讨。
参考文献:
[1]姚品文,洛地.太和正音谱笺评[M].北京:中华书局,2010:1.
[2]王骥德.曲律[A]//《续修四库全书》编委会.续修四库全书(一七五八·集部·曲类)[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420.
[3]夏写时.朱权评传[J].戏剧艺术,1988,(01):121-129.
[4]洛地.《太和正音谱》著作年代疑[J].江西社会科学,1989,(02):89-93.
[5]黄文实.《太和正音谱》曲论部分与曲谱非作于同时[J].文学遗产,1989,(06):110-111.
[6]周维培.《太和正音谱》成书考论[J].南京大学学报,1990,(04):38-41.
[7]姚品文.《太和正音谱》写作年代及“影写洪武刻本”问题[J].文学遗产,1994,(05):115-117.
[8]冯燕群.《太和正音谱》成书年份及两个相关问题[J].四川戏剧,2006,(02):55-57.
[9]李健.《太和正音谱》版本源流考[J].戏曲与俗文学研究,2019,(01):16-30.
[10]李健,黄仕忠.《太和正音谱》现存版本叙録[J].戏曲与俗文学研究,2020,(01):136-173.
[11]李健,李国庆.美国国会图书馆藏抄本《太和正音谱》系书贾伪造考[J].戏曲与俗文学研究,2019,(02):102-116.
[12]杜雪.盐谷温《太和正音谱》排印本研究[J].戏曲研究,2018,(04):137-154.
[13]杜雪.日本内閣文庫藏明刊《太和正音譜》考[J].戏曲与俗文学研究,2019,(01):44-57.
[14]杜雪.长泽规矩也《太和正音谱》手校本研究[J].中国典籍与文化,2020,(01):36-43+16.
[15]李万营.姚燮旧藏明钞本《中原音韵》《太和正音谱》考[J].戏曲与俗文学研究,2019,(01):58-71.
[16]龙赛州,陈艳林.康海刻本《太和正音谱》及其戏曲史意义[J].戏曲与俗文学研究,2019,(02):77-87.
[17]郑嘉靖.鸣野山房抄本《太和正音谱》系陈乃干伪造考[J].戏曲与俗文学研究,2019,(02):88-101.
[18]陶晶.朱权《太和正音谱》中唱论及其古代歌者史研究[D].武汉音乐学院,2012.
[19]石富林.北曲格律的形成—— 《中原音韵》与《太和正音谱》的比较[J].当代音乐,2021,(02):158-160.
[20]周维培.《太和正音谱》及其裔派北曲谱[J].艺术百家,1993,(01):110-114.
[21]宋海容. 《太和正音谱》的“曲品”及“曲史”研究[D].重庆师范大学,2014.
[22]俞为民.朱权《太和正音谱》研究[J].浙江艺术职业学院学报,2011,9(02):7-16.
[23]施向东,高航.《太和正音谱》北曲谱考察——兼论周德清“入派三声”问题[J].南开语言学刊,2006,(2):26-36,164.
[24]庄红梅.《太和正音谱》用韵研究[D].陕西师范大学,2009.
[25]周一依.元明时期古入声字声调归派研究——以《太和正音谱》为立足点[D].华中师范大学,2023.
[26]叶天山.《太和正音谱》考异二题[J].中国古代小说戏剧研究,2015,(00):187-193.
[27]陈艳林.《太和正音谱》所载杂剧数目与“二本”考[J].戏曲与俗文学研究,2019,(01):31-43.
作者简介:
徐晶晶,女,安徽安庆人,安徽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汉语史、音韵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