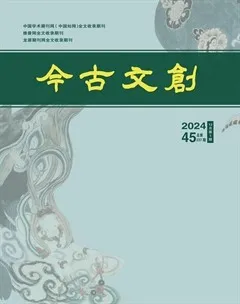西汉水运发展对东汉定都洛阳的经济作用研究
【摘要】东汉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时期,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都取得了巨大的发展,学术界关于该时期定都洛阳的研究一直络绎不绝。本文主要从水运的视角出发,将水运与都城命运相结合,以西汉水运的发展为历史发展主线,从水运所带来的经济作用研究水运在东汉王朝选择以洛阳为都城中起到的重要影响。史念海先生指出,都城的存废都可反映出王朝或政权的若干面貌,以至国运的盛衰,这是因为都城为王朝的中枢所在,从这里可以清楚了解到全国的情况,有助于我们对历史的研究。
【关键词】西汉水运;洛阳水系;水利建设;经济发展;定都洛阳
【中图分类号】K23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4)45-0082-04
【DOI】10.20024/j.cnki.CN42-1911/I.2024.45.020
一、西汉时期洛阳范围及其水系
(一)西汉洛阳所属的行政区划及其范围
西汉时期,中央政府为了治理中央核心区域,一共建制了七个郡级行政区合称“三辅”“三河”。[1]其中“尹”则是首都所在的郡级行政区的,京兆尹负责治理整个京师,“内史,周官,秦因之,掌治京师。景帝二年,分五左、右内史。右内史武帝太初元年更名京兆尹,属官有长安市、厨两令丞,又都水、铁官两长丞。”[2]
公元前205年,刘邦在打败项羽之后,曾以洛阳为都,“帝乃西都洛阳”[3]。后在娄敬的建议下,刘邦“徙诸侯子关中”[3],迁都长安。西汉建立后实施郡国并行制,但汉郡比秦郡的幅员小,数目多,汉武帝时期又把全国除近畿六郡外分为十三刺史部,而洛阳一直归属于河南郡并成为河南郡治所在。河南郡在西汉时郡域有较大的变化,《汉书·地理志》中记载的河南郡:
河南郡……县二十二:雒阳,荥阳,偃师,尸乡,京,平阴,中牟,豫州薮,平,阳武,河南,缑氏,卷,原武,巩,穀成,故市,密,新成,蛮中,开封,成皋,苑陵,梁,新郑。[4]
(二)洛阳周边水系
河流在中国古代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不仅对城市的发展有着密切关系,而且对一个王朝的经济、文化、军事等都有着或多或少的影响。在中国古代史中,大部分都城与繁荣的大都市都位于水系发达的地区,“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城市水源是城市赖以生存的生命线,没有水源的城市难以兴起,也无法延续发展”[5]。作为东汉都城的洛阳,它的地位的确立与洛阳地区的水系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
1.主要天然河道概况
黄河,在《山BXya2w9ipHsKBRS6bYGRiw==海经》中称黄河为“河水”,《水经注》中称黄河为“上河”,《史记》中称黄河为“大河”。它发源于青藏高原,是流经多个地区的母亲河。在西汉到北魏时期,黄河一直是洛阳北方的地理分界线,而古代洛阳地区也一直是黄河的中下游分界地,“河水又东迳洛阳县北,河之南岸有一碑,北面题云,洛阳北界,津水二渚分属之也”[6]。
洛河,在古代称为洛水,“出京兆上洛县 举山”。《水经注》卷十五记载:“洛水又东径宜阳县故城南……又东北过河南县南……又东过洛阳县南……又东过偃师县南……又东北过巩县东,又北入于河。”[7]洛河流经洛阳地区的河南县、雒阳县、偃师县、巩县,之后在巩县汇入黄河,整体上从西南流向东北。洛河冬无断流的情况,因此也被称为“温洛”,丰富的水源使其对农田的灌溉和航运的发展都起到了很大作用。
伊河,又称伊水,《水经注》记载:“伊水自熊耳东北径鸾川亭北……又东北过陆浑县南……又东北过新城县南……水出梁县西……伊水又北径当阶城西……又东北过伊阙中,伊水径前亭西……又东北至洛阳县南,北入于洛。”[7]伊河流经地区几乎都在汉魏时期的洛阳地区内,流经陆浑、新城、梁县、洛阳县之后汇入洛河,与洛河合称伊洛河。整体流向也为自西南向东北。而且根据《水经注》的记载,伊水在出伊阙之后注入洛水之前,右岸分出一条灌溉农田的水渠,左岸则分出一条水渠积水成湖,可见伊河水源的充足。
涧河,因其由谷、涧二水汇合而成,又称涧水、涧谷水或谷水。
《水经注》记载:“涧水出新安县南白石山,东北流历函谷东坂东。谓之八特坂,东南入于洛。”[7]涧水发源于新安县也从新安县东流入洛水,虽然并不是很长,但却是洛河下游在洛阳地区的主要支流。谷水“出弘农黾池县南谷阳谷……谷水又东,迳函谷关南……谷水又东,涧水注之,自下通谓涧水为谷水之兼称焉”[7]。谷水发源于现在的渑池县,自西向东在新安县东与涧水河流,并最终流入洛水。东汉曹魏时期为了解决都城内的用水问题,多次引谷水入城,比如东汉时期的阳渠,可见当时谷水不仅水量充沛,也十分清澈以便引用。
瀍河,又称瀍水,《水经注》卷十五载:“出河南谷城县北山县北有替亭,瀍水出其北梓泽中……又东过洛阳县南,又东过偃师县,又东于洛。”[7]瀍水发源于谷城县,也就是现在的孟津区,自西北流向东南,经过洛阳县和偃师县后流入洛河。瀍水为山间来水,水流较为湍急,所以夏季容易出现洪水泛滥。
2.主要人工河道概况
人工河道不仅仅是指在没有天然河道的土地上开挖的新河道,也包括对原河道大规模的扩挖。古代人工河道与天然河道相比,虽然具有水量不稳定、受地形影响较大、挖掘成本高等问题,但是人工河道的开挖,对洪涝灾害的治理、灌溉和引用以及漕运等都有很大的影响。秦汉时期是水利事业得到空前发展的时期,以运输为主要目的或兼及运输效益的水利工程在各地兴建。在洛阳的地区新建以及重新修复的运河有汴渠、阳渠等,这些运河不仅成为维护专制帝国生存并保证其行政效能的重要条件,而且为后世河运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狼荡渠即为战国时开通的鸿沟,在西汉时称为狼荡渠,在秦和西汉时期,狼荡渠作为黄河与淮河之间的重要水道,就发挥出突出的作用。楚汉战争时,敖仓在狼荡渠引黄河口附近,东南粮食多囤积于此,刘邦占领敖仓,掌握了楚汉战争的主动权。敖仓积粟,说明了该运河通航能力之强。《水经注》二十二记载:“渠出荥阳北河,东径荥泽北,东南分济,历中牟县之圃田泽北……渠水又左径阳武县故城南,东为官渡水。渠水又东南而注大梁也,渠水右与氾水合,渠水又东南流径开封县。”[8]狼荡渠从荥阳北边的黄河分出后与当时的济水乱流,在流经荥泽后才从济水中分流而出,后整体自西北流向东南,流经中牟县、阳武县、开封县后,“至陈入颖”,最后流入淮河。狼荡渠不仅有黄河、五池沟、氾水等河流的水源补充,也有来自荥泽、莆田泽等湖泊的水源,也正是因为其丰富的水源,以至于其在西汉时期也长期通航,只不过后来因为黄河泛滥,河道淤塞严重,狼荡渠联系黄河和淮河的作用,逐渐被后来治理的汴渠所取代。
二、西汉水利建设
西汉初期,黄河经常泛滥,虽然直接发生于河南郡地区的没有直接记载,但黄河的决堤依旧给当时河南郡带来了极大的灾难,使得当时以洛阳为核心的河南地区时刻面临黄河泛滥的威胁。汉文帝十二年的冬天,黄河在当时的酸枣地区决口,《史记·河渠书》载:“汉兴三十九年,孝文时河决酸枣,东溃金堤。”[9]之后汉文帝派遣大量东郡的士兵修堵决口,“东郡大兴卒塞之”使得黄河暂时恢复平静。酸枣地区紧邻当时河南郡的原武、阳武等县,所以这次决堤,让河南地区受灾也颇为严重,还使当时流经阳武地区的狼荡渠受到黄河泛滥的影响逐渐淤塞,不过汉文帝对黄河的治理也进一步减轻了黄河泛滥对河南郡的直接危害。
之后对河南有影响的则是汉武帝元光三年时黄河在瓠子口决堤,“河水决濮阳,泛十六郡”[10],这次决堤,虽然不是紧邻河南郡,但是因为刚开始治理不当等原因,致使黄河泛滥二十余年,直到元封二年才得以治理,使得位于濮阳南方的河南郡遭受灾难,后来汉武帝发动数万人,趁着干旱,黄河水量较少时堵塞瓠子决口,《汉书·沟洫志》载:“天子既封禅巡祭山川,其明年,旱,乾封少雨。天子乃使汲仁、郭昌发卒数万人塞瓠子决。”[11]这次治理,使得黄河在这一地方得到了根治,原来的黄泛地区重新安定下来,社会经济逐步恢复。在经过这两次对黄河的治理后,直到东汉建立,黄河在河南郡地区没有再出现大的泛滥,受水灾影响较小,使得河南郡地区农业得到了发展,水路运输也得到了保证,社会更为安定。
水利是农业发展的命脉,对促进农业的发展起到关键的作用。[12]西汉时期,黄河流域多地挖掘水井进行灌溉,在对洛阳的考古挖掘中作中,就发现了许多西汉时期的水井,如在洛阳卜千秋墓和在洛阳张就墓发掘的陶井,以及在洛阳汉河南县城出土的古水井,这些考古发掘已经充分表明当时已经出现了汲水灌溉的设施。此外,汉武帝时期各地兴修水利,“它小渠披山通道者,不可胜言,”而且司马迁本人也曾记录过自己巡视洛水等河所修的人工渠,“行淮、泗、济、漯、洛渠”。[9]由此可知,在西汉时期洛阳地区不仅有大量的水井设施,也有些许引自境内天然河流的灌溉水渠,遍布各地的水利设施,为人们的生产生活提供了充足的水源,促进了农业的发展。
农业生产是古代中国经济的主要组成部分,农业的发展与否决定着该地区的经济水平以及在全国的地位,而水利对于农业生产具有决定性意义。不管是西汉对黄河的治理,还是水井以及灌溉渠道的挖掘,都改善了原本河南郡地区的农业生产环境,不仅促使西汉时期该地区的经济获得了充足的发展,也为之后该地区农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三、西汉漕运与粮仓
西汉定都长安,关东的粮食运往关中,黄河成了当时西汉漕运的重要河流地。终西汉之世,黄河漕运不均如履。《史记·平准书》记载:“孝惠、高后时……漕转山东粟。”[13]可见在汉初时便已经重视黄河漕运,将河南之东的粮食运往关中。因为三门峡有砥柱之险,汉武帝时有人上书开通褒斜道进行漕运,从南阳进入关中,但是后来因为施工难度作罢,黄河依旧作为向关中漕运的重要河道。《史记·河渠书》记载:“其后人有上书欲通褒斜道及漕事,漕从南阳上沔入褒,褒之绝水至斜,闲百余里,以车转,从斜下下渭……而水湍石,不可漕。”[9]这次开通新航线的失败,也促使了东汉为了更方便将山东、江淮等地粮食运往都城,减少途中的风险,将都城选择在洛阳。这时的黄河漕运更为兴盛,已经由汉初的“岁不过数十万石”到汉武帝时的“而天下河漕度四百万石”。[13]西汉后期,虽然王朝日益衰败,但是河南附近的黄河漕运始终平稳发展,《资治通鉴·汉纪二十二》记载:“汉成帝‘谒者二人发河南以东船五百艘’”[14],仅河南以东就能轻易征收五百艘船,可见平时用于漕运的船只也不在少数,从船的数量不难看出当时黄河漕运的发展。黄河漕运的发展,加强了河南地区与其他地区的经济联系,同时也带动了洛阳周边贸易的繁荣,而且为后世开展黄河漕运奠定了基础。
除了对黄河漕运的发展,为了便于将南方地区的粮食经黄河运往关中,还在荥阳地区修建了漕渠,用以运输东南物资,加强南北方之间的交流,《资治通鉴·汉纪二十五》记载:“汉成帝时‘恐议者疑河大川难禁制,荥阳漕渠足以卜之’。”[15]可见在此之前荥阳地区便有了漕渠。荥阳漕渠北接黄河,向南分为两道,一道由鸿沟向南,至陈入颖,另一道由陈留向东南,至阳夏入涡水。虽然荥阳漕渠经常遭受黄河侵扰,但其长期作为南北运输的重要渠道,带动了河南郡东部地区的经济发展。
由于西汉对漕运的依赖,使得位于漕运关键点的河南地区成了西汉重要的粮食储存和中转地,修建了大型粮仓——敖仓。西汉建立之初,刘邦与项羽对峙于鸿沟,刘邦采纳郦食其的建议,将位于荥阳的敖仓占据,《汉书·郦陆朱刘叔孙传》记载:“夫敖仓,天下转输久矣,臣闻其下乃有臧粟甚多。”[16]这一举动为刘邦战胜项羽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表明了当时敖仓之大和储梁之多,这也使得敖仓的地位更为突出。[17]敖仓在西汉一朝都被统治阶级所重视,七国之乱时,谋士应高曾言,“大王诚幸而许之一言,则吴王率楚王略函谷关,守荥阳敖仓之粟,距汉兵”[18],虽然在西汉时期长安附近有许多重要粮仓,但是敖仓的所处的关键漕运位置也使得敖仓成为关东地区甚至全国的重要粮仓。敖仓在战争中具有的重要意义,也恰恰说明敖仓所储粮食的丰厚,而且长安在西汉末年农民战争时被起义军洗劫一空,位于河南地区的敖仓则为当时东汉政权提供了粮食和粮食储放的地方,再加上敖仓距离粮食主产区更近,便于各地运输来的粮食的储放,进一步提高了当时河南郡地区在统治者心中的地位。这也是为何汉光武帝即位第二年便派人攻占敖仓。
四、西汉水运船只的建造
西汉时期,位于关中地区的中央政府依赖于漕运,再加之西汉一朝对内对外战争的需要,促使了造船业的发展。《资治通鉴·汉纪二十二》记载:“汉成帝‘谒者二人发河南以东船五百艘,徙民避水居丘陵’”[14],成帝征收河南东部地区五百艘的船,用来载着百姓迁徙,为了迁徙受灾地区的百姓,专门派遣船只运输,而且仅河南东部就能征收五百艘船只,可见西汉时期造船业发展兴盛,整个河南地区所拥有的船只数量也相当可观。西汉时期,运输粮食的船只称为漕舫,将两船相并加板于上,以便运输更多的粮食。早在楚汉战争时,便有漕舫,《史记·郦生陆贾列传》记载:“诸侯之兵四面而至,蜀汉之粟方舟而下。”[16]这种相较于之前可以运输更多粮食的漕船,使得水运的作用更为突出。1951年,湖南长沙出土1.54米西汉“十六浆木船模”,在船尾部有一只浆,用于代舵,这属于内河航行的快速航行,对客运、漕运以及军事运输都具有深远意义。此外,《汉书·食货志》记载:“山东漕益岁六百万石”[19],山东地区向关中地区每年运输粮食六百万石,除了粮食外肯定还会运输其他,每年的货运量如此庞大,没有庞大且数量多的漕船是难以实现的,可见当时船只的发展已经有了相当高的水平。在西汉时期,已经出现具有专门功能性的船只,《西京杂记》卷六记载:“太液池中有鸣鹤舟、容与舟、清旷舟、采菱舟。”[20]客船、漕船的发展和各种专门性能船只的出现,减轻了当时水上作业的困难程度,同时也进一步打破了河流对地域的阻隔,促进了河流沿线的经济交流,增加了遍布河流的洛阳地区的便利性和经济发展。
为了提升水军的战斗力,汉武帝还命人建造了高达十多仗的楼船,《史记·平准书》记载:“治楼船,高十余杖,旗帜加其上,甚壮。”[13]因其船大楼高,成为当时水战的主力。水战的船只还有戈船。《汉书·武帝纪》记载:“归义越侯严为戈船将军”[10],虽然戈船在这里是将军的名号,但是通过之前的楼船将军我们不难得知,当时已有以戈船为主组成的水军。战船的建造,提高了水上作战的能力,加强了水上防御的力量,为以洛阳地区为代表的河流附近的地区提供了坚实的军事保障。
五、水运与丝绸之路的密切联系
丝绸之路分为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汉武帝时期,张骞两次出使西域,开辟了东起长安,西到西域、中亚、西亚以及地中海地区的陆上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是由陆上丝路衍生而来的,从先秦时候就已经形成,主要通过海上交通路线和西方国家进行丝绸贸易。[21]西汉时期海上丝绸之路共有两条,一条是从山东沿海到日本,另一条是从南方沿海到南亚。丝绸之路的开通促进了各国人民之间的文化艺术和科技交流,同时也促进了沿线城市和地区的经济发展。[22]位于中部的洛阳地区,在西汉时期虽然距离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较远,但是通过当时便捷的水路运输,不仅使丝绸之路延伸至洛阳,更是因其所处水运的关键位置,使丝绸之路的影响通过洛阳扩大到其他地区,《史记·货殖列传》载:“洛阳东贾齐、鲁,南贾梁、楚。”[23]在此基础之上,洛阳也成了西汉时期的商业中心之一。
西汉时期,从长安到洛阳,有水路和陆路两种。陆路被即崤函古道,起于潼关,然后进入豫西山地,至函谷关后,经灵宝老城抵陕州,最终向东抵达洛阳。[24]因为所经地区多为山地,道路险隘,运输往来十分不便。再看水路,船只从长安出发,经渭水或汉武帝时修建的漕渠直接到达黄河,关于漕渠,《史记·河渠书》载:“引渭穿渠起长安,并南山下,至河三百余里,径,易漕,度可令三月罢。”[9]到达黄河后,沿黄河顺流而下,经过到达洛阳。从长安到洛阳的水路,全程是顺流而下,不仅在航行过程中更为省力,也大大节省了航行的时间,虽然在三门峡处有“砥柱之险”,但是水路运输相比陆路运输,可以运输的货物更多。综上所述,在西汉时期,长安与洛阳之间水路运输更为重要。在丝绸之路开辟后,作为连接长安与洛阳的重要水路,无疑承担着丝绸之路功能的延伸,使得洛阳也能尽最大可能地享受丝绸之路带来的红利。在洛阳发掘的西汉墓中,出土了许多汉画空心砖,其中有些许骏马的画像,或在地上矫健奔跑,或插上翅膀翩然欲飞。中原马匹体型较矮、速度慢,画像中的马躯体浑圆、四肢细长,尾巴斜后上翘,与当时西北和中亚地区的马匹形象相似,而且画中的“天马”形象,也来自张骞开辟丝绸之路后,汉武帝将乌孙马命名为天马。[25]由此证明西汉丝绸之路开通后,随着东西方的交往日益频繁,交通便利的洛阳也成为丝绸之路在中原地区延伸的重要节点。
西汉丝绸之路的开辟后因为水运的延伸,再加上洛阳东贾齐、鲁,南贾梁、楚的优越条件,使得洛阳的商业经济在西汉时期获得了充足的发展,到王莽时期成为全国的六大都市之一。在东汉面对都城选择的问题时,拥有深厚商业经济底蕴的洛阳,无疑增添了统治者定都洛阳的决心。
六、结语
在古代,水运对一个地区乃至一个王朝的发展是具有深远意义的,包括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多个层面,但是我们从水运最为直接的作用来看,水路运输是古代大规模运输最重要的方式,而在中国古代经济中占主导地位的农业,也离不开水源,因此水运发展直接影响推动的便是一个地区经济的发展。两汉时期,长安、洛阳、襄阳、成都、建业等经济繁荣的地区,无一不是位于水运发达的地区。发达的水运网线,让原本毫不相连的两个地区密切联系在一起,使之在河流的串联下更为繁荣。两汉时期,洛阳都曾作为全国的政治中心,究其原因,很重要的一点则是洛阳自身的经济发展潜力,这一时期洛阳各种各样的经济运作不绝如缕络绎不绝,而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使得洛阳的经济发展潜力快速实现并发展的便是其较为发达的水运网线。西汉时期对水运事业的重视以及洛阳地区水运的发展,对东汉定都洛阳无疑起着强大的推动作用。
参考文献:
[1]史念海.中国古都和文化[J].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3,(04):1-39.
[2]班固.百官公卿表[A]//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
[3]班固.高帝纪上[A]//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
[4]班固.地理志[A]//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
[5]马正林.中国城市历史地理[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9.
[6](北魏)郦道元.水经注(卷5)[M].北京:中华书局,2009.
[7](北魏)郦道元.水经注(卷15)[M].北京:中华书局,2009.
[8](北魏)郦道元.水经注(卷22)[M].北京:中华书局,2009.
[9]司马迁.河渠书[A]//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73.
[10]班固.武帝纪[A]//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
[11]班固.沟洫志[A]//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
[12]卢昉.从“二重证据法”看汉代农业发展[J].中国民族博览,2016,(03):90-92.
[13]司马迁.平淮书[A]//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73.
[14]司马光.资治通鉴(汉纪二十二)[M].北京:中华书局,1956.
[15]司马光.资治通鉴(汉纪二十五)[M].北京:中华书局,1956.
[16]班固.郦陆朱刘叔孙传[A]//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
[17]邵鸿.西汉仓制考[J].中国史研究,1998,(03):32-41.
[18]司马迁.吴王濞列传[A]//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73.
[19]班固.食货志[A]//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
[20](汉)刘歆撰,(晋)葛洪集,向新阳,刘克任校注.西京杂记校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
[21]于国方.海上丝绸之路[J].问答与导学,2019,(33):21-22.
[22]王茹芹,兰日旭.陆上丝绸之路[J].时代经贸,2018,(10):54-75.
[23]司马迁.货殖列传[A]//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73.
[24]李久昌.崤函古道开通的历史地理基础[J].三门峡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9,8(03):45-50.
[25]徐婵菲,郭开红.洛阳西汉空心砖画像解读[J].荣宝斋,2018,(10).
作者简介:
贾琛轲,男,汉族,河南郑州人,河南科技大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