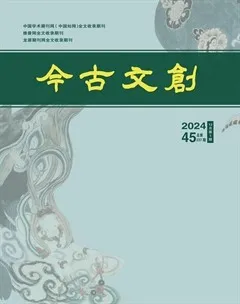论托妮·莫里森笔下美国黑人女性的身体困境和突围
【摘要】本文从福柯的权力与身体的理论视角探讨莫里森笔下的美国非裔女性身体意象,通过剖析莫里森代表作《最蓝的眼睛》《秀拉》和《宠儿》里的黑人女性的身体困境,揭示美国黑人女性在遭受权力惩罚、规训、压制、弱化的同时,如何通过自己的身体对权力进行消解、反抗甚至颠覆,并建构自我主体性。
【关键词】托妮·莫里森;美国黑人女性;福柯;权力;身体;主体性
【中图分类号】I7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4)45-0056-04
【DOI】10.20024/j.cnki.CN42-1911/I.2024.45.014
基金项目:本文为江苏高校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莫里森笔下美国黑人女性的身体困境研究》的阶段研究成果(项目编号:2019SJA1615)。
一、引言
托妮·莫里森(Toni Morrison)是当代美国最重要的作家之一,也是迄今为止唯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黑人女作家。黑人和女性的双重身份,使得莫里森洞悉黑人女性的生存困境,并对黑人女性的命运投入深切的关注和深入的思考。
近年来,国内学者对莫里森作品的研究不断深入,研究主题日益丰富,涵盖了女性主义、叙事学、文化研究、心理学、伦理学、身体政治等多个领域。尽管国内对莫里森的研究已取得一定进展,但从福柯的权力与身体理论视角进行的探讨仍相对不足。在国际学术界,近年来关于莫里森的研究同样成果斐然,相关专著已超过20部。这些研究也呈现出多元化趋势,涵盖了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解构主义等多种理论视角。
本文选取莫里森的代表作《最蓝的眼睛》《秀拉》和《宠儿》作为研究对象,是因为这三部作品集中体现了莫里森对黑人女性身体困境的深切关注。本文从权力与身体的理论视角探讨这三部作品中的美国黑人女性的身体境遇,揭示黑人女性在遭受权力惩罚、规训、压制、弱化下,从主体性丧失到反抗意识逐渐觉醒,再到主体性完成建构的艰辛历程,以期对其相关研究作出新的思考和有益的补充。
二、托妮·莫里森笔下的黑人女性形象及其身体境遇
黑人女权主义者贝尔·胡克斯认为:“在美国,黑人女性是最被忽视的边缘化群体,她们从未被单独识别,既不与黑人男性区分,也未在更广泛的女性群体中获得独立地位。”[1]身为黑人女作家,莫里森塑造了许多鲜活的黑人女性形象,不论是年幼的佩科拉、不婚不育的秀拉,还是为母亲的塞丝,都深陷白人霸权和黑人父权所带来的困境,而造成她们不公待遇的根本原因就是性别与种族的双重束缚。
在《最蓝的眼睛》中,佩科拉是一个自怜自艾、身心皆不健全的黑人小女孩,却渴望拥有符合白人审美标准的蓝眼睛,她对自身黑人身份的自卑和对白人文化的盲目崇拜,导致了她对自身身体的厌恶和自我否定,最终沉沦于拥有一双蓝眼睛的幻觉世界而迷失自我。
在《秀拉》中,秀拉是一个挑战传统道德观念的女性,她对性自由的追求和对传统家庭模式的颠覆,体现了她对自身身体的掌控和对社会规训的反抗。秀拉虽然有着强烈的自我意识,却因特立独行、离经叛道的行为而被社区孤立抛弃。
在《宠儿》中,塞丝是一个在奴隶制下遭受严重创伤的女性,她被剥夺养育孩子的权利,被当作生育工具,她的身体成为男性权力争夺和压迫的对象。残暴的虐待和强暴使塞丝的自我意识逐渐觉醒,并通过携子逃跑进行反抗。在被奴隶主发现后,为了阻止年幼的女儿重蹈沦为奴隶的悲剧,塞丝亲手将其杀死。多年后在家庭和社区的理解和帮助下,塞丝终于走出弑女的心理阴霾,完成主体性的建构。
三、权力与身体的相互作用
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作为西方最有影响力的后现代主义哲学家之一,密切关注身体问题和身体与权力的关系。福柯在《规训与惩罚》中展现了一个全景敞开式的监狱,小部分人在暗中窥视犯人,以规范和惩罚的方式驯服犯人。在福柯看来,监狱是权力的产物,权力是身体的主体,身体是话语权和权力规训的客体,权力在背后操纵身体,从而保证其统治地位。[2]而社会中人类身体深受社会权力关系的影响,身体是权力的作用对象,被无限度地使用与损耗,压抑与弱化,惩罚和规训权力塑造了听话的、驯顺的、有用的身体,并制造了各种各样不正常的身体。当然,身体虽然处于被塑造被规训之中,但其也有反抗和颠覆强加的权力的能力和要求。作为权力化身体的一部分,性身体越来越多地受到权力关系的生产和管理甚至压制和迫害,同时性身体也是反抗权力最有效最直接的手段和武器。身体和权力的这种相互关系在莫里森作品中的黑人女性身上表现得尤为深刻。
(一)权力对身体的铭刻——身体的困境
1.被权力剥夺身体的话语
在《宠儿》中,权力剥夺身体的话语现象尤为突出、令人惊骇,莫里森就是“要言说不可言说的问题”,帮助处于“失语”状态的黑人女性群体发声。
小说以19世纪六七十年代为背景。在废奴声明发表前,黑人奴隶被定义为白人奴隶主的合法财产,其中黑人女性奴隶因其生育能力更被当作有更多利用价值的财物。数百万甚至数千万的黑人女性不能拥有和支配自己的身体,没有自己的名字,不知道自己的父亲是谁,被剥夺母爱,完全丧失身体的自由和人格的尊严。她们的身体被买卖、被拘禁、被鞭打、被强暴、被凌辱、被践踏、被烧死……女主人公塞丝自小就被剥夺母爱,只模糊地记得肋骨上有“一个圆圈和一个十字”的奴隶烙印的黑人是自己的母亲。塞丝的婆婆贝比·萨格斯的八个孩子来自不同的父亲,有白人奴隶主,也有黑人奴隶。他们刚出生就被像牲畜一样被卖到各地,而贝比却无能为力。黑人奴隶的权利、自由都被白人剥夺,其中黑人女性的处境更是苦不堪言,根本没有身体的话语权。
2.被白人权力惩罚与规训的身体
在奴隶制度的社会权力关系下,黑人奴隶的身体是白人权力的作用对象,被最大限度地使用与损耗,压抑与弱化,惩罚和规训权力塑造了驯服有用的黑人身体。正如福柯所言,男性权力和男性话语在黑人女性身体上得以施展,规训着她们的生存。
在《宠儿》中,庄园的老主人采用规训的方式驯化黑人。这种比较温和、宽松的庄园管理方式与雇佣关系相似,给塞丝和其他奴隶造成一种自由和平等的错觉,因而不能清醒地认识其本质仍然是剥夺黑人自由、压榨奴役黑人的奴隶制。新主人“学校老师”是个地道的种族主义者,为了证明黑人的种族劣等性,他像检验牲畜一样,用工具测量奴隶的身体和牙齿。奴隶们稍有反抗,便会遭到鞭挞、挨饿等多重惩罚。塞丝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屈辱和侵犯——她被白人“学校老师”以及他的两个侄子残忍地性侵,他们甚至无情地吸食她的乳汁,这不仅是对她的身体摧残,更是对她作为母亲的权力的精神践踏。白人滥用他们的权力,对黑人女性奴隶进行肆无忌惮的惩罚和身体侵占,将她们的人性尊严踩在脚下。
3.被黑人男权压迫的身体
作为权力化身体的一部分,性身体越来越多地受到权力关系的生产和管理甚至压制和迫害。在父权文化中,性是父权规范女性身体的一种形式。男性是主体,而女性则是体现男性性欲望的客体。所以在黑人社区时,常有黑人男性施加性权力,对黑人女性进行强暴、侵犯等种种行为。
正如《最蓝的眼睛》中的佩科拉在年幼时就遭受自己亲生父亲的虐待,甚至是被其侵犯以致怀孕生下死婴。可怖的是,在黑人男权的压迫下,遭受众人唾弃的不是施害者,而是受害的佩科拉。佩科拉怀疑自己、否定自己、厌恶自己。她认为一切不幸都源于自己丑陋的外貌,如果自己能拥有一双美丽的蓝色的眼睛,父亲将会不同,母亲将会不同,一切将会不同。
母亲是塞丝在《宠儿》中的典型身份,其男权社会赋予她的“神圣”责任是生儿育女。她的丈夫选择和她结婚并不是因为爱情,而是将她作为自己的所有物,目的仅是生育儿女,完成传宗接代的任务。当塞丝因为奴隶主的追捕而杀死女儿,从此被贴上“疯子”和“坏女人”的标签,被黑人社区抛弃孤立,因此塞丝是一位缺失自己文明的黑人女性。
(二)身体对权力的反抗——身体的突围
身体虽然被权力不断惩训压制,但其本身也能反作用于权力,甚至颠覆权力,以实现身体的突围。
1.身体之残
身体既是黑人女性最容易遭到侵害的软肋,也是其反抗男性权力压迫的最强大的武器。
在《秀拉》一书中,秀拉的外祖母伊娃虽然只有一条腿,却是一位勇敢无畏的女性。在被丈夫抛弃后,她独自一人养活孩子,甚至让火车碾压自己的一条好腿来获取保险赔偿金。这个方法虽然极端,但获得的金钱却足以养活她的三个孩子。最后,当看到儿子沉溺毒品时,她绝望地放火烧死了自己的儿子。在那个黑人社会地位低下、普遍遭受贫困与歧视的年代,伊娃用自己的残疾之躯,为整个家庭博得了金钱与一线生机,同时也对那个不公的社会发出了一声响亮的反抗。秀拉和好友奈尔遭受四个白人男孩多次欺负,秀拉没有退缩隐忍,而是拿出小刀削去了自己的左手指尖,吓得白人男孩四散而逃。秀拉的行为颇具象征意义,她“以自残的极端行为证明了为捍卫自己不受侵犯而激发的阉割阳具的决心”[3],颠覆白人对黑人女性强加的权力。
《宠儿》里,塞丝的母亲被迫整日在农场劳作,白人奴隶主在她身上烙上奴隶烙印,她没有自己的名字,更不会读写,就让塞丝牢记自己身上的烙印来识别自己的身份延续黑人的血脉。塞丝成长为母亲后,因为反抗白人抢走自己给女儿留的奶水而被鞭挞,后背被划烂。塞丝再次怀孕后忍受身体的剧痛毅然逃跑,并在奴隶主追捕下愤然杀死女儿,并准备自杀。身为奴隶的母亲,塞丝只能用这种残害甚至毁灭自己身体和孩子身体的极端方式来对抗奴隶主的迫害。
2.身体之美
福柯在《性经验》史中指出:“性是权力为了控制身体及其力量、能量、感觉和快感而组织的性经验机制中最思辨、最理想和最内在的要素。”[4]福柯揭示了人类社会通过建构身体的性与性别来实施权力管控,而黑人女性正是通过解构身体的性与性别来反抗男权对其身体管控,消解男权社会对其身体施加权力的目的。
传统男权社会认为,只有男性拥有性的权力,女性只能作为性的客体,女性的主要功能和职责是满足男人的性欲望和养育后代的需求。因此,女人应该扮演好顺从的妻子、尽职的母亲的社会角色,但秀拉却通过性爱来寻找身体带来的愉快和美好,并用这种独特的方式捍卫身体的自主权。秀拉沉迷于性爱,这种看似放纵的行为,违背当时社会严格的性别角色与道德规范,实则是她用自己独特的方式对身体自主权的捍卫和自我追求的满足,也是对男权社会的对抗。在那个女性被视为男性附属品,女性的欲望与需求常被忽视和压抑的时代背景下,秀拉选择了一条截然不同的道路。秀拉享受着性爱的自由和快乐,并在和谐的性爱中寻找自我、接纳自我、愉悦自己。这不仅仅是为了个人的生理或情感需求,更是一种对自我存在价值的肯定,对既定社会秩序的挑战。秀拉不愿意被传统的性别角色所束缚,拒接结婚生育,以身体力行的方式探索并实践着女性主体性的可能。
通过自由性爱,秀拉展现了一种对传统性别权力关系的颠覆,试图打破那些将女性定义为弱者、依附者的刻板印象。
3.身体之爱
秀拉的外祖母伊娃用自己残疾的身体为整个家庭博来了金钱与希望。这充满了对爱与责任的坚守,是对社会不公的沉默抗议,也是母性力量的极致彰显。
塞丝因为面对女儿宠儿可能重蹈自己覆辙的恐惧——劳动价值被无情剥削、婚姻自由被剥夺、身体遭受侵犯、一生被奴役的命运,她做出了一个震撼人心的决定:亲手结束宠儿的生命。这一行为,在外人看来或许残酷无情,但实则是塞丝深沉母爱的体现,是她对女儿未来幸福与自由的极度渴望所驱使。她相信,与其让宠儿在这样一个充满压迫与不公的世界中挣扎求生,不如让她以身体的死亡换取灵魂的解脱与自由。塞丝的这一选择,是对那个时代奴隶制度无声的控诉,也是她作为母亲对女儿最深切的保护与爱的表现。
(三)重构主体——身体的确立
黑人女性的自我意识逐步觉醒,她们通过各种方式积极重构女性主体。这一过程必然是一场场漫长的、艰辛的、充满险阻但又义无反顾的探索。
1.自由的身体
自由的身体对于黑人女性的独立精神以及个人的身份的确立有着重要的作用。自由身体是黑人女性自由意志表达的前提。通往自由的道路对于奴隶制时期的黑人女性,必将是困难重重但又值得用生命相搏的。
塞丝年幼时被卖至种植园,当她意识到在白人眼中黑奴与动物无异时,毅然携子逃跑。面对奴隶主的追捕,为了防止孩子遭受非人的厄运,她决定杀死孩子,然后自杀,最终只来得及杀死了不到两岁的女儿。这一行为虽令人悲痛,却是黑人母亲的无奈选择与绝望抗争。在一次访谈中,莫里森对此评论道:“塞丝做了正确的但是她却没有权利去做的事。”[5]这种自我毁灭的行为,不仅是母爱的极端表达,更是对奴隶制度深重罪恶的强烈抗议,同时也向外界宣告了黑人女性对自由身体的渴望和追求。
与塞丝的命运形成鲜明对比,秀拉要幸运多了。秀拉完全拥有自己的人身自由,不仅能自主决定自己的身体和性,还能自由选择是否结婚生育。尽管秀拉拥有这样的身体自由,但她的生活并不尽善尽美,她经常遭受家人和社区的辱骂与排斥。缺乏家庭温暖和社区支持,秀拉在建构自我主体性的道路上遭遇了重重障碍。秀拉因拒绝赡养自己的外祖母而被社区非议,因与不同的男人交往却不结婚而被社区诟病。因此,不管是生前还是死后,秀拉从来没有真正融入社区,没有得到家庭和社区的接纳和尊重,难以建立完整独立的自我主体性。
2.家庭之爱
家庭的关爱和支持是女性正确认识自我并构建自我主体的重要条件和关键因素,其中父爱和母爱更是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黑人小女孩佩科拉正是因为缺失家庭的温暖才丧失自我,走向毁灭。
佩科拉的成长环境是不幸的。酗酒的父亲和冷漠的母亲带给她的只有争吵和伤害,她能做的只有祈祷自己消失。“当她每次努力祈祷的时候,在想象中,身体的确一段又一段的消失,可消失到最后,她的全身,只剩下眼睛还固执地呆在那里。”[6]佩科拉从未得到家庭的关爱、教育和引导,恶劣的家庭环境使其养成胆小、懦弱、自卑、隐忍的性格,加之外貌的丑陋,便更加卑微。遭受亲生父亲的强暴并产下死婴给其带来致命的打击,而她却将所有遭遇的一切归结于自己没有“一双蓝色的眼睛”。家庭温暖的缺失使黑人女性在遭受到歧视、欺凌时更加孤立无助,从而陷入自我怀疑和自我否定的恶性循环中。
自由不仅意味着身体的自我控制权,也象征着心灵的自主独立。在经历弑女悲剧后,塞丝虽然重获了肉体的解放,但心灵却依旧困于无形的囚笼。她深陷于对往昔的愧疚中而无法自拔,过着离群索居的生活。因此,唯有重建与家人及社区的纽带,才能帮助塞丝摆脱过去的阴霾,才能实现精神的解脱,确立完整的自我主体性。情人保罗·D不仅是塞丝饱受苦难的见证人,同样是奴隶制的受害者。他用爱与宽容唤醒了塞丝沉睡的意识,将她从死亡的边缘拉回来,赋予她重新面对生活的勇气。他慰藉塞丝,让她认识到自身的价值,激励她以积极的心态迎接未来,治愈心灵的创伤。塞丝的小女儿丹芙,也以极大的关怀和支持陪伴着母亲。成年后的丹芙,肩负起家庭的重任,努力工作以养家糊口,并主动向黑人社区寻求援助,帮助母亲摆脱梦魇的困扰。
3.社区互助
社区互助,是黑人女性主体构建的重要方式之一,因为黑人享有共同的文化之根、生存境遇、民族情感和传统纯朴的生活方式,属于同一个群体。
在《最蓝的眼睛》中,每一个角落都充斥着白人至上的审美观念和文化影响,导致黑人和其他有色人种不自觉地追捧白人的生活方式和审美标准。在此过程中,他们抛弃了本民族文化原有的纯真与简朴,以及真挚的情感,反而陷入了愚昧、自我憎恨和绝望的境地。这不仅加剧了他们的精神困境,还无意中促使他们成为白人进行精神奴役的共犯。
年幼的佩科拉不仅得不到家庭的关爱和引导,还要遭受来自社区的厌恶、歧视与敌意。上到白人店主的冷漠与厌恶,下到有色人种邻居的戏耍与欺负,再到黑人男同学的辱骂和欺凌,使佩科拉陷入深深的羞耻感和愤恨,但她不能反抗,只能屈辱忍耐、无助哭泣,只能感到更加自卑,甚至自我厌恶、自我憎恨。因为白人主流文化认为黑人“像苍蝇一样成群结队地飞行,像苍蝇一样散落下来”[7],令人鄙夷厌恶。
与孤独无援的佩科拉形成鲜明对比,塞丝的命运显得相对幸运。她不仅赢得了家人的理解与支持,最终也收获了社区的宽容与接纳。塞丝的婆婆贝比·萨格斯,作为黑人群体中的精神导师,她定期在林中举行的布道会成了族人聚集和交流的圣地,唤醒了他们沉睡的自爱意识,引领他们探寻文化的根源。贝比·萨格斯让她的同胞们在大笑、哭泣、祈祷和歌唱中融为一体,在彼此的慰藉中愈合伤口。她的鼓舞揭示了黑人对完整自我的认知,对个人与集体身份的认同,这对于他们身体和精神上的存续都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非洲歌舞,作为黑人民族特有的交流方式,承载着他们独特的审美情趣。在黑人社区中,这种艺术形式不仅助力塞丝重新融入集体,更是一种深情的接纳与拥抱。非洲民谣的旋律与驱鬼舞蹈的节奏,共同强化了黑人群体对民族文化的认同感和自信心,也激发了他们对自我主体性的坚定信念。在社区的温暖关怀和本族文化的感染下,塞丝终于从弑婴的阴影中挣脱出来,重新接纳了自我,重塑了一个更加坚强、更加完整的自我主体。
四、结束语
本文从福柯的“权力”与“身体”理论出发,探讨了莫里森笔下的美国黑人女性身体面临的多重困境和反抗策略,揭示了身体作为权力运作场域的复杂性以及黑人女性自我主体构建的艰巨性,深化了对美国黑人女性身体经验与生存现状的理解,并为推动社会性别平等提供理论参考。
参考文献:
[1]吴新云.身份的疆界——当代美国黑人女权主义思想透视[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145.
[2]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M].刘北成,杨远婴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
[3]李雪梅.黑人女性的身体诉求——酷读《秀拉》[J].重庆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27(06):102-107.
[4]米歇尔·福柯.性经验史[M].佘碧平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116.
[5]Wilfred D.Samuels.Toni Morrison[M].Boston: Twayen Publishers,1990:111.
[6]托妮·莫里森.最蓝的眼睛[M].胡允恒译.海口:南海出版公司,2005:28.
[7]托妮·莫里森.最蓝的眼睛[M].胡允恒译.海口:南海出版公司,2005:60.
作者简介:
赵燕,女,汉族,江苏淮安人,南京师范大学英语语言文学硕士研究生,淮阴师范学院外国语学院讲师,研究方向:英美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