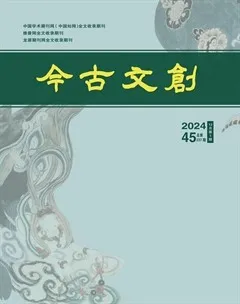论中国古代文学中的“桑” 意象
【摘要】在中国古代文学中,“桑”这一意象频频出现,其形成背后蕴含着丰富的社会、历史、文化及心理动因,与神话传说和祭祀风俗紧密相连。本文分析“桑”意象的起源,阐释桑意象的发展演变,从男女情爱与家园的隐喻、生命意识的集中表达两大方面来说明桑在文学中是生命的象征这一问题,并梳理桑意象影响下文学的嬗变,进而展示其特定时代先民们的文学创作方式、精神面貌及其所追求的审美价值,凸显出社会的进步与发展。
【关键词】“桑”意象;起源;发展演变;文学嬗变
【中图分类号】I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4)45-0044-04
【DOI】10.20024/j.cnki.CN42-1911/I.2024.45.011
基金项目:本文获浙江农林大学学生科研训练项目资助(项目编号:2023KX079)。
意象,作为中国传统审美艺术的基石,它源自创作主体对客观物象进行独特情感活动的加工与提炼。其中“桑”意象独树一帜,在文学表现领域中占据显著地位。古代人民对桑树怀有深深的崇敬,它承载着丰富的社会文化意涵。桑树与生命、繁衍、祭祀、家园等紧密相连,它承载着古人对自然、生命与社会的深刻理解和情感寄托。本文将深入剖析“桑”意象的起源,通过多角度地探讨,以期更好地理解这一富有象征意义的文学元素在古代文学中的地位与价值。
一、“桑”意象的起源
“桑”意象在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频频出现,它与先民的日常生活密切相关,它的形成受当时的社会政治、文化、社会环境等影响巨大,并且与神话传说和祭祀风俗密切相关。
(一)神话传说
在中国古代文学中,“桑”意象最早可追溯到神话传说。《山海经·中山经》当中记载道:“大五十尺,其枝四衢,其叶大尺馀,赤理黄华青柎,名曰帝女之桑。”赤帝女居桑而升天,此桑被称为“帝女桑”。此外,还有白马通人性救父舍女的“桑马神话”等。其中,最为著名的神话传说便是“日出扶桑”“空桑生人”,这两个神话传说说明桑在先民的原始信仰中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桑树被视为生命之树,其强大的生殖力受到先民的崇拜。
“扶桑太阳”是中国古代描述神树扶桑与太阳关系的神话,在这个神话中,扶桑树为太阳女神羲和与她的儿子提供了舒适的居住环境,当太阳爬上树梢时带来晨昏的交替,说明扶桑树与太阳难舍难分的关系:扶桑神木不仅是日之所出同时还是太阳神的栖息地。《淮南子》记载的扶桑:“日出于旸谷,浴于咸池,拂于扶桑,是谓晨明。登于扶桑,爰始将性,是谓朏明。”[1]在古代社会,先民们主要从事农业耕作,太阳能够给农作物带来能量,所以太阳与人类的繁衍有着密切联系,太阳崇拜可以说是先民们的原始崇拜。桑树与太阳之间的紧密联系,源自它们共同象征生命的起源。黄河沿岸温暖湿润的气候为桑树提供了得天独厚的生长环境,桑树苗展现出非凡的生命力,即便在干旱贫瘠的土壤中也能顽强存活,而且桑叶在采摘后还能重新生长。这种循环再生的顽强生命力,使桑树在人们心中成了不朽的象征,代表着生命的持久与更新。受农耕文化的影响,人们对桑树怀有一种原始的生殖崇拜。
先民对桑树的生殖崇拜还体现在桑树生人的神话传说中。《吕氏春秋·本味》写到伊尹的母亲化身为桑树,而伊尹便在这神奇的空桑之中孕育而生。桑树经常被看作先贤圣人的出生之地,《吕氏春秋·古乐》当中记载了颛顼生于若水,实处空桑,登为帝;夏朝的开国君主启,也是他父亲大禹与母亲涂山女在桑树旁深情相爱的美好结晶。先民将生殖力与桑树结合,将先贤圣人的诞生与桑树紧密相连,以此神化。他们寄托于神桑形象,祈愿子嗣繁盛、功成名就。
其他的神话传说也能说明桑在先民心中的重要性。《山海经·海外北经》中记载了桑蚕起源的故事,在巨人国东方的原野上,一位女子食桑后倚树吐丝,初步描绘了蚕神的形象,并揭示了桑蚕间的紧密联系。《神仙传·麻姑传》中提到“沧海桑田”说,外表看似十八岁的麻姑,却已目睹东海几度化为桑田,这一对比,令人深刻感受到生命的短暂与无常。这些都反映了原始先民对自然现象敏锐的观察与深入的认识。
(二)祭祀风俗
桑树的生殖力意象展现出的生命力令人惊叹,它枝繁叶茂,深深扎根于大地,叶片仿佛触及天空,象征着旺盛的生长与无尽的繁衍,深深影响了古代统治者的宗教祭祀活动,并渗透到青年男女的幽会之中。
人们深信桑树拥有与上帝神鬼沟通的神秘力量。因此,他们选择在桑林中举办庄重的社祭活动,将桑树与社祭仪式紧密结合,使桑树与宗教祭祀之间建立了深厚的联系。这一传统使得桑树的形象被赋予了原始宗教文化的浓郁色彩,充满神圣与庄严的气息。在远古的农耕时代,人们于茂密的桑树林间举行庄重的祈雨仪式,以虔诚之心呼唤上苍的眷顾,祈求天地之间气候适宜,雨水适时而至,滋养大地,让农作物茁壮成长。《吕氏春秋·顺民》曰:“昔者汤克夏而正天下,天大旱,五年不收。汤乃以身祷于桑林……于是翦其发,断其手,以身为牺牲,用祈福于上帝,民乃甚悦,雨乃大至。”[2]当雨水过少,大地陷入干旱时,商汤便亲自前往桑林,祈求上天降下甘霖。
先秦时代,桑林不仅是古人寻求天降甘霖的圣地,还有着祈求子孙满堂、家族兴旺的意义,是年轻男女幽会的场所。《周礼·地官·司徒》记载周代存在“会男女”的古老礼俗。通常在“仲春之月”举行,举办地点设在庄重而神圣的社祭场所。《诗经·小雅·隰桑》中隐晦地描述了男女桑林幽会场景:“隰桑有阿,其叶有难。既见君子,其乐如何。”春天是万物复苏、生命蓬勃生长的季节,桑林中的幽会也融入了大自然的生命热情,成了生命力量的自然流露。从古老的神话传说到统治者庄严的祭祀活动,再到普通青年在桑林中的私密聚会,都深刻体现了桑树在古代社会中的生殖力象征意义。《左传·成公二年》:“巫臣聘诸郑,郑伯许之,及共王在位,将为阳桥之役,使屈巫聘于齐且告师期,巫臣尽室以行,申叔跪从文,将适郢,遇之,曰:‘异哉!夫有三军之惧,即又有桑中之喜,宜将窃妻以逃者也。’”[3]揭示了周初时期男女在桑林间欢会的习俗,展现了当时相对宽松自由的社交环境,男女可以在桑林中自由相会。后世以“桑中之约”来指代男女之间的秘会。
二、“桑”意象的发展演变
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桑”意象不断演变与发展。无论时代如何变迁,它始终深深根植于原始宗教信仰中的生命意识和生殖崇拜,并承袭了《诗经》中独特的审美原型意义。作为后世文学艺术的重要主题,“桑”不仅生动还原了质朴勤劳的农耕生活风貌,更成为描绘男女间深厚情爱的典范。“桑”还被赋予死亡、长生与家园情怀等多重意蕴,展现出丰富的文化内涵与情感价值。
(一)男女情爱与家园的隐喻
在先民的观念中,桑树象征深不可测且充满活力的生命力量。它孕育了蚕的生命,而蚕作为制造丝绸的原材料,与民众的生计紧密相连。随着时间的流转,以“桑”为代表的生生不息的自然力量,更蕴含了男女情爱的象征意义,最终升华成为家园的象征,寄托着人们对故土和生活的深情厚意。
1.男女情爱的隐晦表达
自古以来女子便肩负采桑纺织之责,桑林成为女子获取纺织原材料的场所,也为桑林成为爱情的萌芽地提供了客观条件。《诗经》中桑林、桑园通常是男女幽会之地,展现了纯粹真挚的爱情体验,是人性与自然相交融的“思无邪”境界。《小雅·隰桑》中,“隰桑有阿,其叶有幽。既见君子,德音孔胶”[5],以桑叶之婀娜多姿、生机勃勃来描绘少男少女的青春美艳,茂密浓荫的桑林成为他们幽会的绝佳场所。《鄘风·桑中》中“桑中”与“上宫”之处,正是恋人们情深意浓的约定之地。诗的主角沉浸在欢乐之后的甜蜜记忆中,不断回味在桑林与上宫中的浓情蜜意和相送淇水时依依不舍的缠绵。
《诗经》的另一类诗作通过以桑比兴的手法,描绘弃妇形象,表现女性的屈辱与不幸。《卫风·氓》用“桑之未落”“无食桑葚”“桑之落矣”展现女子从对爱情的美好憧憬到年老色衰后惨遭背叛的愤慨,尽诉弃妇之悲,决绝之情扑面而来。《小雅·白华》中“砍那桑枝作柴薪,烧在灶里暖在身”,那位女子曾是身份显赫的贵人,然而婚姻的变故却让她被无情地抛弃,如今只能以炉中烈火温暖心窝。这些诗作以桑比兴,无论是贵族还是平民,女子在爱情中都受到不公正的待遇。
《诗经》将“桑”作为男女爱情的象征,是劳动分工的自然产物,也是基于对生殖繁衍的崇拜。这种象征意义深深扎根于中华文化的土壤之中,对后世爱情诗的创作与发展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为诗人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创作灵感。
2.家园情怀的深情流露
先民对森林的神秘敬畏之情深深植根于民族集体无意识的深处,他们把生命与树木紧密联系在一起,视树木为家园的象征,最终形成家园意识。
《管子·牧民》中曾提到“藏于不竭之府者,养桑麻、育六畜也”[4]。可见,种植桑麻与饲养六畜同等重要,事关人们的衣食住行。因此,先民经常在家园周围植桑栽梓,所谓“五亩之宅,树之以桑”,游子便常用桑梓表达思乡之情。这里的“桑”也阐释为父母先辈所栽种的桑梓树,因此带上了思乡的色彩。
《幽风·鸱鸮》一诗中,桑树坚实的枝干和茂盛的枝叶,成了母鸟加固巢穴的工具,她以此保护尚未孵化的雏鸟。在这里,“桑”承载了对家园的坚守之意。在《小雅·黄鸟》中,人们反复告诫黄鸟不要落在桑树上,从中表现出先民守护家园的心愿。《小雅·小弁》更是直接指出“维桑与梓,必恭敬止”。桑与梓是父母亲手种下的,一定要对它们充满恭敬之心,这种对家乡的桑树的敬畏之情,无不彰显出深厚的家园情怀与浓烈的归属感。后世文学作品在表达思乡之情时,亦常借用“桑”借代家园。唐代诗人柳宗元《闻黄鹂》:“乡禽何事亦来此,令我生心忆桑梓”,借回忆桑梓(即故乡的桑树),深情地表达了对家乡的思念之情。东晋陶渊明《归田园居》诗云:“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fDkTzskl/CBFXC567Fxi05+FV6xPbBxoz4Jpre8etk=颠”,以狗吠、深巷、鸡鸣、桑树道出一片浓浓的乡土家园气息。
古代诗歌在描绘“桑”这一意象时,深植于崇拜的礼俗之中,从源头上将“桑”的社会属性和文化内涵融入诗篇,使得“桑”充满浓郁的家园意识,成为古代诗歌中不可或缺的家园象征。这种家园意识在诗歌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被用来表现先民对于家乡的眷恋和对家乡人的认同和尊敬。
(二)生命意识的集中表达
桑树常被视为具有神秘力量的树木,在文学作品中具有特殊符号意义,与人类的初始生命观念紧密相连。从“桑”所寄托的情感来看,“桑”常与丧葬、不祥与长生联系在一起,体现先民对于生命的思考。
1.死亡:生命的终结
在先民的传统观念中,“桑”带有神灵的属性。因此,在古代的祭祀仪式中,桑木常被用作制造桑木棺和桑木牌位等重要物品,使得“桑”这一意象烙印上了丧葬的意味。闻一多先生的《释桑》中说:“五曰桑,读为丧、动词,丧之也。”[5]由于“桑”与“丧”谐音,后世的人们常常将“桑”与不祥、死亡等负面意义联系在一起。在风水学中,更是有“前不栽桑”的讲究,意指门前不宜种植桑树,以免带来厄运。《吕氏春秋·音出》中以“桑间之音”比喻淫靡的音乐,桑在此间接性地作为不吉利的象征。据《晋书》记载,晋惠帝时,东宫西厢突生桑树,日长一尺,旋枯死。班固预言此象示小人将窃居高位,危国亡家。十二月,愍怀太子果被废,应验预言。[6]此处的桑树同样作为不祥的象征。
在《诗经》时代,“桑”与死亡并没有明显的直接联系,常被用来营造悲凉的气氛[7]。《秦风·黄鸟》一诗中,深刻讽刺了秦穆公以人为殉的残忍罪行。诗中每章开头都运用了“交交黄鸟,止于棘(桑、楚)”的描写,巧妙地以黄鸟栖息于不同树木的景象,隐晦地表达出对秦穆公不仁不义行径的强烈谴责。这三句诗句巧妙运用了语音相谐的双关语,诗中的“棘”字寓意“急迫”,“桑”字则暗示“丧事”,“楚”字则代表着“痛楚”。全诗形成凄婉哀转、潸然泪下的悲伤基调。
由此可见,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桑树的死亡意象往往与深奥的风水学说以及个人或家庭的命运紧密相连。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影响下,桑树的生长或死亡,常常被视作一种自然与人之间微妙关系失衡的象征,从而引发人们对命运多舛的深深忧虑。除此之外,也不乏以“桑”意象为介体,将景与情融合在一起表现伤感怆然的心境的例子。
2.长生:生命的延续
桑树被视为长寿之灵木,具有象征时间的意味,古人在追求长生不老之时,常将自己与桑树联系在一起。因此,先民对桑树的崇拜体现了对长生不老的向往。《中国神话传说》一书中,描述了一种名为“穷桑”的大桑树,其树叶红得像枫叶,桑葚大而肥,紫晶光亮,一万年才结一次果实。吃了这种果实可以活得比天地的寿命更长久,这即为长生不老。这种描述将桑树与长生不老紧密联系在一起,赋予了桑树神秘而神圣的特性。古书中也常以“桑榆”一词比喻垂老之年,《后汉书·冯异传》:“失之东隅,收之桑榆。”以桑比喻人的垂暮之年。晋代葛洪在《神仙传·麻姑》中也以沧海桑田的变迁来比喻人生的短暂和无常,人生犹如白驹过隙,转瞬即逝,深深表达了对生命短暂的感叹和对永恒的追求。
古人认为时间是宝贵的,流动的生命不能逃离时间的管控。但“桑”始终焕发着源源不断的生命力,是生命的象征,因此历来受到人们的敬仰。同时,古人希望掌控时间,延续生命,达到长生,是生命观念的强烈写照与升华。
三、“桑”意象影响下文学的嬗变
在“桑”意象文化的不断积淀之下,衍生出了特定的桑林母题,这使得桑林文学蓬勃发展。并且随着朝代的更迭,社会历史条件的持续演变,桑林文学也随之发生一系列的嬗变。虽然其核心内容仍然是以“桑”意象为原型,但在创作艺术与思想主旨上却发生了变化,具有不一样的时代特征,表现了特定时代先民们的文学创作方式、精神面貌及所追求的审美价值,凸显出社会的进步与发展。
(一)创作艺术的嬗变
“桑”意象的发展演变与时代的演进,都对于桑林文学的创作者提出了新的要求与挑战。为了更好地展现出“桑”意象代表着的情感与特定的时代特征,创作者们在创作艺术上不断寻求创新,使得桑林文学在创作艺术、情节模式等方面发生了一系列的嬗变。
1.创作手法上的嬗变
首先,桑林文学在创作手法上有一些新发展。桑林文学的创作从最早的《诗经》中采用的文本内容的铺陈直叙、句式的简单重复,描绘出桑林间的劳作场景和人物形象,发展到后来情节跌宕起伏,通过语言、动作、细节等方面的具体叙写来展现人物形象。如《十亩之间》作为《诗经》中的一篇,通过“十亩之间兮,桑者闲闲兮,行与子还兮……”这样简单句式的重复,以及铺陈直叙的手法描写了采桑女的日常生活及其形象,而到后来桑林文学的创作手法逐渐成熟和丰富,创作者塑造出更加立体、生动的人物形象。在刘向所著的《列女传》中,通过对于女性角色陈辩女与男性角色晋大夫“女为我歌,我将舍汝!”“墓门有棘,斧以斯之。夫也不良,国人知之……”[7]等具体的对话描写以及句式的不断转变展现出了采桑女拒绝男主角的挑逗时,表现得不卑不亢、贞正而有辞的人物形象,她巧妙地运用语言,化解了被拒的尴尬,为对方留下了情面,展现出了高度的应辩能力和机智勇敢的品质。
2.情节模式上的嬗变
从情节模式来看也有了一定的创新发展,故事情节的复杂化、曲折化使得故事变得更加丰富多彩,人物形象更加生动鲜活,创作更具有张力。以桑的爱情象征为例,从最初的简单描写男女双方之间的爱情感受,情感表达直接而朴素,到后来作品中出现了除男女双方外的第三人的情节,且着重笔墨于采桑女与第三人之间的角色互动,淡化丈夫形象,甚至是出现了第三人轻佻形象以及调戏的情节,增加了故事的复杂性和趣味性。如《陌上桑》中通过第三人使君向罗敷求爱被拒的对话描写以及对于行者、少年等第三人被罗敷吸引的动作、神态描写,直接或间接地讴歌了罗敷的美貌与坚贞,更突出了罗敷在面对金钱的诱惑与权威的压迫之下不卑不亢、恪守道德底线、机智化解困境的采桑女形象。
(二)思想主旨的嬗变
在“桑”意象影响文学的嬗变过程中,除了在创作艺术上的嬗变,更为核心和深刻的嬗变体现在文学思想主旨上。这种嬗变不仅反映了古代先民独立自主意识的发展,更是社会进步和发展的重要体现。
1.人民主体地位的凸显
在面对阶级关系这一社会核心问题上,桑林文学的思想主旨发生了一定的嬗变,从以维护贵族阶级的利益出发转变为维护人民利益的角度出发,展现了先民们独立自主意识的觉醒与发展。在古代,桑树作为农事祭祀中的圣物,承载着深厚的文化意义。在《诗经》等早期文学作品中,“桑”意象多与贵族阶级的生活和价值观相联系。例如对于《诗经》中的《关雎》一文,有的学者认为其描绘的是一幅后妃躬耕图,展现了“后妃之德”。而其思想主旨则是想通过贵族的引导示范作用来规劝民众勤耕,以维护社会的稳定和繁荣;而后来的文学作品中,对“桑”的描写更多地与农民劳作和心绪相联系,如《七月》中:“嗟我妇子,曰为改岁,入此室处……”表现出下层农民的艰苦生活与繁重劳动状况,让他们开始在心中感到暗暗的不满,这种变化体现了作者对人民生活的深刻关注和同情,也反映了人民独立自主意识的萌芽。而白居易的《杜陵叟》作为唐代深刻反映社会现象与人文情怀的作品,诗中所言“典桑卖地纳官租,明年衣食将为何?”则是更加明确地表达了人民对于农民疾苦的同情之情和对上层阶级的不满,深刻揭露了农民在沉重赋税压迫下的悲惨生活,表达了对上层阶级剥削行为的强烈不满。这种情感不仅是作者对农民疾苦的同情,更是对人民独立自主意识的觉醒和表达。
2.女性主体地位的凸显
在男女关系中,桑林文学的思想主旨则转变为重点突出女性独立自主意识的觉醒。展现出女性的力量,是文化与社会的双重进步。从最初《豳风·七月》中“女执懿筐,遵彼微行,爰求柔桑。春日迟迟,采蘩祁祁。女心伤悲,殆及公子同归……”中采桑女面对公子哥的要求时,虽然内心充满不满,但她不敢反抗,只能忍气吞声被动地接受,位于两性关系中的从属地位。到后来刘向《烈女传》中的陈辩女、《陌上桑》中的罗敷两位女性形象,则展现出了女性更多的独立性与自主性,她们面对权贵不卑不亢,机智勇敢地应对,坚守了自己的底线。这不仅展现出了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更展现出当时的人们开始重新审视女性的价值和地位,给予女性一定的肯定,促进了社会的进步与发展。
四、结语
“桑”意象不仅仅是文学作品中的客观物象,它的起源、发展演变以及在其影响下文学的嬗变都值得探究。“桑”意象代表着远古先民们的原始崇拜,是他们的精神信仰。“桑”意象的起源与神话传说和祭祀风俗密切相关,在神话传说中“桑”意象就已经频繁出现,不仅如此,在对桑生殖力崇拜的影响下,人们到桑林祭祀以祷雨和祈求子嗣。它不仅巧妙地展现了神话与文学之间的紧密联系,还极大地丰富了文学作品的文化意蕴。“桑”意象的发展演变有着丰富的象征意蕴,包括男女情爱与家园的隐喻、生命意识的集中表达等,给后人文学作品的创作赋予了更深刻的思想蕴含和文化意义,影响深远。在“桑”意象影响下桑林文学经历了创作艺术和思想主旨上的嬗变,不仅展现了创作者们在创作手法上从铺陈直叙、简单重复到运用具体描写,情节模式变得更加复杂化、曲折化,而且反映出先民们的思想进步,体现了人民自主意识的觉醒和女性社会地位的提高,凸显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对“桑”意象进行分析和解读,能够从中窥探“桑”意象背后联结着先民的精神底蕴,揭示其所承载的生生不息的生命情怀,有助于后世人们更好地认识先民们生活的时代特点以及精神内涵。
参考文献:
[1](汉)刘安撰,(汉)许慎注,陈广忠校点.淮南子[M].北京:中华书局,2016.
[2](秦)吕不韦编,许维遹集释,梁运华整理.吕氏春秋集释[M].北京:中华书局,2009.
[3]杨伯峻.春秋左传注[M].北京:中华书局,1990.
[4]黎翔凤.管子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9.
[5]闻一多.闻一多全集[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2.
[6]房玄龄等撰.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
[7]刘向.列女传[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3.
[8]韩惜花.桑意象的文化内涵及其演变[J].现代语文(学术综合版),2015,(10).
[9]曹佳琦,黄凌霞.“桑”的生殖力、生命源头意象:在早期神话文学及现实中的体现与流变[J].蚕桑通报,2022,53(04).
作者简介:
郑安迪,女,汉族,浙江温州人,浙江省浙江农林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2021级本科生。
朱玲娣,女,汉族,浙江杭州人,浙江省浙江农林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2021级本科生。
应柯珊,女,汉族,浙江绍兴人,浙江省浙江农林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2021级本科生。(指导老师:王秋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