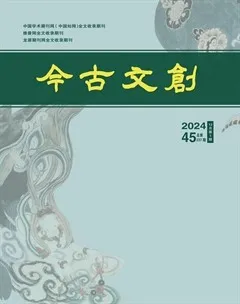作品中的社会性别分析
【摘要】简·奥斯汀与艾丽斯·沃克来自异质的社会文化环境,在作品中塑造的女性角色贴合自己的生活经历和社会文化环境。《劝导》与《紫颜色》两部作品的女主人公在社会性别的初始阶段有着相同的“隐身”特征,在把握自身命运轨迹的选择上也表现出各自的特质。本文拟用社会性别理论,对两位女主人公在婚姻选择、家庭地位、社会角色等方面的异同进行解读。
【关键词】《劝导》;《紫颜色》;社会性别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4)45-0036-04
【DOI】10.20024/j.cnki.CN42-1911/I.2024.45.009
《劝导》(Persuasion, 1817)讲述了女主人公安妮因遵从理性的“劝导”,与恋人错过八年又重新结合的故事。《紫颜色》(The Color Purple,1982)则以女主人公西丽的成长历程为线索,描绘了以西丽为中心的黑人女性的生活,表达了作者对黑人女性当下生存处境的关注。根据肖瓦尔特所指出的妇女文学发展阶段,“在1840—1880年间,英国妇女写作力图达到男性文学的水平……这一阶段最明显的特征是女作家普遍采用男性笔名”[1]。奥斯汀的文学创作便属于这一阶段,她的诸多作品也成为英国文学系列中的经典之作。奥斯汀颇擅长用中规中矩的文笔,描写乡村门户人家的生活,并且从微型的生活中隐含着对大问题的思考与批评,因而她的作品被称为“象牙上的精雕”。黑人女权主义文学批评以反抗种族压迫和性别歧视为主旨,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左右,其中不少作品尝试颠覆西方白人中心论。沃克则以浓墨重彩的笔触,赞扬了黑人女性彼此支持的美好情谊,表现了她们争取平等人权与社会地位的不易,在主题广度、批判力度上更加多元、深刻。
两部不同国别的文学作品,反映出不同时代、种族、阶级的女性生活状态。在女性主义文学发展的脉络上具有典型性。本文拟用社会性别理论,在比较不同时代的女性追求婚姻幸福、人格独立的基础上,尝试运用新的视角进行文本分析,探讨女性扮演的社会角色。
一、屈服:婚姻规范的顺从与选择
1817年,在兄长Wmwo+t19OEXmWpDPEG4hU8yKW3P6fN7DUMD+bZZcxLE=亨利·奥斯汀(Henry Austen)的努力下,《劝导》作为简·奥斯汀的遗作问世。有研究者认为,《劝导》深刻展现了初入社会的年轻女性在社会实践中获得认知提升的过程[2],而提升的过程发生在安妮屈从于父亲、友人的权威,转而觉醒的过程之中。1982年,美国非裔女作家艾丽丝·沃克(Alice Walker,1944—)创作了《紫颜色》。作品一经问世,便获得了美国普利策小说奖、美国国家图书奖等多项荣誉。小说以女主人公西丽的成长轨迹为主线,展现了非裔女性实现社会化的艰难历程。两部作品的女主人公在经历各自的成长过程后,都找到了自身理想中的社会位置。
依据性别研究理论,“社会性别是以文化为基础、以符号为特征判断的性别,它表达了语言、交流、符号和教育等文化因素构成的判断一个人性别的社会标准,社会性别概念强调性别的文化特性。”[3]安妮与西丽各自的成长历程,日常生活中的言行举止,均符合各自社会文化所要求“对应的社会想象”[4],成为解读文学作品中社会性别的切口。
按照19世纪的社会状况,男女在婚姻选择上有不同的标准。女性处于极低地位,年轻时靠父亲、成婚后靠丈夫生活;男性要娶得好妻子,良好的人品倒在其次,外在的殷实财产与好风度才居首位。安妮作为这种社会文化浸染的女性角色,她要做的是通过各种宴会、社交活动结识地位、家产与自己相当的丈夫。这些社交活动将安妮的交往圈子限制于家庭内部,语言表达也离不开生活上的琐屑小事。因此,安妮“在教育上,生活经验与价值观的养成多数依靠家庭教师或年龄较长的同性”[5],《劝导》中担任这一角色的是安妮母亲生前的密友拉塞尔夫人。她在安妮的成长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直接影响了安妮的婚姻选择。在拉塞尔夫人看来,安妮与温特沃斯的真挚情感远远比不上财产与地位的重要性,她认为“这桩婚事是不幸的,安妮·艾略特出身名门,美丽而又聪颖,年方十九便断送了自己的一生”[6]。安妮经不住她一向信赖和热爱的拉塞尔夫人的劝说,忍痛和恋人分手。
安妮不仅在恋爱对象的选择上顺从了社会期许。在家庭生活中,她也处处包容家人对自己的不公,遵从依赖者的规范。父亲和姐姐从没把她放在眼里,“她的意见无足轻重,她的安逸总可以牺牲——她只不过是安妮罢了。”[7]在父亲、姐妹决定带着“品行不端”的克莱太太前往巴思,而不选择自己陪同前往时,安妮选择恪守自己的本分,忽略自己受到的屈辱,主动留下陪伴妹妹玛丽。在此期间。她不仅教导两位外甥,还协调着妹妹的家庭矛盾。安妮的行动符合“社会想象”中的高洁品行和恰当的举止。林文琛在文章中曾说,“安妮不是一个只会宣泄或沉溺于个人感情的人,她总以自己细腻的体察、真诚的关心感染他人,所到之处总能形成和谐、惬意、融洽的感情氛围,给人们以美好的人性感受。”[8]面对亲人的疏离,安妮没有抱怨他人、责备自己,而是照旧扮演好自己在家庭、社交中的角色,将他人的便利作为自己幸福的前提。
安妮在他人的劝导下主动放弃了爱情,在家庭和社交生活中,她也总是隐藏自己的苦痛给他人带来方便与幸福。安妮的言谈举止体现的文化特征不仅符合出身名门的小姐的身份,也符合社会对于当时的想象——既不过分表露自己,又能恰当处理生活中的各类矛盾。西丽同安妮具有同样的特点——没有婚姻的自主权利,心甘情愿地接受生存环境带来的考验。相较于安妮主动承担性别角色带来的责任,西丽则是在外界威胁与暴力恐吓之下,麻木机械地承担自己的责任。因此,西丽面临的困境比安妮更深一层。这种困境既表现在畸形的原生家庭给西丽带来的童年阴影,更强烈地表现在她对男性权威主导的生活苦痛的不自知。这些痛苦使原本蒙昧无知的西丽更难以确定自己的性别与社会位置。
缺失正常父爱的西丽,被继父掌控,不仅被他剥夺接受正规教育与去教堂的权利,甚至还被其强奸,生下了两个孩子。后来她又在继父的安排下,与某某先生结婚。身体是权力的记号[9],西丽同继父和某某先生的这两段关系,她的身体不能被自己掌控,成为男性施加权力的场域,而且方式往往是暴力的。两位男性几乎成为西丽与社会接触的全部关系网,他们的角色与相处的结果形塑着西丽对社会中自我与他者关系的认知。在封闭环境中,西丽对自己所处的地位是麻木的,这种麻木来自对社会正常规则的无知。而与外界接触甚少的西丽在潜意识中认为自己的生活本该如此。她整日忙于照顾某某先生的孩子、下地干农活,无人倾诉,只能与不存在的上帝写信交流。面对丈夫的毒打,西丽从不反抗,而是“拼命忍住不哭……把自己变成木头……对自己说,西丽,你是棵树”[10]。此时的西丽对自己的性别没有明确的认识,更没有意识到自己做人的权利,她只是某某先生照顾家庭的工具。
性关系是社会中的典型秩序之一,“传统性观念使人们相信男性在性方面是活跃的,具有掠夺性的;女性是被动、顺从的。这建构了性活动中的性别压迫秩序。”[11]西丽生命中接触的继父和某某先生带给她的都是性压迫,在这种性别秩序的压迫中贯穿着男性凌驾于女性之上的传统性别秩序。西丽接受并认为这样的生活方式对女人来说是理所应当的,类似西丽这样的女性必然无法进入社会正常秩序之中。
二、突围:婚恋自主意识的觉醒
尽管安妮与西丽的婚恋选择顺从了外界的安排,但觉醒之后她们都能勇于打破桎梏——八年过去,安妮遵循内心对温特沃斯的真挚情感,与他破镜重圆;西丽则在同性恋人莎格的指引下,逐渐认清生活的本真面目,明确自己的性征,实现更高的自我价值。安妮与西丽做出了相同的选择,即遵循自己的内心想法而非“社会想象”。但在选择的过程中,两位女性又有显著的不同,体现了异质社会环境的女性在追求婚姻自由、确立社会身份过程中的不彻底与彻底、犹豫和果决。
安妮缺乏追求感情的主动性,将自己的婚姻选择依附在男性身上。与温特沃斯分手八年之后再度重逢,安妮极力避免与之见面,生怕掩饰不住自己对他的感情,干脆不去参加墨斯格罗夫先生的聚会,但内心却“很想知道,弗雷德里克对他们俩人的见面会怎么想”[12];得知温特沃斯结束与路易莎的感情纠葛,“安妮垂下眼帘,掩饰她的微笑”[13]。奥斯汀用简单几笔描绘了安妮含蓄、温婉的名门女子的形象。尽管安妮只钟情于温特沃斯,但听到拉塞尔夫人的劝导,让自己与父亲财产的继承人结合,她又显出了犹豫不决,理性再度与感情起了冲突。“她的想象和心灵曾一度受到迷惑。想到她将成为母亲那样的人,想到‘艾略特夫人’的珍贵头衔将是她第一个使之重生,想到她回到凯林奇,再次以之为家,为她永久的家,安妮一时间难以抵御这种想法所具有的魅力。”[14]面对理想的感情与现实的诱惑,安妮表现出了徘徊犹豫。最终还是温特沃斯主动迈出了愈合感情的第一步。由此可见,安妮在这段感情中始终是被动的一方,她处处留意温特沃斯的行为举止,以此来判断他的感情动向。安妮观察得来的判断主导着自己情感的悲喜,这种悲喜又要恰当地掩盖而不至于被周围的人察觉。
安妮与温特沃斯的成功结合是由多种因素促成的。“传统社会强调经济功能的婚姻”[15],以经济功能为基础,再发挥爱情的功用才使得二人的结合顺理成章。婚姻中的经济功能由男性承担,女性则依附于男性。这是女性自主做出婚姻选择的原因。因此安妮才在听说拉塞尔夫人的劝导考虑与艾略特先生结合时产生了犹豫。温特沃斯八年后归来,已经与之前的他完全不同,他“现在拥有两万五千镑财产,他的优点和功绩已使他在海军中获得很高的职位,他不再是小人物了”[16]。正是他积累的财产与翩翩风度,提升了他在安妮家人心中的形象,而安妮只需保持她的忠贞,再加上出身名门的头衔则完全可与之相配。
相较于在爱情中被动等待的安妮,西丽在周围人的帮助下显示出摆脱自己悲惨境地的主动性。这种主动性一步步促使她获得自由,最终取得独立的经济地位,获得了某某先生的尊重。第一个给西丽带来思想冲击的人是儿媳索菲亚。索菲亚明白“在以男人为主的家庭里女孩子很不安全”[17]。如果丈夫有揍自己的念头,索菲亚会先揍死他,即使自己真心爱着对方。索菲亚做了西丽不敢做的事——和自己的丈夫打架,这深深地震动了西丽的神经。此时,反抗的萌芽在西丽的心中已经萌发。这是西丽打破男权的枷锁,确立自己性征的开始。
索菲亚让西丽认识到婚姻关系中,与男性相处的另一种的可能。而真正帮助西丽成长的是莎格。莎格有两点特质使得她带给西丽的影响较索菲亚更大:一是她有独立的事业,通过自身的努力拥有了物质基础;二是她依靠女性独立的精神气质吸引男性。追求自由的莎格在私人情感与社会活动两方面帮助西丽逐步建构起对自己处境的认知。莎格既颠覆了西丽脑海中至高无上的上帝,还帮助她打破了潜意识中父权至上的观念。这一阶段,是西丽实现自我确认的第一步。
莎格帮助西丽明确了自身的性别意识,在身体上成为一位精神解放的女性。西丽摆脱了自我强加的枷锁之后,跟随莎格到了孟菲斯开始新的生活。这是西丽成长的第二步。在孟菲斯,西丽的角色又丰富了一层,她“有了爱,有了工作,有了钱,有了朋友,有了时间。”[18]此时的西丽完成了社会化的转变,她的事业得到了周围人的肯定,甚至成立了自己的裤业公司。“社会化是指使人们获得个性,并学习其所在社会生活方式的个人与社会相互作用的过程,它是联系个人和社会的必要环节”[19],西丽通过裤业公司参与社会生产劳动,与之前在家庭中无性别的劳作工具相比,是一个崭新独立的女性形象。西丽主动追求自己渴望的生活、获得独立的经济地位,这些是比安妮更高层面社会化的显现。
三、女性成长的诗学意义
如果说《劝导》旨在建立女性自己的写作传统,形成“与男性文学传统不沾边却同样不断前行的湍急而强大的潜流”[20],那么《紫颜色》则具有更广阔的视野与格局。沃克的作品显然不甘心做“潜流”,而是旨在建立与男性文学传统并行的“共流”。她从自身的成长经验将女性社会角色的刻画置入性别与种族的双重困境,由此描写女性成为具有独立精神女人的历程。两部作品反映的主题,表现了不同时代女性确立自身社会性别的历程,作品人物反映出的特点与作者所处的社会环境是分不开的。
《劝导》的主人公安妮相较于奥斯汀其他小说中的人物有着进步性,也表现出作者本身对当时女性婚姻观念的思考更加深入。例如,安妮对海军工作的看法与其他人不同。在她眼里,海军的职业比贵族的头衔更值得尊敬,他们不加修饰的真诚行为比虚与委蛇、精雕细琢的绅士举动更为动人。奥斯汀对女主人公婚嫁对象更改,展现出她创作思想的变迁。从让女主人公嫁入稳定的贵族门第,转变到让安妮嫁给一位无门第依靠的海军,这离不开参军兄弟对奥斯汀的影响,“他们常常把军旅生活中的所见所闻告诉简·奥斯汀,她由此深深地感到,贵族和地主阶级的子弟只知道贪图享受。”[21]
其次,安妮十分注重利用阅读打开自己的视野。例如,她与本威克上校一同讨论现代诗歌,并让他多读散文。尽管这一行为,“并非帮她们提升认知和思辨能力”,只是如同“音乐、绘画或说法语等才艺一样,是装饰女性外表的一种手段”[22]。
最后,安妮不再遵循拉塞尔夫人的“理性”劝导,转而追求内心的浪漫爱情,也体现出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理性主义向浪漫主义思潮的转向。但总的来说,在这些以出身名门的女性为主角创作的小说中,不可避免地将女性社会性别的塑造过程局限在家庭范围内。这种局限造成了“男女两性有极为不同的社会经历,两性之间看事情的方法也不尽相同,因此男性和女性从社会生活中得到结论也有差异”[23]。女性在19世纪的社会环境中确立的社会性别是恪守社会规范,在经济、婚姻选择上依附男性的。在这种对女性的社会准则近于严苛的境地下,奥斯汀依旧用笔书写着她的反抗之语,塑造了安妮这位既进步又带有时代烙印的女性形象。
科林斯认为美国黑人女权主义的认识论是学者“自己的设身处地的具体经历才能表达黑人妇女的立场”[24]。例如,沃克的集子《寻找母亲的花园——女性主义散文》(In Search of Our Mothers’ Gardens:Womanist Prose,1983)“凝结了沃克自己作为黑人、女人的亲身经历和她对黑人妇女生活长期细致观察后的理性分析”[25]。她将黑人的女性主义与白人的女权主义区分开来,确立黑人女性自己的话语理论。黑人女性不仅要承受男女之间的性别差异带来的歧视,还要忍受种族间的歧视。因此,西丽社会性别的确立较安妮来说更为艰难。由此可见,黑人女性要确立社会性别首先要克服传统思维中男权统治的观念,以此明确身为女性的独特性征。其次,在种族范围内由边缘走向中心,在以白人中产阶级异性恋妇女为主的女性经验中,为自己的女性经验争得一席之地席,而姐妹情谊是黑人女性争得一席之地的保证。
与《劝导》异性间的爱情不同,《紫颜色》是同性之间的“姐妹之爱”。莎格给西丽的同性之爱,弥补了她对爱的渴望,一步步站起来成为真正的女人。这种姐妹情谊是黑人女性成为“大写的人”的力量源泉。在黑人女性之间扩大自己的生存空间,争取表达权力的自由形成了共同体的共鸣。这些诉求汇聚成的姐妹情谊,使得个体的吁求凝结成集体的力量。
社会性别概念的提出者斯科特(Joan Scott)认为,关于社会性别定义的核心基于下列两个命题的相互关联上:“社会性别是构成社会关系的一种要素,这种社会关系是基于人们认为的两性差异之上的;并且,社会性别是指涉权力关系的基本方式。”[26]也就是说,两性之间的差异是社会关系的组成部分之一,而差异往往对标着社会权力上的不平等。在这种二元相对的逻辑之中,男性始终凌驾于女性之上,这种社会性别结构的形成必然导致男性掌握社会秩序的主导权。安妮与西丽的生活历程表现出她们所处的社会环境中,男性相较于女性在婚姻与社会地位的选择上有更多可以自由施展的空间。这些差异表征着女性将自我价值的实现挂钩于男性或屈从于男性的现实。
从19世纪的白人女性到20世纪的黑人女性,她们都处在父权至上的社会中,都为自己做出了有悖于社会对她们角色的定义的选择。安妮不再听从“理性”的“劝导”,与温特沃斯完美结合;西丽打破性别、种族、阶级的枷锁,拥有的生活空间、家人的爱、艾伯特的尊重,成为精神独立、经济自主的女性。社会性别将原本局限在性别理论内的文学批评扩展到种族、阶级,将这三者作为文本分析的综合理论架构,为文本解读提供了新思路。
参考文献:
[1]马新国主编.西方文论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623.
[2]罗贤娴.弗朗斯丝·伯尼与简·奥斯汀小说女性观比较研究[D].北京外国语大学,2021:71.
[3]佟新.社会性别研究导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3.
[4]佟新.社会性别研究导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4.
[5]佟新.社会性别研究导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54.
[6]简·奥斯汀.劝导[M].裘因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27.
[7]简·奥斯汀.劝导[M].裘因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6.
[8]林文琛.《劝导》简论[J].外国文学评论,2000,(1):112-118.
[9]王逢振.西方文论选[M].桂林:漓江出版社,2004:111.
[10]艾丽斯·沃克.紫颜色[M].陶洁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8:18.
[11]佟新.社会性别研究导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97.
[12]简·奥斯汀.劝导[M].裘因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61.
[13]简·奥斯汀.劝导[M].裘因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118.
[14]简·奥斯汀.劝导[M].裘因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173.
[15]佟新.社会性别研究导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124.
[16]简·奥斯汀.劝导[M].裘因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272.
[17]简·奥斯汀.劝导[M].裘因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30.
[18]简·奥斯汀.劝导[M].裘因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147.
[19]简·奥斯汀.劝导[M].裘因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52.
[20]朱立元.当代西方文艺理论[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347.
[21]裘因.从《劝导》看简·奥斯汀创作思想的发展[J].复旦学报,1992,(1):50-54.
[22]罗贤娴.弗朗斯丝·伯尼与简·奥斯汀小说女性观比较研究[D].北京外国语大学,2021:36.
[23]佟新.社会性别研究导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248.
[24]佟新.社会性别研究导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249.
[25]嵇敏.美国黑人女权主义批评概观[J].外国文学研究,2000,(4):59-63.
[26]Joan Wallach Scott.Gender:A Useful Category of History Analysis[J].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1986,(5):1053-1075.
作者简介:
庄静,山东青岛人,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中国文化研究院,2021级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