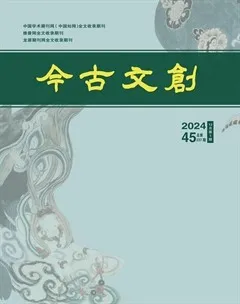《菽园杂记》的文学价值及史料价值探析
【摘要】陆容的《菽园杂记》号称“明代说部第一”,是明初具有代表性的一篇文人笔记。本文整理剖析《菽园杂记》的史料价值和文学价值,归纳出其价值体现的具体模块与领域方向,并总结出《菽园杂记》中的明初文人笔记书写特征,进一步彰显其史料及文学研究价值。
【关键词】《菽园杂记》;文学价值;史料价值;文人笔记
【中图分类号】I26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4)45-0016-04
【DOI】10.20024/j.cnki.CN42-1911/I.2024.45.004
《菽园杂记》是明代陆容创作的一部文人笔记。它历史底蕴深厚、文化价值丰富、内容形式广泛,着重讲述了明初以来当朝军事、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的体制改革,以及著名学者的轶事和生活。明史专家谢国桢认为,明代笔记小说,往往此因彼袭,抄撮成说,只陆深所著《俨山外集》和这部书,可取的地方较多。[2]但目前国内学者们对其的关注度不高,议论不够全面。《菽园杂记》存在其独特的史料价值和文学价值。可以通过对其文学及史料价值的归纳简述,窥得其创作特点及文人笔记书写特征,补足明初文学史料研究、文人笔记研究的空缺之处。
一、陆容与《菽园杂记》
(一)生平经历
陆容,字文量,号式斋,生于明英宗正统元年(1436),卒于孝宗弘治九年(1494),江苏太仓人。陆容于南直隶苏州府太仓(今江苏苏州)出生。他的祖先因为嫁给了徐家,就以徐姓为自己姓,故其于进士登第榜上姓徐,后又恢复了原姓陆。他的外祖父名叫陆福,与爷爷陆继宗皆不仕。其父陆裕,母为陈氏。陆容从小接受优秀的家教。其父陆裕虽不仕,但具有较高的文化修养。耳濡目染,陆容作诗之才在九岁时便显现,十六岁步入县学以后更为刻苦,经常废寝忘食攻读儒家典籍。即使在做官的时候也依旧手不释卷,曾亲手勘录万余册藏书。同辈人都不理解他的学习方式,他却说道:“只不过是与你们玩耍的时间相抵罢了。”其少时与张泰、陆釴二人关系非比寻常,三人俱以文行于乡,被称为“娄东三凤”。尽管陆容诗才不如另二人,但是其致力于学习经史百家之长,典礼、兵刑、漕运、水利工程等方面就没有他不精通的,因此以博闻多识闻名于世。
陆容成化二年(1466)进士及第后入仕,不久之后就被授予南京吏部验封司主事的职位。成化七年父亲去世,他为父守孝回到太仓老家,后相继担任兵部职外司、武库司员外郎、职方郎中、武选司和浙江布政司右参政。他当政时清正廉明,性情秉直磊落,深谋远虑,刚正不阿,常常直谏,不讳犯谏。在兵部任职期间,陆容在处理公务方面异常辛勤,边防急报三四日后就能上疏,基本都是几千字以上。他还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纠正了当时政府滥用权力、高官权贵欺骗和伤害人民的事情。据《太仓县志》记载,曾有百户韦瑛逮捕了十多名百姓在都城起诉造反,陆容连夜上章至工部尚书为民请命,希望能由招法司推究,韦瑛才终于对诬告百姓的罪名供认不讳。
(二)性格特点
陆容的此种个性让他屡受谗言,仕途维艰。弘治初,他直言上疏为朝廷不悦,被任为浙江布政司右参政。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中写道:“复条奏两浙不便者八事,后以‘浮议’罢归”。当时听闻这件事的人都非常吃惊,为仕者议论纷纷,但陆容却泰然处之,与众老赋诗告别。程敏政因此感慨“士独求无愧于己”。陆容罢官后亲筑“成趣庵”“独笑亭”“菽园”,于其中著书休憩,远离庙堂,直至弘治七年七月病逝。
陆容平日为人虽不喜言笑,以礼待人,但与人相处时却平易近人,能够与人交谈甚欢。且他极为好学,家中藏书甚广,除《菽园杂记》外,还著有《式斋集》三十八卷、《太仓志》和《水利集》等书,都具有不可替代的文学价值和史料价值。读书报国的思想使得他不论入仕还是出仕之时都手不释卷。他不论是做京官还是游宦各地,都在过程中时刻关注民生民情、朝野新闻、世间百态,同时随看随记,很多都写出了他的即时感受。得益于此,每每遇到新的情况、有了不一样的心得,也很容易找出之前的记录进行比较论述。从陆容的著述笔记中,不难看出他在不懈地思考一条经国济世之通途,而《菽园杂记》更是他人生见解及国政观点之大成。他在《菽园杂记》中批判现实现象,品评政治人物,阐发经义见解,其中的很多观点都独树一帜,并在学术方面已经超出了当时士人之见。但在字里行间也依旧存在着程朱理学的价值观模式,“理”与封建伦理道德观念依旧密不可分,十分认同并高度评价廉洁清正之官、高风亮节之士和忠烈道义之人,而旗帜鲜明地对势利无耻之徒、狡诈阴滑之辈和社会阴暗面进行无情辛辣地批判和讽刺。虽然如此,他也能在行文中跳出封建礼教腐朽之处,将目光放在那些在人世间苦苦挣扎以求存的下层人物上,在某些方面上认同他们,给予不具有色眼镜的评论。在这里,“礼不下庶人”被给予了全新解答,陆容对于贫农、风尘女、工商业从业者、江湖暴客“胡子老官”乃至黄巢也都会在深度剖析之后给予一定程度的人格肯定。这些都是他“观人不囿于其类”处事原则的鲜明体现。
二、《菽园杂记》的史料价值
陆容生活在明初时期,明初文化政策、政治高度专制,宦官专权现象出现,后至明中期文化专制的慢慢崩塌和瓦解,都可以在其笔记中找到缩影。故《四库全书提要》称《菽园杂记》“于明代朝野故实,叙述颇详,多可与史相参证;旁及谈谐杂事,皆并列简编”[6]。这非常准确地说明了其内涵与性质。书中所讲述的历史典故和文章都能看到作者别具一格的理解,并且不会避讳上位之人甚至皇帝的事迹,大胆叙述并发表观点。
(一)多样全面的历史人物及事件类型,完善历史人物形象
《菽园杂记》中所讲述的历史典故和文章都能看到作者别具一格的分析方式。书中记载了皇帝、名臣轶事的条目约有90条,可补正史之不足,并大胆直言,不为尊者讳。在很多条目中都能看到他对当朝皇帝执政的公允评价和对统治阶级的独到见解,较为真实生动。如卷七第26条中记载道,施纯以“照例”两字换掉“是”字,深得帝心,至此际遇恒隆。陆容将众人对此事的评价记录入册:“两字得尚书,何用万言书。”此类庙堂杂事于正式史料记载中难以寻迹,而在杂记中得以一窥,能从细微处完善当时的国政见解、官场风云。
我们也可以从本书中窥见明代一些文人名士的生活痕迹。全书提到名字者近百人,有见诗文或史迹者近70人,如李贤、叶盛、白圭、周文襄、于谦等。而他们的相关趣闻轶事在正史中却不见得记录,从《菽园杂记》中可以丰满这些历史人物的形象,从事件中看出他们的为人和性格,从而对他们的理解研究不再片面死板,多角度来归纳人物。如关于汤允绩之死正史并无所载,而《菽园杂记》卷五中记载他被一箭穿喉而死。通过本书我们可以更详细地了解某些影响较小的文士为人处事方式及生平记录,能够窥见更多当时人物的历史风貌,作用于当代的史实研究及史貌还原上,其史料价值不可小觑。
(二)真实详尽的明初政治制度及社会风貌记述,补正史之缺漏
《菽园杂记》对于当时的政治制度和社会风貌具有非常详尽的叙述。如卷一中对《御试录》《进士登科录》等进行了概述;卷七中,有对陕西驻军之所的详尽记述;卷九有对成化以前,明朝巡抚总督的具体岗位设置、官阶和驻守方式进行记录;卷十一中对军中旧制军职子女抚恤安排进行了记述。
明代没有专职的史官,《菽园杂记》第十四卷中分析了史官与翰林二者合二为一“官名虽异,然皆不分职”其实是一种弊端。在本书中也能够阅读到关于当时重大历史事件的记述、民间神话传说、庙堂之上的为宦为官之风、各地的银课以及盐运记载等等,此间种种都与明代社会风貌、地理环境息息相关,成为不可多得的文献资料,能够很好地填补《明史》未及之处,且明代人记述明代事,既近水楼台先得月,可信度又高。
(三)丰富的物产资源及生产方式考证依据,支撑明代自然人文生态研究
作者对于当时一些动植物进行了记载,也介绍了很多当时手工商业的制作和生产特色,这是对当时社会生产力水平非常直观真实的反映,也深切地反映了当时劳动人们的生活状态。明代采矿、造纸业有着一定发展,文中也有着对此类活动的描述。如卷十三中记载明代衢州常山、开化等县造纸的过程:
其造法:采楮皮蒸过,擘去粗质,糁石灰,浸渍三宿,蹂之使熟。去灰,又浸水七日,复蒸之。濯去泥沙,曝晒经旬,舂烂,水漂,入胡桃藤等药,以竹丝帘承之。俟其凝结,掀置白上,以火干之。白者,以砖板制为案卓状,圬以石灰,而厝火其下也。[1]
这段不仅对造纸所需的原料进行了介绍,而且简略完整地叙述了造纸的过程,是研究明代造纸技术及水平、造纸术的发展过程很好的史料。在卷十二中,也有着对农具设备的记载,并介绍了严州山中使用水轮灌溉田地的技术。人们对于更高效、自动化的生产工具的需求也越来越迫切,因此推动了相关技术的不断发展和创新。[8]
卷十四中也对五金之矿的开采、青瓷的质地和制作方法、韶粉的用途及使用方法以及采铜法和香蕈做了详细记述,最后又说道以上五条于《龙泉县志》中引用:作者不仅严谨地标明了文段引用来源,而且表达了自己的观点,并为“蕈”字做了文献考证,此字由土音之讹而来,并在《广韵》中查有此字,为我们史料和文献学的研究提供了思路和依据。
三、《菽园杂记》的文学价值
(一)作为相关文学著作成书参考依据,拓宽文学经典考证思路
对于《水浒传》的成书时间,很长一段时间学界共同认为是元末明初,然而《菽园杂记》卷十四中一段对叶子戏的记载,却让这个认同在史料记载的面前发生了动摇。“叶子戏”是一种大众娱乐,它具有大众性、时代性,紧跟潮流,吐故纳新,与具有独立性、选择性的文学作品来讲,更适合考察成书时间。[3]陆容写道,斗叶子戏,好多城市上到士大夫下到孩童百姓都会玩。他游历许多学校八年之久,唯独不理解叶子戏玩法,最近了解到它的形制,并对叶子戏的玩法进行了介绍。陆容在文段中描述了叶子上绘制的二十位水浒英雄后,对叶子戏进行了评论:有人说赌博中能赢了别人的都是强者,因此叶子戏谋取的都是才力绝伦的人,但陆容认为并不是这样。宋江等人可能都是大盗,具体可以参见《宣和遗事》及《癸辛杂识》。他认为写这本书的人,大概是想说赌博就像盗贼掠夺的恶行一样,以此来警示世人,但人们却被利益所迷惑,自身不能领悟罢了。而将叶子戏记录在此,是希望后人能明晓此事并自重。其中说道:“盖宋江等皆大盗,详见《宣和遗事》及《癸辛杂识》。”[1]可见陆容当时对于《水浒传》可谓是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由此似可证明《水浒传》在弘治七年,也就是陆容离世前尚未成书一说的可能性。
(二)关注市井人物及民风民情,具有现代主义人文色彩
陆容也记录了不少社会中下层小人物的故事,这也是《菽园杂记》的难能可贵之处。尽管受到当时生活阶层影响,对许多贫困地区缺乏过多笔墨的描绘,但在本文中仍有大批明代市民、低阶官吏,以及尚未考取功名的普通读书人存在。他在文中偏向于现实事件及人物的记录,一味讲述鬼神故事少之又少,即使出现也是为了衬托人生百态和道德教化,志人大于志怪。此部分对于明代文学研究具有重要价值。
如卷七中陆容讲述了武人陈五阻止家中女巫信仰的故事,此则故事中陈五运用计策动摇了家中对女巫的信仰,体现了小市民阶级的智慧,也侧面反映出陆容对巫蛊之术的态度,他的关注点主要在于人身上,关注现实中的众生百态,而不是虚无缥缈的鬼神之说。
还有一些官方历史上不为人知的低级官员和布衣文人。如卷十二中汝州学正王琦“提督学校,士风为之丕变”,他为官时虽然“以清介自持,在官门无私谒,平生不治生产”,最后却贫病交加而死。他也在卷二和卷十二中记述了太仓未有学校时,“吾乡文事之盛,有自来矣”的原因是有海宁寺僧人和布衣沈玙为学生讲解四书五经。勾勒出明初文人群像,通过小人物事件的情感表达,给予读者世俗化反馈。
明初受宋明理学影响还颇为严重,理学家们认为鬼神也要对其进行格物穷理的剖析,儒家也在弘扬“博物”之价值。然而后来对于“博”“约”的认识已然渐渐分化,“博物”的价值被空前拔高。陆容在这样的社会大环境下,对于志怪部分的关注度不多,所作文章也都是着眼于现实,不会志怪语怪去寄托个人抱负或是影射社会,而是从民生民情的讲述来体现人文关怀。尽管他的主要目标就是弘扬道德,或是警示后人,但是把那些在中国社会历史大发展、大事件中默默无闻的小人物都记录了出来,还是使陆容的文人笔记作品富有了现代人文主义色彩,是明代启蒙思潮萌芽的体现。
(三)多样的语言民俗记录与分析,为语言学及民俗词汇的考证和收录提供相关素材
《菽园杂记》在语言学与民俗文化方面也有很详尽的记述与分析。因为太仓是陆容的故乡,所以文中有他对故乡附近的方言民俗很多记录与个人进行典籍考辨后的见解。如太仓未建有学校之前,是邑中海宁寺、淮云寺的僧人进行的“四书”等儒家典籍的启蒙教育,第一卷也记载了吴中的俗讳:如将舟行讳“住”,讳“翻”,以“箸”为“快儿”,“幡布”为“抹布”等。从中可以发现当时吴方言的一些语音特点。从中古音韵来看,“住”为虞韵澄母去声,“箸”为鱼韵澄母去声,两者同音,这说明当时老百姓所说的吴方言,鱼韵和虞韵已不分。[5]
此外,还有很多民俗语汇出现。《菽园杂记》民俗语汇的演变,亦遵循着“语随俗变”的规律,且“语”和“俗”二者的变化,具有同步性,即该书的某些民俗语汇,随着具体民俗活动的消失,亦不再被当代人在实际的语言环境中运用,而是进入了历史词汇、语汇的行列。[4]杂糅当地方言语音的官职称谓、“川字、画卦、斜插花”等在社会上广为流传的消遣放松方式、“释菜礼”学子祭祀先圣先师的典礼历史词汇等等,在语言学和民俗学方面都有其独特的思考价值。
(四)分析《菽园杂记》的创作模式,从而归纳明初文人笔记的写作特征
1.文体自由的写作方式
在近代西方文体概念传入中国以前,传统文人很少像刘勰的《文心雕龙》那样对文体进行严格的定义或总结文体特征,撰写系统的文论,他们做得更多的是大量的创作实践或对经典作品的模拟。[7]《菽园杂记》的写作方法是相对随意的,作者一般没有明确官方的写作目的,通常是随听随写,或是有文意灵感和写作兴致后随笔写就。同时作者也不必担忧其他人的眼光和评价。如卷十二中由农业知识灌田之法降暑到冯妇搏虎,又讲姓氏字音、水母碑篆、后又记叙金焦二山名字由来、清风岭王节妇、温州乐清县学三贤祠……笔记记述顺序和内容完全随心而动,没有任何的规律性和分类可言。可见文人笔记作者对于所写内容体制没有很结构性和严谨性的心理设想。
从文体学的视角分析,笔记的来源与中国史学传统以及古体小说发展有关。从广义上讲,它是指散文和非正式的作品,它的主题也很广泛。受古今相承小说发展观点的影响,在我国传统文体类型中笔记并没有作为一个单独类别。所以笔录也可称为随笔、杂识、漫录、笔谈等,涉及的领域也没有明确规范,因此历史文化、地理环境、社会经济等皆有涉猎,或泛泛而谈,或针对某一方面大篇幅论述。也就是说,文人笔记因其文体性质,具有较大的创作自由。
2.议论丰富有感而发
《菽园杂记》中陆容对事件或史籍的观点评论内容丰富,观点独特。他在对各地百姓民生的考察中,也不乏自身态度立场的议论和抒发。陆容入仕26年(1466-1492),他的生活时代跨越了正统、景泰、天顺、成化、弘治五朝。他做过吏部和兵部的京职,居官多年曾多次奉命出使四方、按部境内很多地方。他每每官职调动出任一地,都会关注明初建朝以来的民生民情还有南北之间不同的风俗差异,事事亲力亲为、手自笔录。在弥补相关史料文献记载不足之处的同时,也能从他丰富繁多的议论中窥见他的立场见解。吏治腐败之象,大都生于毫末。如卷三中记载“满朝升保傅,一部两尚书。侍郎都御史,多似柳穿鱼”(《菽园杂记》卷三)。卷六记载成化年间,鸿胪少卿施纯彦善体上意,以献“照例”两字竟得尚书,擢太子少保,“两字得尚书,何用万言书”(《菽园杂记》卷六)。[6]都是在讥讽代宗、宪宗时期对朝政的懈怠,对宦官也是藐视讥讽的态度。
在弥补相关史料文献记载不足之处的同时,也能从他丰富繁多的议论中窥见他的立场见解,从而归纳出其文学性特征。明初文人文学素养积累较高,并乐于结交志同道合之友,使得他们对人、对事、对经史典籍都有着独到丰富的见解。更有人在朝廷为官,对于官场弊端嗤之以鼻,有着不同于现世的政治理念。
3.精简叙述与详尽描写相结合的写作特色
陆容在对事件的记述中详略得当,熟悉的、感兴趣的,或者个人经历进行详尽描述,占据很大的篇章,而对于不认同或者不重要的事件会一笔带过,简明扼要地阐述自己的观点即转至下一话题。
如卷十二中简略记述了河南湖广的“炙树”习俗:树木衰老即将死去,用沸水浇灌它们,让它们被普遍沾润,就又恢复了繁茂之态,这被称作炙树。用水浇灌竹林,因此竹子不会衰败。而又在介绍雁荡山之时极尽描写之能:
山下有东西二谷,东谷有剪刀峰、瀑布泉,颇奇,大龙湫在其上。西谷有常云峰,在马鞍岭之东,展旗、石屏、天柱、玉女、卓笔诸峰,皆奇峭耸直,高插天半,而不沾寸土。其北最高且大,横亘数十里,石理如涌浪,名平霞嶂。灵岩寺在诸峰巑岏中。于此独立四顾,心目惊悸,清气砭骨,似非人世,令人眷恋裴回,不忍舍去。回视西湖飞来峰等峰,便觉尘俗无余韵矣。[1]
这段文字中对雁荡山下东西二谷进行了介绍,运用比喻描写平霞嶂中“石理如浪”,又写人独立在山中的感受,并与西湖飞来峰进行对比,侧面衬托出雁荡山景色的清绝超凡。
卷十二中也对浙江银课情况进行了详尽记载,按照年号时间顺序,每一年都列出详细数字,增加了条目的真实性;后又对“投壶”活动进行了详尽的规则和类型介绍,可见作者对于朝事关注度之高,也十分乐于进行文人雅士之间盛行的娱乐活动。
这种精简叙述与详尽描写相结合的写作特色,也是文人笔记写作的重要特点之一。它使笔记的结构性更加合理,更能体现作者的写作态度,彰显了一呼一吸、一张一弛之间的生态美。
四、结语
陆容的《菽园杂记》中繁多的历史人物事件和当时社会风貌记述以及生产方式描绘等都可以作为史料文献研究参考,也可以作为相关文学作品考证依据和语言学民俗学探究素材。从该笔记文体创作自由、议论观点丰富、叙述与描写相结合的写作方式中也可窥见明初文人笔记的部分典型特征。在关注到皇帝名臣、文人雅士轶事的同时,还能记录下社会中下层小人物的生活趣闻与民间故事,体现了难能可贵的人文情怀。
参考文献:
[1]上海古籍出版社编.明代笔记小说大观[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2]戴小珏.陆容《菽园杂记》研究[D].华东师范大学,
2010.
[3]王齐洲,王丽娟.从《菽园杂记》、《叶子谱》所记“叶子戏”看《水浒传》成书时间[J].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03):37-46.
[4]黎燕.《菽园杂记》民俗语汇演变与民俗文化变迁[J].文化学刊,2012,(04):99-101.
[5]唐七元.试谈《菽园杂记》的方言学价值[J].西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31(04):50-54.
[6]陈麟德.《菽园杂记》与兴化[J].江苏地方志,2016,
(03):60-62.
[7]马兴波.论笔记文体的“杂”与“同”——以明代笔记为例[J].平顶山学院学报,2022,37(06):34-41.
[8]姚登程.《菽园杂记》及其中的科技史料[J].台州学院学报,2024,46(04):7-11+33.
作者简介:
陈香宇,女,辽宁沈阳人,云南师范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