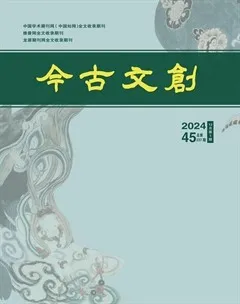从多重感官看《西游补》的“幻梦” 与“关心”
【摘要】《西游补》给大多数读者的第一印象是“幻”,读者在阅读时会有游历在梦中的感觉。本文将从感官的角度分析《西游补》中梦境塑造的独特之处,并在此基础上探讨《西游补》中梦的塑造与主人公破情根、悟道根的隐秘关联,揭示“正心”在其中的关键作用及其现实的映射。
【关键词】《西游补》;五色五感;梦境;情根
【中图分类号】I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4)45-0004-04
【DOI】10.20024/j.cnki.CN42-1911/I.2024.45.001
一、引言
人往往是动用感官来感受认知世界的,即使身处梦境之中也是如此。佛教中有五根五境的说法,日常生活中所说的五感在佛教中是由眼、耳、鼻、舌、身五根所幻生出的“色声香味触”五种感觉对象。《西游补》是一部关乎梦境的小说,其中自然也不乏造梦者感官的使用。在第十三回中,孙悟空在饮虹楼见小月王与唐僧听三个弹词女子唱曲,于是取了金箍棒,跳上楼前乱打,但总是打空,其余人都看不见听不见他,于是大怪,道:“老孙做梦呀!还是青青世界中人,都是无眼无耳无舌的呢?” ①这句话正是体现了这三种感官在孙悟空梦境中发挥的作用。而其中的舌根味觉主要体现在梦中人物除了要寻驱山铎和师父的下落外,还独独心系吃茶一事,其余并没有明确提及凭借味觉来感知梦境的地方,因此便略过不谈。
而董说在《西游补》问答中又有这样的补充:“情之魔人,无形无声,不识不知,或从悲惨而入,或从逸乐而入,或一念疑摇而入,或从所见闻而入。” ②在这句话中作者首先说明了情是无形无声、不识不知的,但走入情魔却有可能是因为意念的犹疑或所见所闻。即小说中孙悟空梦的构设,虽并非是真的情却又是关乎心关乎情的。孙悟空历情劫,是心动、染着的过程,也是迷情、悟情的过程,许多对外物的描写最终都归回并指向人物的内心。因此,本文将从梦境的营造和孙悟空幻梦中的内心变化两个角度来探讨“梦”与“情”的关系,并将其纳入更广阔的社会语境揭示其现实的映射。
二、“梦境”的营造
在阅读《西游补》时首先带给读者的是“目艳”之感,读者的眼睛像是在看一个万花筒,梦境世界的色彩绚丽得令人眩晕。从第一回唐僧的百家衣再至第十五回的五色旗乱,整部小说由颜色开始又以颜色结束。而《西游补》中对外界颜色和事物的描写采用了大量而无节制的铺陈,光是在唐僧百家衣处的描写就罗列出了25种颜色,而之后在万镜楼中对镜子的花式也罗列了27种,另外对绿袍判官、黄巾判官、红须判官、白肚判官、玄面判官各式判官衣着的尽数陈列足以见得作者用何等铺洒的笔墨和书写的耐心来描绘梦中色彩的绚烂以及场景的繁复。一般来说,过度的铺陈和平摊式描写往往会让行文变得笨重凝滞,但是作者采用了走马观花式的呈现方式,虽然能分出这些事物的类别却仍看不出明显的个性,作者很少让人物将目光聚焦在某一处,端详凝视它,而是在精致繁密的屏风中游走,最后只留下了最深刻的瞬时印象即颜色。这些被铺陈的事物没有细节,人物虽在其中却少有驻足停留,体现出了梦流动的、无序的特质。
同样给人感官上冲击的是梦中的奇观,梦的诡谲在于它异于现实世界。《西游补》中的梦境世界重叠繁复,它有着区别于三维现实世界的时空观。《西游补》全书共分十六回,描写了三层梦境:第一层,新唐;第二层,青青世界;第三层,万镜楼。而万镜楼中又有头风世界、古人世界、未来世界和蒙瞳世界。梦境世界是多维的且嵌套的,从一个时空可以跌落到另一个时空,镜子、水池、暗洞都可以成为进入另一个时空的入口。而在这多重维度的时空之中,还有许多如真假新唐的出现、一群人浮在空中凿天等让人难以辨识的、充满末世感的场面。这些陌生的时空限度和与现实生活经验相背离的奇观,给人以梦境的难以琢磨。
再次是奇闻。奇闻是指孙悟空入情后听到的来自梦境的声音,这些声音既包括“引路人”的转述,也包括项羽说的平话和弹词女子唱的弹词和新戏。首先值得注意的是孙悟空入梦后有两个主要的任务,一是寻找驱山铎,二是寻找师父的下落。他作为梦境的闯入者,往往是在何处撞见了什么场景或在何处打听到了什么消息才会引发下一步的动作,如孙悟空在新唐世界时听到新天子诏玄奘作杀青大将军、在扫地宫人处听说了有“驱山铎”这一法宝的存在,在凿天人那处知晓凿天之事的缘由以及唐僧也在青青世界的消息,又在万镜楼遇到刘伯钦得知万镜楼台乃小月王所造之物等。每遇到一位引路人,他便对这个世界有多一分的把握。这说明听觉也是孙悟空把握这个幻境的重要方式。但大多数引路人的出现就像阿拉丁神灯一样,只能出现一次解答一个疑惑(甚至只是半个),继而便像一阵青烟般消失,不再在故事中出现,而人物的行踪始终是如梦般向前流动,不可回溯的。
在这些引路人的口中,包括弹词女人唱的弹词和新戏中,孙悟空的身份也在不断地被颠覆,充满了不确定性和荒诞性。孙悟空身份的颠覆是多层次的。首先在入梦前期孙悟空的法术失效,不能再帮他唤起土地爷,也不能使他的猴毛分身,齐天大圣成了一个平庸的凡人,神圣的光环就此祛魅。而在梦境中人的口中,孙悟空不仅变成了“杀人如草,西方一带,杀做飞红血路”的杀人魔头,还做了丞相有了妻子和儿子。孙悟空自身也穷尽变换:化身虞美人、代做阎王继而又自称“悟幻”。再加之孙悟空还在梦中遇到了六耳猕猴与老去的自己,更使得孙悟空的身世和“真我”显得扑朔迷离。此外,孙悟空听见弹词中正在唱孙悟空自己昨日在万镜楼之事,在叙事上形成了一个嵌套结构,将现实与虚构的界限模糊了,而弹词内容在孙悟空梦境中则反映出梦里梦外、虚实间的不可把握。
三、情根与心猿
那么作者是怎么说明情和心的关系的呢?在佛教中,眼根、耳根唯取不至境,被称为离中知;鼻根、舌根、身根三者唯取至境,被称为合中知。也就是说,若只是通过眼睛和耳朵来认知外界,我们与外界本来就存在着间隔。而梦中眼花缭乱的幻象与扑朔迷离的奇闻,更是让人物感受到了这个梦境世界的虚幻以及不可靠,也对自我的身份产生了疑惑和不安,而显然借写梦境之虚幻来凸显情关乎心的主题正是作者着意之处。我们认知外界,从而在内心中做出真假、善恶、是非的判断。当我们对外界产生怀疑失去把握的时候,如在梦境世界时,比起梦境,在梦中表现出的心理状态反而显得更为真实可靠,由此种种外物的幻象在不同程度上都指向了人物的心理和意志,也就说明了情难无关幻境只是关心。
孙悟空在梦境世界中常表现出惊骇、焦躁、愁闷等不安的心理状态,这正是由于无法与外界建立起可靠的联系而产生的。如孙悟空看见新唐世界之时,难辨真假,不断思量,一共转念五次也未有定论,展现出百念交攻、六神无主的状态。而每愈入情,孙悟空焦躁之心愈重;走出情魔时,心境则渐明,此时外界的变化对左右他的心已没有太大的关系了。在考虑情与心的关系时,我们同样选择红色这样一个在梦境中极具视觉冲击力的颜色来加以阐述。
正如学者赵红娟所言,《西游补》中出现的颜色并非只是自然色相,而是具有文化意蕴和内涵的象征与暗示。特别是“青”与“红”两个颜色,学者认为“青”和“红”是生命力旺盛和情感欲望强烈的象征。③
首先三一道人评语:“情天每从色界入”,而最能象征色界的莫过于艳丽的颜色,以牡丹红入情,是以“色莫艳于红”,因而引之。红色的出现,最先是在师徒二人争辩牡丹花红不红的段落。“牡丹不红,徒弟心红”与《传习录》中“你未看此花时,此花与汝心同归于寂;你来看此花时,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便知此花不在你的心外” ④一句似有映照。未见牡丹时,牡丹应与心同在寂静中;而看到牡丹时,因为心动了有了着,所以花的颜色便明白了起来,呈现出艳丽的红色。而后文万镜楼中将行者绑住的红线和孙悟空棒打鲭鱼精变成的小和尚时,“小和尚忽然变作鲭鱼尸首,口中放出红光”,皆能说明“红”是对情的象征,文本中红色的出现关乎心动关乎入情,与行者的心理状态有着密切的联系。
除此之外,红色的出现也为梦境营造出了血腥诡谲的氛围,象征着外界对人物施加的无明的骚动。越鲜艳的事物往往越危险,在这个绮梦之中,有一层压抑的底色。作者在《西游补》中塑造的孙悟空形象是嗜血的。红色在文本中除了作为情欲的象征出现,在其他时候往往都与打斗场面和流血相关。《西游补》作为一部神魔小说,以降妖除魔为主旨,出现打斗或斗法的场景似乎是在情理之中的,但《西游补》作为《西游记》的续书,在降魔环节的描写上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西游记》中孙悟空与猪八戒和牛魔王大战的场面一直为人称道,下面以孙悟空与牛魔王的打斗为例:
狠得他爆躁如雷,掣铁棒,劈头便打,那魔王就使扇子搧他一下,不知那大圣先前变蟭蟟虫入罗刹女腹中之时,将定风丹噙在口里,不觉的咽下肚里,所以五脏皆牢,皮骨皆固,凭他怎么搧,再也搧他不动。牛王慌了,把宝贝丢入口中,双手轮剑就砍。那两个在那半空中这一场好杀:齐天孙大圣,混世泼牛王,只为芭蕉扇,相逢各骋强。粗心大圣将人骗,大胆牛王把扇诓。这一个,金箍棒起无情义;那一个,双刃青锋有智量。大圣施威喷彩雾,牛王放泼吐毫光。齐斗勇,两不良,咬牙锉齿气昂昂……⑤
这大圣收了金箍棒,捻诀念咒,摇身一变,变作一个海东青,飕的一翅,钻在云眼里,倒飞下来,落在天鹅身上,抱住颈项嗛眼。那牛王也知是孙行者变化,急忙抖抖翅,变作一只黄鹰,返来嗛海东青。行者又变作一个乌凤,专一赶黄鹰。牛王识得,又变作一只白鹤,长唳一声,向南飞去。行者立定,抖抖翎毛,又变作一只丹凤,高鸣一声。(《西游记》61回猪八戒助力败魔王 孙行者三调芭蕉扇》) ⑥
以上的选段是孙悟空和牛魔王因争夺芭蕉扇而引起的争斗,在第一段中可以看出整个打斗过程充满了细节的刻画,孙悟空与牛魔王在争斗时有关双方的攻势守势、心理状态、使用的兵器、做出的动作的描写十分的自然流畅,生动惊险。包括后面穿插的作者对这场打斗的评价,同样是以活泼调侃的笔调来写的。第二段中展现了孙悟空与牛魔王的神通广大与变化无穷,以精彩的变形和想象让读者觉得意趣盎然。在阅读这些打斗场面时,读者的感官很容易被本就声势浩大的场面所引起的刺激感和新鲜感占据,再加之以作者信手拈来的笔调,即使段落中出现“搧”“砍”等动词,也并不觉得血腥暴力。
而在《西游补》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打斗杀戮场面有:孙悟空打杀一干春男女、孙悟空借项羽之刀斩下真虞美人的头、孙悟空兼职阎王爷审判秦桧以及最后两军的混战。在这些情节中,孙悟空的形象不再是神通广大的,也不再是以慈悲为怀的,梦境世界的孙悟空在凿天人口中成了“杀人如草,西方一带,杀做飞红血路”的杀人魔头。在《西游补》中的打斗也更像凡世的杀戮,以孙悟空假冒虞美人教唆项羽斩杀真虞美人为例:
项羽听罢,左手提刀,右手把戟,大喊一声:“杀他!”跳下阁来,一径奔到花阴榻上,斩了虞美人之头,血淋淋抛在荷花池内。⑦
此中虞美人只是个弱女子,自然不需凭借什么高超的神力就能将她命葬黄泉,但是作者以堪称白描的方式描绘了一幅极具冲击力的画面,以冷静的笔调叙述一场血淋淋的杀戮。这个过程中孙悟空的行为也表现得十分耐人寻味,先是化作假虞美人教唆项羽杀了真虞美人,继而又扮起疯魔模样要黄衣道士退妖,最后又自己好了起来,道:“我如今甚清爽,饮酒去罢。”若起初孙悟空因心中焦躁打杀一干春男女后,因滥杀无辜,害了不妖精、不强盗的男女长幼五十人,不觉涕流眼外,尚还称得上心存仁慈的话,此时的孙悟空似乎已经走火入魔到了最深。
再言孙悟空兼职阎王爷审秦桧一案,秦桧是偷宋贼,孙悟空在阴府中对秦桧用尽了酷刑,先是以六百万只绣花针刺遍全身,又叫小鬼掌嘴,再将秦桧拉上小刀山、碓成细粉变成百万蚂蚁,又将他滚油海,拆开两翼作蜻蜓模样。再以铁鞭、锯子、铁泰山处置,施以如剐刑这般极残忍的刑罚,却将模糊的血肉称为“桃花红粉水”,将剐刑的种类称为“鱼鳞样”“冰纹样”“雪花样”,最后将秦桧化作一杯血酒让小鬼喝了。作者将杀戮细化到各式各样的肢体上的折磨,以游戏戏谑的方式将丑陋残酷的东西写得具有美感,带给读者一种血腥可怖之感。
这些情节中弥漫着的血腥气味,并没有在作者戏谑的笔墨下完全消解。但因为在这个过程中,孙悟空是以“报仇雪恨,尊正诛邪”为由,以惩恶扬善的判官身份来主持这场正义的审判,对欺君叛国、罪行罄竹难书的秦桧的千刀万剐便给读者带来了一种极为快意的道德获得感,从而也使孙悟空在此中表现出的残酷快意合理化了。
两处同样是血腥杀戮的场面,审判秦桧较之前者甚至更为血腥残酷,我们无法在表面上解释这两场血腥的杀戮行为究竟有何不同,但在虞美人处是坠魔而在审判秦桧处是断情正念,前者意在妒情争宠,后者意在惩恶扬善,正是因为孙悟空的意念发生了变化。由此观之,作者对梦境的种种书写正是依托梦境之虚幻,来展现人物的感官情绪虽受外界变化的影响,但最为核心的还是人物内心的染着,围困孙悟空的并非是梦魇而是心魔。
四、现实之“镜”
关于《西游补》与原著《西游记》的关系,学界一直存在着两种看法,一种是续书说,一种是独立说。续书说的依据主要建立在作者的创作意图和内容情节之上。《西游补》在书名和序言里都传递出了这本书是《西游》补缺之作,可以说为《西游记》写续书本就是董说的创作意图之一。而学者赵红娟则是从《西游补》对《西游记》内容的萦带、主题的继承、情节构思的关联等角度抽丝剥茧了《西游补》与原著《西游记》的内在关系,尤其指出《西游补》对《西游记》中所蕴含的佛教“明心见性”与儒家心学“求放心”思想的继承。⑧另一种看法则认为《西游补》只是借用了《西游记》中的人物情节为引,而内容旨趣实则已经脱离了原著,展现出强烈的现实隐喻特性,从而成了一部独立完整的作品。
然而,即使《西游记》中的孙悟空也经历了“心猿归正”的过程,两部作品中的孙悟空形象以及风格氛围却全然不同。后者轻松戏谑,读起来趣味盎然、异彩纷呈,而《西游补》却在纷繁的梦境中传递出无名的焦虑和残酷的冷意。正如前面提及的两个杀戮画面,同样两场血腥杀戮,为何在虞美人前是坠魔,而在审判秦桧之处是断情正念?为何红色在《西游补》中除了“情”的隐喻还在行文之间传递出一种血腥的暗示?这些问题一方面揭示了《西游补》对“学问之道无它,求其放心而已”的心学主旨继承,另一方面却为读者留下了超出梦境世界之外的疑问。《西游补》中的无名焦虑究竟从何而来?作者又为何会安排孙行者审判反贼秦桧?显然,这已不是游历在梦中的孙行者能回答的问题,而唯有深入到作者所处的社会环境和内心世界才能探知。
公元1644年在中国历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明朝的终结和清朝的入主都发生在这一年。而《西游补》成书约在崇祯十三年(1640年),正值明清两朝更迭,明朝大厦将倾不远。明朝北方皇太极觊觎中原不断进犯,而朝廷贪污腐败现象愈演愈烈,各党派之间的斗争此起彼伏,民族兴亡、家国兴衰、人生哀乐在个时间段剧烈地显化。面对内忧外患、世风愈下的明朝社会,《西游补》可以说是作为亡国目击者的董说痛苦、愤懑、无奈情绪的痛快宣泄,展露出一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压抑氛围。黄人在其《小说小话》中认为《西游补》是董说“身丁陆沉之祸,不得已遁为诡诞,借孙悟空以自写其生平之历史”。⑨孙行者其实就是董行者,孙悟空在梦中展现出的焦躁、烦闷的状态也是董说基于时局的情感体验,董说正是借孙行者在梦中的一番游历来展现自我的内心。梦中荒诞诡异的奇观奇闻奇景,也如明镜一般映射出作者在“易代”之际焦虑而寄身空幻的人生况味。
传统的忠君传统与爱国精神往往是一体两面的,面对天下之变,君臣父子相失而永诀,明朝文人遗民普遍有着至恨至痛之情,这一点在《西游补》之中也有具体的体现。第二回里孙行者见绿锦旗上写着“大唐新天子太宗三十八代孙中兴皇帝”暗道一月换一个皇帝,是在用只管在“眠仙阁”与倾国夫人风流快活的醉天子来讥讽明末的统治者。董说写到这里,感叹道:“到如今,宫殿去了,美人去了,皇帝去了”,三个“去了”恻然可思;而入镜中世界是对科举制的讽刺,“纱帽文章”暗讽天下文士胸中无物只为升官做呆板文章。古人世界的秦始皇,今人世界的项羽,未来世界审判恶人秦桧,帝王将相轮番登场,孙行者在这梦中梦、楼中楼、镜中镜中体验着“思梦”“噩梦”与“惧梦”,实则是作者借眼前之景和行者内心之种种感受寄托自身的政治理想和向往。
因此,对卖国求荣的秦桧施以酷刑因为他欺君叛国,对大英雄岳飞的赞颂实际上流露的是董说强烈的民族意识和对民族悲剧命运痛苦的预感。而再回过头来谈红色,所谓“牡丹不红,徒弟心红”,其实心乎朱赤者,不只是大圣,更是董说。董说借扫地宫人之口说出的“天子庶人,同归无有;皇妃村女,共化青尘!”既是作者对强弩之末的时局生出的强烈幻灭之感,也是作者对摇摇欲坠的山河袒露的无限的痛惜与无奈。
五、结语
《西游补》中与血色相关的打斗共有四处,自孙悟空打杀春男女至五色旗乱洒下的荔枝血色,这种猩红诡异的压抑感贯穿在整个故事中。孙悟空因见到牡丹花红多生出了一个意头动了情念、生了妄想,由此更入情中;而在化身虞美人时入情魔最深;再至化身阎王审秦桧时断情正念,心智渐明;再至五色旗乱、满地荔枝红血,孙悟空在打斗中被虚空主人喊住终悟幻境之空。从绚丽的颜色、诡谲的奇景再到似真似幻的奇闻,梦境混乱而虚幻,而孙悟空却经历了从无主无张到逐渐有了主张再至最后奋力反抗的过程。梦境是虚是幻,而唯有正心才是悟道出情的不二法门。由此观之,作者的梦境书写正是依托梦境之虚幻,来讲魔是心魔,而情只关心,而这也从潜意识层面映射出了作者的现实焦虑以及在家国之业上有所作为的渴望。
注释:
①(清)董说:《西游补》,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53页。
②(清)董说:《西游补》,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1页。
③赵红娟:《补天石·镜子·颜色——试论〈西游补〉与〈红楼梦〉的象征意象》,《浙江学刊》2013年第3期,第91-98页。
④(明)王阳明:《传习录》,北京时代华文书局2014年版,第233页。
⑤(明)吴承恩:《西游记》,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3年版,595页。
⑥(明)吴承恩:《西游记》,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3年版,第598-599页。
⑦(清)董说:《西游补》,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25页。
⑧赵红娟:《〈西游补〉与〈西游记〉关系新探》,《浙江学刊》2006年第4期,第96-100页。
⑨朱一玄、刘毓忱:《〈西游记〉资料汇编》,中州书画社1983年版,第328页。
参考文献:
[1](清)董说.西游补[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2](明)吴承恩.西游记[M].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2.
[3](明)王阳明.传习录[M].北京:时代华文书局,2014.
[4]朱一玄,刘毓忱.《西游记》资料汇编[M].郑州:中州书画社,1983.
[5]化萌钰. 《西游补》的“无名焦虑”与梦境书写初探[J].中国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35(05):83-88.
[6]蒋寅.遗民与贰臣:易代之际士人的生存或文化抉择——以明清之际为中心[J].社会科学论坛,2011,(09):26-
37.
[7]孔定芳.明清易代与明遗民的心理氛围[J].历史档案,2004,(04):47-56.
[8]苏兴,苏铁戈. 《西游补》中破情根与立道根剖析[J].北方论丛,1998,(06):50-55.
[9]王为民.对于《西游记》的一种阐释:《西游补》与《西游记》关系[J].明清小说研究,2001,(01):195-201.
[10]赵红娟.《西游补》与《西游记》关系新探[J].浙江学刊,2006,(04):96-100.
[11]赵红娟.补天石·镜子·颜色——试论《西游补》与《红楼梦》的象征意象[J].浙江学刊,2013,(03):91-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