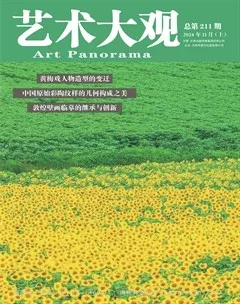论倪瓒画学思想之辩证性
摘要:倪瓒作为中国绘画史的代表人物之一,他的画学思想在中国绘画理论的发展历史中占有重要地位。“逸气”“逸笔草草”“不求形似”等观点是其画学思想的主要内容。在这些观点的影响下,人们会产生一种误解,即将倪瓒的画学思想直接与单纯的不求形似相等同。本文以《云林画谱》为切入点,从另一个角度分析倪瓒画学思想的真实面貌,进而梳理出倪瓒画学思想的辩证性。
关键词:《云林画谱》;倪瓒;画学思想
一、倪瓒画学思想概述
作为“元四家”之一的倪瓒,是元代绘画乃至整个中国传统绘画发展历史进程中的一位笔墨色彩相当浓重的代表人物。这种浓重的笔墨不仅仅体现在他流传数量最多的绘画作品上,还体现在其复杂玄妙的画学思想上。
之所以将其画学思想归纳为“复杂玄妙”,是因为在将其画学思想仔细梳理之后,会发现倪瓒的主要绘画思想与理论圭臬主要体现在其两个主要文本之中,一是其所著文集——《清閟阁全集》,其多见之于各种史论研究著作中的画学观点均主要出自该作,其中就涵盖了其著名的“逸气说”“逸笔草草,不求形似”以及“聊以自娱耳”等观点。这些观点也构建起了倪瓒在整个中国传统绘画理论发展嬗变过程中的基本形象,基于此,倪瓒也无法避免地成为元画发展中“高逸”风格的集大成者。二是所著《故宫书画录》第六卷中的《云林画谱》,其中表现出了“另类”的思想。严格意义上说,与专门收录个人诗文画跋的文集性质的《清閟阁全集》不同,《云林画谱》只是作者提供给后人临摹习画的范本,在每一个学习专题中,充斥着作者对于研习绘画的一些文字论述,这些文字论述体现出了倪瓒的另一绘画思想。全画谱先后有九段文字论述,都是以对应的画面范本为切入点,用精练的语言将学习绘画时对于树木、竹石形象塑造的技法以及所需要遵循的模式进行高度概括。其中不乏一些科学的绘画观,如对树叶与枝干的描画,倪瓒在文本中明确提出“随景斟酌”“春则墨叶浓而稠,夏则密而郁,秋则疏,冬则落”等观点,深入解析这些观点的内涵,即要求在描绘树木的枝叶时,必须科学地将季节时令之于树木枝叶形态的影响考虑在内,进而使画作符合自然规律。而这种在作画时必须遵循的自然法则规律,在倪瓒看来就可以归纳为一个概念——“画理”。所谓画理即可视作绘画时所要遵循之圭臬法则,而谈及法则,谢赫的“六法”便会浮现于眼前。倪瓒在《云林画谱》中所提及的“随景斟酌”,应该正是与“六法”中的“应物象形”与“随类赋彩”相和。似乎为了从反面去论证这样的观点,倪瓒在《云林画谱》中针对“画树许尺,山不满尺”这一类在绘画布局层面出现的乱象做了批判。由此,将《云林画谱》中的九段论述通览一遍后,就不难发现倪瓒作为职业画家对于画理的“较真”态度,细细咀嚼这种态度之后,就会明白倪瓒又在践行中国古代画理中另外一则亘古不变的法则——“外师造化”,将尊重大自然客观规律作为习画的必要前提,认真做到笔笔皆在理,同时告诫后人,对于规律的掌握方式需要灵活且警惕机械式的照搬照套。在尊重客观规律的同时,对于主体经验性的重视显得格外重要,“耕当问奴,织当问婢”就是对之前理论的重要补充,实际上,倪瓒已经触及中国绘画理论发展的两面性与矛盾性、客观规律与主观经验之间的冲突性,让倪瓒在自我画学思想体系的构建过程中显得格外独特。这种独特性就体现在重视画理的理性思维模式与其之前所提及的“逸笔草草”“不求形似”的天马行空之间产生了巨大的冲突。
那么,该如何去理解两个文本之间这些充满矛盾性的观点?倪瓒画学思想该如何去正确解读?
二、矛盾中的统一
首先必须从倪瓒画学思想中争议最大的“不求形似”切入,大部分对其思想理解的误区都集中在此。借用黄纯尧先生的话,倪瓒“把形似和抒胸中逸气对立起来……绘画的目的仅仅在于自娱……把形似抛弃,是芦是竹都不管。这些不正确的地方为后世某些文人画家带来不良影响[1]。”这种不良的影响时至今日仍然存在。清人王原祁就曾在《麓合画跋》中说:“学画至云林,用不著一点工力,有意无意之间,与古人气韵相为合撰而已。至设色更深一层,不在取色,而在取气。点染精神,皆借用地。推而至于利家,当必精光四射,磅礴于心手,其实与着意不着意处同一得力。学者无过用其心,亦无误用其心,庶几近之[2]。”这固然在强调学习倪瓒时需要注意气韵的营造与笔外的无意之意境,但也从另外一个角度概括了很多人在学习倪瓒绘画时的一种状态。
绘画对于“工力”的要求很高,所谓“工力”即绘画之功力,是对于绘画基础技能熟练程度的要求,其中包括笔法墨法、设色法、构图法等方面。所有习画之人均需在不断的创作实践积累之下,将所谓“工力”不断地进行量变,然后在此基础之上通过自身的天赋、才思或者灵感进而达到质变,从而能够在“能妙神逸”的境界里不断攀登。而所谓基础性“工力”,尤其是对于初学者而言,一言以蔽之——达到形似,也就是画谱中所说的要先要掌握“画理”。而这个观点的背后隐藏着的就是艺术创作过程中在充分尊重自然规律及充分发挥自我主观能动性的双要素下,经过无数次创作实践的磨炼积累的规律。
倪瓒的一句“不求形似,聊以自娱耳”为这种牢不可破的模式带来了极大的冲击,绘画的基础可以不建立在把握外在物象的形似上了,是芦是麻都可以“岂复较其似与非”。那么在画面中所出现的物象是否与现实中相符已经可以忽视了,这无疑将绘画学习的门槛大大地降低了,甚至可以“用不着一点工力”。
基于这个问题,首先需要梳理一下关于“不求形似”这一观点的发展历程。从中国绘画理论的发展来看,“不求形似”并非倪瓒最先提出来的,这个观点的雏形应追溯到北宋时期苏轼在《书鄢陵王主簿所画折枝》二首之一中所说的:
“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赋诗必此诗,定知非诗人。诗画本一律,天工与清新。边鸾雀写生,赵昌花传神。何如此两幅,疏淡含精匀。谁言一点红,解寄无边春[1]。”
全诗中的“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与“诗画本一律,天工与清新”两句成为苏轼画学思想的核心部分,在画论史上基本被视为文人画思想的开山之言。其中就认为绘画如果以追求形似作为唯一目的,无异于孩童般幼稚可笑。由此可见这时已经将“追求形似”在文人画中的地位大致确立了下来。
文人画发展真正的高潮时期则为元代,基于苏轼的观点,元人赵孟頫继续对这一观点做了更为深度的阐述,并正式将“不求形似”作为明确的画学思想观点公布于众。在元人汤垕的《画鉴》中就有详细的记载:
“……子昂尝题云:唐人善画马者甚众,而曹(曹霸)、韩(韩幹)为之最,盖其命意高古,不求形似,所以出众之右耳[3]。”
汤垕在记录赵孟頫观点的同时,自己也在书中阐述道:
“今之人看画,多取形似,不知古人以形似为末。即如李伯时画人物,吴道子后一人而已,犹不免于形似之失。盖其妙处在笔法、气韵、神采,形似末也。东坡先生有诗云:‘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赋诗必此诗,定知非诗人。’仆平生不惟得看画法于此诗,至于作诗之法,亦由此悟[1]。”
在赵孟頫与汤垕看来,当书画艺术发展至元代,文人画已经成为一种完全独立于其他绘画体裁的存在,其美学价值似乎更高,而所谓的“不求形似”则成为区分文人画与其他绘画体裁的一条重要美学标准。
纵观倪瓒创作的一生,在绘画之道上可以说是深受赵孟頫的影响,特别是在绘画思想上,当赵孟頫明确将“不求形似”总结为衡量文人画审美标准的重要标尺后,倪瓒也进而将其作为自我画学思想体系中重要的核心部分,并且在赵孟頫的论述基础上提出“不求形似”的观点。除了《答张仲藻书》重申了“不求形似”的观点之外,明人沈颢的《画塵》中还有这样的记载:“一日在灯下作竹树,傲然自得,晓超展观,全不似竹。迂笑曰:‘全不似处,不易到耳。’[4]”
从此处就可以看出,倪瓒对于赵孟頫观点的继承绝非简单的机械式照搬,而是存在着自我咀嚼后的飞跃:将“不求形似”延伸到了“全不似”,这一点可以视作倪瓒在赵孟頫绘画思想的基础上进一步将不求形似的追求推向更高的美学定位。
总结以上诸人的各种观点,不难看出,“不求形似”的观点发展到最后将“似”与“不似”两个相互对立矛盾的概念高度统一了起来,并最终成为界定文人画的一个重要标准。
三、倪瓒画学思想的实践
纵观倪瓒一生的绘画实践创作过程,重视写生和追求形似始终是他所关注的基本环节。特别在其绘画创作早期,他曾在《清閟阁全集》的诗文中这样说道:“我初学挥染,见物皆画似。郊行及城游,物物归画笥。”(《清閟阁全集》卷二)所谓“见物皆画似”与“物物归画笥”就是在阐明形似与写生的重要性,尤其是对于初学者来说,这就更好地解释了为什么倪瓒会在《云林画谱》一开篇就提出“若专讲士气,非初学入门之道也”,正是因为倪瓒在“我初学挥染”的阶段的切身体会与心得。
虽然倪瓒到了晚年又写出了“写图以闲咏,不在象与声”(《清閟阁全集》卷二),但同时更加强调了“若草草点染,遗其骊黄北牡之形象,则又非所以为图之意[5]”(《清閟阁全集》卷十),“下笔能形萧散趣,要须胸次有篔簹”(《清閟阁全集》卷八)[5]。
篔簹,即大竹子,这一诗句就是在强调,准确把握住客观事物的特征对于追求“萧散”的逸笔来说是多么重要,同时鲜明地将倪瓒那种既追求胸中逸气,又坚持把握形似的观点阐述得淋漓尽致,进而揭开了正确理解“不求形似”观点的真正途径。
文人画追求“不求形似”的真正目的不在于忽视形似的重要性,而是将目光放在了隐藏在形似背后的神似之上,而这种“目光”,可以理解为艺术创作的终极目标与追求。倪瓒所强调的并非单纯的再现,而是将心血更加投注于深层次的“表现”之上。
倪瓒的“逸气”说也是以这个思想为核心,虽然从表面上来看,该观点产生歧义的可能性非常大。但如果将《云林画谱》中所涉及的画学观点进行参照,这种介入就及时地补充了倪瓒自身画学观点的科学性,并进而使其更加丰满且更具辩证性。
在《云林画谱》中,倪瓒就树、石、竹的具体形象的画法都提出了遵循客观事物规律的要求:“布置时自当夹杂,亦要随景斟酌,春则墨叶浓而稠,夏则密而郁,秋则疏,冬则落。”
“若近山则当写残山半壁,庶几相称,此半壁而以远山相佐者地。”“石脚可写小石为佐,随地坡广窄为之,用墨浓淡正反寓焉。”
从绘画教育的角度去看,倪瓒的这些要求均是从细节入手,将所描绘之客观事物形象的准确性、画面整体的逻辑性与构图的合理性都提高到近似于法则的高度。而这些环节总结起来就是在追求形似方面的具体要求,从而使得绘画的研习成为“可操作”“可总结”“可实现”的科学过程。在这一点上,倪瓒的绘画风格体现出明确的现实主义。
而所谓的“士气”“逸气”或者“不求形似”,现在看来是倪瓒画学思想的一个层面,一个与追求形似共存的层面。准确理解它们是需要设立某一种前提的,即这些思想主要是针对文人画高层次的美学要求,对于初学者并不值得提倡,倪瓒在当时必然也关注到了这一点,因此其在《画谱》中及时向初学者抛出了不可“专讲士气”的告诫。
四、结束语
进一步通过对《云林画谱》以及《清閟阁全集》这两个文本中的观点进行对比分析后,不难看出,从本质上讲两个文本中所涉及的观点并不是对立的,它们分别是两个层面的不同深度的阐述,是统一在倪瓒“逸气”学说的整体结构之中的,可以理解为对于绘画不同阶段提出的不同主张。再结合对于倪瓒不同时期的具体作品风格的分析,文章得出在提倡“不求形似”的“逸气”学说背后,形似这个概念始终没有被忽视。而《云林画谱》中观点的出现正是印证了这一点。
“下笔能形萧散趣,要须胸次有篔簹。”这句诗,不仅是对《云林画谱》最好的概括,也可以视作倪瓒整体绘画思想体系最好的注脚。在大量绘画实践的锤炼下,用遒劲的笔触描绘出具有丰富意境和人文气息的画面来,这就是倪瓒绘画思想的全貌。
参考文献:
[1]周积寅.中国画论辑要(增订本)[M].南京:江苏凤凰美术出版社,2019.
[2]沈子丞.历代画论名著汇编[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2.
[3]周积寅.周积寅美术文集[M].南昌:江西美术出版社,1998.
[4]俞剑华.中国古代画论类编[M].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1998.
[5]陈高华.元代画家史料汇编[M].杭州:杭州出版社,2004.
基金项目:2022年江苏高校“青蓝工程”资助“2022年江苏高校‘青蓝工程’中青年学术带头人培养对象”(项目编号:苏教师函[2022]29号)。
作者简介:杜江(1982-),男,山东潍坊人,硕士研究生,副教授,从事艺术理论、艺术教育、美术史论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