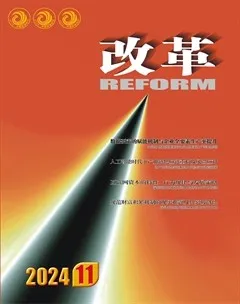互联网资本的特性、行为规律与发展策略
摘 要:互联网资本及平台企业作为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核心主体,是推动先进生产要素向发展新质生产力集聚的关键力量。从性质看,互联网资本是极富创造力和黏合力的新兴资本要素,是带有网络外部性、兼具技术垄断和自然垄断属性的社会先行资本。从行为看,互联网资本通过投资开发互联网关键硬件和软件并创建数字堆栈,成为数据资源采掘和经济创新变革的主导力量,同时通过对前沿技术和数据资源的掌控而形成平台垄断,具有较强的全球流动性与跨界扩张倾向。一方面,互联网资本适应新的生产社会化需求,驱动数智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共享模式创新和治理现代化,为新质生产力发展及人类福祉增进注入创新动能、制度势能和治理效能;但另一方面也可能导致资本无序扩张并引发垄断侵权、数字鸿沟乃至数字安全和意识形态风险,侵蚀高质量发展与共同富裕的经济基础和安全保障。为此,应处理好互联网资本发展与规范的关系,既要充分发挥互联网资本的创新引领功能,又要构建互联网资本健康发展新秩序,加快形成数智经济发展新格局。
关键词:互联网资本;平台经济;新质生产力
中图分类号:F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543(2024)11-0084-16
世界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与我国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构建新发展格局、推进高质量发展实现历史性交汇。生产力的进步必然要求生产关系的调整,表现为新兴资本形态与组织类型不断涌现,并呈现性质不断融合、主体更加多元、跨国流动加快等特征。以互联网“大厂”和数字平台为组织形态的互联网资本在重构国际创新版图、重塑世界经济结构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提出,“健全相关规则和政策,加快形成同新质生产力更相适应的生产关系,促进各类先进生产要素向发展新质生产力集聚,大幅提升全要素生产率”。互联网资本及平台企业作为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创新行为主体,是推动先进优质生产要素向发展新质生产力集聚配置的关键力量。
互联网资本是随着互联网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而出现的一种新型资本形态,它以互联网关键技术革命性突破和产业化运用为前提,以数据要素采掘和创新性配置为基础,以数字平台创建和运营为核心标志,通过提供数字商品或互联网科技服务而获得增值和盈利,其特点是创新,本质是科技资本。互联网资本的诞生是生产力发展的结果,生产力的发展要求社会生产和经济关系在更高水平上实现互联和协调,互联网资本突破实体空间束缚,满足了更高水平社会化生产的要求。互联网资本作为数智经济发展的核心要素和主导力量,为科技创新、产业升级、治理现代化、民生福祉提升作出了较大贡献,也产生了诸如无序扩张、垄断侵权、数字鸿沟、数字安全等问题、风险和隐患,对高质量发展、共同富裕乃至国家安全产生了一些消极作用。依法支持和引导互联网资本健康发展,既要发挥其积极作用,又要控制其消极影响,对于我国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以及形成与之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构建新发展格局、构筑国家竞争新优势具有重要意义。
促进互联网资本健康发展,须从理论上厘清这一新型资本的特性与行为规律。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强新的时代条件下资本理论研究。用科学理论指导实践,促进各类资本良性发展、共同发展,发挥其发展生产力、创造社会财富、增进人民福祉的作用[1]。只有科学认识互联网资本的特性与作用,把握其行为规律和发展趋势,才能明确这类资本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功能定位,制定最优发展策略,使之成为促进先进生产要素向发展新质生产力集聚的纽带。
目前,学术界针对互联网资本的理论研究相对较少。邱泽奇等[2]从资产市场化视角,将互联网资本界定为既往投入形成的、具有互联网市场进入机会并可以通过互联网市场获益的资产,且在互联网资本框架下考察了互联网红利差异的来源和机制。相关文献更多的是基于数字资本或平台资本的概念,进行数字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批判[3-4],而较少涉及这类资本的创新特征、行为规律和经济功效。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资本的本质是生产关系,同时体现为生产要素等各种具体形态,也称为“资本一般”和“许多资本”[5]。“资本一般”对应的是资本的本质特征,而“许多资本”则对应于各种资本形态在竞争、积累等方面的具体特性。互联网资本既具备一般资本的本质属性和矛盾关系,同时,作为一种特定资本形态,又体现了生产力进步的新要求。而且,在新的生产力条件下,其运行规律和矛盾关系都呈现新的特征。本文以互联网资本这一特殊资本形态为研究对象,基于全球视角探究互联网资本的特性和行为规律,审视其经济社会效应,提出促进互联网资本健康发展的策略。
一、互联网资本的特性
(一)互联网资本是一种极具创新性、创造活力和黏合力的资本要素
从经济性质看,互联网资本作为一种极具创新性、创造活力和黏合力的资本要素,将货币资本与知识、技术、数据等具有高科技属性的资源要素,以及劳动、土地等传统要素进行集聚融合、集成配置,成为重组要素资源及技术经济形态、重构组织模式和市场规则、重塑经济结构和产业方向、改变竞争格局和治理方式的新兴要素力量,是生产社会化趋势在更高水平上的集中表现。
互联网资本和工商金融资本一样,本质上都是作为生产要素的资本。资本是市场配置资源的工具、经济发展的方式和手段,是促进各类要素集聚配置的关键纽带、生产力发展的主体力量。马克思指出,货币资本是“每一个新开办的企业的第一推动力和持续的动力”,是“发动整个(生产)过程的第一推动力”[6]393,“各种生产要素的总和从一开始就表现为生产资本,因而生产过程本身也表现为产业资本的生产职能”[6]94。新古典增长理论将资本形成和技术创新作为驱动增长的关键因素,资本和科技、人力、自然资源构成经济发展“四大要素之轮”[7]580。
互联网资本又是一种特殊的资本要素。相较于工商业资本和金融资本,互联网资本与知识、人力资本以及信息技术、数据要素的结合更为紧密,具有鲜明的高科技属性和“亲数据”特性。在货币资本形态上,互联网资本投资于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领域;在生产资本形态上,互联网资本购买、配置、利用乃至创造的资产是互联网关键软硬件、数据要素、数智科技及相关人力资本;在商品资本形态上,互联网资本主导生产和交易的产品是数据商品、数字基础设施及数字财富。互联网资本作为创新要素集聚配置的纽带,在生产领域主导了数据资源要素化和数据要素市场化,推动市场主体融合与组织模式的重构、数字基础设施的建设、平台经济的兴起以及数字产业集群和国家竞争新优势的构筑;在分配领域重塑了规模经济、范围经济、共享经济范畴及商业逻辑,将劳动、知识、技术、数据要素有机纳入“线上线下”价值创造与收益共享体系,重构了知识和数据参与分配、影响共富的机制,促进科技、人才等创新要素的价值释放;在治理领域驱动了国家治理在技术、组织结构、运行机制上的现代化。
(二)互联网资本是一种具有网络外部性的新兴社会先行资本
从功能属性看,互联网资本作为一种新兴的社会先行资本(social overhead capital),通过投资创建数字平台这一新型基础设施,为产业数字化转型、国民经济循环提供数据要素和数智科技支撑,在追求商业目标的同时成为新质生产力培育和高质量发展的核心资本动能。互联网资本作为社会先行资本的属性,是生产力发展社会化趋势的体现,使其可以获得相较于传统先行资本而言更大的市场影响力。
互联网资本首先是社会先行资本的一种具体类型。社会先行资本致力于为市场经济发展、私人资本经营、产业部门运行提供必要的基础设施和经济架构,包括旨在促进商业和贸易的前期工程投资,如公路、灌溉和饮水工程以及公众医疗保健事业等。这些大型基建投资呈现块状化,具有不可分割、规模收益递增属性,常因外部经济或溢出效应而难以实施广泛的商业收费操作,需要政府介入以保证这些基建投资的可持续进行。20世纪后半叶发生信息技术革命后,计算机、互联网等软硬件技术创新催生了以信息通信系统为代表的新型基础设施类型和形态。互联网资本通过投资创建数字平台为数字经济和新兴产业发展提供了包含数据要素、互联网软硬件服务等在内的新型基础设施支撑。萨缪尔森和诺德豪斯指出,计算机和信息高速公路的兴起对21世纪所起的作用,如同当年铁路和公路一样,不仅提高了全社会生产力,而且提供了整个新兴产业赖以兴起的基础设施[7]558。
互联网资本又是一种新兴的具有网络外部性的社会先行资本。互联网资本主导的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具有网络外部性,即项目收益或效率取决于使用人数的规模和密度。传统先行资本投资创建的是道路、水利、公用事业以及商场、金融平台、科技孵化器等物理实体平台,而互联网资本投资创建的是一种新型基础设施载体,即数字平台。具体而言,互联网资本通过对关键软硬件的商业开发控制以及大数据积累和商业化,创造了数字堆栈(digital stack)这一新型基础设施和空间网络,控制了可发掘数据资源和引领变革创新的基础设施力量。有别于带有公共产品属性的传统基建平台,具有网络外部性的数字平台突破了因外部经济而难以收费营利的公益属性局限,不再依赖于政府投资或公有资本发起,而更多地由私人互联网资本创办或投资运营。事实上,全球数字平台几乎都是由私人资本创建的。比如,美国的基础设施力量即获取和调配社会资源、发起和利用技术创新的能力,越来越多地由私人互联网资本开发,并由数字平台掌控[8]。
(三)互联网资本是一种兼具技术垄断和自然垄断属性的新型垄断资本
从组织形态看,互联网资本作为一种新型垄断资本,通过对大数据的积累和垄断以及对数字平台基建力量的掌控,对工商业资本进行渗透和控制。互联网资本的垄断性扩张是私人商业逻辑运行的结果,将对政府监管和国家安全形成挑战。
互联网资本是一种垄断资本。垄断资本是随着生产和资本集中,为获取高额垄断利润而对某些部门的生产和市场实施独占或控制的资本,包括工业垄断资本、商业垄断资本、银行垄断资本等形态。银行垄断资本和工业垄断资本相互融合或渗透,产生了诸如金融资本等复合型垄断资本形态,金融资本或金融寡头通过信贷、股权或人事结合,控制了银行与工商业企业,并通过资本输出、国际垄断联盟等方式向全球扩张[9]。相较于金融资本基于信贷或股权的垄断方式,互联网资本更多地是通过对数据资源的垄断,对关键互联网技术及数字平台基建力量的掌控,从资金、技术和供应链上控制工商业资本乃至国民经济,并寻求全球性扩张。
互联网资本又是一种新型垄断资本,它通过发起和主导关键互联网技术创新以及数字平台创建强化垄断优势,因而带有技术垄断、数据垄断和自然垄断(数字基础设施的网络外部性)的复合属性。私人互联网资本为全球数字堆栈中软硬件基础设施的设计和建设提供资金,从而获取商业利益和全球投资回报[10],由此形成的数字平台通过对“实时云存储”中大数据积累的垄断来行使数字基础设施权力[11]。这种基于互联网技术创新及数字基础设施权力掌控的垄断优势产生于既有监管体制忽略的外围空间。一方面,数字平台在形成之初因其“颠覆性创新”属性而得以规避国内外监管;另一方面,私人互联网资本对数据资源的积累和掌控强化了数字平台的创新领导地位,使之有能力挑战主权国家在国家安全领域的垄断地位。在互联网资本主导的数智经济领域,人工智能、物联网、大数据和云存储可带来巨大的网络经济效应及社会回报,这种经济效应及回报使国家减少了对数字平台安全监管的考虑和行动[7]。
二、互联网资本的创新行为
互联网资本既是科技创新的结果,又是新技术条件下科技创新的新动能,其创建的数字平台通过提供数据、科技等要素以及基建服务,推动了数字时代的产业创新和新质生产力发展。互联网资本具有底层创新、平台垄断、虚拟主权型扩张等行为倾向和特征。
(一)互联网资本发起的创新是一种底层性的数智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
资本的逐利动机推动其通过创新获得竞争优势和超额利润。资本“必须变革劳动过程的技术条件和社会条件,从而变革生产方式本身,以提高劳动生产力”[12]366,现代工业的技术基础是革命的,“通过机器、化学过程和其他方法,使工人的职能和劳动过程的社会结合不断地随着生产的技术基础发生变革”[12]560,“大工业则把科学作为一种独立的生产能力与劳动分离开来,并迫使它为资本服务”[12]418。作为科技资本和工业资本的结合,互联网资本有强烈的创新冲动和独特的创新行为逻辑,它主导的是一种底层性技术创新和基础设施再造,即通过互联网关键技术革命性突破,驱动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和生产力质变,催生新产业、新基建和新模式的兴起。互联网资本通过对关键软件和硬件进行商业开发,以及对数字平台提取、分发大数据能力的投资,发挥数字资源采掘与创新变革引领的功能,构建数字经济关键基础设施,并创造出新的网络空间和虚拟领土。这种关键基础设施的内核是数字堆栈,数字堆栈黏性“全面重塑了在无主网络中的经济交换条件”,而这种对无主网络的“物质化和合法化”在传统市场中是不可能实现的[13]50。互联网资本通过开发“增强现实”“虚拟现实”、可穿戴设备等沉浸式技术系统,使居民和消费者参与式地融入数字堆栈空间网络的万物互联(IoE)、人工智能(AI)和大数据的融合结构,从而借助公众数据信息的直观投放、人工智能辅助的人机交互,以及加密安全的信息和数字支付,创造了新的网络空间和虚拟领土并将之不断拓展[14]。当前,谷歌、亚马逊、微软、Meta等互联网巨头携手OpenAI 等科技新势力,主导全球人工智能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推动人工智能向生成式乃至通用方向进行创新突破,培育出涵盖基础层(芯片、数据服务和计算平台)、技术层(算法、通用技术)和应用层(解决方案、产品)的AI产业链。
(二)互联网资本主导了全球数智经济的技术创新、基础设施建设和商业变革
互联网资本为全球互联网硬件的研发制造以及大数据的快速积累、存储和实时性商业提取或商品化提供资金,从而通过投资开发互联网硬件科技和数据资源,掌握采掘社会数字资源的权力。全球范围的数字堆栈等关键基础设施及其资源采掘权基本都是由私人互联网资本开发和掌控的,后者在数字堆栈的人机界面,以及地理空间陆地、海底和太空领域的各个层面创建并部署商业上可行的数字软硬件[8]。以美国为例,自20世纪80年代起,从美国在线公司(AOL)、远景公司(Altavista)到谷歌、Meta、苹果和亚马逊,私人互联网资本通过对数字堆栈的创建和控制获得了美国数字经济领域的创新主导权和平台控制力[15]。进入21世纪后,美国政府在引领技术创新和国民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减弱,过去由政府掌握的采掘和支配资源的权力,以及传输命令和控制信息的手段越来越多地由私人商业平台掌握或共享[16]。互联网资本致力于创建和升级数GEbjpYg2NkpFVeSAy/TgsgGhJVP4DqLSSNN8NePUIpQ=字平台,热衷于为前沿技术创新及商业化应用提供资金。如美国私人互联网资本对初创企业的支持,以及互联网数字平台对大型商业研究预算的承诺远远超过了美国政府的支持及承诺,甚至在国防和安全领域也出现了这种迹象。在一些互联网和数智经济关键技术领域,美国政府在很大程度上放弃了发起、赞助技术创新的兴趣和努力。
(三)私人互联网资本与政府形成创新协同,成为国家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
私人互联网资本通过投资创建数字平台,为科技创新和产业变革提供“孵化器”和基础设施支撑。从技术路径看,私人互联网资本通过创建虚拟空间为数字平台行使创新性质的基础设施权力开辟了新前景。若将互联网资本发挥科技基础设施影响力与美国政府在历史上发挥基础设施影响力的方式进行比较,可发现前者的独特性在于其通过开发软硬件创造了数字堆栈,开辟了新的虚拟领土、数字平台,获得了本该由政府行使的创新支配权[17]。依托数字堆栈,数字平台通过算法以及大数据商业化操作对参与者的思想和行为进行管理,形成不受政府监管或控制的“虚拟主权”,并在数字景观虚拟领土上获得一种“准主权”,行使先前限定为国家特权的基础设施权力[8]。政府和互联网资本对数智基础设施权力的获取和行使并非“零和游戏”,公共权力和私人权力网络是动态的、流动的,私人资本追求技术创新并获取新型基础设施权力的行为有时是在国家支持或默许下发生的[18]。如硅谷互联网技术创新最初受益于国家财政支持,美国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和国家科学基金会为谷歌公司提供了援助[19]。但此后,数字经济利润丰厚的商业模式吸引了大量私人互联网资本进入数字平台开发和应用领域,国家作为孵化器和受益客户的角色在淡化,而私人互联网资本取代国家主导的新兴数字技术资金,成为数智科技创新和产业变革的主要资本[8]。互联网资本商业创新与国家基础设施权力运行不是二元对立的,数字平台行使基础设施权力并不意味着国家创新能力下降。在数字时代,美国企业的权力和利润愈发受到这种共生关系的保障,过去由政府主导的军民两用技术创新和孵化已转变为由私人互联网资本主导,后者为数字平台技术创新提供资金以寻求商业利益[20],国家(政府)和互联网资本演化为“接受治理的依存关系”[17]。“二战”后美国政府通过控制和管理私人技术创新巩固其霸权地位,与私营部门形成所谓的“旋转关系”,如政府通过国家安全计划项目为私营部门创新提供资本、资助和项目管理服务,推动大学与情报机构协作,孵化技术创新成果并将其商业化[20]。截至2018年,私营部门在美国研发中所占份额已超出国家安全部门所占份额的3倍,且在军工复合体中的研发份额更大[21]。高科技工业是国家竞争优势的主要来源,私人互联网资本及其主导的商业技术界凭借人工智能研发能力,对国家竞争新优势塑造的贡献逐渐超越传统国防工业基地。
(四)中国互联网资本正担负起科技自立自强和驱动高质量发展的创新使命
互联网资本主导的数智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共享模式创新和治理现代化,为新质生产力培育和共同富裕推进注入创新动能和治理动力。第一,互联网资本作为数智经济和新质生产力发展的主导力量,为高质量发展提供技术创新引擎和新型基础设施支撑。互联网资本主导的平台经济发展驱动我国科技、产业、经济结构变革向信息化、数字化、智能化演进。平台企业加强基础研究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夯实数智底层技术根基,扶持和带动中小科技企业创新,依托工业互联网平台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发展先进制造业,助力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与财富创造。互联网资本开发数字基础设施及公共物品,建设高速泛在、天地一体、云网融合、智能敏捷、绿色低碳、安全可控的智能化综合性数字信息基础设施,打通经济发展信息“大动脉”,提升生产交换效率,使市场更为繁荣有序、线上消费更加便捷优质。第二,借助数字平台和数智技术,国家治理不断迈向智能化、全域化、个性化。互联网资本为政府调节收入分配、推进公共服务均等化提供了平台支撑,提升了再分配的精准性和公共服务的供给效能,推动互联网公益等慈善新形态的产生以及公益和商业资源的转换。依托数字平台,人民群众诉求及“急难愁盼”问题得到更快反馈和解决。第三,数智经济是国际竞争重点领域,互联网资本主导的核心技术攻关和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影响着“卡脖子”问题的解决,关系到科技自立自强和国家竞争新优势的构筑,以及数字经济自主权和数字主权的维护。与欧美国家相比,中国互联网资本在科技创新和产业变革领域的投资运营呈现“国民共进”的制度特征,即不同所有制的互联网资本(企业)都有机会参与数智科技研发和数字平台开发,为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贡献力量。然而,中国互联网资本的创新能力与美国等数智强国相比仍有一定差距。欧盟执委会的一份统计报告显示,2023年全球研发投入最高20家企业榜单中,美国Alphabet、Meta、微软、苹果占据前4位,中国只有华为和腾讯入榜,分列第5位和第19位。
三、互联网资本与平台垄断
互联网资本创建了具有网络外部性的数字平台,形成平台垄断这一兼具技术垄断和自然垄断属性的新型垄断形态。互联网资本通过提升对数字平台与大数据资源的控制力来强化垄断地位,既适应了生产社会化的新要求,又为互联网资本带来了巨大的市场控制力,但也引发了一系列风险、问题和挑战。
(一)互联网资本基于对数字堆栈和数据资源的开发、掌控而形成平台垄断
互联网资本垄断的形成是其通过数智技术创新与基础设施开发来获取前沿技术垄断及数据垄断地位,进而追求超额利润的必然结果。第一,互联网资本及其平台取代政府,在数字经济领域行使基础设施权力。这是因为后者不能实时控制由算法生成的大数据收集和分发:这些活动的场所是平台,即一个在物质上和算法上进行互动的虚拟场所。平台(包括在线市场、桌面和移动计算环境、社交网络、虚拟劳动力交易所、支付系统、交易系统等)成为越来越多经济活动以及社会和文化活动的场所。平台不是连续的物理空间,而是由使用协议、数据流和算法所定义的虚拟空间,但这种虚拟空间在技术逻辑或经验事实上都是可以被清晰划分的空间;平台“警惕地”守卫着数字经济运行的虚拟边界[22]。第二,大数据自动生成和配置利用的特性影响了数字平台的垄断形态。大数据“无休止、指数级”自动生成的模式使数字平台可以在竞争和监管难以起作用的虚拟领域中推进私人互联网资本的网络互联,使之形成新的组织形式[23]。互联网资本及数字平台对那些开放性数据资源的控制力超出了传统意义上国家对资源采掘和创新变革的控制力范畴[13]41。第三,互联网资本及数字平台借助数字堆栈中的网络力量对数字基础设施行使垄断权力。数字平台对数据资源的发掘力和支配力是通过其在数字堆栈中的网络力量积累起来的,网络服务的多样性和多变性及其由此形成的随机而可控的模块化结构限制了外部竞争者的进入,确保了网络在全球发展中的“黏性”[13]41-51。数字平台成为数字堆栈中软件和硬件系统的“看守者”和独家服务提供商,数字平台垄断利益使私人互联网资本能够对消费者智能设备和应用程序所依赖的软硬件进行投资[8]。
(二)互联网资本垄断在强化技术创新领导力的同时对国家安全构成挑战
互联网资本掌控了巨大的经济社会资源,强化了数字平台在技术创新上的领导地位,但也挑战着主权国家及其政府对国家安全事务的“垄断地位”。第一,互联网资本借助其对关键软硬件商业开发的颠覆性技术优势,以及由此对人类行为的影响,获得了所谓的“虚拟主权”以及超越传统监管的技术能力。美国出台了《2022年数字平台委员会法案》《美国数据隐私和保护法案》《开放应用市场法案》《美国在线选择与创新法案》等反垄断法案来强化对数字平台的监管,政府对平台资本在数字经济领域的控制权表达了担忧。美国国会于2018年召开听证会试图追究数字平台一些不当行为的责任[24],但以上试图对平台垄断行为“绳之以法”的一系列做法并未充分奏效,即使有了立法,国家对数字平台进行监管的有效性仍被质疑[8]。第二,互联网资本垄断并非只是单纯的技术垄断,还体现为平台对新型基础设施力量的垄断。因此,应从数字技术的社会建构层面理解这类平台垄断。互联网资本投资开发的数字堆栈结合了人类、社会、计算和物理形式,成为虚拟主权和基础设施权力的社会来源。数字堆栈构成数字基础设施的聚合层,包括人机接口、地面传感器、本地数字蜂窝和区域通信网络、互联网网关(包括海底电缆)、着陆点和卫星系统,以及地理空间价值、资源和供应链[25]。一些跨国互联网资本和平台,如Alphabet(谷歌)、Meta、亚马逊、苹果和微软,在数字经济领域取得了本应由政府行使的基础设施权力。这些数字参与者所取得的涉及关键互联网技术的基础设施力量包括:采掘权,即在社会同意和合法情况下提取和部署资源的能力[17];变革力,即发起、赞助和利用实质性技术创新以造福国家的能力[26]。互联网资本及数字平台主导的数字经济变革在某种程度上以国家安全控制权的转移为代价,“商业激励和国家安全需求通常是不一致的”[27]。第三,国家对领土主权的法定垄断地位受到数字平台虚拟主权方面垄断势力的挑战。互联网资本在数字经济与虚拟主权领域的垄断冲击着国家主权在网络事务上的主导地位[28]。数字干扰可能影响国家的资源动员能力,即政府获得社会公众同意并向之传递命令的能力。如国内外敌对行为者可能利用数字平台和社交媒体,对国家合法性发起认知攻击,放大国内社会问题,加剧社会认知的脆弱性。
(三)互联网资本通过算法和大数据引导消费者行为并引发隐私安全问题
互联网资本通过大数据发掘、积累和商业化获得数字平台或基础设施的垄断力量,进而影响个人和消费者的思维和行为。数字堆栈为数字平台提供了商业监控的技术可能性和机会,使之能够通过算法实时完成大数据的积累和销售,引导或塑造“消费者选择”——这会使消费者在不知情的情况下个人隐私权被侵犯[29]。如平台企业和广告商通过经济手段诱导和激励智能设备用户保持在线并使用App,借以获取这些用户的个人信息,寻求营利机会[30];平台通过信息发掘和算法精准锁定消费者品位、偏好和需求,实时塑造消费模式及其空间联系[31]。有研究指出,美国数字平台及其背后的互联网资本借助数智技术和算法,通过“窥探”个人信息实时采集大数据,或从中间商处购买大数据,出售给有意愿的广告商,从而影响消费者的认知和行为[8]。因此,保护消费者个人隐私,除避免其被“无限制地采集数据”外,还需防止其受到监控系统算法“固有偏见”的影响[32]。互联网平台及数字技术并不能完全做到价值中立。2010年美国脸书(Meta前身)对6 100万用户进行了未公开的定向广告实验,研究如何最大限度地提高广告利润[33]。这种在线“广告技术”生态系统是数字平台行使基础设施权力的关键证据,其利用网络对个人选择施加影响,以消费者看不到的方式策划和塑造信息环境,使平台滥用垄断权力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不仅主宰了在线广告市场,还主宰了消费者对信息流的访问[34]。如谷歌及母公司Alphabet在各业务市场上都表现出上述垄断趋势,但其否认这种垄断势力的存在及其对消费者隐私的侵犯。美国《2020年数字市场竞争调查》指出,若不加以干预,谷歌所在市场的进入壁垒和网络效应会导致单一归属和整体集中的市场现象[35]247,谷歌正演变为一个连锁垄断的生态系统,这违反了反垄断法[35]15。此外,基于对法律漏洞的利用,脸书对全球约17.9亿用户的信息环境也产生了类似影响。其通过一系列违反竞争原则的商业行为保持了垄断地位,而缺乏竞争导致了“用户的隐私保护更弱,平台上的错误信息急剧增加”[35]14。随着社交网络成为消费者沟通的主要方式,脸书通过垄断获得了一些辅助优势,其在假装重视用户隐私的同时不断积累用户心理档案,并利用其主流社交平台的地位,将消费者访问权出售给一个数据代理生态系统——该系统渴望个人数据,对用户访问所涉及的隐私权进行肆无忌惮的侵犯[36]。
(四)中国互联网资本的平台垄断主要是数据资源垄断而非前沿技术垄断
互联网资本既可通过数智技术创新形成前沿技术垄断,又可通过创建具有网络外部性的数据平台而形成数据资源垄断,这两个方面往往是耦合推进的。如一些大型互联网资本通过对关键软硬件的商业开发获得大数据资源的采掘权和控制权,从而形成兼具技术垄断和数据垄断的数字平台。与美国等数智强国的互联网资本致力于追求前沿技术上的垄断优势不同,中国的互联网资本更倾向于做大数字平台而获得数据资源垄断地位并寻求流量变现。美国互联网平台的垄断逻辑是行业垂直深耕,如亚马逊做零售,谷歌做搜索,苹果做手机;中国平台的垄断逻辑偏向于“跨界通吃”,即超级平台利用基础服务能力形成流量优势、数据集中优势,并运用杠杆将垄断地位延伸至其他领域。美国平台注重技术创新和对中小企业的扶持;中国平台强调市场规模,在消费互联网领域竞争流量。美国最大的5 家互联网平台企业研发经费是中国五大平台(腾讯、阿里、美团、京东、百度)的7.4 倍,研发强度是后者的1.3倍。中美两国专利数量相当,但中国专利集中于应用层面,芯片、操作系统等关键技术上仍存在“卡脖子”问题。中国产业互联网发展处于起步阶段,大型互联网平台以“C 端”消费为主,倾向于选择以消费互联网横向扩张为主的流量经济发展模式,平台功能重叠,变现需求强烈,从粉丝经济、社交网络、直播视频到小程序,直至走向流量变现的带货模式[37]。中国互联网资本通过做大数字平台取得数据资源垄断地位,本质上是一种发挥网络外部性的“自然垄断”,一旦演变为“跨界通吃、消费为王、变现至上”的平台垄断行为,就会陷入“重数据垄断、轻技术创新”的低水平垄断扩张陷阱,既会妨碍其开展基础性的数智技术攻关,又容易对市场秩序造成破坏。近年来,中国出现了一些大型互联网平台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进行不正当竞争的现象,如强迫“二选一”、“大数据杀熟”,烧钱抢占“社区团购”市场、“掐尖并购”,以及纵容假冒伪劣、隐私侵犯等,妨碍了小企业创新,侵害了经营者、从业者和消费者的利益,对高质量发展和共同富裕造成不良影响,必须依法规范、从严监管、有效治理。
四、互联网资本的扩张行为
资本的逐利性推动着资本不断积累和扩张。垄断资本具有更强烈的扩张动机:一方面,生产社会化带来的规模优势促使资本通过扩张巩固其市场优势;另一方面,垄断资本巨大的体量加大了彼此的竞争压力。互联网资本为这种扩张赋予了科技竞赛色彩,将其扩张从实体空间延伸至虚拟空间,并在获取数字资源的诱使下,不断挑战虚拟空间中社会、企业、政府三者模糊的边界,带来新的风险和挑战。
(一)互联网资本主导的科技创新与商业运营具有全球化属性
互联网资本主导的科技创新及产业化是由少数国家的互联网科技公司具体推进的,但其资本来源并不限于某一国或地区,其科技创新成果的商业化实现以及平台网络外部经济的释放依赖于全球市场。全球互联网硬件开发大多是由全球财富链中的互联网资本提供资金,其中包含诸多国家的私人或国有资本;互联网软件多由科技发达国家的公司设计和开发,但其商业用户分布于各个国家或区域,为全球用户创造更好的科技服务成为这些公司商业的优先事项。如国际海底电缆、卫星、云存储和宽带等数字基础设施是由一些大型互联网公司依托全球财富链和供应链体系创建的。互联网资本及平台对基础设施网络的开发和控制与地缘政治利益存在交叉。一方面,互联网资本投资发展高科技制造业时,往往采用“多司法管辖区”(multi-jurisdictionally)的资本运作交易形式进行跨国扩张并融入全球供应链,不断增强其对全球科技创新和产业变革的引领力。同时,互联网资本及平台的技术创新研发和商业化行为离不开全球供应链和价值链的支撑,这一供应链和价值链涵盖全球金融合作伙伴、项目合作及技术共享方,甚至有来自战略竞争国的公司。跨国互联网资本正演化成为一种“在创造金钱财富过程中寻求责任逃避”的关联资本组织形式,其投资运营所采用的商业模式及行为方式转为全球“财富链”隐秘做法,倾向于采用一种混合金融产品形态[38]。另一方面,随着互联网科技知识产权和专利成果创造趋于全球化,那些与数字基础设施开发相关的创新活动不再限于某一国或地区,数字基础设施具有了全球公共产品属性,意味着私人互联网资本及平台在全球进行商业扩张时,可能会忽略对国家安全利益因素的考量[17]。如美国互联网资本商业利润很大一部分来自国家监管之外的全球生产和分销链,“去属地化”的互联网资本及平台对全球科技和资本市场网络具有较强的技术和金融依赖性,从而与国家安全利益形成一些潜在冲突[8]。
(二)互联网资本表现出高度的流动性以及跨界扩张倾向
互联网资本表现出高度的流动性,为全球范围内的数字服务创造和网络基础设施建设提供投融资,其资本触角延伸至具有商业可行性的所有数字经济空间和领域。如互联网资本投资创建的大型数字平台,包括亚马逊、微软、谷歌和IBM等,几乎开发和控制了全球大部分的云物理基础设施和平台服务[39]。与传统电信供应商不同,作为互联网科技服务商的平台在开发和供应数字科技服务、推动超大规模数据商品化时,往往超出了政府常规监管的范围或能力,使互联网资本加速流向网络连接和服务供给的各个维度或空间。美国Alphabet公司的战略影响力是在数字堆栈多个层次上发展起来的,涵盖了从互联网科技产品供给到全球医疗服务的各个层面。正如谷歌所宣扬的,其使命是运用优质软硬件以及最先进的人工智能成果,为大众提供从搜索到地图、从Gmail邮箱到照片的各种产品和服务,以及便于大众获得知识、成功、健康和幸福的工具,为家庭创造高像素手机、可穿戴设备、笔记本电脑和Nest设备等产品[40]。互联网资本借助数字平台力量或算法算力、通用技术优势,进入诸多行业领域提供硬件和软件服务以及技术解决方案,表现出强烈的跨界扩张倾向,在经济社会生活各个领域日益形成“数字统治”态势。一些跨国互联网资本进入金融科技服务领域进行技术创新和商业开发,并将其服务范围扩展到全球任何有商业机会的地方。近年来,苹果公司推出了信用卡服务,谷歌也启动了消费者银行账户开发计划。苹果公司自研ARM微架构处理器并用之取代英特尔处理器,展示出一种带有跨界性质,涉及企业整合或独立产能、权威控制的新型技术范式[41]。
(三)互联网资本不断开辟和拓展虚拟空间,以获取更大的虚拟主权
互联网资本通过对关键软硬件的商业开发和控制,以及由此产生的对人类经济行为的影响,开辟了一种超越国家主权范畴并引发国家安全风险的虚拟主权形态。数字平台虽然声称保持技术中立,如微软提出“作为一个全球科技行业,我们需要成为一个值得信赖的、技术中立的数字瑞士”[42],但其在网络空间与数字领域实际获取了所谓的虚拟主权。虚拟主权是指在数字时代发展的虚拟领域中,在互联网创建和数字平台调节的新的社会技术空间中,由互联网资本与数字平台开发和掌控的关键基础设施权力或创新变革引导力[8]。新的组织技术的发明“极大地提高了控制人民和领土的能力”[43],在越来越多的生活领域,“算法正在取代人所作的判断”,却不能像人一样被“识别和追究责任”[44]。从虚拟主权的技术成因看,数字平台通过开发和控制数字堆栈的软硬件,获得了与关键互联网技术相关的基础设施力量,而数字堆栈的不透明性和不定形性阻碍了国家对其进行审查[8],由此产生了网络形式的“虚拟主权”。从虚拟主权的实际效力看,互联网资本及平台塑造着经济主体与社会个体的思想及行为,主导了科技创新要素及资本的跨境流动,展示出引领全球数智经济变革的强大力量。但是,虚拟主权也面临着合法性问题,如互联网资本和数字平台开拓的“虚拟主权”能否获得类似国家主权的权威、权利或合法性?互联网资本及平台获得数字资源采掘和创新变革引领能力的同时,其创造的数字堆栈“虚拟主权”可能与主权国家“以领土为中心的自治”形成一些冲突,如私人互联网资本对数字平台的融资和主导缺乏必要的问责和透明度,有时会忽略对国家利益的考量。在缺乏程序合法性和安全性的前提下,虚拟主权与公民或消费者间的契约很难建立,数字平台和个人消费者间的商业合同不总是保证合法性,而且数字平台提供的服务具有不透明、不可竞争或不负责任的特性[8]。互联网资本“虚拟主权”还会衍生出一些地缘政治问题。数字平台基于虚拟主权进行商业扩张,客观上可能会纵容国外战略竞争者利用平台施加不利影响。如平台出于商业动机向全球供应链中的企业买卖技术和数据,但这些企业及其母国可能与平台所在国存在战略竞争关系。此外,数字平台通过对实时云存储大数据的积累和垄断而行使数字基础设施权力,有时会违背传统的地缘政治规范。当数字平台以保护用户权利的名义回避国家监管时,一些战略竞争对手会利用数字平台谋求敌对性质的战略利益,有些敌对行为者将社交媒体“武器化”,从而引发国家安全风险。鉴于国家权力的合法性和韧性受到敌对行为者的挑战,有必要设计制度以约束数字平台在虚拟空间的扩张行为[8]。
(四)中国互联网资本及平台全球化发展成效初现,但面临一些问题和挑战
中国互联网资本具有一般互联网资本的全球化属性。近年来,字节跳动、阿里巴巴、拼多多、腾讯等大型互联网企业携其所建的TikTok、Aliexpress、速卖通、Temu、Shopee等品牌,连同SHEIN等跨境电商新势力出海抢滩国际市场,构建起海外全链条跨境供应链服务平台。中国平台企业“出海”在短视频、直播、游戏、网约车、社交娱乐等多个赛道都有亮眼表现。当前中国平台企业持续推进技术和产品迭代创新,从产品和资本输出转向技术和模式输出,阿里云、华为云、腾讯云等中国“云厂”走向海外,随着大模型的纳入,这些平台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得到新的提升。但是,中国互联网资本的国际化也面临着日益严苛的准入限制、安全审查和监管约束,平台企业海外市场拓展遭遇合规性、本土化、产品能力等方面的问题和挑战。与美国互联网巨头推进垂直深耕式的创新拓展有所不同,中国大型互联网资本和超级平台表现出显著的跨界扩张倾向,热衷于终端的横向扩张和用户垄断,追求流量变现——势力范围囊括零售、医疗、消费金融、网络支付、出行、住房、媒体、旅游、商业服务、物流等领域。互联网资本具有极强的渗透性和控制力,若不加以监管规范、明确规则和边界,任其无序扩张和“野蛮生长”,可能会导致垄断侵权、秩序破坏,甚至引发金融风险、数字安全和意识形态问题。过去一些互联网资本在金融保险、教育培训、文体娱乐、医疗保健等领域出现了过度扩张倾向,甚至产生非法集资、洗钱等金融犯罪行为。超级平台跨界扩张或无边界渗透形成对经济生态和大众社会的算法支配与数字控制,容易引发隐私侵犯、信息泄露和数据安全风险,也不利于纵深性质的自主创新[45]。互联网资本与平台是数字时代社会治理与意识形态引领的关键技术主体,是一国参与国际数字竞争及数字规则塑造的重要市场力量,对其进行规范和引导关系着意识形态阵地的坚守、数字安全的维护、数字竞争优势的塑造。一方面,数智技术应用催生了治理变革,互联网平台作为公众表达诉求、参与治理的重要渠道和线上社区,成为各类利益群体的舆论交锋与话语权争夺地。互联网科技公司作为平台创建者、技术员和运行管理人,理应担负起舆情民意观察监测与意识形态安全守护的责任和使命,避免其脱离正确的政治方向和法治轨道。另一方面,中国互联网资本若不能在“卡脖子”技术和数字基础设施上形成核心竞争力,就难以在与国外平台的竞争中取得战略优势、为中国的全球话语权竞争提供国际传播平台支撑,难以抵御外来互联网资本的冲击和渗透、保障国民数字福利和数字主权安全。
五、促进互联网资本健康发展的策略
正确认识和把握互联网资本的特性和行为规律,是为了更好地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发挥互联网资本的积极作用,抑制其消极影响,使之成为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扎实推进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要素和主体力量。为此,应处理好互联网资本发展与规范间的辩证关系,既要支持和激励,又要规范和引导,构筑互联网资本创新发展新动能和健康发展新秩序,形成中国数智经济发展新格局。
(一)支持互联网资本创新发展,培育新质生产力,构筑国家竞争新优势
在思想认识上,应重视互联网资本对发展新质生产力、塑造国际竞争新优势的关键作用,引导互联网资本及平台创新发展,激发其对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与国民经济创新变革的引导力。数智化时代的新质生产力是由数智技术革命性突破及商业应用、数据驱动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数智化转型升级而催生的先进生产力质态,具有创新链和产业链快速融合的特征,即不断迭代的数智化创新成果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加速现代化产业体系成长。互联网资本作为高科技资本的代表,是驱动数智技术突破及商业应用、大数据等新兴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数智化转型的主体力量。中美科技及产业博弈焦点转向人工智能及智能经济,互联网资本及平台的创新能力及其所构建的数智产业集群竞争力大小决定了大国竞争的成败。鼓励和支持互联网资本创新发展,培育更多全球顶尖的平台企业,是赢得人工智能之争、构筑国家竞争新优势的必然要求和根本途径。
在发展着力点上,应充分发挥互联网资本的资源配置功能、创新先导作用、福祉创造效应;发挥互联网资本对创新资源的“集成配置”作用、对经济循环的“融会贯通”功能,运用工业互联网平台发展先进制造业,引导实体企业数字化转型;发挥互联网资本的创新创业驱动力、就业消费带动力,强化其对治理现代化的赋能作用;发挥互联网资本的福祉创造效应,满足人民群众的数字生活需要。支持消费领域平台企业增加优质产品和服务供给,加强对低技能劳动者的教育支持,强化信息化服务普及,降低应用成本,让老百姓用得起、用得好,使其在共享数智财富上有更多获得感。
在制度和法律上,应把平等对待包括民营互联网资本及平台企业在内的各类资本及市场主体的要求落到实处,为互联网科技企业加大创新研发力度、可持续投资经营创造更加有利的市场环境和法治环境。在数智产业和平台经济领域,不断完善落实“两个毫不动摇”的体制机制,弘扬企业家精神,激发互联网资本及平台的内生动力和创新活力。构建资本和数据等要素市场的基础制度,完善非国有互联网资本和平台企业产权保护制度,推进资本、数据等要素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健全互联网资本发展的法律制度,加快数字经济和人工智能立法,形成框架完整、逻辑清晰、制度完备的治理框架和规则体系,为互联网资本和平台发展提供固根本、稳预期、利长远的法治保障。全面推进制度型开放,以富有活力并可预期的优质市场环境吸引更多高水平外资和高科技企业来华投资兴业;积极参与数字经济国际规则制定、强化国际技术交流和研发合作,支持中国互联网科技资本和平台走向世界。激励互联网平台创新、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形成与之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做好顶层设计,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和科技体制改革,优化人才培养和激励机制、新型要素参与分配机制,促进各类先进要素向发展新质生产力集聚配置。
在政策和舆论上,应强化支持互联网资本创新发展价值取向的一致性,提升互联网资本发展信心和投资预期。将支持引导互联网资本创新发展和平台企业做优做强作为标志性、实效性工作来抓,稳定包括互联网资本在内的各类非公有资本的政策预期和发展信心,激发数智经济领域各类投资经营主体的创新动能和创造活力。聚焦互联网资本创新发展目标,做好财政、货币、就业、产业、区域、科技、环保等政策的协调配合,把非经济性政策纳入政策取向一致性评估,强化政策统筹,确保同向发力、形成合力。聚焦互联网资本及平台的发展瓶颈和政策需求,在扩大市场准入、优化公平竞争环境、畅通创新要素流动等方面加强服务保障,在要素获取、公平执法、权益保护等方面落实关键举措。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巩固高科技外资企业在华发展信心,提升贸易投资合作质量和水平。加强互联网资本及平台发展前景与政策预期的正向宣传和舆论引导,坚决抵制将规范资本发展曲解为节制和打压民间资本的炒作和攻击,提升互联网资本等科技资本的发展信心和预期。
(二)促进互联网资本健康发展,做好平台垄断及扩张治理,维护数字安全
正确认识和处理鼓励民营资本发展与防止资本无序扩张的关系,坚持疏堵结合、分类施策,统筹发展和安全、效率和公平、活力和秩序,优化引导资本健康发展的方针政策,使之有序融入高质量发展和共同富裕大局。一方面,鼓励互联网资本及平台创新攻关,营造各类资本竞相发展助力新质生产力形成和国民福祉增进的制度环境,推动中国互联网资本及平台更好地走向世界。另一方面,依法规范平台垄断、治理互联网资本无序扩张行为。健全与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相关的法律法规,构筑平台反垄断和互联网资本无序扩张治理的法治框架。设立互联网资本“红绿灯”制度,形成框架完备、逻辑清晰、制度完备的平台资本发展规则体系,以及公平竞争、创新发展、开放共享、安全和谐的平台经济发展新秩序。构建互联网资本全链条治理体系和新型监管机制[46],严防资本无序扩张,确保经济社会安全;严防垄断失序,确保市场公平竞争;严防技术扼杀,确保行业创新发展;严防规则算法滥用,确保各方合法权益;严防系统封闭,确保生态开放共享。
依法制定互联网资本准入负面清单,明确严禁进入和鼓励进入领域,引导其流向高科技和数字前沿领域,开展数字科技攻关,解决“卡脖子”技术问题。支持国有资本进入基础性、战略性数字经济领域,参与重大数智科技攻关、核心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发挥国有数字平台的创新引领和数字安全维护功能。基于并购方式、用户规模、投资金额等方面的差异,甄别并规范平台资本并购行为,打击平台资本对中小创新企业的恶性收购行为。严防互联网资本利用垄断势力、大数据和算法进行金融投机、危害金融安全;加强互联网资本领域反腐力度,打击以权力为依托的互联网资本逐利行为;查处平台资本无序扩张、平台垄断等背后的腐败行为。高度重视国家数字安全,落实数据安全责任制,筑牢网络安全防线,在国家安全、国民经济命脉和国计民生领域切实做到互联网平台和数智科技自主可控。
坚持按劳分配和按要素分配相结合,既要发挥互联网资本在带动创业就业、激活知识数据要素参与生产分配循环中的作用,又要防止互联网资本侵害劳动、知识等要素分配权益。推进平台企业劳动保护立法、数字安全立法,明确平台企业劳动保护责任,健全灵活就业劳动者福利保障体系,督促平台企业承担商品质量、食品安全保障责任。强化平台企业数据安全责任、维护用户数据权益及隐私权。优化“全链条”监管框架,充实平台反垄断的专业监管力量,提升平台金融活动监管专业化水平,防止平台滥用市场地位或利用数据、算法损害消费者权益。 [Reform]
参考文献
[1]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八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依法规范和引导我国资本健康发展 发挥资本作为重要生产要素的积极作用[N].人民日报,2022-04-30(001).
[2]邱泽奇,张樹沁,刘世定.从数字鸿沟到红利差异——互联网资本的视角[J].中国社会科学,2016(10):93-115.
[3]蓝江.一般数据、虚体、数字资本——数字资本主义的三重逻辑[J].哲学研究,2018(3):26-33.
[4]孟飞,程榕.如何理解数字劳动、数字剥削、数字资本?——当代数字资本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J].教学与研究,2021(1):67-80.
[5]顾海良.马克思“资本一般”和“许多资本”理论与中国资本问题研究[J].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2022(8):4-16.
[6]马克思.资本论:第二卷[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7]保罗·萨缪尔森,威廉·诺德豪斯.经济学[M].萧琛,等,译.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2007:580.
[8]KELTON M, SULLIVAN M, ROGERS Z, et al. Virtual sovereignty? Private internet capital, digital platforms and infrastructural power in the United States[J]. International Affairs,2022, 98(6): 1977-1999.
[9]鲁道夫·希法亭.金融资本[M].福民,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
[10]HOWARD P N. Pax technica: How the internet of things may set us free or lock us up [M].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5: 35.
[11]FARRELL H, NEWMAN A L. Weaponzed interdependence: How global economic networks shape state coercion[J]. International Security, 2019, 44(1): 42-79.
[12]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13]COHEN J E. Between truth and power: The legal constructions of informational capitalism[M]. New York, N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9.
[14]加布里埃尔·雷内,丹·马普斯.智慧空间[M].徐锷,孙亚洛,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20.
[15]BARRINHA A, RENARD T. Power and diplomacy in the post-liberal cyberspace[J]. International Affairs, 2020, 96(3): 749-766.
[16]BENJAMIN B H. The stack: On software and sovereignty[M]. Cambridge, MA: MIT Press,2016: 375.
[17]WEISS L, THURBON E. Power paradox: How the extension of US infrastructural power abroad diminishes state capacity at home[J].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2018, 25(6): 784-785.
[18]DENARDIS L. The global war for internet governance[M].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4.
[19]NESBIT J. Google's true origin partly lies in CIA and NSA research grants for mass surveillance[EB/OL].(2017-12-08)[2024-02-06].https://qz.com/1145669/googles-true-origin-partly-lies-in-cia-and-nsa-research-grants-for-mass-surveillance.
[20]WEISS L. America Inc.?: Innovation and enterprise in the national security state[M].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14.
[21]SARGENT J. US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funding and performance: Fact sheet[M]. Washington DC: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2021.
[22]COJEN J. Law for the platform economy[J].UC Davis Law Review, 2017, 51: 133-136.
[23]SCHNEIER B. The battle for power on the internet[EB/OL].(2013-10-30)[2024-02-06].https://www.schneier.com/blog/archives/2013/10/the_battle_for_1.html.
[24]CHOUCRI N,CLARK D D. Cyberspace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oward an integrated system[Z]. Working Paper No. 8-25 for ECIR Internal Review, 2011.
[25]ROGERS Z,BIENVENUE E. Combined information overlay for situational awareness in the digital anthropological terrain: Reclaiming information for the warfighter[J]. Cyber Defense Review, 2021, 6(3): 89-107.
[26]MANN M. Infrastructural power revisited[J]. Studies in Comparative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2008, 43: 355-365.
[27]LEWIS J A. Mapping the national security industrial base[EB/OL].(2020-05-19)[2024-02-06].https://www.csis.org/analysis/mapping-national-security-industrial-base-policy-shaping-issues.
[28]CHOUCRI N, CLARK D D. Integrating cyberspace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 co-evolution[EB/OL].(2012-11-07)[2024-02-06].https://papers.ssrn.com/sol3/papers.cfm?abstract_id=2178586.
[29]VILJOEN S. Democratic data: A relational theory for data governance[J]. Yale Law Journal, 2021, 131(2): 654-781.
[30]KHAN L M,POZEN D E. A skeptical view of information fiduciaries[J]. Harvard Law Review, 2019, 133(2): 526-528.
[31]BRADSHAW S,HOWARD P. Challenging truth and trust: A global inventory of organized social media manipulation[M]. Oxford: Oxford Internet Institute, University of Oxford, 2018: 21.
[32]MATZNER T. Surveillance as a critical paradigm for big data?[EB/OL].(2014-02-16)[2024-09-17].https://nomadit.co.uk/conference/easst2014/paper/23437.
[33]STARR P. The new masters of the universe: big tech and the business of surveillance[J]. Foreign Affairs, 2019, 98(6): 191-197.
[34]SRINIVASAN D. Why Google dominates advertising markets: Competition policy should lean on the principles of financial market regulation[J]. Stanford Technology Law Review, 2020, 24(1): 55-175.
[35]US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Investigation of competition in digital markets: Majority staff report and recommendations[R/OL].(2020-10-04)[2024-02-06].https://www.documentcloud.org/documents/722283
6-Investigation-of-Competition-in-Digital-Markets.
[36]SRINIVASAN D. The antitrust case against Facebook: A monopolist's journey towards pervasive surveillance in spite of consumer's perference for privacy[J]. Berkeley Business Law Journal, 2019, 16(1): 39-101.
[37]欧阳日辉.互联网平台高质量发展:影响因素与推进策略——基于中美两国互联网平台发展现状与态势的分析[J].人民论坛,2023(16):90-93.
[38]SEABROOKE L, WIGAN D. Global wealth chains in the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J].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2014, 21(1): 257-263.
[39]BALA R, GILL B, SMITH D, et al. Magic quadrant for cloud infrastructure and platform services[EB/OL].(2021-07-27)[2024-02-06].https://azure.microsoft.com/en-us/blog/microsoft-named-a-leader-in-2022-gartner-magic-quadrant-for-cloud-infrastructure-and-platform-services/.
[40]OSTERLOH R. Made by Google: Helpful, simple and personal[EB/OL].(2023-10-04)[2024-02-06].https://blog.google/products/devices-services/made-by-google-2023-collection/.
[41]THE GUARDIAN. Apple ditches Intel for ARM processors in Mac computers with big sur[EB/OL].(2020-06-23)[2024-02-06].https://www.theguardian.com/technology/2020/jun/22/apple-ditches-intel-for-arm-processors-in-big-sur-computers.
[42]SMITH B. The need for a digital geneva convention[EB/OL].(2017-02-14)[2024-02-06].https://blogs.microsoft.com/on-the-issues/2017/02/14/need-digital-geneva-convention/.
[43]MANN M. The sources of social power: A history of power from beginning to AD 1760[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6: 1-3.
[44]CRAWFORD M. Algorithmic governance and political legitimacy[J]. American Affairs, 2019, 3(2):73-94.
[45]靳文辉,苏雪琴.数字资本无序扩张的风险与规制[J].改革,2024(1):82-93.
[46]尹俊,孙巾雅.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治理的困境与破解之道[J].改革,2023(7):35-46.
The Characteristics, Behavior Rules and Development Strategies of Internet Capital
HE Li-long LUO Zhen
Abstract: As the core subject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revolution and industrial reform, internet capital and its platform enterprises are the key forces to promote the agglomeration of advanced production factors to develop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eces. In terms of nature, internet capital is an emerging capital element with great creativity and cohesion. It is also a social first capital with network externalities and the attributes of technological monopoly and natural monopoly. In terms of behavior, internet capital plays a leading role in data resource mining and economic innovation and reform by investing in the development of key internet hardware and software and creating a digital stack. At the same time, it forms a platform monopoly by controlling cutting-edge technology and data resources, showing a high degree of global liquidity and cross-border expansion. On the one hand, this has adapted to the needs of new production socialization, driven the revolution of digit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y and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innovation of sharing models, and modernization of governance, injecting innovative momentum, institutional potential, and governance efficiency into the development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and the improvement of human well-being. However, on the other hand, it may also lead to disorderly expansion of capital, causing monopoly infringement, digital divide, and even digital security and ideological risks, eroding the economic foundation and security guarantee of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and common prosperity. To this end, we should properly handl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development and standardization of internet capital. We should not only give full play to the innovative leading function of internet capital, but also build a new order for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internet capital and accelerate the formation of a new development pattern of digital an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economy.
Key words: internet capital; platform economy;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