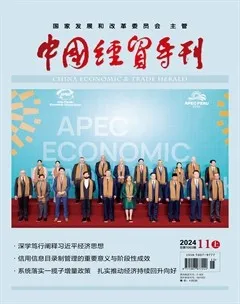新阶段汽车产业政策面临挑战和优化建议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指出,科学的宏观调控、有效的政府治理是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优势的内在要求。产业政策,是我国宏观调控和政府经济治理的重要手段,主要包括选择性和功能性产业政策。在我国汽车产业从小到大、从大到强的“追赶”过程中,产业政策以选择性政策为主,通过财税金融支持、试点示范、设置限制措施等方式,“引进模仿”日本、德国等领先国家经验培育有能力的汽车企业,达到缩小市场、技术差距等目标。目前,我国新能源汽车初步建立起全球“领先”优势,产业规模、电动化智能化技术具有全球竞争优势,但产业结构和技术升级方向有待探索,国际竞争日趋激烈,管理工作难度加大,选择性产业政策支持效果减弱。建议汽车产业政策向以功能性产业政策为主转变,同时统筹发展和安全,调整政策方向和目标、优化政策工具和实施方式,以“自主创新”为主,达到技术领先、结构优化等目标,持续巩固和扩大我国汽车产业发展优势。
一、选择性产业政策推动我国汽车产业完成“追赶”目标
改革开放伊始,我国汽车年销量仅10多万辆,2009年突破1000万辆,成为全球汽车产销第一大国,2015年成为全球新能源汽车产销第一大国,2023年汽车和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出口量均位居全球首位。我国汽车产业从小到大、从大到强并在新能源汽车领域建立领先优势过程中,产业政策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两部产业政策推动我国汽车产业从小到大发展
一是1994年《汽车工业产业政策》重点解决汽车供给不足问题,奠定了我国汽车产业现代化体系框架。1994年,中国品牌汽车全球市场份额约2%、远低于德国品牌的10%和日本品牌的34%,RCA指数仅0.01,企业生产规模小,产品和技术竞争力弱。《汽车工业产业政策》确定培育汽车产业为支出产业,提出产量规模、骨干企业数量、产品技术国产化等政策目标和鼓励利用外资、鼓励个人消费等发展重点。10年间,吉利、长城、比亚迪、奇瑞等中国企业进入汽车领域,通用、丰田、现代、福特等外资企业通过合资进入中国市场,我国汽车产业体系初步建立,2004年产量超过500万辆。
二是2004年《汽车产业发展政策》重点解决适应入世后全球化发展形势、提升产业规模质量问题,推动汽车产业发展成为国民经济支柱产业。2004年,我国品牌汽车全球市场份额约6%、产业规模逐步扩大,但RCA指数仅0.02、产业竞争力有限,同时存在结构不合理、自主开发能力弱等问题。《汽车产业发展政策》提出使我国成为世界主要汽车制造国的政策目标和继续扩大规模、鼓励结构调整、支持自主研发等发展重点。在《汽车产业调整和振兴规划》(2009年)等政策共同支持下,我国建成了较为完善的汽车产业体系,长安、长城、奇瑞、比亚迪、吉利等企业快速发展,产品技术水平和自主创新能力明显提升,2009年起产销量位居全球首位,2014年中国品牌汽车全球市场份额达14%、RCA指数提升至0.13,国际竞争力有所增强。
(二)系列新能源汽车支持政策推动我国汽车产业从大到强
2009年,我国提出大规模发展新能源汽车的战略方向,但由于技术积累不够、基础设施不完善、市场认可度有限等,新能源汽车发展缓慢,2013年渗透率仅0.1%,新能源汽车发展前景“不明”。
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发展新能源汽车是我国从汽车大国迈向汽车强国的必由之路。同年印发了《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的指导意见》,系统提出了发展新能源汽车的政策措施。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接续制定面向2020年和2035年的产业发展规划。一是《节能与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规划(2012—2020年)》重点解决技术路线和产业化问题,提出以纯电驱动为汽车产业转型的主要战略取向,通过财税金融、试点示范等支持政策,重点推进纯电动汽车、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产业化和规模化。二是《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规划(2021—2035年)》重点解决产业发展规模和质量问题,提出深入实施新能源汽车国家战略,重点通过提升技术创新能力、完善基础设施建设等加快汽车产业电动化转型和高质量发展步伐。2018年《汽车产业投资管理规定》再次强调了汽车电动化转型方向,并明确了产业布局要符合“区域集中、主体集聚”原则。
在一系列产业政策支持和引导下,我国新能源汽车快速发展,2023年中国品牌新能源汽车全球市场份额达48%、远高于德国品牌的14%和日本品牌的2%,RCA指数为1.05、具有较强的出口比较优势;汽车全球市场份额也达到23%、高于德国品牌的16%、略低于日本品牌的27%,RCA指数提升至0.52。我国新能源汽车已具有全球领先优势,并带动汽车产业整体竞争力显著增强。
二、产业政策在我国汽车产业“领先阶段”面临三方面挑战
(一)需进一步推动产业提高发展效益、突破技术瓶颈
一是尚未实现结构升级和发展效益的“既要又要”。2017—2023年,我国新能源汽车销量从78万辆增长至950万辆,但由于多数新能源汽车企业尚未实现盈利、燃油汽车企业利润下滑、新能源汽车享有税收优惠等原因,同期汽车行业重点企业利润总额下滑了41.8%、销售利润率从15.9%下滑至4.9%,汽车行业主要税收(包括汽车企业所得税和增值税、车辆购置税、车船税、汽车消费税)从8094亿元下降至7557亿元。
二是尚未促进汽车电动化智能化技术瓶颈的突破。固态电池是汽车电动化发展重要方向,目前处于技术研发阶段。我国在半固态电池应用方面具有优势,日韩在专利方面领先,美欧也加大布局和投入。率先实现固态电池关键技术突破的国家,将在新能源汽车未来竞争中占据先机。芯片、操作系统等汽车智能化底层技术仍受制于人,汽车芯片自给率不足10%、设计和制造工具被美欧日韩垄断,安卓、QNX、Linux占据车用操作系统绝大多数市场份额,操作系统内核、认证等依靠国外,存在丧失产业发展主导权风险。
(二)需进一步考虑日趋复杂严峻的国际竞争环境
我国与传统汽车强国在全球汽车产业竞争中的力量对比正发生变化,逐步呈现“攻守易位”的竞争态势,我国汽车产业全球化发展面临复杂的国际环境。一是针对我国新能源汽车的贸易争端增多。如美国、加拿大对我国电动汽车加征100%关税,欧盟对我国电动汽车开展反补贴调查并已加征17.4%—37.6%的临时关税。二是围绕新能源汽车产业竞争加剧。如美、欧、东南亚等均出台产业政策支持新能源汽车发展,将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作为竞争对手,在技术、市场、资源等方面展开激烈争夺;欧盟《电池与新电池法》、碳边境调节机制等设定碳壁垒限制我国新能源汽车进入欧洲市场。
(三)需进一步优化产业管理、统筹发展和安全
一是严格准入易,推动退出难。《汽车产业投资管理规定》等加强了准入管理,近年来仅有小米等少数企业新获得生产资质。但由于落后企业退出机制不健全等原因,推动落后企业退出进展不畅,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数据显示2023年我国有64家企业销量小于10000辆,其中15家企业为0、处于停产状态。如何完善准入和退出管理,有效提高产能利用率,构建进出有序、优胜劣汰的良好产业生态,是产业管理工作的一大难题。
二是“引进来”和“走出去”要统筹协调。近年来,外国汽车企业积极寻求与我国企业开展合资合作,我国汽车企业也加快“走出去”。这有利于拓展我国产业优势、深化国际合作、增强企业竞争力,但也存在遭遇打压遏制、集中扎堆投资、产业链外迁等风险。如何统筹发展和安全,推进高水平开放合作,是产业管理工作的又一挑战。
三、汽车产业政策应向功能性政策转变并统筹发展和安全
我国汽车产业从燃油汽车领域追赶者成为新能源汽车领域领先者,目前正处于巩固扩大领先优势关键时期。产业政策应向功能性政策为主转变并统筹发展和安全,调整政策目标、优化政策工具、转变政策实施方式,在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中继续发挥重要作用。
(一)调整汽车产业政策实施的主要目标
一是从数量到质量。未来,我国汽车产业在稳步扩大产业规模的基础上,更加注重提质、降本、增效。尽快提升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效益,加快突破固态电池和汽车芯片、操作系统等关键技术,增强我国汽车技术创新能力和自主可控能力,支持骨干企业发展成为世界一流汽车企业集团,巩固扩大产业全球领先优势。
二是统筹发展和安全。在制定新的汽车产业政策时要有更强的竞争意识和风险意识,充分考虑传统汽车强国的汽车产业战略以及全球化发展趋势的影响。合理设定我国汽车产业全球化发展目标,有序推进我国汽车产业海外投资,防范技术外流、产业链外迁等风险,构建“以我为主”的全球汽车产业链供应链体系。
(二)优化产业政策实施的主要工具
一是支持政策以激励创新、优化环境为主。完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参与国际专利规则制定和修改,指导新能源汽车企业开展全球专利布局。加快新能源汽车产业标准化进程,凭借我国新能源汽车特别是电动化环节领先优势,推动以中国标准引领世界标准。加快制定新能源汽车碳排放、碳足迹国家标准,推动新能源汽车碳排放、碳足迹核算体系国际互认。
二是管理政策以完善机制、强化引导为主。加强部门协作,压实地方属地管理责任,按照总量控制、有进必有退、集聚集中发展等原则,完善落后汽车企业退出机制,畅通退出渠道。引导骨干汽车企业根据国家外交大局和企业发展实际需要,稳步有序开展与跨国企业合资合作和赴海外投资布局。结合产业发展实际,因时制宜,适时优化产业管理,努力实现既“放得活”又“管得住”。
(三)转变产业政策实施的主要方式
一是支持重点从制造生产端转向产业发展环境端和技术研发创新端。强化对充换电、智能交通等基础设施的建设,围绕技术短板和薄弱环节的基础研究,有利于汽车芯片、操作系统等关键技术自主可控的产业化应用,创新研发能力强的新能源汽车产业链中小企业等方面的支持。
二是支持方式更加合规化、多样化。完善汽车产业有关支持政策相关的法律体系,夯实产业政策的法律基础,设定客观、公平适用的标准和条件,减少产业政策转向性。加强汽车产业政策与科技政策、竞争政策等协调联动。加强新能源汽车领域科技创新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增强全球优势资源整合、组织和协调能力。
(作者单位:国家信息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