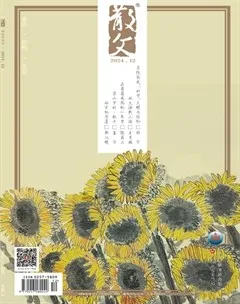釉惑
一
走在南平,有脚踏福建半省的豪迈。
建瓯、建安、建州、建阳、建宁……闽北历史上带“建”字的地名洋洋洒洒,典藏在武夷山脉深处。八闽大地,“建”地占籍三成,成就了“福建”之命名。取福州与建州各一字,名副其实,皆大欢喜。
厥福之地,自然物产丰饶。建兰、建漆、建盏,这些带“建”的名词,都与福建息息相关,当是以“建”地而得名。
建盏,蒙尘数百载,光彩不减。那一日,在建盏文创园,透过玻璃展柜与它对视的那一刻,一袭惊艳的黑彩让我惊诧不已,瓷中极品从我眼前轻轻掠过,从此便定格在我的脑海中。它有一个好听易记的名字——建盏。建韵悠悠,兔毫、鹧鸪斑、油滴,是它在烈火中燃烧出的辞章。
建盏滥觞于五代时期,兴盛于宋,一度成为宋人的“掌上宇宙”,几有得一盏而得天下之欣喜若狂。
建盏,一“黑”当先,将黑釉发挥得淋漓尽致,与青瓷、白瓷三分天下。古代建州人不拘泥守旧,敢于创建,黑釉的绚丽多彩、千变万化闪耀在两宋的天空,幻化星云,缀连珍珠,令多少茶人痴迷。龙凤团茶成就了最好的遇见,一只只建盏荡漾起醉人的茶汤,“兔褐金丝宝碗”“甘露来从仙掌”……
一方水土孕育一方器皿。建阳特有的高铁黏土、天赐的釉矿,在工匠的精心调理、打磨下,领受熊熊窑火的加持,瓷中黑牡丹横空出世,飞出武夷山麓。
建盏用另一种方式诠释了黑色。黑,原来也能魅力四射,将深沉、静谧、古朴之美深藏其中。这黑,并不仅仅是单一、单调的黑。在戏剧里,黑脸“属于性格很严肃、不苟言笑的角色,属于中性,代表猛智”。建盏之黑,与此有异曲同工之妙,黑得含蓄,黑得空灵。
一盏立于掌心,“兔”的惟妙惟肖,令我简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远看近看,正看斜看,用放大镜看,有时还能看到一道蓝光的折射,不喝,先就美醉了。那釉是怎样泼洒上去的,然后自然渐次分布其上,纹丝不乱?那釉色,那斑纹,看似本无一物,却又蕴藏乾坤。
再看盏上的鹧鸪斑,还有油滴、曜变,谁施展了神来之笔?一物在手,美上心头。一盏成名,高耸武夷,被宋人誉为“斗茶神器”。
原来与建盏也有过浅浅的缘分。早些年曾有人送我一个从古玩市场淘来的老建盏,残缺不全,兔毫不明朗,器型不正,釉泪也不规整,便搁置一旁,觉得扔掉可惜。后问一名修复的师傅,告知翻新要花上大几百,心想那还不如买一只新的出自名家的。高阁于是便成为它的归宿,偶尔也会拿出来瞧一瞧,那散发着时间意味的包浆,终于让我不忍丢弃。
二
一只鹧鸪身披花斑羽衣,在山边大摇大摆地觅食,小男孩在不远处自由自在地放牛。鹧鸪望了望四周,依然泰然自若,我行我素。这一幕,竟幻化成眼前的一只建盏,想必是老家山坡上飞走的那只鹧鸪变成“盏”,飞进了某个工匠的记忆,从此凝固成如此人间尤物。
假使山中鹧鸪见了建盏,比照之下,恐怕也要自叹弗如,觉得自己漂亮的外衣还是逊色。林地兔子看了建盏,摸一摸一身毛色,也会发出感叹,真是不谋而合,人类的高超技艺简直几可乱真。
手中有一款“非遗”传承人潘建信手做的建盏,摸起来有金属的质感,分量很沉,盏身内外荡漾着逼真的鹧鸪斑,敛口器型。我每日用它喝茶,茶汤微漾,如一阕宋词入耳,时光慢下来,有一种返璞归真的感觉。一盏在手,内心安宁,似有那典雅的《鹧鸪飞》笛声在耳畔萦绕。
“看天做盏,看盏做盏,做盏的人,要懂盏。”潘建信对做盏要求非常严格,他认为每一个盏都是代表着他的一张名片,不允许有瑕疵的作品出厂,要求釉色纹理均匀并能析出晶体的美观。走进他在建阳的工作室,展柜、博古架、工作台上摆满了各种盏与制作工具,整个大厅弥漫着浓郁的文化氛围,合着四溢茶香,透射出一名文化守望者的执着。一边泡茶,他一边说,文化要靠大家去传播,就是要让每个来这里的人,都能认知建盏,都能领略到从宋代走来的这一种文化。
明代《茶疏》记载:“茶滋于水,水藉于器。”喝好茶,更要配好器具。附庸风雅也好,颐养性情也罢,把玩着手中建盏,注视那满身的鹧鸪斑,心便长了翅膀一样在山林溪水间飞翔,融于那山水之中,生出无边的憧憬。
三
建盏,是一抹温暖的色泽,因茶而生,在袅袅茶烟里靓丽绽放,历经六百多年沉寂,终迎来高光再现。一批批工艺师重返建阳,致力于复原传统老工艺,追逐宋式美学。
我曾多次踏访武夷山北麓铅山境内的盏窑里。废弃的文化堆积层历经千年,一块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竖立的“县级文物保护单位”字样的石碑掩藏在树林中,蓬头垢面,藤蔓缠绕,依然坚守着最后的体面。匣钵、残盏、黑瓷片,满山都是,我想拾拣几个回来,捡起来,终于还是轻轻放回原处,它们是属于这片山林的,是这片土地上的精灵。
壬寅秋日又去了一次铅山盏窑里,惭愧的是,一开始居然找不到偌大的废弃的窑址,是拆建的指挥棒改变了村庄模样。直到遇见一位老人,在他的指引下,才如愿到达。
顺着山路慢慢往上爬,堆积层上长满了高高低低的杂木,蓊蓊郁郁,却还是覆盖不了数百甚至上千年前的窑火痕迹,时有暴雨,把不少瓷片、匣钵冲刷下来。山腰上,盏窑废料依然气势恢宏,一堆又一堆,让人以为一直往上攀就能抵达宋朝。树叶婆娑,送来历史深处某个清晨的声音,“我看中了这个”“那个我要了”“这一窑我全包下”……我的眼前浮现出一幅茶盏交易的喧闹图景。
艰难地攀爬,累了,就随意坐在哪块说不定会是文物的匣钵上。这里烧制的黑釉盏,其实和建盏无异,有兔毫、鹧鸪斑,也有油滴……我想,当时这里是不是武夷山那边建盏的加盟合作方,又或是山寨品的地下工厂?此地出品的盏器是不是会翻过武夷山脉挑到福建去,以满足市场需求?或者,它是自有追求独立的存在?山林空茫,没人回答我。
四
老实说,对建盏,我所知不多。从五代、两宋走来的建盏,一路风雨,携带了一杯杯积淀丰厚的文化,岂是一知半解能够说清道明的?
不过,拿釉色来说,建盏的兔毫和鹧鸪斑之间的区别,我还是基本能够独自识别的。兔毫,是长长的线条;鹧鸪斑,是圆圆的。
但是我怎么也分不清鹧鸪斑与油滴的区别,总感觉差不多,都是用来比喻建盏上的点状斑纹。专家级收藏者是能够说出个道道来的,听他们丁是丁卯是卯地解说,那油滴可大可小、可圆可扁,分布可密可疏,彼此融合又各自独立,迟钝如我在实际认读时还是不能完全分辨,常常混淆彼此。好在古籍上统称其为鹧鸪斑,这悄悄地安慰了我,否则我简直要开始怀疑自己的几何认知能力了。
试看五彩缤纷的建盏:金鹧鸪斑、银鹧鸪斑、窑变兔毫、黄兔毫、金油滴、银蓝油滴、曜彩油滴、曜变极光……真令人想变成一滴黑、一团火,去追随那釉彩在高温下千变万化的自然流动,探寻它如何化育出一个个独一无二的“出窑万彩”的未知惊奇。
责任编辑:施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