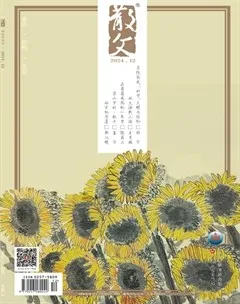在往事中
一
下楼过草坪,是一幢高楼,三十三层,比我住的那栋还高一层。
如果时间往回走,我会在那些打霜的夜晚,灯亮起来的时候,穿过下面的水泥操场,绕过屋角修剪整齐的桂花树,走向那条上山的石板路。路灯稀疏,漆黑的灯柱比别处的矮,底座长锈的灯泡杵在顶上,几乎伸手可及。暗淡的光线落在石板路上,跟深夜一样荒凉。路左弯右折,我拾级而上,偶尔踩到一块松动的石板,发出咔嗒的响声,身子随即跟着晃动一下。路边生着野生的麦冬,结了蓝色的籽粒,像藏族女子衣服上坠着的绿松石。麦冬上面有灌木、藤蔓、荆棘,也有人工种植的南天竹和石楠。
折过两个小于九十度的弯,高高的樟树上爬着苔藓和青藤,大过脸盆的柿子树把光秃秃的枝条伸得老长,亮出一串串灯笼般的柿子。不时能听到鸟叫,山鼠和四脚蛇爬过枯叶窣窣的响声,沁凉的风把枝丫摇得瑟瑟抖动。
朋友的房子就在几棵柿子树后面。矮矮的一层,红砖砌的,刷了层石灰,曾经雪白的墙壁,经过风风雨雨,已经打上了星子般的霉点。枯枝败叶落在瓦屋顶上,一年年累积,一年年腐烂成尘,仿佛积攒了很多季节,有一种曲终人散的冷寂。大隐于市的古人,大概就是选择这样的闹市之隅,从生活撤退,回到自己内心的吧。
月亮还没出来,我站在台阶上,把气喘匀,就着窗口的灯光,抬头望了眼树上通红的柿子,准备往屋里走。门开着,朋友从里面迎出来,平头,清癯的脸,蓝色的裤子,上身一件条纹衬衫。他不会热情地伸出手来,也不会再三说欢迎的话。他用不大的声音喊一声我的名字,接着加上两个字:来了。然后不管我是否答应,就转身往回走。我嗯一声,跟在他后面,迈着愉快的脚步。我习惯了这样的见面,我能猜到下次见面也还会是这样。
书房收拾得干净,水泥地面在白炽灯下泛着青光,书架上摆着整齐的书,多是西方文学,都是他熟读过的。他是外地人,长我十来岁,是山下那所进修学校教外国文学的老师,在业界有相当的名气。木茶几上放着热茶,打火机搁在烟盒上,摆了杯子和酒壶、一碟花生米、一碟炒南瓜子。这些,是接到我的电话之后准备的。他坐在茶几边的藤椅上,我在对面的藤椅上坐下来。他隔着茶几对我笑,像一朵即将开败的花。很有可能,这是这个晚上第一次笑,也是最后一次。
开场白过后,气氛慢慢活跃,我们聊读书、写作,也聊生活中的七七八八,直到没有话题可以继续,陷入各自的沉默。他夹着烟,把身体的重心调整到藤椅靠背上,灯光落在他写满释然的脸上,烟雾在他右手的上方缠绕,像极了一幅信手拈来的速写。这样一帧人生风景,适合安放在他书房背阴的老墙上,他想告诉世界和世界想告诉他的,都在这一根根柔和的线条中了。夜风摇动窗外树木的枝丫,呼呼地响,草绿色的窗纱被吹得唰啦唰啦地颤动,有时候能听到熟透的柿子啪一声掉落下来。
兴致好时,他给我讲普鲁斯特,像在教室里上课那样。这个过程有点长,中间没有停歇,他手中的烟悬着老长一截烟灰,也忘了要敲掉。刹住话尾时,他忍不住叹息一声:唉——贡布雷,斯万家那边。我一时没搞清他叹息什么,只看到他脸上稍纵即逝的惆怅。那些东西,我居然听过后就忘了。等到后来真的读《追忆似水年华》时,只能恍惚想起只言片语,记得清楚的,反倒是他描述窗外的鸟如何啄食柿子。
那些柿子树高得吓人,一串串的柿子年年压弯了枝条,没人去摘,这对鸟来说是一件幸福的事情。柿子熟时,绣眼鸟、喜鹊、红嘴蓝鹊、黄臀鹎,结伴飞来,树上到处是鸟声和鸟影。最打眼的是红嘴蓝鹊,灰蓝色的羽毛,长长的尾巴,尾尖那一小截洁白如雪。这种搭配,高贵而美丽。它们啄食柿子,从底部开始,一点点往里啄,从不浪费,到最后把整只柿子吃完。其间,它们双脚悬在空中,翅膀不停地拍打,看得我的心也跟着悬在半空,生怕一不小心跌落下来。等到柿子吃完,它们就飞走了,第二年柿子熟时又飞了回来。他讲得绘声绘色,缝合了每一年的细节,比我看到的还要生动。
夜深了,我带着几分醉意离开。他关了书房里的灯,走出屋来。月光铺满了台阶,瑟瑟秋风从手臂上爬过。我们在台阶上的月光里默默站立片刻,他抬头望向天空,用感叹的语气说:今晚只怕又会打霜了。我没有回话,向下山的路走去,他在背后喊我的名字,说着下次再来。我没有回头,答应一声,拖着我的影子继续往前走。
后来,朋友去了深圳的女儿那里,不知道他是什么时候从那座房子里搬出来的。过后不久他给我打电话,有请我谅解的意思。他又说不想惊动任何人,老早处理了屋里的东西,只带走了那些书。临走那天,在空房子里放了挂长长的爆竹,踩着满地的爆竹屑来回走了几趟,蹲在上面抽了根烟。他的语速偏慢,声音有些干涩。挂断电话,我发了会儿呆。我搬过多次家,面对过多次去留两难的选择,理解这种沉默而孤独的告别。朋友和我不同,他是迫于无奈才从这里搬出去的,他在这不起眼的屋子里完成了一生中的大事,结婚,生子,退休。这里,是他生命扎实的段落。
那时年轻,以为一切都会这样延续,觉得“沧海桑田”不过是停留在书上的词语。直到朋友去了南方,屋子被推掉,山坡被铲平,一山的树不知所终,没有了灿烂的柿子,朋友和那些鸟一样,离开之后再也没有回来。这才想起没拍几张照片,用画面和色彩,用光和影,留住一段温暖的时光。
已多年没见到朋友,也很少通电话,他已融入南方的生活。我们一样没有逃过时间的劫数,逐渐沦为对方的茫茫人海。
那片土地,变成了对面的高楼。秋天的夜晚,风来来回回,窗口晃动着陌生的灯火,像啄柿子的鸟拍打着翅膀。
二
傍晚回家,围墙上多了几个“拆”字,刚喷上去的,一股刺鼻的油漆味。扫了一眼继续往前走,我不太相信这片房子最后真的会被拆掉。
确是有些旧了,墙褪了色,不知名的草从水泥的裂缝里钻出来,门窗上的油漆正在剥落。这些不难处理,稍微修葺一下就行。这里是一所进修学校,还有一所附属小学,老师学生加在一起有两千多人。谭嗣同的夫人李闰在这里办过新学,县城里的人把这一带称为“龙脉”。
反对声一片,到底敌不过城市中心的寸土寸金,几轮协调会过后,里面的人风流云散,一夜之间不见了踪影。一天早晨,各种机械张牙舞爪地开来,把房子轰隆隆地推倒,腾起漫天灰尘。又来了六七台洒水车,嚣张的尘埃在水柱的嘶叫声中最终落了下风。我看着房子推倒后的残垣断壁,在心里惋惜了一回。这样的惋惜,除了表达一下个人的小情小绪,没有任何实际用处。
我决定在这里买一套房子,我原来的住房就在附近,和这里隔着一条小巷、一扇围墙,也就是几步之遥。我习惯了这里的风雨、阳光、树木、河流和天空,并由此想到,这世间不只人与人之间讲缘分,人和土地之间,或许也一样。
城市中心最后一个楼盘,卖得十分抢手,破天荒地采用了抽签的方式。我抽到的是169号,待选房时,只剩下有限的几套了。我被动地接受了靠北一栋三十楼的四居室,那里原来是附小开垦的菜地,老师带着孩子们在里面种白菜、萝卜、南瓜、丝瓜、黄豆。每一畦的两端各插一块木牌子,上面写着班级的名字。那些菜踩着季节的拍子,在那片新垦的土地上张灯结彩。
房子在施工,像植物一样一天天向上长,每天路过时我都要抬头看看,想象一番住进去的情形,有一丝年轻时想与恋人见面那样的期待,但又无法说清具体期待的是什么。
房子装修的时候,我正在外地采访,十天半月回家打个转。每次傍晚下车后,拖着行李箱,第一件事都是去看装修的房子,给装修工递烟,自己也点一根,然后坐在窗台上,和他们说话,看他们贴地砖、粉墙、抛光、做背景墙,像燕子筑巢一样,衔来泥土,一点点垒。
这时,我反倒不急着住进来了。我往窗外眺望自己原来住的房子,红色的屋顶,楼下有一个小院,隔着空间打量,如看到故人一样亲切。这样的黄昏,我喜欢站在窗前凝望远处,夕阳轻轻一捺,把河对岸的山头涂成玫瑰色,满河波光映在窗玻璃上,夹杂着云影、树影、街影。在黑夜到来之前,我会在心里画春风、画马、画纯粹的雪山,那些遥远的事物,仿佛在我眼前成了温驯的现实。或者什么也不做,就泡一杯茶,慢慢地喝,看杯子里的茶叶一片片舒展,搭建起一座雨后的峰峦。街边的樟树被风吹得呼呼地响,柔和的光把我的影子投在洁白的地砖上。
三
新房空了一年之后,我还是搬进来了,没有看皇历,也没有打爆竹,只带了些半新的生活用品、一摞常看的书。我还保持着买书的兴趣,空空的书架有待时间去填充。
装修称得上简约,用的是浅色。浅褐色的橡木地板、浅白色的墙壁、浅蓝色的窗帘、普通的吸顶灯,家具也选了浅黄色的胡桃木。我热爱浅色的明亮与柔软,像鱼在江河中怀抱着澄澈,我期待用色彩消解自己与房子之间的隔膜。我又一次感受到了色彩的力量,它们沉默而执着,接纳我,贴近我,宽容我,目送我离开,等着我归来,给我制造出一种若无其事的氛围,像时间,悄无声息地稀释我心中的那份疏离。
不适应的是坐电梯。在有限的空间里,我尽量拉开与陌生面孔的距离,把头低下,努力假装对方并不存在。并非每次都能这样,碰上拥挤,还是会有压迫感,能听到对方的呼吸,闻到他们身上明显的烟草味,还有隐约的汗臭和刺鼻的香水混合着洗发水的味道,看到他们脸上夸张的欢乐和尽力隐藏的悲戚。有时里面只两个人,就只能调动面部肌肉,拿出绅士风度,礼貌地笑着向对方点头。这是母亲和老师小时候教的,他们不像如今教孩子一样轻言细语极尽温柔:宝贝,要做个懂礼貌的孩子。他们板着脸,极其严肃地说:做人,要懂规矩。
过去的操场铺上了草皮,黄昏,斜阳抚摸着满地青草,犹如南方的草原,仿佛能听到一匹老马在其间嘶叫。夜晚,我坐在草坪里的小石凳或木棚架下抽烟,在飘散的烟雾里,能看到人家看不到的东西:教学楼、菜地、朋友的房子、高大的柿子树、光芒照耀的柿子、吃柿子的鸟、朋友那张清癯的面孔,还有茶几上的酒。似乎从搬来这里开始,我就生活在往事之中,我在那幅经线和纬线曲折纠缠的时光地图中奔走,停驻,和生活对峙,然后,再与它握手言和。
责任编辑:田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