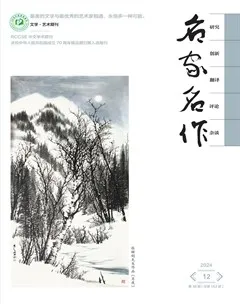传统文化视域下的担当与情怀书写
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认为,人通过学养达到“仁”的境界,修养为谦谦君子,有浩然正气,心怀苍生,道济天下,不会陷溺于物欲、色欲和权力之中。石清礼先生的长篇小说《孤独的爱》将近50万字,波澜壮阔、大气磅礴,叙写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七十多年的奋斗征程,从20世纪60年代初的自然灾害写起,一直到“飞鹰”翱翔中空的科技时代止。小说人物形象生动鲜明,故事情节跌宕起伏,传达出的价值观、人生观引人深思、催人奋进。
首先,塑造了宋志纯这个爱国爱民、有情有义、忠诚有担当的清官形象。小说重要的一条线索是“让信仰坚定起来”,作者也直言“想写一个好官”,主人公宋志纯确实是当之无愧的人民好公仆。他成长在心怀赤诚干革命的老党员之家,他的父亲宋晨勇于担当,让社员保留自留地,安稳度过饥荒难关;遇到叛徒陷害同志也有勇有谋,将计就计地解除危机。父亲的所作所为对年幼的志纯有很大的影响。所以,当十岁的小志纯得知因家里缺粮会威胁两个弟弟的生命而迫不得已需将自己“送走”后,尽管有百般不舍,还是毅然决定离开父母温暖的怀抱,主动去柴房适应独居生活。
心之所之谓之志,心中的高远向往就称之为志。主人公宋志纯“立志做大官,还百姓以温饱”。在去乌兰布统的路上看见成群的饥民,他花光了从同学吴云生那里借来的钱买了饭,办了“糊糊宴”救济饥民,这样的经历也更加坚定了自己的理想——做个好官。宋志纯有这样的志向,一是源于老党员父亲宋晨的影响,二是源于自己心底的那份善良。因这份善良,所以他能为处于困难中的人设身处地考虑,并出手相助。作者在书中也一再强调“同情心是人性的最高表现”。《孟子·公孙丑上》中说:“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孟子说:“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就是说,当我们看到一个小孩即将掉入井里的时候,无论是谁都会伸手去救,不会考虑利害得失。这正如小说主人公宋志纯看到饥民,就不忍心让他们饥肠辘辘一样。这也是他在“华美洗浴”遇见落入风尘的于佳佳,又一次挺身而出,救她出火坑的原因;还有看到凡云乡村民居住在危险的土窑洞而毅然决定尽快开展建设新兴民居的原因。
恻隐之心,人皆有之,但为什么像刘世道、李继峰、康熠、吴全之流却没有。关键还是在于立志和习性的熏染。立志做什么,就是排除万难也要做,信仰志向坚定,就不会改弦易辙。而没有高远志向的人,往往会在人生旅途中受形形色色的利益、权力、美色的诱导而误入歧途,掉进深渊无法自拔,最终难逃厄运。小说中刘世道、段明被灭口横死,李继峰纵酒纵欲而猝亡,康熠被绳之以法,吴全接受中纪委的调查等,都印证了这个道理。
宋志纯心系乡民、国家、民族,在从政的道路上尽管受到排挤、陷害,但心志不改,初心未变。洪州、宇通在宋志纯主政时改善民生、发展经济、传承文化、创新科技,面面俱到,四处开花。离开哪里,民众都依依不舍;去到哪里,百姓都热烈欢迎。这样的官是真正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的好官、清官。他为人质朴、清贫,一直坚持住单位宿舍,出行坐公交车,不占百姓便宜,不吃回扣,拒收红包、信封,坚决不收“书包”“蛇皮袋”。正是有这样坚定的信仰,才在升任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时急流勇退,辞官潜心著书立说。辞官的情节的确有些出乎人意料,但又合情合理,也正是有这样的情节,才表明主人公超越了功名利禄,没有陷溺在权力和欲望之中,真正凸显了“让信仰坚定起来”的信念。
其次,歌颂了纯真的感情,对感情的坚贞与热烈感人肺腑、动人心魄。爱情之于生命是不可或缺的靓丽色彩,追求爱情是人之为人的本能,也是生命活力的体现。冯友兰弟子蒙培元先生从情感的角度谈中国哲学、中国智慧的特殊性时,他认为“情感是最原始、最基本的,同时又是最‘形而上’的。谈生命问题而不谈情感,就犹如观花而不观蕊一样,是难以理解的”。中国哲学特别是儒家哲学尤为重视人的情感,孝悌思想就源于人最天然的感情,父母以爱抚育子女,子女以爱孝敬回报父母,兄弟姐妹之间相亲相爱,朋友之信、夫妻之情、上下级之看重与尊敬,莫不是从肝膈中天然流露出的真情。
主人公宋志纯拥有广博的爱,爱国家、爱百姓、爱父母、爱同学,更珍惜美好的爱情。他将初恋视若珍宝,可惜那颠倒的无常世界和邪恶的“两脚动物”摧残了她的恋人,令人感动的是,他能以博大的胸怀容纳被摧残的恋人,并且很理性地做了清晰判断:这不是恋人方倩的错。即便如此,他还是被爱人“抛弃”,受伤的心化成无言的动力,四处奔波为百姓谋福利,将百姓的吃、穿、住、行都挂在心上,只有在深夜,才会舔舐着伤口,默默承受孤独的滋味。踽踽独行数十年,直到遇到了比他小二十多岁的宁若云,他才打开尘封已久的心门。宁若云缺失父爱,被稳重踏实、文采斐然又散发着成熟男人魅力的宋志纯深深吸引,坠入爱河不能自拔。在滔滔的塞纳河边,激情四射、感情充沛的年轻姑娘宁若云热烈地表达了对宋志纯的痴迷与深爱:“志纯哥若拒绝我,我会把生命托付给塞纳河的滚滚波涛……”在宁若云“威胁式”的多次表白中,宋志纯才正视了渴望爱的心灵。也许,这种“忘年交式”的老少恋会招来世俗的睥睨甚至声讨,小说的此番创作虽有讨新奇之嫌,却也合情合理。试想,如若不是遇到年轻而充满炽热之爱的少女宁若云,怎么会让宋志纯重新开启爱之心门?
作者把宋志纯塑造成遇到美女依旧坐怀不乱的“柳下惠”,他跟方倩在乌兰布统临别前夜秉烛夜谈,在方倩复员后送她去林岩县的那晚,两人以夫妻名义在卫东旅社度过一宿,但没有越雷池半步。当欲望的闸门升起,洪流肆虐,情爱混杂其间,分不清是情还是欲时,“让爱情高尚起来”却是一股清流,告诉人们“发乎情止乎礼”的谦谦君子原来这么难能可贵。“礼之用,和为贵”,任何失衡的放纵都会变质走样。正如小说中所言:“利益扭合的利用之情,男女苟合的欲望之情,都会在信仰铸就的真情面前被埋葬、被揭露、被抛弃!”
再次,关于生命、社会的思考发人深省、引人深思,哲思意味浓烈的“欲之论”很有深度。情欲是真实、自然、原始的生命“动力”,向上升腾就有了道德意味,“以礼节之”,再向上升腾就到了信仰阶段。西方的信仰在宗教,华夏的信仰在文化,在文化中可以找到人生的使命,进而就能找到生命的意义。正如《论语》中的最后一句话:“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大学》开篇就说:“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人生的意义就是要拂去蒙尘,唤醒生命之光,而后“止于至善”,经定静安虑得,方可修齐治平。
小说通过宋志纯、方倩、宁燕等人的多舛命运,写出了世事的无常与不可捉摸,作者多次把不可把握的命运比喻成万花筒:“多彩的碎玻璃粒,装在纸筒中,筒端用透明玻璃盖实,转一下,给一个条件,就是一个图像,一个近似测色盲那样的图景,人的命运,何尝不是这样呢?”在时代的洪流中,人犹如波涛中的一滴水,不知道命运的河流会流向哪里。但正如作者有坚定的写作宗旨一样,“让信仰坚定起来,让爱情高尚起来”,就是想写一个好官。所以,小说主人公宋志纯亦有坚定且崇高的志向,他高大光辉的形象就站立了起来。
贯穿小说始终的“欲之论”颇有精辟之语,发人深省。处在贫穷饥饿之中且没有尊严的人们追求美好生73784833af8a2e3659a6a652ed9cef8c22e2734d3be37a7ba093abdb9c2dbb6e活的愿望,东方哲人称之为天理,姑且解释为合理的欲望。但“当欲望膨胀的时候,人格就被扭曲了”。小说中李继峰、吴全之徒便是如此。小说借主人公宋志纯之口表达了作者的观点:“信仰与欲望相连,一切正义与一切罪恶,都源于信仰与欲望。欲望有两重性。正欲,即代表大众利益的欲望,可以培植高尚的信仰;反之,会是恶念恶欲,会祸害这个社会。恶欲毁灭一切,正欲创造一切。”其实,善恶只在于公私上,关键在于利人还是利己,如果是为大众、为人类造福的,就是善,就是信仰;如果是为了满足个人私欲,就是恶。无止境地追求私欲,就坠入了恶的深渊,很难回头。
华夏的哲人心怀光明,他们笃信人性本善,不愿意吹灭那盏暗夜里的灯,所以他们认为所有的恶,不过是人心之上蒙尘纳垢暗淡了心之光明,导致他们误入歧途干了很多“荒唐事”,仍坚定地为误入歧途者留有后路,时刻期盼“浪子回头”,还给予极高赞赏,夸其“金不换”。
小说名叫《孤独的爱》,主人公宋志纯的官场之路、情爱之路确实走得不热闹,甚至真的有点孤独。作为省市级干部,跟新入职的员工一起住单身公寓,那么多个日日夜夜,踽踽独行在林荫小道,默默咀嚼在餐桌前,他的身影多少有些孤单,甚至落寞。被方倩“莫名其妙”抛弃后,感情生活出现的空档那么长,拒绝过很多追求者,让夜夜笙歌者着实无法理解。但也正因为是小说,这个高大的主人公形象可以被作者塑造得这么伟岸、这么纯正、这么清晰,他不应当被放在俗世中与众人比对是否失真,他犹如暗夜中的灯塔,指引信仰坚守者航行的方向。在波涛汹涌里、在狂风暴雨中、在乌云压顶下,给善良者、正直者、有信仰者孤身闯暗巷的勇气,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最后,引用《论语》中的一句话作结:“德不孤,必有邻。”
作者单位:朔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基金项目:校本课题“师范院校基于地方文化精神的立德树人教育实践策略研究”(项目编号:2024XBY006)。
作者简介:王黛(1980—),女,山西五台人,副教授,朔州市文艺评论家协会理事,研究方向:明清文学、传统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