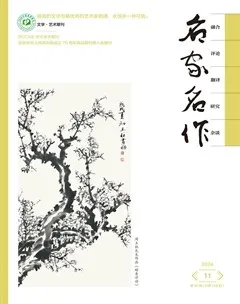贡布里希的图式-矫正理论研究
[摘 要] 为了扫除黑格尔的历史决定论在人文领域长久以来的消极影响、理清艺术风格的发展规律,贡布里希借助心理学、美学、哲学等各类学科知识,提出图式-矫正理论,指出写实作品的创作是依靠图式开始并且由对图式的不断矫正完成的。贡布里希在《艺术与错觉——图画再现的心理学研究》一书中系统地阐释了图式-矫正理论的内涵,指出艺术风格的真正成因是艺术家对图式的研习和应用,并且不同的图式应用又造就了不同的艺术风格。试图对贡布里希在《艺术与错觉——图画再现的心理学研究》一书中对图式-矫正理论的阐述进行系统梳理,探究图式-矫正理论的来源、内涵以及应用,尝试总结贡布里希关于图式-矫正理论的核心。
[关 键 词] 图式-矫正理论;心理定向;贡布里希;投射;艺术风格
贡布里希关于图式-矫正理论的提出要追溯到他对艺术风格的探讨上,而这就不得不提德国哲学家黑格尔关于艺术史发表的见解。在黑格尔的著作《历史哲学》中,他认为人类历史必然会经历由早期萌芽到发展再到晚期衰败三个阶段,艺术的发展也必然会经历这三个阶段:“象征的艺术在摸索内在意义与外在形象的、完满的统一,古典型艺术在把具有实体内容的个性表现为感性关照的对象之中找到了这种统一,而浪漫型艺术在突出精神性之中又越出了这种统一。”在黑格尔看来,人类的一切活动都应是彰显其“时代精神”的,而艺术的主要任务就是要担负起时代的使命,艺术风格则是源于其“时代精神”的,是一个时代的表现。[1]贡布里希并不认同“风格是时代的表达”这一观点,他反对黑格尔宣称的所谓“大写的艺术”,认为黑格尔的历史决定论严重压缩了艺术的发展空间。为了摒除艺术研究中的进化论、历史决定论、时代精神、文化相对主义等非理性的思想,贡布里希开始了关于艺术的研究,并提出了图式-矫正理论。
一、理论提出的渊源
首先,康德提出“图式”概念,并把概念运用到哲学层面。在康德看来,图式是先验产物,是一种能够与感觉和知性相互联系的纯粹形式。它先天存在于人脑中,是获得其他知识的前提条件。这一“图式”概念的提出,说明了人在认知过程的主体作用。康德认为,主体在解决认知问题时要调用预先存在的图式对其进行知觉分类。让·皮亚杰在康德的基础上对儿童认识论发生的心理过程进行了研究,提出人会通过“同化”“顺应”的方式使自身适应环境的不断变化。其次,乔尔乔·瓦萨里认为,新艺术形式的再现是依靠一批批艺术家来完成的,后人就是在前人的基础上不断地做出矫正才使得艺术技术不断精进。贡布里希在瓦萨里的基础上,对他的观点进行了革新。贡布里希赞同他对于艺术家创造使用新图式的赞赏,同时也否认了关于艺术家的创造仅是模仿现实的锦上添花的观点,说明画家之所以会画出不符合现实的图像,仅仅是因为他们没有合适的图像与之相匹配。
在此期间,贡布里希的老师尤里乌斯·冯·施洛塞尔对贡布里希的支持与影响,也帮助贡布里希完成了这一理论的建立。同时期的瓦尔堡学派也对贡布里希对图式的探讨产生了深厚的影响,瓦尔堡对艺术史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文艺复兴时期的作品上,他发现这一时期的艺术家在艺术创作上虽然强调要通过观察去描绘事物,但在实际创作过程中,他们会反复地去借鉴古典形式以求得处理新形式的公式。这种在创作过程中对公式依赖的观点影响了同一时期对图像学进行研究的施洛塞尔,而这种观点也同样深刻地影响着贡布里希。贡布里希的图式-矫正理论还吸纳了格式塔心理学的内容,在鲁道夫·阿恩海姆的著作《艺术与视知觉》中就运用了心理学的知识,受本书的启发,贡布里希也将其视为处理视觉理论的一个新的角度。在提出理论期间,贡布里希与其好友卡尔·R.波普尔也在不断地进行探讨,好友在科学观点上的新见解也影响了贡布里希图式-矫正理论的建立。波普尔认为,科学的根本性质在于猜测与反驳,在不断地建立假设与推翻假设中,逐渐摸索到真相的轮廓,而这种不断地试错才是探索科学的唯一方法。这一观点的提出启发了贡布里希,他也因此对黑格尔的历史决定论提出了质疑,合理地推测出图式的发展应该是依靠艺术家不断地修正和完善。
二、图式是什么
图式就是图画的公式,是艺术创作之前要学习的绘画方法或是创作范式。相较于个别某一形象时,图式是这一类形象的共相,或者说是这一类形象的普遍形式。贡布里希认为,没有图式就没办法进行再现性的绘画,“他不是从他的视觉印象入手,而是从他的观念或概念入手”[2]63,被描绘的形象首先要嵌入艺术家已有的观念中,然后再加上那些有特征的、个别的视觉信息作为对图式的矫正。这种已有的对某形象的概念就是图式,没有这种图式作为基础框架,形象将无法被把握,“仅仅观看一个母题是毫无意义的,除非你已知道在那些图式形式的网络中怎样予以分类和捕捉”。所有的艺术家在再现新对象时都是先将对象与现有的图式进行比较,选择较为相近的图式,再对原有图式进行进一步的补充、修改、矫正,以达到再现要求的最低限度。作为艺术创作的开端,图式不同于柏拉图所讲的理念,它不是形而上意义上的存于理念世界的。柏拉图将世界分为三类,即理念世界、现实世界、艺术世界。现实世界是对理念世界的模仿,艺术世界又是对现实世界的模仿。柏拉图认为,艺术这种对理念世界“模仿的模仿”是粗鄙的,应该被排除在理想国之外的。艺术家创造的仅仅是“形相”、是错觉世界,这种远离理念世界的模仿是远于真理的、是不合法的。这种形而上的理念存在于理念世界中,与贡布里希所谈的在实际创作与绘画过程中所使用的图式不是同一概念,不应进行混淆。
贡布里希认为,艺术家在进行写实艺术创作时,必须掌握图式,这些被整理归纳出的绘画公式能辅助画家更好地完成创作。像我们熟悉的《芥子园画谱》就是一本由大量的图式汇编而成的用于指导绘画的教材类书籍,这类书籍的存在就为艺术家提供了最初的图式参考与借鉴。贡布里希指出,写实艺术并非在摹写共相的模式,或是某一事物的理念。“不论是在思想上还是在知觉上,我们都不是学概括。我们所学的是把毫无差别的一个整体特殊化、分节化,做出一些区分。”[2]86“图式并不是一种‘抽象’过程的产物,也不是一种‘简化’倾向的产物;图式代表那首次近似的、松散的类目,这个类目逐渐地加紧以适合那应复现出来的形状。”[2]64艺术家越是要创作,就越离不开图式,这份对于图式的依赖源于对事物规律性的追求,艺术家“必须努力增加对于共相的知识,必须十分全面地掌握事物的结构,以求能呈现这些事物在任何一个空间上下文的样子”[2]77。
三、如何选择图式
在贡布里希看来,画家在观察再现物的形象时会在脑海中搜刮一个与之相符合的图式,比如艺术家要画一只他从未见过的鸟,他就会迅速地在画布上画下他所学习过的关于一般鸟的图式,然后经过不断地与实物进行比对,逐一矫正图式中那些与再现物不相符的部分,使它最终符合再现物的形象;如若再现物是艺术家从未涉及的新形象,他无法在脑海中准确找到同类型的图式进行绘画,这时关于图式的选择就要依靠艺术家对其进行的心理投射来筛选,他可能会将其类比成一种特殊的鹰,或者是长着猫脸的鸟。在摹写的全过程中,摹写对象和观察到的形象以及复写出的形象不相同时,这一概念可以类比郑板桥的“眼中之竹、胸中之竹、手中之竹”,依照赞格威尔的话来讲,这一过程是包括“对形象的构成或再构成性质”的。在这种转写过程中,如果没有对应的图式,艺术家将会运用旧有的图式对形象进行复写,而这种复写将使得这一新形象被旧的图式和模式同化,此过程被称为“同调意志”。
原始艺术之所以给人一种不协调、生硬的感觉,正是因同调意志的影响。在原始艺术中,创作者更多地关注那些区别性的特征,当时的写实艺术强调区分要多于对真实性或相似性的追求,又因为旧有的图式很少,所以造成画面的生硬。贡布里希在此强调,虽然传统图式没有办法准确无误地描绘新形象,但通过认知的分节过程,对新形象进行试错法的分类与匹配,还是能够将其与其他类目分开的,所以“虽然不是忠实地记录一个视觉经验,而是忠实地构成一个关系模型”,但是仍然不妨碍它所传递的概念的清晰性。由此出发,贡布里希尝试对最初的图式来源进行摸索,他认为最初的图式很可能来源于原始人将偶然在岩壁上或是石头上发现的图形视为熟悉之物的这种心理投射作用,“这就是观者通过尝试性的投射,逐步排除画面的多义性……而将视觉世界的外貌投射上去,以完成从形、色密码向视觉信息的译解、转换过程”[3]。这些偶然的形象使人感到一种熟悉之物的身影,这种错觉的暗示来源于原始人最初的心理定向,他们对生存环境的探索、对狩猎物的观察、对死亡威胁的恐惧,构成了他们的心理定向,使得原始人对一切的类似物都保持着高度的机警。这同时也造就了他们不同于现在艺术家而拥有的那种宽泛且模糊的投射范围,使得原始艺术的图式远离它的母题,以至于直接造就了原始艺术生硬的风格。
虽然图式是艺术创作的第一步,但并不说明图式完全是有益于艺术创作的。“图式表现为速记表示法的形式,一旦时机到来,艺术家便予以扩展和填充”,“但是,这样依赖图式显然会阻碍走向有效描绘的道路,除非艺术家还始终愿意予以矫正和修改”[2]132。长久以来,受制于柏拉图形而上学观点的艺术家们不敢撼动旧有图式的权威性,“艺术家应该再现共相而不是再现个体,艺术家绝不应该奴隶般地摹写自然中的偶然事件,而是应该坚定地着眼于理想”,于是他们能做的就只有沿袭学习到的图式,面对新的母题进行不着一处修改的应用。也因此,柏拉图对埃及艺术大加称赞,对希腊艺术却嗤之以鼻。这种现象一直到中世纪以后才有所好转,“对于中世纪而言,图式就是图像;对于中世纪以后的艺术家而言,图式是进行矫正、调整、顺应的出发点,是探索现实、处理个体的手段”[2]148。
四、矫正受到的影响
(一)受绘画目的影响
16世纪,德国报纸为了报道罗马当地的水灾曾刊出这样一幅木刻画,画面的主体是位于罗马的圣天使堡。作为新闻的说明画,它绝不存在艺术家的主观构想,也不存在为了展现个人的审美偏好而偏离母题的问题。但尽管这样,这幅木刻画依然偏离了它的再现物。画家在这幅画中,将罗马的圣天使堡冠以德国城镇中城堡的样貌,很显然画家是将母题嵌入了他对于一般城堡概念的图式中,并将他所知的关于圣天使堡的特征形象作为细节加入了对图式的矫正里,这样一来,这幅画既符合当时人们对于城堡的定义,又有不同于图式的属于圣天使堡的区别性特征,以此分辨新闻专指的水灾发生的场所。艺术家对新形象的处理是将它嵌套进原有的图式中,再加入那些观察或记录到的显著性区别,将图式矫正至能够被区分为止,他们不会再去进一步比对图式与新形象究竟有哪些不同,因为“他没有理由去观察那些没有要求他传达的东西”[2]103。
(二)受心理定向影响
“艺术家会被可以用他的惯用手法去描绘的那些母题所吸引。他审视风景时,那些能够成功地跟他业已掌握的图式相匹配的景象就会跃然而出,成为注意的中心。风格跟手段一样,也创造了一种心理定向,使得艺术家在四周的景色中寻找一些他能够描绘的方面。绘画是一种活动,所以艺术家的倾向是看到他要画的东西,而不是画他所看到的东西。”[2]73受心理定向影响,艺术家总是倾向去看他要画的东西,选择他所熟悉的内容进行矫正。上文中所提到的心理投射作用正是受心理定向的影响。罗夏实验说明了心理知觉与心理投射只存在程度上的差异,意识到这种知觉过程的被称作“解释”,没有意识到的快速的投射被称之为“看见”,这一结果也证实了阿尔贝蒂在《论雕塑》中将模仿自然创造物的艺术的起源归结于原始人对自然物的偶然投射的猜想。贡布里希赞同这一观点并指出,不同的族群有着不同的心理定向,所以对同一图形会产生不同的心理投射。“我们把这些偶然形状读解为什么形象,取决于从它们之中辨认出已经存储在自己心灵中的事物或图像的能力。”[2]155模糊的指称作为图式可以充当投射图像的对象。能够将什么投射上去则取决于他们的心理定向,人只能看到他想要看到的东西,于是在面对这一片“可能状态的合集”时,能够分解出什么形象,就完全依靠观察者自身的经验与状态。
(三)受绘画工具的影响
艺术家所选用的工具在很大程度上会限制艺术创作,“当艺术家手执铅笔坐在母题前面时……他倾向于从线条的角度去看他的母题,而当他手执画笔时,他就从块面的角度去看母题”[2]56。受限于绘画工具,艺术家会倾向于考量那些他能够再现出来的地方,运用铅笔进行绘画时,他们会更多地考虑明暗关系或是排线;当他们用毛笔去再现景物时,他们会更注重画面的留白、墨汁的饱渴或晕染的深浅;当他们用油画去再现自然时,他们又转而去留心色彩的关系。
(四)受时代限制影响
不同时期的艺术作品反映的艺术要求不同、追随的主流艺术类型不同,促使艺术家对图式的矫正也不同。古埃及艺术受正面律的限制,艺术家便不会去完全依照着事实进行作画,他们创作的人物形象统一、风格规整,并且受到信仰的限制,艺术家无法也不敢对图像进行自由的创作,如在墓中的那些被看作具有神圣性和信仰效力的“图画文字符号被弄得残缺不全,意在防止其危害到 死者”[2]119;古希腊时期的艺术追求“高贵的单纯,静穆的伟大”,对人体的刻画更彰显其细腻,中世纪的艺术作品则受限于宗教信仰,艺术创作大多服务于基督教。
参考文献:
[1]穆宝清. 理性与传统:贡布里希艺术美学思想研究[D].杭州:浙江大学,2015.
[2]E.H.贡布里希. 艺术与错觉:图画再现的心理学研究[M].杨成凯,李本正,范景中,译.南宁:广西美术出版社,2012.
[3]周彦.视觉艺术心理的经验描述贡布里希《艺术与幻觉》研究[J].新美术,1987(3):61-72.
作者单位:黑龙江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