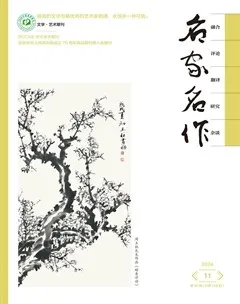中西文化融合和民族艺术深化的体现
[摘 要] 作为西藏第一代藏族油画家,次仁多吉无论是对现代艺术的理解,还是对民族艺术的认知,都打破了区域的局限性,开拓了新的道路,为西藏艺术甚至是中国艺术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他是西藏美术史上探索写意性油画的第一人,画作先后受到欧洲古典油画、后期印象派以及表现画派等艺术表现形式的影响。从历史背景、求学经历、情感等方面进行阐述,抛砖引玉,让更多人认识这位在西藏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艺术家。
[关 键 词] 民族艺术;次仁多吉;艺术风格;绘画语言;中西文化融合
作者简介:田苒苒(2000—),女,汉族,山东聊城人,硕士研究生在读,研究方向:美术与书法(油画方向)。
2024年8月中旬,西藏油画家次仁多吉于西藏美术馆的展览——色彩与幻想正式开幕。作为西藏第一代藏族油画家,次仁多吉无论是对现代艺术的理解,还是对民族艺术的认知,都打破了区域的局限性,开拓了新的道路,为西藏艺术甚至是中国艺术作出了很大的贡献,是西藏美术史上探索写意性油画第一人。其画作先后受到欧洲古典油画、后期印象派以及表现画派等艺术表现形式的影响。在中国现代艺术语境下,对西藏题材的艺术创作工作者提供了新的启示与可能性,在探索多样性艺术道路上起到了引领作用。他将西藏文化与内涵中奔放潇洒的一面幻化作笔触与色彩恣意挥洒在画布上,用细腻入微的情感做链接,使画面与观赏者内心产生共鸣。这是触动心灵的艺术盛宴,引领我们透过岁月,去细细聆听这位艺术家的内心世界与艺术征程。
一、历史背景及求学经历
在20世纪,西方现代艺术环境因为新艺术扰动不安,各种相互对立的艺术运动流派都锋芒毕露,都认为自己将会赢得国际的关注,积极地发布各种宣言。立体派、表现派、野兽派、未来派、后印象派与漩涡画派都大肆宣扬自己的艺术。在20世纪的中国现代艺术发展的历程中,特别是在20世纪30年代前后,上海作为一个包容性、接纳性极强的国际化大都市,与巴黎、纽约、东京等城市建立了文化思想传播互动的交流地。20世纪前期,中国洋画运动的演变和发展以上海为交流和发展的活动中心,呈现出上海现代艺术与国际接轨的精英化和大众传播的格局,串起了中国与西方的联系,出现了国内最初的现代主义艺术的对话,推动了中国艺术界与国际艺术舞台接轨,使国内艺术家在国际艺术语境视角下,更加理性地对待中国艺术的发展,意识到中国油画站在前人的肩膀上会走得更坚实且铿锵有力。中国绘画由此逐渐融合西方绘画关于客观结构、色彩、形式表现的诠释。
次仁多吉先生正是在这种大环境下到上海戏剧学院舞台美术系求学。当时,上海与西方艺术的联系增加了他成功探索国内少有人涉足的艺术领域的可能性。舞台美术是一个统称,它综合了布景、化妆、灯光、道具、装置、音响等因素,其中每个组成部分都紧密相连。简单来说,通过改变灯光的色彩与方向,再与搭建的景、音效配合进行演绎。因此在上戏的理论系统学习加之多年舞美的经验让次仁多吉先生愈加理解如何利用色彩对艺术感情进行输出。之后,机遇再次来临,次仁多吉得以在中央美术学院油画系进修,同期研修班同学是来自全国各地较成熟的艺术家,持有不同观念的艺术家聚集在一处交流,在共同绘画中容易摩擦出全新艺术思想的火花,对于自身艺术思想的选择会产生更深刻的理解。中央美术学院的教学以全因素素描为主,更全面地考虑画面的各种元素,使得画面富有体积感和块面感,完成度高且大气,为今后创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二、绘画语言的探索
艺术家在作画时要找出侧重点,一般根据细节的刻画程度来进行区分。在他的画作中不仅细节描绘很到位,更充分利用了光线。就像舞台剧运用灯光对重要事物着重照射,以此提醒观众关键处的位置一样。他非常巧妙地将理论知识融入了油画创作中。
造型的建立离不开扎实的基本功。戴士和在《戴氏论坛》中说:“造型的‘整体感’,就是在还没有五官细节前,人物的神韵风采、动态、比例,什么都已经在里面了。”这句话也适用于各种题材的油画创作中,创作力求以简略几笔画出韵味,次仁多吉便是这样。他规避了只着眼于处理局部细节的陷阱,更加注重画面整体效果。对画面整体性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去理解分析,在阶段性的画作中有所体现。另外,整体性也使他最大化发挥了个人能力,想象创造力也达到最大化。
当拥有对画面整体性把握的能力时,便会主动赋予画作新的生命力。培养再创造的想象力是主动性的基础,对客观存在事物选取加工,造自己的“形”显得尤为重要。造自己的“形”能更明确表达次仁多吉在画面中想要描绘的思想感情。还有次仁多吉是主动地进行创作,主动与被动这两种方式看似毫无区别,实则天差地别。主动性创作具有激情与活力,观察会更仔细、思维会更活跃、处理会更加灵活且具有个人特性。次仁多吉作品画面的规划是缜密、密不透风的,从打动自己内心的点出发,进而思考为何要选择这个切入点,将怎样打动人心,自己将如何表现它?他在进行创作前,大脑对画作进行精细、全面的计划,画面处理以整体性为重点,进而寻找打动内心的点,从这一突破口切入进行创作。紧接着确定色调、画面形状安排、设计细节位置、画面的动态走势等。
次仁多吉的画作也具有一定的写意性。写意油画的概念是由罗公柳先生最先提出的,当时他刚从苏联留学归来,提倡将中国传统绘画的写意性与欧洲油画的强大表现力结合起来。无论是王维的“凡画山水,意在笔先”,还是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中论顾恺之画“虽笔不周而意周”,都能看出中国写意画更偏向强调写意中的“意”,将“写”排在了后面,并且以“意”为目标。而所谓的“意”,是建立的整体美学观,也是画家对世界的整体看法。近代以来中国写意画创作的突出特征是更加侧重于色彩的表现与运用,这也恰恰是次仁多吉画作所呈现出来的精神理念。通过在色彩上所做的各种尝试,使油画的色彩表现力达到最大化。同时因为次仁多吉牢固坚实的绘画功底,让画作既有色彩表现力又有画面整体的平衡感。
三、个人情感、经历对绘画语言形式的影响
次仁多吉深受夏加尔、德朗、库尔贝、苏丁、凡·高等启发,尤其是梵高与苏丁。他与梵高、苏丁在个人性格以及环境背景上似乎有着千丝万缕的共性,都曾在困难环境中生存并勇于追寻自己所爱的事业。次仁多吉选取前人艺术家的艺术表现方法融入自己的绘画技法中,并且将这些绘画语言的作用最大化,将它们作为媒介用以表达自己内心丰富的情感世界。
毋庸置疑,次仁多吉的画作属于表现主义画派,苏丁提供了具有指向性的灵感使次仁多吉走向了属于自己的绘画道路。但当把他的画作与表现主义画派的启蒙者苏丁的画作放在一起看时,发现他们具有截然不同的情感表达。苏丁早期油画中会带有死亡、屠杀的意味,他在一次次的重新作画甚至毁画中将情绪释放在颜色里。苏丁的画作给人的感觉是更加凌厉、更加暗黑以及偏执的,是具有毁灭性的。但次仁多吉的画作表现出的恰恰是与其相反的力量感,用刮刀刮掉颜料重新作画是为了更好地表达自己正面的情感,其中有对家人浓烈的爱,也有对宗教的尊重与情感寄托,更有对消失古迹的惋惜以及对它们曾经存在过的辉煌感到震撼!
次仁多吉早期在广袤的高原农村边劳动、边学习,不断地进行艺术探索。改革开放以后,他接受了系统的艺术教育,早期的绘画风格是偏向西方古典油画与印象派的。其中《第十世班禅》正是受到欧洲古典油画技法的启迪而创作出的一幅画作,也加入了印象派对光影、色彩的应用,对细节、体积的塑造非常全面,色彩更偏向于表现画面中人物的存在,符合现实人物面部色彩的表现,收敛不张扬、用笔沉稳,人物的刻画十分传神、灵动。此时他的绘画理念已经有蛛丝马迹可寻,他笔下的人物不只有外形,还将人物性格雕琢得很细腻,直截了当地呈现在观众的眼前。但是,他内心清楚这并不是他在艺术道路上追求的终点,有更远的艺术之路在召唤他,在等着他去踏上旅程。当时,西藏从事艺术的人们大都喜爱画国画或者唐卡,很少有人选择画油画,而他毅然决然地选择了油画,而且也并没有选择当时的主流流派而是尊重自己内心的呼唤,选择了当时大家并不关注的表现主义流派。
因其在上海、北京求学进修的经历,他已经拥有了对细节描写与整体把控的能力,但他不满足于只描绘客观事物的存在,渴望追求表现主观精神力和自己内心激昂的情感。《展佛的日子》是其非常重要的作品,在2008年入选北京奥运会美术展并被收藏。利用沉重的色调去烘托庄严、隆重的气氛,采用红与绿、黄与紫、蓝与橙等对比关系,颜色互补得恰到好处,就像无数匹未被驯服的野马,听到某支曲子不再躁动不安,一个个小个体串联成和谐的整体。
次仁多吉最让大众熟悉的画作可能就是“布达拉宫”系列。布达拉宫是他从小就接触的一座建筑,甚至他之后工作的剧团也是在布达拉宫前的广场上。他似乎觉得最能代表家乡的建筑就是布达拉宫。他一生非常喜爱描绘布达拉宫也是通过布达拉宫寄托自己对家乡无法用言语表达的爱意。次仁多吉说:“有人说,我最喜欢画布达拉宫,的确是这样。从十几岁开始,我画布达拉宫已经四十几年了。每次经过布达拉宫,我的感受都不一样,它从里到外精美绝伦,绝非一座普通的建筑。它是浓缩了的西藏,是数十代藏族人民用心血和汗水凝筑而成的,是伟大祖国的一颗璀璨的明珠,我将用毕生的精力去表现它。”
“布达拉宫”系列作品大量地采用冷绿调颜色进行表现。他非常擅长用对比色增强色彩的表现力。布达拉宫的墙面大部分是红色的,他在画天空与前面的山体草地的时候有意识地处理成了蓝绿色,布达拉宫的形状也随着笔触的变化律动起来,这不是一座固定在原地的建筑,在其笔下是一个鲜活的生命,熠熠生辉。每个角度的特写都反映出次仁多吉心中布达拉宫的面貌,此时更注重对形状、色彩、纹理等绘画语言的坚持。
受当时大环境的影响,次仁多吉对故乡产生了一种不安的陌生感。他的家人给予了他很大的帮助,渐渐地他走出了这种不安。家人一直是他的后盾,给他力量,支持他前行,对他来说家人是最难割舍的。他并没有明确地画过家人的形象,更多的是寄物言情,将浓烈的爱隐晦地表现在景物中。次仁多吉是个感情细腻又不爱直接表达的人,他将自己对生与死的感悟以及对家人的爱都浓缩进了《祈愿》这幅画中。对于生活在西藏拉萨的藏族人而言,出生以后都想要求得大昭寺的庇佑,它既是一个人人生的起点又是人生终点。次仁多吉画这幅作品的时候,已经走过自己人生的大半路程,经历了自己身边大多数的生与死,见过人们面对大自然灾害或者疾病时的恐慌与无助,他的内心植种了大多超脱语言的情感。这些经历使他对生命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而他将这种情感寄托在了大昭寺。
我们再以废墟为切入点进行分析,废墟在他的作品中多次出现,他是以怎样的情怀去创作的呢?先生说站在它的面前,似乎看到了它曾经无比辉煌的样貌,它不是砖石与水泥的堆砌,而是人类智慧的结晶,是充满历史气息的遗迹,因此,对其产生了特殊的感情。作品或许在惋惜这失去的美丽,但更多的是对遗迹曾经的辉煌感到惊叹,遗迹仿佛诉说着千年的故事,震撼着次仁多吉的心灵。
由于他对作品本质有了新的领悟,所以放弃了对造型的“形”的首要追求,转向如何更好地表现自我内心的传达。以某次次仁多吉在帕崩岗的写生为例,也是在画一座废墟,在那幅作品中亮面的冷色也运用了夸张,跳跃出了生活的局限,即达到艺术来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的状态。但他画完第一遍会把颜料刮掉开始修改,直到把物体的亮面和暗面表达清楚才停笔。而现在对于造型的“形”在画面中的需求似乎在慢慢减少,走向了更加高超、玄妙的境界,每一笔都是在对作品进行阐述,笔触本身变成了一种表现。
无论何种题材,都表现了次仁多吉对艺术的完美诠释、对生命领悟的真义以及对情感强烈又似含蓄地表达。次仁多吉对绘画语言的探索没有停止,会穷尽一生去寻找他的终点。
四、结束语
综上所述,次仁多吉对油画的探索在国内是前沿的,具有引领作用,为后世的艺术创作者开辟了一条新颖的道路,帮助他们思考艺术的多种可能性。次仁多吉以多种物象为情感寄托,再以形状、色彩、光源色等绘画语言加强情感宣泄。画作看似因笔触、纹理堆积而显得厚重,实际画面色彩堆积极其轻薄。暗部颜色处理得当,不会生出违和感,符合整体画面布局。回看中国艺术发展历程,西方现代艺术对中国现代艺术的发展仍有着重要影响,中西方艺术结合依旧值得后辈继续研究,这是一个适合深究的重要课题。次仁多吉在艺术上的贡献是值得我们铭记的,警醒着我们每一个艺术创作者要认真对待艺术,其对艺术的坚持与谦虚的态度也值得后辈学习。
作者单位:西藏大学艺术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