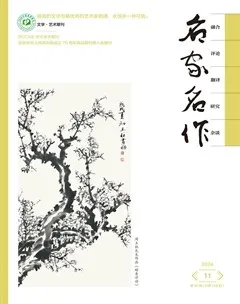论朱光潜艺术创作中的灵感
[摘 要] 自柏拉图为艺术灵感赋予系统性的理论阐释起,灵感作为艺术创作的来源在艺术哲学和美学研究中具有了里程碑式的意义。通过对朱光潜艺术创作中的灵感观念进行溯源,分析其对于灵感获得与爆发的审美主张,并探寻人工智能飞速发展的大环境下其灵感观念的当代价值。
[关 键 词] 朱光潜;艺术创作;灵感;柏拉图;当代价值
灵感是朱光潜分析艺术创作时一再关注的主要问题。艺术创作除了需要创作者人为的想象和对技巧的把握,还少不了对艺术创作重要来源“灵感”的研究。正如朱光潜所说:“艺术须赖灵感,这是古今中外的共同信仰。”[1]186本文拟通过对朱光潜艺术创作中的灵感观念进行探讨,分析其文化根源,探寻其当代价值。
一、朱光潜灵感观念的中西方文化渊源
朱光潜的灵感观念受到西方哲学家柏拉图、康德和黑格尔以及心理学家弗洛伊德的灵感观念的显著影响,同时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艺术创作的灵感思想也对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尽管西方早就提出了关于艺术创作时对作者迷狂状态的描述,甚至灵感一词在古希腊语的原意是“神的气息”[2],但直到柏拉图《伊安》篇中灵感才摆脱侧面形象的描述,成为系统性、理论性的概念。柏拉图强调灵感具有“神性”且能“人传人”,不仅艺术家创作需要灵感,欣赏者也需要灵感,因为没有灵感就无法感受到作品的魅力。因此,柏拉图认为最好的艺术不是艺术家凭借个人技艺完成的,而是因为得到神的指示,灵感就是神力。柏拉图认为灵感源于灵魂对前世理式世界的回忆,灵魂一旦回忆起理式世界就会欣喜若狂,灵感也就因此而生。[3]
朱光潜认为艺术的创造在未经传达之前,只是一种想象,而这种想象就是在心中见到的一种意象,朱光潜对于意象的定义是“所知觉的事物在心中所印的影子”[1]178。这与柏拉图认为艺术是理念的影子的观念较为相似:知觉的事物留在心中的影子,就像灵魂曾经在天国看到过的理念,创造人间就是理念的影子,创造艺术作品也是对于艺术作品留下影子。
康德在其著作《判断力批判》中讨论了“天才”的概念,他提出“天才”一词可能源自“genius”,意指一种独特且天赋的精神力量,那些原创性的思想火花正是源自这种天赋灵感的激发。康德不仅指出天才具备创造审美理念的能力,还具备创造独特形式规则和概念规则的能力,这些规则新颖且富有创造力,赋予既有概念以全新内涵,使得艺术内外皆呈现出独一无二的特性。最终天才通过具体的艺术形象来传达这些审美理念和独特规则。朱光潜把这种“无规则的规则”解说为灵感。[4]
朱光潜还深入剖析了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特别指出潜意识这一层次往往隐匿于意识深处,难以被个体直接察觉,且时常受到显意识的压制与束缚。基于弗洛伊德的理论框架,灵感根植于潜意识中,当潜意识受到外界刺激或内心触动,则突然跃升至显意识层面,从而实现了从隐性到显性的转化。
黑格尔也强调,灵感并非凭空产生,而是艺术家长期内在积累的结果。他反对将灵感神秘化,认为它并非古希腊所认为的“神灵附体”,而是艺术家长期努力和积累的必然结果。尽管他承认了艺术家的天才因素,但这种天才必须依靠思考、对创造方式的思索以及实际创作中的练习和熟练技巧来培养,同时需要外在机缘的触发。黑格尔总结灵感“是完全沉浸在主题里,不到把它表现为完满的艺术形象时就绝不肯罢休的情况”[5]。朱光潜认为艺术创作过程也是如此,作者日常积累诸多思想见解,也在潜意识中蕴藏丰富情感和创作欲望,直到某个时刻爆发后流露为可见可感的艺术表达,这个过程就是灵感的体现。
尽管朱光潜的诸多学术概念都基于西方哲学的概念或命题,但他的思想内容中不乏中国传统哲学的底蕴。中国古代诗歌创作方法之一的“借物起兴”就是诗人在文学创作时灵感的乍现。庄子强调“心斋”“坐忘”等心灵修养方式,认为在忘却尘世纷扰、达到心灵纯净的状态下,灵感会自然涌现。虽然庄子没有直接论述灵感,但他的思想中也蕴含着对灵感来源的深刻洞察。西晋陆机在《文赋》中最早系统地论述了艺术创作的灵感问题,他认为灵感是“天机骏利”,来不可遏,去不可止,具有突发性和难以控制的特点,自此中国文人真正在文艺创作里开始使用灵感一词。南朝刘勰在《文心雕龙》中虽然没有直接以灵感命名,但他对“神思”的论述与灵感有相似之处。“神居胸臆,而志气统其关键;物沿耳目,而辞令管其枢机。枢机方通,则物无隐貌;关键将塞,则神有遁心。”他认为“神思”是艺术创作中的想象活动,超越时空限制,自由驰骋。“积学以储宝,酌理以富才,研阅以穷照,驯致以绎辞。”就是在说灵感的产生需要后天多方面的努力和积累才能得到。“思表纤旨,文外曲致,言所不追。”[6]描述的就是灵感到来时受到外界的激发,从而进入一种不自主的迷狂状态。[7]再如《沧浪诗话》中的“妙悟”“兴趣”,从形而上的角度解读了灵感在创作活动中的作用。除此之外,还有清代画家石涛所说的“搜尽奇峰打草稿”等。这些关于日常经验的积累和灵感爆发时的描述都能在朱光潜对灵感的分析中找到影子。
二、朱光潜对于灵感获得与爆发的审美主张
在艺术创作的来源中,朱光潜批判了席勒、斯宾塞的精力过剩说,认为过剩的精力发泄完毕后游戏应当停止,但在实际生活中爱好游戏的人或动物都常常玩到筋疲力尽还不肯放手;还批判了谷鲁斯的联系说,因为谷鲁斯也把游戏和模仿看作是人的本能,认为游戏等不足以成为本能,只是天然的倾向。但他肯定了游戏和艺术有许多类似的地方,二者都是在人追求自由生活和快感的前提下产生的,游戏是创作的第一步,相比较游戏,艺术创作需要有进一步的表达,即把意象客观化为具体的情境,以具体作品表现其中的意象和情趣。
“艺术的创造在未经传达之前,只是一种现象。”[1]178朱光潜认为,知觉到的事物在心里留下的印记就是意象,譬如眼前之竹与心中之竹的关系,当回忆起这个东西的时候,是一种记忆的复现,也是一种想象。但与单纯的回忆不同的是,朱光潜认为艺术是创造的想象。首先,这说明艺术来源于想象,想象来源于经验中所得的意象,因此艺术是取材于现实生活的。其次,他说明艺术的创造必须有新的成分,但人们所能运用的内容都是从现实生活实际经验中得到的,因此想要创造新的艺术,就只能把已有的意象进行“剪裁综合”,形成一种新的形式。在朱光潜看来,艺术的创造是将有创造力的想象付诸实践,“凡是艺术创造都是平常材料的不平常综合,创造的想象就是这种综合作用所必须的心灵活动”[1]179,其中“创造的想象”包含三个部分:理智的、情感的和潜意识的。潜意识指的就是灵感,是人的意识无法察觉到的部分。
灵感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灵感往往出乎意料,不受控制。第二,灵感往往是无意中得到的,是突然获得的,无法刻意追寻。朱光潜在《文艺心理学》中引用了柏拉图《斐德若》篇的原文。柏拉图认为灵感是神的启示,艺术家在得到灵感时,通常不用费尽心血就可以写出完美的作品。但朱光潜否定了灵感是神赋予人的观点,他引用近代心理学家的说法,认为“灵感大半是由于在潜意识中所酝酿成的东西猛然涌现于意识”[8]。在朱光潜的概念里,灵感和潜意识是同一类的,他举例催眠对人的潜意识的影响,说明潜意识的活动大半仍依据联想作用,在潜意识中,情感的支配力比在意识中更大。第三,灵感的爆发有日常积累的成分。他指出:“灵感既起于潜意识的酝酿,所以虽似突如其来,却不是毫无预备。”也就是说,看似“凑巧”“偶然”的灵感爆发实则源自日常积累,生活素材在潜意识中酝酿,待到时机成熟就会自然而然地涌现,杜甫的“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便是如此。
对于灵感如何日积月累地成熟,朱光潜进一步阐述:在意识作用弛懈时,潜意识中的意象最容易涌现。他举例很多艺术家的创作都是在梦境中完成的,人在做梦的时候是最放松的时候,梦境中的许多内容是来源于白天的生活经历,夜晚以梦的形式重现或经由幻想改编,无论是做梦还是进行艺术创作,大多数内容都是源自日常生活经验。这点现代医学也可佐证,有学者认为做梦就是对记忆的加工过程[9]。
西方哲学家自柏拉图起多认为灵感作为神的赋予,人只能被动地接受。对于如何主动地招邀灵感,朱光潜举例说明了不同作者的独特方法,如李白饮酒、伏尔泰和巴尔扎克喝咖啡等。他总结这些招邀灵感方式的目的各有不同,有些在于提起精神,但大部分是造成梦境,使得潜意识中的意象容易显现。
还有一种方法就是在其他的艺术范围中获得一种意象,然后让它在潜意识中酝酿,再在自己的艺术中“翻译”出来。[1]192文学翻译追求信雅达,即在忠实于原意的基础上,融合双语特色,巧妙运用语言优势进行加工润色,超越简单直译,实现意境与表达的双重升华,艺术的“翻译”同样如此。朱光潜的“翻译”与王维的“诗中有画,画中有诗”异曲同工,皆借他形之长绘难言之境,灵感源自跨界暗示。再如张旭观公孙大娘舞剑悟得书法之道,以及吴道子剑画相通的故事,都是如此。因此朱光潜认为,意象可以旁通,如果艺术家想要得到深厚的修养,应该多向其他领域探索学习。
三、朱光潜灵感观念的当代价值
灵感在创作过程中发挥着不可估量的作用,它不仅能显著减少创作者构思所需的精力,更能促进作品质量的飞跃。朱光潜在书中多次举例,如歌德创作《少年维特之烦恼》和音乐家柏辽兹谱曲,都源自灵感的骤降。
然而当代社会,艺术创作的构成要素已然发生巨变,灵感与生活经验虽仍保有重要地位,却已非唯一的决定性因素,数字媒体技术使得艺术作品的生产、复制与传播方式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变革。本雅明认为,机械复制虽然保留了原作的外在形式,但无法复制其内在的灵韵。因为灵韵是与作品的独一无二性、即时即地性、历史文化背景和膜拜价值紧密相关的,而这些因素在复制过程中往往会被削弱或丧失。尽管机械复制技术使得艺术的传播更直观便捷,然而展示价值的凸显也意味着原有的神圣性和崇高感被削弱。
同时,原本艺术创作最重要的形式、技术也已逐渐淡化,诸多先进的人工智能绘图工具极大地简化了创作流程,使得创作者无须具备传统的绘画技艺,仅通过文字指令即可获得绘画作品。且随着指令的不断优化与精细化,人工智能还会逐步调整与诠释创作者的意图,最终生成与创作者预期高度契合的艺术作品。对此,麦克卢汉认为,“即使有意识的计算机,仍将是我们意识的延伸”[10]。智能工具始终是受人类操控的实体,其功能的强大与多样性,归根结底是人类思维与创造力的延伸与辅助工具。麦克卢汉精准界定了技术在人类社会进步中的角色:技术并非为了取代人类意识或凌驾于人类意识之上,而是作为人类智慧的扩展与延伸,旨在强化我们探索未知、解决复杂问题及表达独特见解的能力。
尽管人工智能能够依据既定指令机械地处理信息并输出作品,但它尚不具备自主思考创作过程的能力。这意味着,追求创新与独特性的艺术探索,依然高度依赖人类自身的思考广度与深度。人工智能的算法虽然能够模拟人类经验的累积,通过信息的整合与再组织来生成内容,但终究无法全面复制人脑的复杂性与创造性,它缺乏的是艺术加工过程中的直觉、情感与原创性,仅能基于既有素材进行组合,难以超越现有框架而创造出前所未有的新元素。
在此情境下,灵感作为艺术创作中不可或缺的催化剂,其在人类下达指令时的作用愈发显著。灵感激发的不仅是一个新颖概念的诞生,更是后续创作方向的指引。而如何将这一灵感转化为具体可感的艺术形式,不仅依赖人工智能在既定框架下的高效执行能力,更得益于人类在语言运用上的精准与灵活。正如肯尼斯·伯克在《语言作为象征行动》中所阐述的,语言不仅是交流的工具,更是艺术家构建与传达作品深层意义的桥梁。艺术家在创作过程中会不自觉地将自己的情感和道德观念融入作品中,通过语言符号的巧妙运用来引发观众的共鸣和情感反应。灵感作为这一过程的原动力,驱动着艺术家运用语言这一象征体系,创造出既富有感染力又充满表现力的艺术作品。
四、结束语
丹托在《艺术的终结》中指出,艺术的终结并非意味着艺术的消失,而是指艺术形式和审美观念随时代变迁发生了深刻变化,我们需要重新评估艺术的价值和意义。[11]同样地,面对科技日新月异的现代社会,我们亟须构建新的认知框架,深入反思灵感在艺术创作流程中的核心作用及其不可替代的价值,这一过程不仅关乎艺术的未来走向,更是对创造力本质与人类情感表达边界的一次深刻探索。
参考文献:
[1] 朱光潜.文艺心理学[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
[2] 朱存名.说中西灵感观[J].文艺研究,1984(6):38-42.
[3] 朱光潜.西方美学史:上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53.
[4]陈诗婕.朱光潜《谈美》艺术创造论中的康德美学基因[J].牡丹,2022(14):49-51.
[5]黑格尔.美学:第一卷[M].朱光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451.
[6]庄适,司马朝军,选注.文心雕龙[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20:14-17.
[7]刘忻怡.论中国灵感思维发展简史[J].戏剧之家,2019(20):233.
[8]朱光潜.美是情趣与意象的契合[M].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2020:88.
[9] 张杰.Continual-Activation Theory of Dreaming[J].Dynamical Psychology,2005(2):1-6.
[10] 马歇尔·麦克卢汉.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M].何道宽,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428.
[11] 阿瑟·丹托.艺术的终结[M].欧阳英,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
作者单位:郑州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