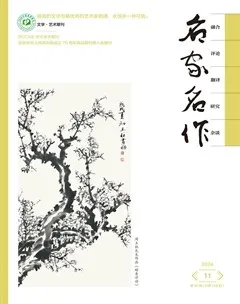风格呈现——黄胄民族人物画的粗犷美
[摘 要] 黄胄先生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创了“在生活中起草稿”的中国画创作观念,创造性地再现了人物的精神形态、性格特征与画家自我感受的融合。纵观黄胄一生的创作足迹,少数民族地区特别是新疆地区可谓是他在艺术上的“生活基地”,他的经典作品大都出自民族写生的所知与所感。黄胄自己也谈到,新疆风光的奇伟和人民豪放的性格都是影响他艺术格调的因素。以黄胄的民族写生之旅和他写生的创作思想为研究基点,进而探寻他的民族人物画粗犷风格的形成原因与影响因素,同时将黄胄的绘画置于20世纪西学东渐的艺术思潮下,深入解读黄胄民族人物画的粗犷美。
[关 键 词] 黄胄;少数民族题材;人物画;写生;粗犷美
一、外界环境促进粗犷风格形成
(一)民族风情题材的衍变
1949年5月, 黄胄和赵望云先生第一次沿途写生,从青海到甘南地区再到少数民族地区,这种特殊的经历使他对这片广袤的土地产生了热爱与眷恋,不仅是黄胄创作题材衍变的转折点,更是为黄胄扣上了创作民族题材的第一粒扣子,成就了他在民族风情题材创作中的重要地位。
新疆各族人民的日常生活成为黄胄人物画创作的主要题材,他先后六次到新疆各地深入生活、写生作画。新疆人民把黄胄看作自己的画家。在黄胄的艺术生涯中,民族地区是他艺术写生与创作的主要阵地。黄胄炙热地爱恋那片充满热情的土地,他不断地勤奋作画,满腔热血地表现民族地区各民族的生活。
(二)民族人物豪放性格的影响
黄胄一生曾六次到新疆写生,他走沙漠、穿戈壁、过绿洲,最长待过9个月,他心中早已对新疆人民产生了深深的情感。黄胄谈到自己为什么多次去新疆、为什么选择民族题材时说:“我想画这个民族豪放的性格,这就是他们本身所特有的美。这山里头有一种泥土气息,是真实生活里的那种美。”黄胄豪爽的艺术个性与新疆少数民族奔放粗犷的性情擦出了激情的火花,他从少数民族人民的生活中找到了与自己艺术理念相互吸引的创作灵感。纵观黄胄一生所创作的民族题材大作,他笔下豪放、粗犷的人物画无疑是和少数民族人民的性格特征彼此关联的。
从黄胄《新疆舞》的画面呈现上展开思考,无论是人物的动感造型,还是笔墨与线条潇洒淋漓的运用,都体现出了黄胄中国画人物创作方法的进步与创新。画面的黄金位置是一位正在跳舞的维吾尔族少女,她舞动的裙摆是以疾笔书写的方式表现的,通过画面上展现的笔墨痕迹,可以直观地感受到毛笔在纸上书写的快感,而在刻画人物面部时则更加细腻柔和,画面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和强烈的冲击感。画面中鼓手的笑容、少女灵动的舞姿以及极富动感的笔墨营造出画面热情、奔放、粗犷的意境,让人身临其境,进入一种放松自在的状态。黄胄精准地捕捉到少数民族人民的文化传统和外貌特征,并将他们豪迈的民族气概表现得淋漓尽致。
二、粗犷风格受绘画观念的影响
(一)在生活中起草稿
20世纪中国传统艺术的继续发展与现代建构,强调艺术家要重新认识和思考艺术与生活的关系,艺术家深入生活是艺术创作中一个不可或缺的途径。黄胄的人物画新范式就是20世纪中国传统画画坛的一股新流,他开创的“在生活中起草稿”是对石涛“搜尽奇峰打草稿”的创新与延续。特别是他的民族题材作品突破传统形式,创新了人物画的表现技法,开拓了全新的绘画观念与审美范畴,直截了当地回答了艺术与生活的关系这一问题。
黄胄的创作灵感来自生活,这里提到的“生活”是他扎根到人民群众中深入体验的生活,例如他的少数民族题材作品,从农田里收割时的欢声笑语到葡萄架下热情的舞蹈再到草原上追逐的马群,都具有很强的生活感。黄胄的作品也体现了生活,这里说的“生活”更多的是他对生活的感受,是对生活的深度表达,而不是表象地记录生活场景和生活迹象。黄胄先生说过:“生活为我出新意,我为生活传精神。”他笃信“生活”是艺术之本,一切不以观察生活和体验生活为基点的绘画作品都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艺术家一旦离开了生活,就像鱼儿离开了水、草木脱离了根。
黄胄一生走遍祖国南北,广泛收集各地的生活素材,为他的艺术创作积累了丰厚的灵感与经验。追溯到黄胄最初的写生经历,可以从黄胄早期创作的《驯马图》中看出其鲜明的创作风格。
画面描绘了一位哈萨克族少女驭马扬蹄的情景,骑在马上的姑娘笑着手握马绳,四蹄翻腾的马十分强壮,流露出好斗的勇敢精神。黄胄通过精心的构图布局和传神刻画,用疾笔描绘草原上奔腾的骏马,描绘了一幅洋溢着乐观精神、豪迈热情的节日盛景,整个画面和谐而又充满张力。从少女腾起在马背上的动态可以感受到有一种强大的民族力量溢出画面,直击观者的内心。画中骏马飞扬的长鬃、少女飘散的碎发、马蹄溅起的长草等局部描绘,都塑造了一种粗犷美的视觉体验。
黄胄曾说过:“只有怀有强烈的表现生活的愿望,创作才能得以开展,而风格也只能在这种创作实践中不断探索与发展,从而逐步形成。”黄胄六次赴疆考察写生,深入民族地区生活,他的艺术理念和绘画风格深受少数民族生活的影响。黄胄作品中粗犷画风的形成,与他在新疆生活时的所见与所感有密不可分的联系。
(二)速写与中国画融合
黄胄的创作灵感源于生活,而他的艺术表现则源于他的速写,他曾评价自己的艺术得益于他一直坚持的写生练习,他存留了许多写生时的练习稿,单是在民族地区的一次写生之旅,就有一万多张作品。黄胄的绘画成就,得力于他的速写、写生功夫。他认为速写的目的有两个:一是作为练习,二是用于创作,这可以是练习中的创作,也可以是创作过程中的练习。黄胄的速写不仅是创作的基础素材,也具有很高的独立艺术价值。黄胄自己的中国画变革奠基于速写,他把速写中的绘画特点运用在自己的中国画创作之中,借鉴速写中的艺术语言和创作手法,改变传统水墨画的创作模式。黄胄的速写是不加约束的,他所画的每一笔线条都是摸索的过程,是不断接近描绘对象的过程,就是在这样的不断探索中逐渐锤炼成了他“复线式”的刻画形式。从黄胄的速写草稿和成品中不难看出复线的应用,这种全新的艺术表现技法是在西方素描线条和东方传统线描中相互取舍形成的。黄胄大胆地运用复线强调造型,其中一些看似废线、错线的线条,都直观表现了他在绘画时对描绘对象反复推敲的修改过程,也是深层感悟的体现。
以《哈萨克舞》为例,作品主要描绘的是一位塔吉克姑娘跳舞的情景。人物的头巾和衣服上的线条都采用了以速写用线入画的方式,裙摆上的长线条具有很强的书写性和速写性,运用“复线式”的表现手法作画,画中重叠交错的线使少女舞动的姿态更加轻盈自然,从作品的侧面也能感受到他的速写向中国画的自然转变以及在捕捉这一瞬间印象时的作画激情。
黄胄的人物画创作中融入了速写的绘画风格,巧妙地将奔放的笔触与生动的形象结合在一起,还注意刻画细节,营造了画面的生动氛围和强烈的视觉效果。黄胄在表现民族地区少数民族题材的速写作品中,用线纵情泼辣、不受约束,形成了强悍、粗犷的风格。
三、中西技法结合展现粗犷美
(一)白描传统和线性素描相互取舍
元代的人物画,从题材上来看已不像壁画那样表现宏观场面。元代书法已走出了唐代尚工尚法的阶段。元代绘画的书法用笔不拘谨,而体现在用笔的“写”意上。从笔法角度来看,元代绘画采用了书法的用笔。这种绘画回归了其本质,题材多围绕文人士大夫的生活理想,展现出更加沉稳含蓄而雅致的趣味。在造型能力方面,元代的人物画家在技法上有了显著进步,包括工笔设色、白描和简笔等方法的运用。此外,这一时期的山水皴法和墨笔花鸟画也体现了共同的传承与风尚变化。元代的壁画多运用细腻如丝的白描与淡彩技法,展现了对线描技艺的熟练掌握。
在表现线条和意境方面,黄胄深受阿道夫·冯·门采尔和珂勒惠支的影响。20世纪50年代,黄胄与老友裘沙等人常常深入讨论珂勒惠支的作品与风格。在她的启发下,黄胄有意识地增强了线条的表现力,突破了传统对单线运用的限制,充分挖掘了复线的表现潜力,使得线条更加直接和生动。不论是在速写还是水墨人物画上,他都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一方面,复线的勾勒记录了画家思维发展的过程,全面呈现了对造型的塑造、修正和补充,有助于表现对象的体量与动势;另一方面,复线挑战了传统中锋用笔的线条模式,通过强调速写的表现性,打破了对精细笔触和传统衣纹线条“十八描”的美学限制。这种技法将笔、墨与线条融为一体,结合了侧锋擦笔、勾描与中锋线条。看似杂乱的笔致,实际上在某种程度上与文人写意画中“笔有误笔,墨有误墨”的意外韵味相呼应,为画面增添了动感与活力。
黄胄写生的基础则主要建立在中国画白描传统和欧洲线性素描的认知和学习上。他认为,中国画家应在自身的笔墨传统基础上,汲取优秀的东西方艺术,目的在于推动中国画的发展,而非改造原有的艺术形式。黄胄的速写线条既不同于传统白描的任何风格,也与传统中国画中“一波三折”的笔法及中锋用笔的要求无关,同时也未采用新中国人物画改革中常见的素描语言,而是凭借他对线条的独特感悟。他借鉴中国画的写生传统,融合西方绘画材料的造型技巧,旨在实现高度写意的传神境界,并且吸取西方全因素素描法中的优点融合在中国画写生和创作中,使画面所构成的笔、墨、线充满丰实感,既有益于对画面的整体把握,也因此形成了豪放的笔墨与强悍的画风。
(二)西方色彩与写意笔墨相互交融
20世纪,由于西式写实主义的刺激,催化了现代水墨人物画语言的衍变。许多当代画家都受到了影响,试图创新传统水墨的表现技法。在学习和回顾传统并吸收西方艺术后,他们有意识地打破中国传统绘画经久不变的僵局,但许多人以实际经历告诉当今画坛,艺术想要创新是艰难的。而黄胄创新中西绘画的新方式和画作风格引领了一代写意新风。
黄胄在作品中灵活运用浓墨重彩与水墨淡彩,打破了中国画雅淡的用色传统。他在保留水墨画意境传达与层次表现优势的同时,创新了色彩的多样性。其用色不是简单地模仿,而是结合了中国民间传统绘画和西方绘画艺术,取之精华并加以创新。在墨色的运用上,也是应景而作。黄胄根据不同的创作主题和情感状态选择色彩与墨色的表现技法。在他的少数民族题材作品中,他更善于运用柔和的重彩和水墨技法,既有水墨渲染与淡彩的运用,也有浓墨的挥洒,利用大块鲜艳的粉质颜色进行对比。因而黄胄作品的用色既不同于民间传统绘画中鲜艳的色彩,也不像西方绘画作品那样强调光与色的对比。
如《奔腾的草原》表现的是新疆柯尔克孜族人民正在进行传统体育项目“马上较力”的比赛场面。从色彩构成角度分析,画面正中偏右的少女和画面最右侧少女的服装颜色都选用纯度较高的蓝色,与画面左侧马背上毯子的颜色相呼应;画面正中偏右少女的头巾和画面左侧女孩的衣服都是选取了红色,只是颜色明度有差别,还有场景远处的衣服和马儿的红色都与之呼应。从这幅作品中完全可以体会到民间传统绘画的用色方式和西方绘画中对环境的注重,但这些关系在黄胄的作品中体现得比较微弱。画面中的马身和马尾则用重墨刻画,这种色上加墨汁、墨上加色的样式,既描绘了新疆姑娘的艳丽多姿、动物的峻峭,也烘托了雄伟的氛围。
由于作品尺幅较大,所以黄胄在作画时多以大笔运墨渲染,排笔挥扫,并用重色复色作画,画面对比强烈,给人以厚实饱满的视觉效果,形成了其粗犷的画风。
四、结论
在黄胄的艺术生涯中,少数民族地区特别是新疆地区可谓是他在艺术上的“生活基地”。他深受少数民族人民豪爽热情性格特征的影响,因此也促进了其粗犷画风的形成。他的创作灵感源于生活,其作品也体现了生活,扎根生活、勤于写生、重视速写是他的代名词。黄胄采用全新的艺术表现手法创作人物画,从西方艺术和国画传统中取舍技法,大胆地以泼辣、迅疾的线条表现造型。他的少数民族题材作品具有很强的情绪渲染与营造能力,作品中豪放粗犷的格调正是从新疆地区的具体感受中提炼出来的。他“在生活中起草稿”“以速写入画”的新观念为中国画画坛注入了一股热流。他在中国画史上创造了前所未有的豪放与欢快相结合的独特风格,营造出浓厚的氛围。这不仅为少数民族题材的美术创作奠定了符合时代需求的审美基调,也塑造了人们对少数民族及其文化的全新想象。
参考文献:
[1]李松.画家黄胄[J].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1(3):50-69.
[2]郑闻慧.黄胄谈艺术[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8:238-241.
[3]王娟. 黄胄绘画艺术风格研究[D].西安:西北大学,2015.
[4]于洋.沉潜与造境:黄胄的人物写生及其对当代主题性美术创作的启示[J].美术,2019(2):93-98.
[5]成佩. 黄胄研究[D].北京:中央美术学院,2010.
作者单位:吉林大学艺术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