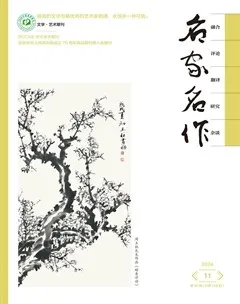中国文人的集体记忆与潇湘文化地理概念
[摘 要] 作为文化地理概念的“潇湘”,是中国古代文人集体记忆的产物,容纳了历代文人的复杂情感,集家国之思、身世感叹、宇宙想象于一体。潇湘之景也成为一个可以承载更多文化内涵的意象,并随着时代的变迁发生内涵与外延的演变,太多后来人的吟咏丰富了这一文化意象,使得“潇湘”成为具有极大文化张力的文化地理概念,远超其他地域文化的影响力。潇湘文化地理概念已经成为深植于中华民族文化母体的基因符号,在当代仍然发挥着巨大的审美感召作用,展示着独特的文化魅力。
[关 键 词] 中国古代文人;集体记忆;潇湘;文化地理概念;《潇湘图》
潇湘图式成为绘画母题有复杂的历史文化背景,是中国古代文人集体记忆的产物。它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绘画图式,更是一种有着更深的文化人类学意义的文化地理概念。涂尔干认为,记忆并不是纯粹的物质事实,不能脱离当下意识而独立存在,是人们在不同阶段相似的心理活动发生互动的结果。[1]14-15在不同的语境、不同的文化形式中出现的潇湘文化符号成为一个可以无限生成新意象的容器,容纳了历代文人的复杂情感,集家国之思、身世感叹、宇宙想象于一体。本文试图从中国文人集体记忆角度分析潇湘图式的形成原因及其文化影响力。
一、为什么是潇湘
在电子通信、交通运输高度发达的今天,人们当天就可以在幅员辽阔的中国大地纵横南北东西,瞬间就可以依靠网络神游世界。每逢节假日来一场说走就走的离乡远游是现代人的日常操作,而在车马很慢、书信传情的时代,山水之隔却可能是生死离别,被派往那些与京城距离较远的偏僻地方为官为吏成为对犯错官员的一种惩罚,这就是贬谪。古代文人被贬去的地方,有西北、东北、西南的很多荒僻之地,对于画家来说是山水形胜,对于文人士夫来说却是仕途折损、离家去国。画家眼中的美景是文人心中的隐痛,美景是有目共睹的,感观上的审美是可以相通的,心灵的感悟却不大相同。有些画家本身就是被贬谪的文人,他们的画与诗互文,共同倾诉心中的郁勃之情。可是同为贬谪之地的潇湘山水与北方的峻岭、西南的大山相比并不醒目,为什么会形成如此缠绵多义的潇湘文化意象?而那些更具有视觉冲击力的画面风格却并未产生如此深刻的文化意象呢?
按当下的中国地理区域划分,湖南属于华中地区,可是在古代交通不发达的时候,湖南区域却是属于远离政治中心地区的远方郡县,所以成为很多文人政客被贬往之所。据湖南师范大学伍英鹰、莫歆的研究,潇湘母题绘画在近年颇受学界关注,对历代相关主题作品的梳理研究趋于对“潇湘图”发展脉络的潜在构建;出现多篇对“潇湘图”作品风格和文化内涵进行剖析及对其创作者进行考评的文章;也有一些学者对“潇湘八景”图式在东亚文化圈乃至欧美文化地区的广泛传播与进一步衍化进行了讨论。[2]总之,潇湘并不只是一个明确的地域景观,其在流传演绎的过程中成为一个内涵丰富的文化地理概念,潇湘图式也成为一个山水图像志。有学者发现,这一主题的山水作品明显多于其他图像,而且有不同于其他绘画表现主题的特殊文化意义,从绘画母题早已演化为一个介于实景与想象之间的文化心灵空间符号[3],这种说法还是比较合理的。潇湘之景因为这种朦胧多义成为一个可以承载更多文化内涵的意象。
二、身处江湖不忘庙堂的潇湘文人情怀
一般认为,潇湘一词始见于《山海经》,这里的潇、湘指的是两条河的名字,后经历代诗人、文士演绎,到唐代中期已成为应用更广的地域名词。几千年来,这片土地上先后登场的众多文化名人带来了厚重的历史文化积淀,因为舜帝和两位妃子娥皇与女英凄美的爱情故事,屈原(约公元前340—公元前278)、贾谊(约公元前200—公元前168)等一代代失意文人、落魄政客的集体文化记忆流脉,潇湘与洞庭湖山都成为特殊的文化意象,被诗人们不断吟咏。
虽然在整体社会记忆和情感形成过程中每个人都做出了独特的贡献,但私人情感不会自动成为社会情感,那么是什么促成了个人情感向社会情感的转化呢?“除非在自成一类的力量的作用下,通过联合中发展起来的结合。在这种结合中(也含有相互之间的转变),它们变成了其他的样子。”[1]25也就是说,这种个人情感要有量的积累才能升华为社会共同情感。中国古代文人的潇湘情结就是这样形成的。他们身在潇湘,处于贬谪与归朝之间的人生低谷期,不同于被流放的官员,这些被贬者虽被排除在核心权力范围之外,但仍拥有官员身份,只是被降级外放。他们大多是因为政见不和被排挤而遇祸,因为朝中权力更迭,他们可能会获取新的机会,又被召回朝中。历代被贬谪文人士大夫思考的问题总是围绕着庙堂之高与江湖之远,来慨叹个人怀才不遇的痛苦,并企盼有朝一日能再回朝堂,得到重用。这种文化精神在千古时空中回荡,在历代文人的精神世界中传递,通过前人的诗文、后人的唱和来延续。缘于此,屈原于荒僻之地因高洁的自我精神投射,在污浊的尘世间也能够自成一美好心象世界,并展开对宇宙和人生的思考与诘问。屈原在自传体长诗《离骚》的结尾处上天入地四方求解不得之后,选择放弃故都之思,效仿殷商前贤,放弃肉身,换取精神不朽,彰显殉国理念。他为后世开创了充满浪漫想象的美学传统,又以其自沉汨罗的悲剧结局成为舍身殉国的先蹈,令后来者唏嘘垂吊,在徘徊迷茫中思考着超越的途径。
保罗·康纳顿把记忆分为纪念仪式(commemorative ceremonies)和身体习惯(bodily practices)两个特殊的社会活动领域来讨论。[4]中国文人以对前代的凭吊追思形成了新的内容,印证了这一说法的正确性。汉初贾谊也是天生聪颖、少年成名,但是生不逢时,遭到最高统治者的冷落。汉文帝四年(公元前176年),贾谊来到了距离都城长安不下千里的长沙,历经长途跋涉,在屈原曾经流连过的湘江之滨,激起同病相怜的感伤。时过境未迁,二人所处时代相隔上百年,却在同一片土地上遭受同样的痛苦煎熬。屈原的感受通过他的文学作品传递给了贾谊。他开篇即引用屈原《离骚》中的原文,并结合自身境况,表达了对屈原的缅怀、对自我命运的不甘。唐宋明清,朝代更迭、岁月变迁之下,太多后来人的吟咏丰富了这一文化意象,使得“潇湘”成为具有极大文化张力的文化地理概念,远超其他地域文化的影响力。
这一忠君爱民、以身殉国的传统成为中国文人风骨的核心精神并得以代代相传,给潇湘增添了厚重的文化内涵,成为中国文人精神诞生的土壤,在后人的行动中被践行、文笔下被拓展。古代文人沿袭屈原香草美人的比兴传统,常常以其表达自己与天子的关系。刘禹锡(772—842)创立《潇湘神》词牌,并填词两首,其一以湘水之流引申到云物之愁,对二妃身后之所作了交待,其二由传说因二妃之泪滴落而形成的斑竹遥想到二妃对舜帝的相思之苦,以自身遭际共情于古人。[5]中国古代文人的归隐只是一种生活表象,并不代表完全与世隔绝,他们把归隐作为一个入世成就大业的酝酿期。他们讲究安贫乐道、遗世独立,也随时关注山外的世态风云,伺机而动,仍渴望建功立业、名动天下。刘禹锡是这一思想的典范人物,他的《陋室铭》成为这一文脉传承的经典文字,至今为人吟诵不衰。
三、典型“潇湘图”式样的形成
我们所熟悉的流传下来的潇湘题材作品以董源(约937—962)的《潇湘图》、米友仁(1074—1153)的《潇湘奇观图》为代表。明末董其昌(1555—1636)把董源的《潇湘图》尊为中国山水画南派祖本,他鉴定了董源的《夏景山口待渡图》《潇湘图》《夏山图》并作了题跋,认为三件作品都是董的真迹,后人对此看法不一。张大千曾收藏过《潇湘图》,庞莱臣曾收藏过《夏山图》。谢稚柳到庞莱臣家看过庞收藏的《夏山图》,并请教其对董画真伪的看法。庞莱臣说自己收藏的画是真迹,张大千的是假的。张大千在去世前几年也表明看法,认为传世的三件董源山水画都不是真迹。谢稚柳并不认同张大千的看法,认为这三幅画风格一致,应都是董源的作品。上海博物馆研究员丁羲元则对张、谢二人的说法表示怀疑,他通过对三幅画的仔细比对,发现三者形制相仿,应有一件为母本。《潇湘图》太新,《夏山图》黑得极不自然,有故意做旧之嫌;如果三者中有一母本只能是《夏景山口待渡图》。其通过对三幅画笔墨技巧、物象表现、画幅接缝、精神气韵等全方位的品察,认为《夏景山口待渡图》为真迹,另外两件是赝品。[6]鉴别画之真伪是鉴定学家研究的问题,从更广阔的文化时空来考察,我们看到的是作为文化符号的潇湘图式视觉母题的生成,它在历代画家笔下以开放朦胧的意象出现。
山水是中国传统绘画中最重要的题材,与人物画的历史纪实性、道德教化性,山水花鸟的装饰性和祥瑞色彩都很不一样,表达的是人类的宇宙观、自然观,折射出人与自然的关系、天人相处的理念。以山水图卷来表达山河之恋、家国情思、隐逸之趣,和画家所处时代、生活阅历、创作动机都有关系。董源的画为什么而作?这一图式为什么会成为经典的文化符号?为什么又会广泛流传?当我们追溯这件作品命名及来历的时候不禁会有些迷惑。因为在潇湘图式的流变中,董源的《潇湘图》来历不明,不能被确切指认。
和一些所据真实山水特征明显且有明确题名的山水画名作不同,董源的《潇湘图》并不是原画上的题名,是董其昌得此画后,根据《宣和画谱》著录、对董源生平的了解、对画面内容的把握,给这件作品新起的名字。关于这幅画作的真实主题还有一种说法,说此画与《夏景山口待渡图》可能是对一件作品的局部分别进行的临摹,两幅画合在一起才是原作的本来模样,而这幅作品表现的是另一个与山水诗情风马牛不相及的“河伯娶妇”题材。此画在南宋画史中是有所记载的,收藏者是元代的赵孟頫[7]。机缘巧合之下,董其昌与这幅画作相遇,并依据自己为文人水墨江南图景张目的想法,重新为这幅画定名,将其纳入对潇湘图式的执着建构之中。董其昌不仅收藏董源的画,还收藏了米氏父子的《潇湘图卷》,可以说是心中有潇湘,故得以神遇。
真正表达出潇湘图景水汽氤氲、烟云变幻的是米氏父子的“墨戏云山”。米友仁的画作与文字是深切表明了他的潇湘情结的。他在《潇湘奇观图》上的题字表述了他对潇湘景色的熟悉,和对这一表现题材的热爱。米友仁还交代了他的父亲米芾所建的海岳庵在江苏镇江,并非湖南潇湘。至于画中景致,他也明确地说“此卷乃庵上所见”,那么为什么他在镇江写景,不是命名为镇江奇观,而是要名之为潇湘奇观呢?他也表明了他的绘画动机,因为他的目的不是为了写实景,而是为了表现山水变化奇趣:“大抵山水奇观,变态万层,多在晨晴晦雨间,世人鲜复知此。余生平熟潇湘奇观,每于登临佳处,辄复写其真趣成长卷以悦目,不俟驱使为之,此其悦他人物者乎?”他与以往画景造境、与山传神的画家不同,把云烟作为主体物,把山峦作为云的烘托物。他的目的在于写烟云变化之趣,着力点不在实体的山而在缥缈的云。他还曾在《潇湘白云图卷》上题写:“夜雨欲霁,晓烟既泮,则其状类此。余盖戏为潇湘写千变万化不可状神奇之趣。”
那么潇湘作为真实的自然景观,有没有被如实地正面表现过呢?答案是肯定的。目前所知明确书写潇湘真景且流传颇广的第一位画家是与苏轼、司马光、文同、周敦颐等同时代的宋代画家宋迪。苏轼还曾为宋迪写诗,对其画作进行评价,有“照眼云山出,浮空野水长”之句来表述画中之景,且有“知君有幽意,细细为寻看”之语来表述画中之境。宋迪曾在湖南为官,他的《潇湘八景》有针对性地表现了一些具体景点,如平沙落雁、远浦归帆、潇湘夜雨、烟寺晚钟、渔村落照等。随着此类画作与诗文的流传,潇湘已不是荒凉之所的代名词,而是成了一个引人遐思的神奇所在,《潇湘图》渐次具有了文化图式的魅力。此生不到潇湘,甚至可能会引为憾事。元人夏文彦在著作中曾记述了宋徽宗派画家张戬前往湖南图绘“潇湘八景”的史实,可惜未等图画绘就进献徽宗,战乱便起,张戬滞留于湖南未能北归。[3]此后北方江山易主,宋室南渡,被当作览胜别景的潇湘山水成了南宋的家国背景、眼前湖山。政治与权力中心的南移,使得“潇湘”不再是表达隐逸思想的寄托之景,曾经的远方不再是诗意的幽居之地,反而成为家国江山的象征。
四、结束语
人始终处于各种复杂的社会文化关联之中,这种关联有同一时代的横向联系,也有不同时代的纵向关系。文化因为代际传承成为传统,形成文脉流动。在历史的上下文中,每一个个体生命贡献出了自己的理解和阐释。正如涂尔干所说:“社会对其基质来说,是一群相互关联的个体。通过统一在一起,他们形成了系统,系统根据他们的地理分布和交流渠道的性质和数量而变化,成为社会生活得以产生的基础。”[1]24潇湘作为一个文化图式和文化地理概念,是中国文人集体记忆的生成物,并随着时代的变迁发生内涵与外延的演变。甚至可以说,潇湘文化地理概念已经成为深植于中华民族文化母体的基因符号,在当代仍然发挥着巨大的感召作用,展示着独特的文化魅力。
参考文献:
[1][法]爱弥尔·涂尔干.社会学与哲学 [M].梁栋,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2]伍英鹰,莫歆. 一个地域概念的时空腾移:“潇湘图”研究综述[J].艺海,2022(7):57-61.
[3]张概. 从地域景观到艺术符号:《潇湘图》的空间过程[J].人文杂志,2011(2):112-117.
[4][美]保罗·康纳顿. 社会如何记忆[M].纳日碧力戈,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2.
[5]刘禹锡.刘禹锡选集[M]. 吴汝煜,选注.济南:齐鲁出版社,1989:274.
[6]丁羲元.《夏景山口待渡图》与《夏山图》、《潇湘图》之真伪 [J].中国书画,2004 (10):67-69.
[7]何微.董源《潇湘图》定名研究[D].北京:中国艺术研究院,2019:10.
作者单位:邵阳学院设计艺术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