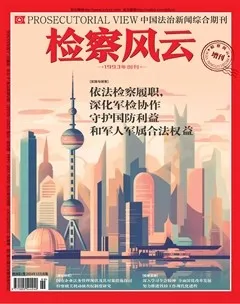检察机关机动侦查权制度研究
检察机关是宪法规定的国家法律监督机关。检察侦查是法律赋予检察机关的重要职能,是严惩司法腐败、维护司法公正的重要手段,也是加强法律监督的重要保障。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9条第2款规定:“对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权实施的重大犯罪案件,需要由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的时候,经省级以上人民检察院决定,可以由人民检察院立案侦查。”理论和实务界将法律的这一授权称为检察机关的机动侦查权。然而长期以来,由于各种原因,检察机关机动侦查权在实践中几乎处于“休眠”状态,其作用没有得到充分发挥。在刑事、民事、行政和公益诉讼“四大检察”全面协调充分发展的背景下,有必要激活有着重大监督潜力和价值的机动侦查权的功效,进一步探索完善检察机关机动侦查权制度建设。
一、检察机关建立与运用机动侦查权制度的必要性与可行性
建立和运用机动侦查权制度具有政治基础、法理基础和实践基础。
一是全面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的需要。检察侦查权应当立足“监督型侦查权”的全新定位,主动融入“四大检察”“十大业务”法律监督格局,着力构建“直接侦查”“机动侦查”“自行(补充)侦查”的检察侦查权法定结构,打造新型检察侦查制度体系。
二是依法对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权实施的重大犯罪案件进行法律监督的需要。机动侦查权充分体现了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属性,与“四大检察”既紧密相连,又适当分离,对“四大检察”的权威性和刚性有着内生性支撑作用。
三是实现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的需要。对于公安机关不宜侦查、不愿侦查或难以侦查的案件,检察机动侦查权的适用可以实现在侦查法定管辖基础上的侦查职能优势互补,增强侦查工作合力。
二、检察机关运行机动侦查权制度的困境和阻碍
检察机关长期以来承担着对国家工作人员贪污贿赂、渎职侵权职务犯罪的立案侦查职能,但实践中却甚少运用机动侦查权立案侦查。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通报,2023年全国检察机关共立案侦查司法工作人员职务犯罪1976人,而全年启动机动侦查权对公安机关管辖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权实施的重大犯罪案件立案侦查仅176人,行使机动侦查权查处人数不足行使直接侦查权查处人数的十分之一。机动侦查权行使频率低的原因在于,人民检察院在行使机动侦查权时面临着适用范围模糊、案件启动烦琐、行使机关权限分工不明等诸多问题。
一是适用范围模糊。机动侦查权的适用范围可以几个层次,分别为:“公安机关管辖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权实施的”“重大犯罪案件”。针对前两项关于管辖主体、犯罪主体和犯罪起因的范围都有具体且确定的法律或司法解释可寻,实践中并无争议。但针对检察机关行使机动侦查权立案侦查的“重大犯罪案件”这一关于案件轻重程度的认定问题,目前法律规定并不明确,实践中难以权衡。在实际办案中往往依据检察官的个人判断,很可能造成本应由检察机关以机动侦查权立案,却在经过主观判断后作出不立案的决定,或检察机关不当行使机动侦查权,造成不应当立案而立案的现象发生。
二是行使权限不明。根据法条规定,只有在“需要由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的时候”检察机关才能适用机动侦查权,然而,对于哪些情况属于“需要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的”,缺乏明确规定。理论上,对于因公安机关有利害或需要回避而不宜管辖、不应管辖以及侦查有难度不愿管辖的案件,检察机关都可以启动机动侦查权进行管辖。但在司法实践中,由于公安机关办案的相对封闭性,检察机关很难对公安机关是否需要回避进行准确审查,因而对于不宜由公安机关立案侦查的案件,检察机关行使机动侦查权进行立案侦查的情况少之又少,进而只能将机动侦查权的适用范围缩减至公安机关不愿立案侦查的案件,从而大大制约了检察机关侦查职能的发挥。
三是启动程序烦琐。机动侦查权的启动需要“经省级以上人民检察院决定”,一方面该规定能够有效遏制基层检察院因其能力不足或心藏私利而滥用机动侦查权的现象,但另一方面,严格的程序控制也束缚了检察机关更好地行使该项权力。严苛的启动审批程序可能会导致犯罪嫌疑人在基层检察院等待省级院批准过程中借机逃窜,也可能导致案件证据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难以收集,这对基层检察院案件侦查极为不利。
四是证据收集困难。一方面,机动侦查权的行使、侦查质效的提升依赖一支有足够的侦查经验、侦查技巧和办案谋略的专业化侦查队伍,但随着“两反”机构的转隶,检察机关侦查人才不足等问题凸显,严重制约了该项权力的行使;另一方面,在数字化背景下,检察侦查技术措施略显匮乏,检察机关行使机动侦查权期间对公安机关已采集的相关数据,如公共场所视频图像、指纹、DNA、旅馆住宿登记信息、通信信息等,当然进行获取并使用尚无授权或依据,影响了机动侦查权对权力对象的支配性和权威性。
三、检察机关运行机动侦查权制度的路径
一是明确机动侦查权的适用范围。建议从案件类型、可能判处的刑罚幅度以及案件社会影响力等角度对“重大犯罪案件”的标准进行相对明确的界定,适度扩大检察机关机动侦查权适用的罪种范围,考虑将可能判处三年以上有期徒刑刑罚的案件以及在本地区或行业领域内具有较大社会影响的案件明确纳入机动侦查权适用范围,同时赋予检察机关在监督公安机关立案这一程序上更加刚性的监督手段。检察机关除对公安机关立案侦查案件能够及时介入并引导侦查外,还应赋予检察机关对消极立案的公安机关工作人员进行处罚的权力,真正使法律监督“长牙带刺”。
二是简化机动侦查权的启动程序。对于检察机关直接受理侦查的案件,修订后的刑事诉讼规则规定“由设区的市级人民检察院立案侦查”“设区的市级人民检察院根据案件情况也可以将案件交由基层人民检察院立案侦查”,即直接侦查权的启动主体及程序均由设区的市级人民检察院主导。因检察机关机动侦查权与检察机关直接侦查权同属于检察机关侦查权的组成部分,建议从权责一致及有利于效率的角度,将检察机关行使机动侦查权的案件管辖同样限制在市级以上人民检察院,既解决机动侦查权启动程序过于烦琐的问题,也有利于检察机关统一侦查权启动程序,建立科学化的侦查权行使制度。
三是确立检察机关启动机动侦查权的主导地位。针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实施的重大职权犯罪案件,《刑事诉讼法》采取了可以由公安机关“管辖”,也可以由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的可选择性规定,两主体无论是哪个主体进行侦查,都有法律依据,说明在此类案件侦查问题上,我国实际上存在着一种“权力共享模式”。但目前何种情形下属于“需要由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尚无明确规定,检察机关在启动机动侦查权中尚处于被动地位,容易造成本不宜由公安机关管辖的案件继续由公安机关立案侦查的情况。在此背景下,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通报,2023年检察机关办理机动侦查权案件110件,涉及虚假诉讼、敲诈勒索、洗钱等26个罪名。随着当前“以审判为中心”诉讼体制不断深入,检察机关应当在机动侦查权行使领域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可以尝试将引导侦查机关进行取证的思路应用于检察机关行使机动侦查权立案侦查案件中,通过与公安机关沟通协调,由检察机关适时介入公安机关立案侦查,指导公安机关调查取证,以检警协作、检察主导的方式行使机动侦查权。同时对于不宜由公安机关侦查的案件,检察机关应当积极独立地承担立案侦查的重任。
四是数字赋能,运用大数据助力检察侦查。检察机关积累了四十年的职务犯罪侦查经验,形成了贯穿线索获取、初查、讯问等各阶段的有效模式。改革前检察机关一直较为重视侦查科技的发展,改革后这一优势应当有计划有重点地延续下去。要在之前的基础上,充分重视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科技成果的作用,将之融入侦查设备,从大数据里找线索,通过大数据技术挖掘、分析案情,建立有检察侦查特色的监督数据库,多渠道归集职务犯罪数据、收集和挖掘犯罪线索、接受群众举报和控告,实现多样化全方位法律监督模式,确保证据的合法性、有效性和关联性,进一步提高检察机关侦查权行使的力度和效果,保障法律监督权的有效行使。
(作者:赵辉,浙江省衢州市人民检察院法律政策研究室主任、浙江省理论研究人才;王占荣,山东省烟台市海阳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委员、一级检察官;杜依宁,浙江省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检察院第二检察部副主任、二级检察官,浙江大学刑法学硕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