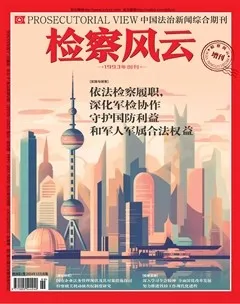执纪执法中对“特定关系人”和“关系密切人”的理解与应用
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以下简称《监察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实施条例》(以下简称《监察法实施条例》)的先后出台,标志着“纪法衔接”“法法融合”的理念真正从国家立法层面得到认可,原先很多在法律和司法解释中的专用语,也真正在执纪监督中得到承认。本文从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中对“特定关系人”和“关系密切人”的表述入手,理清二者的法律渊源,分析两者与《监察法》和《监察法实施条例》的关联,并探讨在执纪执法中的具体运用范畴。
一、“特定关系人”与“关系密切人”的法律渊源
(一)“特定关系人”的法律概念和定义范畴
“特定关系人”这一概念首次提出是在2007年5月中纪委制定的《关于严格禁止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谋取不正当利益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规定》)中,其明确了“特定关系人”是指与国家工作人员有近亲属、情妇(夫)以及其他共同利益关系的人。《规定》第6条、第7条中对涉及“特定关系人”的违纪行为分别作了如下禁止性具体表述:严格禁止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要求或者接受请托人以给特定关系人安排工作为名,使特定关系人不实际工作却获取所谓“薪酬”;严格禁止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授意请托人以本规定所列形式,将有关财物给予特定关系人,特定关系人以外的其他人与国家工作人员通谋,由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收受请托人财物后双方共同占有的,以共同违纪论处。
同年7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两高”)联合印发《关于办理受贿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中沿用了《规定》中“特定关系人”的提法和解释,如在第7条“关于特定关系人收受贿赂问题”中规定了关系人与国家工作人员共同受贿的3种情形:1.双方事前无通谋,国家工作人员为请托人办事后授意把钱款交给特定关系人的,此时国家工作人员构成受贿罪,特定关系人不构成犯罪;2.若双方通谋实施了前款行为则构成受贿罪共犯;3.若特定关系人以外的人与国家工作人员通谋并符合共同占有财物的要件的,二者认定为受贿罪共犯。
从2007年先后出台的几个纪法条线规定中对“特定关系人”的表述,我们可以看出“特定关系人”具体定义范畴包含两方面:一是特定身份关系人,二是共同利益关系人。特定身份关系人根据法律规定系近亲属和情妇(夫)。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82条第(六)项的规定,近亲属是指夫、妻、父、母、子、女、同胞兄弟姊妹;根据《现代汉语词典》,情妇(夫)是指男女两人,一方或双方有配偶而发生性关系,女方为男方的情妇,男方为女方的情夫。而关于对“其他共同利益关系的人”认定,法律规定较为模糊,并未予以列举。笔者认为:共同利益关系,应当判断关系人是否与国家工作人员具有共同的经济利益关系,诸如合作投资、借贷关系等。如仅仅是纯粹的同学、战友关系,由于没有发生过共同经济利益所涉及的事项,则不属于文中所提的共同利益关系。当然,共同利益关系除了共同财产关系之外,必然还包括财产利益和财产性利益。共同利益关系人应该还包括除近亲属以外的家族其他成员。
(二)“关系密切人”的法律概念和定义范畴
“关系密切的人”这一概念首次出现是在2009年《刑法修正案(七)》(以下简称《修七》)中,《修七》第13条新增了利用影响力受贿罪,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88条之补充条款。该法条规定了近亲属、关系密切的人通过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或者利用该国家工作人员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索取请托人财物或者收受请托人财物的,构成利用影响力受贿罪。该罪的主体还包括了离职的国家工作人员及其近亲属、关系密切的人。
《修七》颁布前,关系人利用其他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行为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而国家工作人员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关系人的此种行为是无法被定罪的。现实生活中,诸如情人、同学、老乡这种“中间人”利用自身关系网、影响力而进行权力寻租的现象比比皆是,产生了大量的违反公平公正的事情,对此法律却无法给予制裁,给当时的司法实践带来了巨大的困扰。在此种情况下,《修七》填补了这一空白,规定了“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确立了关系人可以单独构成利用影响力受贿罪。也就是说,关系密切人将会构成利用影响力受贿罪。
对于“关系密切人”的具体定义范畴,《修七》并未如“特定关系人”般予以列举。有学者认为,“关系密切人”的用语具有模糊性,有悖于法律用语应当准确、清晰的原则,这种模糊性用语会导致法律适用中的不确定性,所以为了避免语义不明而引发认识分歧,应以列举方式予以确定为妥。确实,从定义看“关系密切人”的表述缺乏一个精确和清晰的边界,具有一定的模糊性。但笔者认为,立法者以该用语来表达是有其目的的,我们可以运用法律解释中“目的论解释方法”,结合“法律用语不能脱离立法机关设立该法条和运用该用语而非其他用语的立法目的”去理解。在《修七》中,立法部门将“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归入了刑法第388条,列入贪污受贿类犯罪,其立法目的已经十分明确,就是想扩大这种利用影响力受贿行为的主体范围,加大对腐败犯罪的刑法惩治力度。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郎胜就《刑法修正案(七)草案》的有关问题回答记者提问时指出:“近亲属的含义是清楚的。其他关系密切的人,有的是他身边的工作人员,或者是与他有特殊的关系。有的司法解释提出了特定关系人的概念,如不正当的男女关系或者是情人关系,或者一些共同的利益关系等。但是关系非常密切的人,有些源自曾经是同学、曾经是老乡、曾经过从甚密等等。这些人在社会上利用与国家公务人员的某些特定关系为他人谋取不正当利益,收受索取贿赂,这也是一种腐败现象,也是对公共权力的侵蚀,所以这次在刑法中作了补充。”
笔者认为,结合郎胜同志的这段话,可见“关系密切人”的“关系”除了共同的经济利益关系外,还存在其他非利益关系。这些关系应该包括:一是事先存在的关系。这种关系不仅当事人均明知,而且当事人所在的社交圈也明知,为大众所知。如在成长、读书、工作、参加各种组织、活动等过程中建立的发小、同乡、同学、同事和朋友关系。又如情妇(夫)、恋人、师生、战友和因业务往来而彼此间比较熟悉的人,或者有相通的兴趣、爱好而彼此相互联系的人,甚至是酒肉朋友、麻友、牌友和网友等。所以,从立法的表述上看,“关系密切人”包含的范围很广,类似一种像法律规范中经常使用的“其他”的兜底性规定。
二、《监察法》体系中“特定关系人”和“关系密切人”的运用范畴
(一)“特定关系人”和“关系密切人”的关系
“特定关系人”与“关系密切人”具有一定的共同点,但又有所不同。“关系密切人”比“特定关系人”的外延更广,但又缺少一些“特定关系人”所涵盖的内容。笔者原以为在2009年“关系密切的人”的用语出现以后,“特定关系人”将不再使用。但是在《修七》提出后,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在2016年的《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中,又复用了“特定关系人”这一用语。由此看来,二者并不是一种单纯的补充与被补充的关系。
对于两者关系的探讨,有不同观点认为:“关系密切人”的范围可以容纳“特定关系人”,当然包括了特定关系人中的“情妇(夫)”和具有“共同利益关系的人”。同时,被“特定关系人”概念排除在外的那些仅仅有情感往来却无明显共同利益的其他人,就有可能属于“与国家工作人员有密切关系的人”。也有观点认为“关系密切人”是与近亲属并列的兜底性规定,与“特定关系人”是一种交叉关系。“特定关系人”的范畴包含了近亲属,而“关系密切人”没有包含近亲属,因此前者范围应大于“关系密切人”。
对此,参与《修七》的学者发表过一篇文章写道:考虑到特定关系人的范围往往限定在近亲属、情妇(夫)、有共同财产、共同利益这类人,然而现实中很多“中介人”其实并没有这些关系。即使有这些关系,证明难度也较大,只能证明他们有密切的关系或者交往。“关系密切人”这样的表述其实是想把这类腐败行为包含得更广一些,更接近我国反腐败方向的要求。从上文可以看出,“关系密切人”不仅涵盖了“特定关系人”,而且包含了“特定关系人”以外的一些人。
笔者认为,“关系密切人”在法律中的设置就是为了规制这类人发生利用影响力受贿的犯罪行为,很有针对性;而“特定关系人”则是为了规范这类人与国家工作人员共同犯罪的行为。两者在规范目的上是不同的,不能做同一理解。在二者的关系方面,笔者更倾向它们是包容涵盖的关系。首先,从法律解释方式之一的文义解释来看:《现代汉语词典》中对“关系”释义是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一种状态;对“密切”的释义是关系近、感情深之义,可以是公开的也可以是隐蔽的。这样,从字面意义上,“关系密切人”是指能够彼此相互作用、影响、制约的关系近、感情深的人,近亲属当然属于这个范畴。其次,从立法的角度看,“关系密切人”是一种类似兜底性的规定。因此,从多方面来看,“关系密切人”包含“特定关系人”且范围更广。
(二)“特定关系人”和“关系密切人”与《监察法》体系的关联
在《监察法》和《监察法实施条例》的条例中有三处使用“特定关系人”的表述,即《监察法》第五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监察法实施条例》第一百八十六条第二款规定、《监察法实施条例》第二百六十二条第二款规定。另外,《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八十七条也有特定关系人的相关规定。在《监察法》和《监察法实施条例》的条例中并未使用“关系密切人”的表述。
由此可见,在《监察法》体系中主要运用的是“特定关系人”这一定义,运用范畴是在涉及监察人员办案范围的表述上,明确了未经批准不得擅自接触涉案人员的特定关系人。在党纪处罚中,对于以权谋私案件的认定主体上将党员干部的特定关系人也认定为实施主体。但笔者结合自身办案的经验,认为现行的《监察法》体系在执纪执法中仅使用“特定关系人”这一定义是存在不足的。笔者将在下文中详细论述本观点。
(三)对《监察法》体系中使用“特定关系人”的一点理解
要讨论《监察法》体系中仅使用“特定关系人”是否恰当的问题,首先要了解当前法律环境下对“特定关系人”与“关系密切人”并行的一些论点。
有观点认为,“特定关系人”与“关系密切人”并行存在很大的矛盾,这种并行会导致入罪要件的冲突,因此建议取消“特定关系人”,统一为“关系密切人”。笔者深思后,认为该说法很有道理。例如,在共同受贿犯罪一项,对“特定关系人”有所规定,但对“关系密切人”并无规定,“关系密切人”只存在利用影响力受贿罪中。因此,“关系密切人”若要构成受贿共同犯罪,必须得满足“与国家工作人员有通谋的情况”和“与国家工作人员有共同占有财物的行为”这两个条件。反言之,在国家工作人员独自占有财物的情况下,该类人并不构成犯罪。此种现象在“关系密切人”涉及的利用影响力受贿罪中也未予以规范。这样,这类人虽参与了犯罪,但该行为却未受到法律的评价,这显然是不合理的。
笔者认为,在执纪执法和《监察法》体系中不使用“密切关系人”的提法会对案件量纪定性存在一定障碍。近年来,随着不法分子也开始翻新花样“围猎”领导干部,除了亲属、情妇(夫)外甚至向领导干部的司机及家里的保姆等人都予以“围猎”,并且从现实中的诸多案例来看,纵容、默许“身边人”利用影响谋取私利,造成家族式腐败的案例比比皆是,危害不可低估。其实现有执纪规则和《监察法》体系中的“特定关系人”的概念范畴早已不单局限于原法律范畴,如最新的党纪处分条例中明确规定了“本人的配偶、子女及其配偶等亲属、身边工作人员和其他特定关系人”的概念,通过此种前置增列(列举)和后缀增补(兜底)两种方式扩大了“关系人”的范围予以规范。从这一概念上看,执纪案件中的“特定关系人”已经逐步向“关系密切人”的概念范畴扩大。因此,笔者认为有必要将“特定关系人”与“关系密切人”的表述统一起来,避免概念混淆、操作不便等情况,这样更有利于打击违纪违法行为,不至于出现上述缺漏。
三、明确“特定关系人”与“关系密切人”概念对于国企执纪执法工作的意义
国有企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物质基础和政治基础,国企领导人员是我们党在经济领域的执政骨干,肩负着管理经营国有资产的责任,掌管着企业的人权、事权、财权。如何为国有企业保驾护航、督促领导人员忠实履职尽责,是我们企业纪委的重要课题。因此,围绕国有企业领导人员的范围及经商办企业的内涵,搞清搞明这些与领导干部自身有紧密关系的概念,是保证他们正确思维的首要条件。
国有企业纪委在加强违纪行为等问题的探讨同时,旨在探索一条政策把握准确,治理范围适当,程序合法恰当,并且能够取得实效的规范国有企业领导人员亲属及其特定关系人经商办企业行为的路径。因此,明确“特定关系人”与“关系密切人”概念,一是能促使国企领导干部懂法知纪,知晓哪些是“底线”不能破、哪些是“红线”不能踩、哪些是“高压线”不能碰;二是更加明确了企业领导干部亲属和其他特定关系人所办企业,禁止与领导人员所在企业发生业务关系、形成同业竞争或存在其他侵害所在企业利益的行为。从而在贯彻落实全面从严治党要求,巩固领导人员亲属和其他特定关系人所办企业与本企业往来专项整治工作成效,促进领导人员廉洁从业等方面具有重要的意义。
(作者单位:上海隧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