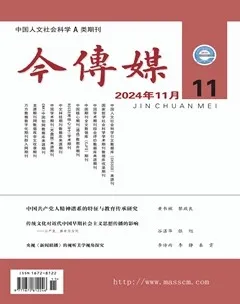中国台湾当代“返乡剧”人物、情节与主题研究(2017-2023)
摘 要:台湾返乡剧多讲述年轻主人公在城市遭遇挫折回到家乡受到亲人治愈的故事,台词以闽南语和汉语混用的方式为主,剧情围绕现实家庭生活内容展开,改编自台湾的乡土小说或漫画,深受观众喜爱。本文以2017年播出的《花甲男孩转大人》为起点至2023年播出的《有生之年》为终点的多部具有代表性的返乡剧为例,探讨其在人物设置与塑造、情节结构与改编以及主题表现与意义上的共性规律,旨在为返乡剧创作提供人物、主题和情节方面的借鉴。
关键词:台湾返乡剧;人物塑造;主题;情节结构;喜剧性
中图分类号: J90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8122 (2024) 11-0085-06
一、乡土剧与返乡剧
(一)传统乡土剧
学者廖信中在《我们台湾这些年》一书中写道:“乡土剧的流行从这两年开始火爆起来(2001年)。或许不应该说是乡土剧,精确来说是用闽南语发音的连续剧。”[1]学者柯裕棻认为,“乡土剧是一个有特殊语言历史的戏剧类型,从早年的七点到七点半播放,都是大众日常生活的故事,后来因为八点档的乡土剧加入了很多元素,使得乡土剧内容和意义比较复杂。”[2]2010年9月25日,曾任三立电视台闽南语八点档《天下父母心》《家和万事兴》编剧的叶凤英在个人访谈中指出,“虽然报纸杂志等媒体多以‘乡土剧’来称呼在八点档时段播出的闽南语连续剧,但是,三立的闽南语八点档已经与以往的乡土剧有所不同,不管是台词使用、服装造型或是故事情节都已经随着时代变化而改变,因此,以‘社会写实剧’来指代这类型的戏剧会更贴切”。乡土剧制播频道的民视国际事务总监蒋政哲认为,以闽南语为主要发音的八点档连续剧,应称呼为“家庭剧”,因为这种戏剧的内容主要围绕家庭[3]。
综合以上业界人士和学者的说法,本文认为,无论是“社会写实剧”还是“家庭剧”,都可以归纳到乡土剧当中。狭义的乡土剧概念单纯指1996年后中国台湾电视台自制自播,全部以闽南语为主,播出时间为周一到周五晚上八点,集数较长(至少一百集)的连续剧。因此,狭义的乡土剧也有“八点档连续剧”的说法。
台湾传统乡土剧大致可分为以下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乡土剧的开创时期(1962—1970年)。
第一部闽南语单元电视剧是1962年10月19播出的《重回怀抱》,之后出现的《玉兰花》(70集)奠定了中国台湾早期乡土剧剧集长度以及内容,但从总体来看,这一时期的八点档电视剧还是由汉语连续剧独占[4]。
第二阶段是乡土剧的曲折发展时期(1971—1980年)。
20世纪70年代,台湾三家电视公司华视、中视、台视为了提高广告利润,逐渐加长电视连续剧剧集,闽南语电视剧开始突破百集,例如《妈祖传》(100集)《西螺七剑》(221集)等,其中, 240集的《傻女婿》有70年代闽南语连续剧最高剧集纪录之称。1976年,台湾颁布的《广播电视法》纳入了相关语言规定,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方言节目的演出空间,使得闽南语电视剧陷入低谷。学者林奇伯指出,闽南语一度被视为“不雅”的语言,导致乡土剧与八点档绝缘,只能于中午时段或晚间六点半播出。
第三个阶段是乡土剧的完善时期(1981—1990年)。
1990年,华视剧《爱》的播出,不仅在商业上取得成功,也获得了文化界与舆论的赞许,这是闽南语电视剧向乡土剧转变的一个标志。
第四个阶段是乡土剧的停滞时期(1990—1996年)。
这一阶段八点档陆陆续续出现了诸如《醒世媳妇》《劝世媳妇》等以苦情时代背景为主的“媳妇系列”乡土剧,煽情老套的剧情让乡土剧开始走下坡路。曾拍出“台湾三部曲”的知名制作人徐进良表示:“为了台湾戏剧的前景着想,今后我绝对不再拍乡土剧!……乡土剧固然反映台湾文化,但大部分的戏只谈婆媳、妯娌之争,巴掌来、巴掌去,内容大同小异,这样下去,只会成为华人地区的小支流。”[5]
(二)当代乡土剧
当代乡土剧的发展以1996年为起点,属于纯闽南语电视剧的成熟期。
1997年,民视的出现带动台湾乡土剧的繁荣,自其成立后播出了闽南语连续剧《菅芒花的春天》。三立台紧随其后,在2000年推出八点档的闽南语连续剧《阿扁与阿珍》, 2002年播出《台湾霹雳火》《天下第一味道》等,都受到观众的喜爱。
2009年,民视《娘家》单集最高平均收视率达7. 97%; 2012年乡土剧《牵手》最终回收视率达7. 23%, 2014年三立大戏《世间情》收视率达4. 62%, 2016年,恶女遭报应的戏码让《甘味人生》的收视率在无线台达到6. 04%,有线台达到7. 51%,创下近三年八点档收视新高。同时,《世间情》集数多达437集,播出时间历时1年8个月,创下八点档播放时间最长乡土剧纪录。此后,重要的乡土剧还有《春华望露》(2016年)、《多情城市》(2019年)、《生生世世》(2020年)和《市井豪门》(2022年)等。
当代乡土剧呈现出三个显著的特点:第一,闽南语的限制使得它无法推广到其他地方。第二,内容以20世纪台湾地区生活为背景,集数多达百集以上。第三,以台视、民视、三立电视台固定的周一到周五八点档的时间播出,延续了传统乡土剧八点档的播放时间。
(三)乡土剧中的返乡剧
在当代乡土剧的发展期间(1996—至今)也出现了一种在纯闽南语电视剧基础之上推陈出新的返乡剧。2018年7月3日,华视推出“优质闽南语影音计划”征选优秀的“精致迷你剧集”,要求是单集60分钟,共10集,要借闽南语来表达本土的故事。该计划制播一系列优质闽南语戏剧节目,其中就包括迷你剧集《俗女养成记》。
自2018年以来,《俗女养成记》《用九柑仔店》《神之乡》《有生之年》等多部返乡剧不仅打破了时间限制——放在周六和周日播出,收视远超周一到周五八点档,还突破了播出频道的限制——在三大电视台之外的东森、龙华等多个电视频道播放,后逐渐在LINE TV、Vidol、CatchPlay、KKTV、myViedeo等网络平台进行播放。这一时期的返乡剧大都在20集以内,以闽南话和汉语结合的方式,围绕乡土剧所叙述的家庭生活和社会现实,浓缩乡土剧百集的长度,并大量取材于台湾本土小说,讲述乡土人物的故事,呈现出了不一样的风貌,从而使得乡土剧再度受到人们关注,也使得传统乡土剧得到又一次的革新与发展。
迄今为止,在返乡剧中有七部具有代表性的作品。第一部是改编自乡土作家杨富闵《花甲男孩》小说的《花甲男孩转大人》,该剧讲述的是年轻人花甲返乡照看弥留奶奶的故事,富含台湾乡土文化特色。第二部是2019年的《用九柑仔店》,改编自台湾本土漫画,以年轻人回乡接管阿公的柑仔店为线索展开叙事,展现大量的乡土人情记忆。第三部是《俗女养成记》,改编自江鹅同名散文,采用双时空叙事结构,展现了女主角陈嘉玲童年在台南的纯真有趣往事与当下她在台北不快乐的生活,其幽默诙谐的调性,引起了观众的喜爱和共鸣。第四部是《月村欢迎你》,讲述的是返乡建设的故事。第五部是2021年的《神之乡》,改编自左萱的漫画,将闽南文化与当代年轻人生活相融合。第六部是《俗女养成记2》,以主角返回台南而展开的乡土人情故事。第七部是2023年的《有生之年》,讲述离家多年的高嘉岳面临事业和爱情的绝境,在决定与世界告别之前选择回到家里,却在这里慢慢找到了自己。
二、返乡剧人物研究
(一)主人公设置及行动轨迹
台湾返乡剧主人公的第一个共性特征:往往于工作生活的大城市(台北)遭遇了事业和感情的挫折,促使其选择返乡“疗伤”。例如《俗女养成记》中,女主角陈嘉玲作为总裁助理,却被其老婆当成了小三,最终不得不辞掉工作。与此同时,本打算结婚的她在组建家庭时遭遇严重挫折,从而成为一个不折不扣的“鲁蛇”。为了夺回人生的主导权,她辞掉工作,结束感情,放空一切回到台南。
台湾返乡剧主人公的第二个共性特征:他(她)与祖辈的关系往往好于父母,形成隔代亲,祖父母是治愈主人公的主要角色。例如,《用九柑仔店》主人公俊龙的父母在城里工作,很少回村里看他,也算是当地的留守儿童,十八岁之前是跟阿公度过的,也是在阿公病倒之后,为了继承阿公的柑仔店,他选择回乡,渐渐感受到了大城市里的日子并不幸福,而在乡村陪伴着阿公和柑仔店是极为治愈的事情。剧中还利用闪回的形式展现俊龙和阿公曾经的幸福生活。
台湾返乡剧主人公第三个共性特征:他(她)的情感线都与乡村异性发小密切相关,对方会成为其情感对象或重要追求者,同时,主人公情感结成正果都是在乡村发生的。原因在于家乡价值的存在,成为唤起人物走向希望的关键,而漂泊的人生都在寻找一处令人心安的港湾。例如《花甲男孩转大人》中,花甲的发小雅婷素有繁星中学校花称号,但她一直拒绝花甲堂弟花明的追求,反而喜欢上花甲。然而花甲一直对爱情之事不感兴趣,可处于弥留之际的阿嬷一直不咽气,花甲猜测是阿嬷担心他一直没能成家,所以就找发小雅婷谈恋爱,但最后发现,他真正喜欢的是一直陪伴自己的同学玮琪。
(二)围绕主人公的群像模式
台湾返乡剧因其特殊的返乡性质——以主人公重新探索家乡,在当地的风土人情影响下完成心灵治愈,因此,常常通过主人公视角展现当地群像人物的故事,并呈现出一个地域与时代的集体风貌。
这些群像式配角是特定时代下当地各色人物的典型代表。
《俗女养成记》导演严艺文接受Podcast访谈时表示:“演绎过往历史时,必须加入现代元素,才能表达出多元化情绪,并赋予新的意义。”一方面,返乡剧中的女性配角代表着不同时代的台湾女性,这些角色一起反映了台湾现代化后乡村的现状。另一方面,返乡剧中的群像式配角通常都是通过与主人公建立关系,并以主人公的参与视角来展现他们各自的故事。以《花甲男孩转大人》为例,剧中花甲的四个叔叔都是拥有完整感情线、事业线以及家庭线的角色,他们的出现都是由主角返乡后带出,勾勒出鲜活立体的人物形象,从而引发观众探讨不同年龄阶段遇到的人生困境。
(三)人物的喜剧性塑造手段
首先,返乡剧人物的喜剧性往往通过设定其性格、性格与职业以及工作之间的反差和矛盾来体现的。在《俗女养成记》中,担当总裁助理的陈嘉玲拥有看似风光的职业,干的却是帮老总处理婚外情的事情。
其次,返乡剧中主角性格常常是懦弱、胆小、表里不一,但内心有着善良、正直的优秀品质,因此产生喜剧效果。在《花甲男孩转大人》中,主人公看起来是一事无成没有追求的青年,可性格中存在温柔与善良的一面,能够成为整个家族关系的纽带。同时,在返乡剧中往往也会设计一个或几个与主角性格和观念几乎完全对立的喜剧性配角。在《花甲男孩转大人》中,与性格懦弱一事无成的花甲截然相反的就是他的父亲,总是教育花甲要有男孩子的阳刚之气,逼着他接替自己的工作,强迫他跟女生去接触,想办法让其成家立业。
最后,返乡剧中人物的爱情线多元化和自由化,打破了观众对传统乡土剧的刻板印象。早期乡土剧所描写的主人公的爱情故事是苦情、悲惨的肥皂式爱情文本,且备受阻挠,历经千辛万苦,剧情往往比较扣人心弦。然而,返乡剧中人物的爱情故事突破了以往的定式,没有苦情和悲苦,没有门当户对或者曲折发展,反而变得多元化和自由化。例如,《花甲男孩转大人》有相依陪伴关系——开了槟榔摊的郑光辉和自己的员工史戴西,两人不结婚,彼此就是陪伴;单向爱情关系——小混混花明追求单纯的雅婷;为爱私奔关系——郑花慧十七岁不管家人意见和江常辉在一起;友谊升华为爱情——花甲和玮琪本是一对挚友,在彼此了解的过程中走到了一起。
三、返乡剧的情节结构
(一)连续主线贯穿下的单元故事模式
首先,返乡剧中每集都会选取一个或一对单元故事内的主人公来展开情节。以《俗女养成记》为例,每集的下半部分都讲述陈嘉玲童年时一个相对独立的故事,如第一集的下半部分是小姑姑退婚的故事。
其次,返乡剧中人物故事的讲述方式不一定按照时间顺序。以《用九柑仔店》为例,讲述了围绕在柑仔店的一群人的故事,有阿公、勇叔、俊龙、昭君等,并没有一个特定的时间顺序或长幼次序。
最后,返乡剧明显借鉴了单元剧一个或多个贯穿式主人公的模式,主角穿插在配角的故事当中,穿插在发生于不同情景的农村或城市环境当中,从而使故事结构完整而不散乱。
(二)回忆与当下双时空穿插叙事
返乡剧的双时空叙事有三种常见的故事模式。
第一种是讲述某个角色时,利用回忆人物前史为现实展现的人物做铺垫。以《花甲男孩转大人》《村里来了个暴走女外科》《有生之年》为例,片中一旦讲到新人物的故事时,都会利用回忆展现此人在过去的经历。
第二种是双时空叙事,即交替表现两个时空里两位角色的故事,最终又汇聚到同一时间点上。以《用九柑仔店》为例,第一集第一条时空线是俊龙收到阿公住院的消息,犹豫是否要辞掉工作回家照看阿公;另一条时空线讲述的是阿公年轻时喜欢上了富家小姐银月,两人私奔的故事。最终,两条线交汇到一起。
第三种是主角双时空叙事模式,通常直接将主角的现实与过往生活分成两个时空,并进行对照。《俗女养成记》中就有两个时空,一个是39岁陈嘉玲所在的时空,另一个是回忆中她还在上小学的时空。
(三)从小说漫画到返乡剧的改编方法
在五部有代表性的返乡剧中,有四部都是非原创剧本,大致具有以下几点改编规律:
第一,提取“返乡”的主旨,构建故事结构。例如,《花甲男孩》原著包括九篇短篇小说,既有人物的衰老死亡、新旧观念的冲突,也包含青少年面临家庭和人生困境,迷失自我等主题。导演瞿友宁将分散人物聚合成一个大家族,由灵魂人物“花甲”穿插其中,确立年轻人“返乡”的主题,接着,创立郑氏大家族。核心故事为花甲收到阿公病危通知后返乡,并围绕家族发生的一系列纷争而获得成长。
第二,强化主要角色的爱情线。例如,原著《俗女养成记》《村里来了个暴走女外科》《花甲男孩》中,主角均没有爱情线,《用九柑仔店》主角的爱情线只是简单带过,但在改编的返乡题材电视剧中,导演均对爱情线进行强化,使其推动主人公返乡后的个人成长,并治愈主人公。
第三,丰富次要人物在剧集中的形象。以《花甲男孩转大人》为例,片中构建的郑氏家族均来自《花甲男孩》短篇小说集,其中,花甲姐姐形象源于《有鬼》中讲述逃离家庭暴力的母女,花甲二叔的形象源于《繁星五号》中带着儿子逃离伤心往事地,却因意外事故导致儿子去世的失婚失业爸爸,这些人物在花甲返乡后的成长过程中占有重要位置,最后也都完成了“转大人”的主题含义。
四、返乡剧主题研究
(一)重返乡土凸显亲情至上
返乡剧固定表现回归家乡与亲情的主题,主要原因在于以下两点:
第一,乡土温情与家乡发展的驱动。《花甲男孩转大人》中,花甲的家庭关系比较复杂,他虽然与父亲关系不好却执意返乡,这样的执念源于难以割舍的乡愁。《用九柑仔店》中的柑仔店承载着街区所有人的记忆,为乡土注入了许多温暖的感情,这也是主角选择回归家乡的原因所在,即他们无法释怀乡土带来的温情。与此同时, 2010年8月中国台湾省政府颁布“台湾再生条例”,强调积极建设新农村; 2017年推行“创生政策”,使得乡村建设被提上议程,地方集市、农村产业也受到重视,重返家乡开始变得更有意义,象征着新的机遇和发展。
第二,当代年轻人在城市发展中遭遇的困境。返乡剧讲述“北漂青年”返乡的故事,“北漂”寓意着充满压力的台北打工生活。《俗女养成记》中在台北工作的陈嘉玲铆足全力在职场中表现出优雅干练的模样,但是,当她发现无论怎么努力都无法符合社会的期待时,不仅对自己产生了怀疑,更承受着许多外界压力——被催婚、跟婆婆之间的矛盾等。这些问题在其它返乡剧中也都出现过,其所代表的是年轻人或中年人在城市所面临的困境,而帮助剧中人物解决困境的唯一方法,就是回归最熟悉的家乡重新开始生活,重新接纳自己、遇到所爱之人,这样的人生才是她真正的人生。因此,回归家乡与亲情一直是返乡剧不变的主题。
(二)对观众的心理疗愈
台湾当代年轻女性面临着职场与家庭的平衡,以及婆媳之间、伴侣相处、父母与子女等多方面的矛盾,但她们更想成为具有独立价值和能够自主人生的个体。返乡剧给予了台湾年轻女性一个合理的答案——我的人生我做主,她们摒弃了家庭与职场带来的束缚,反而通过自己的奋斗活出尊严,找到自我价值,拥有决定权,这恰好满足当代台湾女性受众对于自我塑造的心理需求。对于台湾男性青年来说,父辈对自己的培养是要变得年轻有为、出类拔萃,能够传宗接代,但是,返乡剧中的男性角色恰恰相反,他们大多碌碌无为,并不完全符合社会的期待,这也是一些台湾青年的现状——没有梦想,没有憧憬,只想通过打工的方式努力生活。随着返乡剧在各地受到好评,说明剧中主角呈现的人生状态以及做出的选择治愈了越来越多年轻的观众群体,使得他们学会接受自己的平凡。
五、结 语
本文通过研究2017—2023年台湾返乡剧的人物、情节与主题,总结了一些共性的创作规律。首先,返乡剧并非昙花一现,它是由沉淀了五十余年的乡土剧发展而来,在人物、情节、语言等多方面具有鲜明的乡土气息。其次,返乡剧照顾到当下的年轻观众,除了改变播出方式、剧集长度、语言外,还找到当下年轻人的困境——在城市奋斗遇到压力而不得不归乡疗伤。它展现了年轻人疗伤的方法——回到家乡,因为家乡有他们眷恋的亲人或朋友,如阿公阿嬷、异性发小,帮助其弥补感情的缺憾。同时,它拓宽了人物视角,不再拘泥主角本身,而是刻画家乡群像人物,描绘地方风貌;它丰富了故事的结构——有一个连续的主线,但贯穿了大量的单元故事。最后,这些片段记忆是主人公在家乡的过往生活,导演融入小说、散文、漫画等多类型叙事元素,努力接近年轻观众的喜好,紧紧围绕回归家乡和亲情主题治愈年轻人,引导他们接受平凡的自己。
参考文献:
[1] 廖信忠.我们台湾这些年[M].重庆:重庆出版集团,2009:204-208.
[2] 柯裕棻.批判的连结[M].唐山:唐山出版社, 2006:158-160.
[3] 程绍淳.媒体生产区域化下被错置的文化消费与生产:以民视的乡土剧《意难忘》为例[J].传播与社会学刊,2012(19):34-36.
[4] 陈飞宝,张敦财.台湾电视发展史[M].福州:海风出版社,1994:110-112.
[5] 刘子凤.为台湾戏剧的前景着想 制作人说重话徐进良 今后绝不再拍乡土剧[N].联合报,2000-02-24(26).
[责任编辑:李慕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