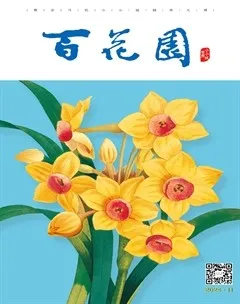王羲之三章
兰亭会
孙绰早就等着这一次兰亭盛会了。孙绰是王羲之的朋友。
永和九年,也就是公元353年,这一年的三月初三,王羲之邀请孙绰参加兰亭会。
参加兰亭会的,主要是士族子弟,包括王家、谢家、袁家、羊家、郗家、庾家、桓家这些显赫的家族。还有清谈名士、文学名流,一共42人。王羲之九岁的儿子王献之也参加了。
论家族,孙绰比不上王、谢、郗、桓。论清谈,孙绰比不上支道林。但孙绰文章写得好。孙绰这人,还喜欢给名流政要作碑文。写文章,有人给自己写,有人帮别人写。帮别人写文章,做的都是锦上添花的事。王、谢、郗、桓再牛,死后的碑文都是要孙绰写的。孙绰写碑文,还总夹带点儿私货,特别爱写与死者生前交情深厚,与死者是灵魂知己。可死者的后代,没几个是这样认为的。孙绰一点儿也不难堪。写着写着,孙绰成了名门贵族圈子里的座上宾。王羲之做会稽内史时,推荐孙绰做了右军长史,后来又推荐他做了永嘉太守。
和孙绰一样兴奋的,还有一个叫支道林的高僧。和孙绰会写不一样,支道林善辩。支道林好谈玄理,亦精通老庄之说,最喜欢的是《庄子·逍遥游》。支道林长得丑,清高如王羲之者,开始是瞧不起支道林的。但后来,支道林硬是凭自己三寸不烂之舌,叩开了王府的大门。支道林讲庄子的《逍遥游》,王羲之完全被迷倒了。《世说新语》是这样记载的:“支作数千言,才藻新奇,花烂映发”,于是王羲之“披襟解带,留连不能已”。
同样兴奋的,还有王羲之。王羲之这段时间正在闹失眠,而且似乎越来越严重。353年,他当会稽内史第三年了。这几年,禁酒节粮,惩治贪官,王羲之忙得很。忙得很的王羲之,突然想起这些年忙于俗务,很久没有和朋友畅玩过了。他开始筹划这样的一场聚会。为了这样的一场聚会,五十岁的王羲之像新婚一样踌躇满志又手足无措。
三月初三这天,整个东晋最耀眼的星全部到位了。
一群人浩浩荡荡而来,依次在小溪边选了位置坐下。
这样的一场盛会,酒杯是有讲究的。有人说用的是漆制的酒杯,有人说是宽而扁平的酒杯才可以浮起来,有人说是将酒杯放在荷叶上。有人说,也不是真正坐在溪边,只是将溪水引入弯曲的水道中。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置杯于水中,任其漂流。这就叫曲水流觞了。杯停在谁面前,谁就要作诗。作不出诗来,乃罚酒三杯。孙绰是早就胸中有诗了。这次聚会,共有26个人作了诗,孙绰一个人就作了两首,一首四言诗,一首五言诗。
九岁的王献之,一个字也吟不出来,他的几个哥哥都作了诗。王献之跑到父亲那里告状,说哥哥们的诗是早就想好了的。王羲之大笑。
这些诗结而成集,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兰亭诗集》了。这些诗,估计是没几个人记得了。
可又有谁想得到呢?将近1700年过去了,山也记得,水也记得,那年的三月初三,一个叫王羲之的风流潇洒的男人,用一管鼠须笔,在一张蚕茧纸上,写下了中国书法史上和中国文学史上不可磨灭的《兰亭集序》。
不妨还原一下当时的场景。王羲之酒喝得微醺,众人的诗写得也差不多了,大家公推王羲之为诗集作序。王羲之也不推辞——大概王羲之也早就等这一天了。借着酒兴,王羲之运气走笔:“永和九年,岁在癸丑,暮春之初,会于会稽山阴之兰亭,修禊事也……”
文思如泉涌,好久没有这样畅快过了。写到“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所以游目骋怀,足以极视听之娱,信可乐也”,众人一片喝彩声。
王羲之笔锋一转,接着写道:“夫人之相与,俯仰一世。或取诸怀抱,悟言一室之内;或因寄所托,放浪形骸之外。”
整个山林都静寂了。
王羲之越写越快,每落一字,众人刚要惊叹,又马上屏住呼吸。王羲之疾笔而行,接着写道:“固知一死生为虚诞,齐彭殇为妄作。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悲夫!”
打破寂静的是王献之。王献之说:“父亲大人作文,一会儿高兴,一会儿悲伤;一会儿生,一会儿死,孩儿看不懂。”
众人皆大笑,寂静的山林突然有了鸟叫声,还有溪流的歌唱。王羲之也笑了,边笑边说道:“有些问题,你长大了,去问那巍峨的山,去问那奔腾的水,去问那悠悠的岁月,岁月是最好的老师。”
支道林在一旁听了大惊——几日不见,逸少(王羲之字逸少)之清谈,已入化境。
说话间,王羲之已写完了。王羲之掷笔,长吁一口气,说道:“各位见笑了,今日景美酒好,喝着喝着就醉了。”
孙绰说:“逸少这话,大有玄理。明山秀水,本是用来化解心中郁结,可今日看羲之这锦绣文章,不由让我等笑着笑着就哭了。”
支道林大笑,随口说道:“如此说来,今日盛会,走着走着就散了。”
公元386年,四十三岁的王献之病重弥留之际,突然想起自己九岁那年参加的那一场兰亭之会,一代书坛大家,拿起笔来想写几个字,却不知从何处下笔。
该写的句子,都被父亲写了。该说的话,那一场兰亭会上似乎都说了。
裹鲊香
郗璿这几天一直忙着做一种叫裹鲊的食品。她不让下人们插手,从选材、腌制,到挑选包裹用的荷叶,她都亲自动手。
这裹鲊,看起来简单,吃起来香,但做起来不容易。很多年了,郗璿做裹鲊从来不敢大意。米饭的蒸制讲究糯而不腻,香而爽口;橘皮丝是存放了五年以上的;鱼一定新鲜活杀,一片片切成长片;再将洗净的茱萸籽一起搅拌腌制。这过程,慢工出细活儿。腌制好后,再用荷叶一层层包裹得严严实实,然后,用文火慢慢地蒸。
郗璿享受这过程。因为王羲之爱吃。郗璿是王羲之的妻子。从小两口到老两口,两人一辈子生了七男一女,其中书法家都好几个。一屋子的风流人物。
王羲之不仅自己爱吃裹鲊,还送给朋友吃。他亲自写信给朋友,说这裹鲊好吃,喜欢吃的话告诉他,他再给朋友寄。
王羲之每次给朋友写了信,就给郗璿看。王羲之是得意自己的字,或古朴小楷,或飘逸行书,或狂野草书。王羲之那点儿小心思,郗璿当然知道。郗璿每次都可着劲儿夸。她知道,丈夫需要她的褒奖。
谢安也喜欢吃裹鲊。谢安比王羲之小十七岁。王羲之做会稽内史时,年纪轻轻的谢安优哉游哉地在会稽过隐居生活。
谢安每次来找王羲之,一边品裹鲊,一边和王羲之谈书法,谈老庄,每每玄词妙句迭出。王羲之每次都为其奇妙玄理所折服。每次,谢安走了,王羲之送到门外,看着谢安的背影,久久不肯转身。回到家,却要长叹一声。
郗璿说:“夫君与安石(谢安字安石)每次相谈甚欢,何故叹息?”
王羲之说:“安石真是一等的风流人物,可惜了。”
郗璿笑曰:“可惜何来?”
王羲之正色道:“安石每天想的就是品美食,读老庄,吟诗作文。当下多事之秋,此等才华,不想着出来为国效力,可惜,可惜!”
郗璿又笑曰:“夫君此言差矣。夫君与安石,都是真名士。夫君风流,看似无为却冀有所作为。安石风流,却是以放达而放飞心灵。夫君在茫茫尘世里还要仰望星空,安石呢,在高谈阔论里俯视众生。”
王羲之大惊,没想到夫人有如此妙论。以前一直以为自己也是风流名士,想不到夫人对自己的评价如此精到。这么想想,其实自己又何尝不是这样呢?做官近三十年了,自己似乎每天都在挣扎,白天是一个王羲之,晚上一回到书房,又是另一个王羲之。“笃不喜见客,笃不堪烦事,此自死不可化,而人理所重如此”,类似这样的句子,写给朋友的,随意乱涂的,不知有多少了。可到了第二天,回到衙门之内,面对繁杂的政务,他又开始一件一件地亲力亲为。
他从没和妻子讲过。王羲之总觉得,自己是个名士,但更是个男人。真名士,自风流。是名士,就要让自己活得风流;是男人,就要让妻子活得风光。
郗璿后来知道,很快,王羲之和谢安又有了一次醉卧清谈的经典对话。谢安酒足后大发感叹:“人世茫茫,林泉高致,醉卧清谈,不负此生。”王羲之力劝谢安出山,语重心长:“今四郊多垒,宜人人自效。而虚谈废务,浮文妨要,恐非当今所宜。”谢安马上答曰:“秦任商鞅,二世而亡,岂清言致患邪?”王羲之无言以对。
转眼就到了355年,王羲之任会稽内史的第五个年头。355年的春天比以往几年的春天来得早。东晋的名士们还一个个比赛着在长袍子里扪虱子,遍地的迎春花已经开得美丽而幸福。泥土一天比一天芬芳,空气一天比一天甜。像往常一样,郗璿开始吩咐下人们做准备工作。她知道,丈夫的朋友们,都等着作为会稽内史的王羲之与民同乐。
但王羲之一直没动静。郗璿不知道,王羲之的朋友们也不知道,王羲之最近在忙什么。
谁也没有想到,王羲之做了一件比兰亭盛会更轰动的大事。他来到父母坟墓前发了一通慷慨激昂的宣言,表示从此远离官场。他发誓:“自今之后,敢渝此心,贪冒苟进,是有无尊之心而不子也。子而不子,天地所不覆载,名教所不得容。信誓之诚,有如皦日!”意思就是,从今以后再也不当官了,再当官就天地不容。
就不当官而已,王羲之闹得惊天动地,不像后来的陶渊明,背起包袱就走。
整个东晋的官场都轰动了。春天的会稽城,百鸟齐鸣,鲜花怒放,从会稽府衙门到家里的那段短短的青石板路,王羲之一个人,第一次走得轰轰烈烈,激情昂扬。
郗璿笑盈盈走出来迎接王羲之。老远,她仿佛看见三十多年前那个袒胸躺在床上吃胡饼的少年,那个率性、真挚,还有那么一点儿孤傲的王羲之。也就在那一天,十五岁的少女郗璿,第一次有了奇妙的感觉。她觉得,她和那个叫王羲之的袒胸露腹的少年,有很多前世今生的故事。
王羲之告诉夫人:“准备搬家,地方都选好了,就在那郯溪的源头。”
郗璿说:“好!”
王羲之说:“在那里,春天的花最香,老远老远,就听得溪水欢快地歌唱。”
郗璿笑着说:“听说郯溪的鲈鱼最鲜美,用这种鱼腌制出来的裹鲊,是世上最香的裹鲊了。”
第二年,鲈鱼最鲜美的季节,谢安收到了王羲之寄来的裹鲊。
公元360年,谢安终于愿意出山,在征西大将军桓温的手下做了一个小官。像当年王羲之辞官一样,谢安出山,朝野为之震动。
十七帖
王羲之没有午睡的习惯。那天午餐,仆人送上来几个蒸饼,蒸饼上还有裂纹的十字花。王羲之对吃有讲究,要是以往,一定赞不绝口,那天却提不起胃口,简单吃了几口就放下了。他不由想起几年前的兰亭雅集,曲水流觞,一切都是那么精美雅致。而那时,自己的创造力是那么丰富,精力还是那么旺盛,每当太阳升起就感觉到生命的火焰在跳跃。
那种潇洒风流,怕是再也没有了。近期服食丹药,效果越来越不理想。他突然感觉很累,就想小憩一下,眼皮一合,很快就睡过去了。
那一年,公元360年,王羲之五十七岁。天奇冷,王羲之也没想到,就闭一下眼的工夫,醒来时,天地间已是粉妆玉砌,纷纷扬扬的大雪还在下。这样的大雪,在江南实在是太少见了。房间里的火炉,不知什么时候熄灭了。下人们怕是出去玩雪了,连叫了几声,没人应。王羲之打了一个冷战。
短短地打个盹儿,他做了一个长长的梦。以往也有做梦的时候,但梦醒后就忘记了。这次的梦,像专门等着他进入,他活了几十年就好像专为赴一个这样的梦境。梦里见到的每个人,他都记得名字。梦里到过的每个地方,他都说得出风物。
梦是从青城山开始的。和他一起游青城山的,是益州刺史周抚。
周抚的头发也白了,满头银发,白得耀眼。王羲之大叫着:“老了老了,你也老了。”周抚笑着:“能不老吗?我今年都快七十了。”王羲之就扳起指头数,扳下一个指头就说一件那一年的趣事,说起在哪一年的哪一天,自己给周抚写过一封什么信,周抚回了一封什么信。周抚说:“这样数下去,你数一天都数不完。自我来四川,你我不相见已经二十六年了。”
两个老朋友,互相看着对方,竟一时无话。
青城山号称西蜀第一山。相传还是轩辕黄帝时,有个叫宁封子的人,是管理制作陶器的官,他就是在青城山修道,后来黄帝筑坛拜其为五岳丈人。再后来五斗米道的创始人张道陵来到青城山,在此结茅传道,青城山成为道教发源地之一。王羲之家族都笃信五斗米道。自周抚来四川,他就心心念念很久了,每写信必提及,想不到今日竟圆此毕生之梦。两个老朋友,手牵着手,从山脚下开始,打算一个道观一个道观好好看看。
王羲之像个小孩,几乎是跳跃着前行。周抚虽是武将,可毕竟年纪大了,才看了几个道观,就有点儿跟不上了。偏偏王羲之还问个不停。周抚虽长期在四川,可哪像王羲之这么知识渊博?周抚说:“这大大小小七十多个道观,你这么走下去问下去,我这老骨头还不散架了?我周抚一代名将,不死在战场上,却要死在你王羲之手上了。我要是死在你手上,还有谁会像我一样,二十多年和你写信的?你做梦去吧。”
王羲之被武将周抚的幽默逗得哈哈大笑。想起这二十多年,自己给周抚不知写过多少封信了。王羲之的信,大都较短,三言两语,想起什么事要和周抚讲,拿起笔来就写。他想起自己给周抚写过的一封长信,在那封信里,他结结实实地表扬了周抚,说扬雄的《蜀都赋》、左思的《三都赋》,都不如周抚信中的蜀地精彩。他恨不得马上就飞过去,看蜀地仙雾缭绕的山山水水。
现在,在七十岁的周抚面前,王羲之就恨不得飞起来。
周抚受他的感染,也不觉加快了脚步。两个人一路笑声。青城山做证,两个男人,一个七十岁,一个五十七岁,在那蓝天白云之下,孩童般地奔跑。
王羲之,这个号称东晋最潇洒风流的男人,突然感觉到生活的全部意义原来都在这儿;自己原来的几十年,都在假装,假装潇洒,假装风流,假装快乐,可他的心里一直都非常在意。他在意别人对他官声的评价,在意自己的官位比别人低,在意孩子们的幸福,在意自己每况愈下的身体,以至不远千里寻找炼丹之药。实际上,几十年来,自己一直没有离开过名利场。
王羲之自己也想不到,两个男人的友情,仅仅通过书信就可以维持二十六年。他看着眼前老态明显的周抚,突然记不起二十六年前第一次见到周抚是一个什么样的场景了,但他记得起每次写信时那份按捺不住的激动。每次在信里他都对周抚说:“老朋友,我要来看你了。你要保重身体,不要到时候老得走不动。”好多次,他制定了详细的计划,但没有一次成行。在最近的一封信里,王羲之写道:“吾有七儿一女,皆同生。婚娶以毕,唯一小者尚未婚耳。过此一婚,便得至彼。今内外孙有十六人,足慰目前。足下情至委曲,故具示。”
王羲之讲的这个“尚未婚耳”的小儿子,就是王献之。似乎心有灵犀,周抚也问起王献之的婚事。周抚说:“等献之解决了终身大事,孩子们都有归宿了,你来青城山住上一年半载吧。”
“好呢。”王羲之一边应着周抚,一边走着,口里念着“献之呢?献之呢”,突然就一脚绊倒在门槛上,醒了。
原来是一场梦,王羲之惊出一身汗来。梦中的场景还是这么清晰可见,周抚的说话声似乎还在耳边。
当晚,王羲之给周抚写信,记述这一场大雪:“计与足下别,廿六年于今。虽时书问,不解阔怀。省足下先后二书,但增叹慨。顷积雪凝寒,五十年中所无。想顷如常,冀来夏秋间,或复得足下问耳。比者悠悠,如何可言?”
这就是被后来无数书家顶礼膜拜的传世名作《积雪凝寒帖》,方处锋棱可截铁,圆处婉转若飘带。
他终究是不敢说刚刚做的这个梦,他不敢写在梦里他那孩童般的快乐。
他知道,周抚一定是懂他的。荣辱得失、离合悲欢,全在每一封信里,在那切笔如铁、圆笔若带里婉转流淌。
写完《积雪凝寒帖》,雪竟还没有要停下来的意思。王羲之信步来到王献之的房间。王献之正在习字。看小儿子这么用功,王羲之目光里突然多了很多柔情。王献之看父亲似乎高兴,又似乎惆怅,这是从来没有过的。看王献之一脸诧异,王羲之不禁又问:“近日习字,可有体悟?”
王献之恭敬对曰:“孩儿近日学书,略有心得。”
“快快说来听听。”王羲之微笑道。
王献之说道:“窃以为,善书者当兼众家之长,集诸体之美。学一门一体固然可成大器,然终究墨守成规。事贵变通,吾当兼众家之长,破体而成。”
看父亲脸色没有变化,王献之又说:“父亲,我反复揣摩研究之后,找到了草书与行书之间突破‘往法’的途径。父亲大人,你也应当‘改体’试试。”
王献之言外之意,其实就是父亲的书法没有变化,太呆!王羲之本想斥骂:“放肆!”话到嘴边又咽下了。看到儿子,他想起自己年轻时的样子。什么是风流啊?这才是风流。“风流为一时之冠”,这曾经是时人对自己的评价。现在,他多想对儿子说:“儿子呀,你,风流为一时之冠!至于我,要死的人了,还有很多未了之事呀!”
没多久,王羲之又亲自写了一封信,为儿子王献之提亲:“献之字子敬,少有清誉,善隶书,咄咄逼人。仰与公宿旧通家,光阴相接。承公贤女,淑质直亮,确懿纯美,敢欲使子敬为门闾之宾……”
他把王献之一顿猛夸。他要给儿子提亲的这个女孩,叫郗道茂。郗道茂是东晋名臣郗鉴之孙女,王献之的表姐。
王献之也当得起这样的夸奖。其博采众长的“破体书”后来大放异彩,在书法史上产生了重要影响。只是,王羲之没想到的是,他看好的王献之和郗道茂的婚姻却不长久,最后竟成悲剧。
公元361年,王羲之去世。365年,周抚死在益州。两个好朋友,终究是没能见上一面。
《积雪凝寒帖》等帖子,被收藏在《十七帖》里。《十七帖》是王羲之的草书代表作,一共不到30个帖子,其中大部分是写给同一个人——周抚的信件。
[责任编辑 王彦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