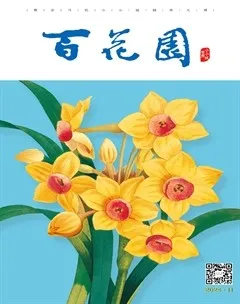麝香蛋蛋

我去大山里看望三舅。三舅是护林员,住在离村五公里远的酸刺沟口。三舅常年巡山,栉风沐雨,腰佝偻脸黧黑。我的到来,使三舅和舅母老两口合不拢嘴。三舅宰了院里跑的鸡,舅母摘来屋后地里的菜,忙乎着做了一桌子晚餐。吃着食材新鲜的菜,喝着辣烈的酒,我和三舅打开了话匣子。脸通红的三舅抿口酒,叹气说:“要是那孩子能保住,现在和你一样大了。”舅母在旁低垂下头,抹起眼泪。三舅和舅母没生养孩子,对此我一直纳闷。三舅向我聊起了往事。
靠山吃山。山高屲大,山林里有狐狸、狍子、旱獭、马鹿等野物,山民们布扣套、挖陷阱、撒迷药、用土铳,争相猎杀野物。在那物资匮乏的年代里,这些野物的肉可解馋,皮可卖钱。尤其是香子,身上的麝香蛋蛋能卖十几元,是天价呀!三舅偷卖了三个麝香蛋蛋才得以娶回舅母,三舅说:“这婆娘是三个蛋蛋换来的。”
香子即林麝,形似鹿,有羊羔般大,耳朵大而直立,全身灰褐色,背部有白色的斑点,前肢短后肢长。香子机敏警觉,有一丁点儿风吹草动,就跳跃飞蹿而去,眨眼间不见踪影。捕捉香子不易,山民把能捕捉到香子的人尊称为“香子匠”。年轻的三舅是有名的“香子匠”。他早上赶羊上山,傍晚回来,肩上常扛着野兔、旱獭、山鸡,隔两三个月能扛回来一只香子。
松树林里,一棵大树下发现了比羊粪蛋稍大点儿的一堆粪蛋,这里是香子固定的“厕所”。林子这么大,香子不随地大小便。离粪蛋十几米,会找到一根高四五十厘米、油光可鉴的枯树桩,散发着浓郁呛人的麝香味,这是香子的蹭桩。香子用麝香蛋蛋蹭树桩,来标记自己的领地。
麝香蛋蛋是公香子肚脐与睾丸之间的香腺,呈袋状。蛋蛋的形成跟珍珠的形成有异曲同工之处:香子水足草饱,伸展开四肢躺在大树下,肚下的腺体外翻,放射香味,吸引来蚂蚁、蚊虫等进入腺体;腺体受刺激而收缩,分泌腺液包裹住虫子,久之腺体内就形成了扁豆大的褐色颗粒。成年香子的麝香蛋蛋有鸡蛋般大,重约二三十克。山里流传着一个故事:两个婆娘去林中拾柴,碰到一只死了的香子。先发现的婆娘冲上去,挥起柴刀割下了香子的睾丸,满脸堆笑地回家向男人报喜。男人脸色酱紫,跺脚骂:“瞎婆娘,天天摸老子的还没摸够吗?”另一个婆娘割了香子肚脐旁的麝香蛋蛋,发了笔意外之财。
三舅和舅母结婚五年,舅母的肚子一直没鼓起来。有人出主意,以马鹿胎作药引补身子准能怀孕。三舅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偷捕到一只马鹿,舅母吃了鹿胎,喝了中药,不久竟真怀孕了。
有身孕的舅母后背痛,前胸胀,身体一天天瘦弱下去。三舅进山了。山民们祸害野物,野物越来越少,香子几乎绝迹了。在酸刺沟半山腰的松林里,发现了新鲜的粪堆,三舅的心怦怦狂跳——天助我呀,有了麝香蛋蛋,就能带婆娘去城里看病了。三舅在粪堆方圆五十米的树木间隙里布下了猎夹、扣套。
第三天下午,山沟里传来香子“呦——”的凄厉嚎叫。三舅撂下挖地的铁锹,飞快地奔向半山腰。香子性刚烈,绝望中的香子有时会吃掉自己的麝香蛋蛋,让山民竹篮打水一场空。
三舅爬到半山腰,被眼前的景象吓呆了。触发了机关的猎夹上留下了半截血肉模糊的香子腿,想必是香子为了活命,生生咬断了自己的腿。三舅心中战栗,可为了有身孕的舅母,三舅咬紧了牙关。
“香子舍命不舍山”,香子痴恋故土。即使逃脱了,香子不久还是会重回到这儿。三舅深谙香子的特性。
一个月后,三舅发现那粪堆上有了新鲜的粪蛋,他抿嘴笑了。这次,三舅在粪堆方圆一百米的树木间隙里铺下了扣套。第六天,三舅去半山腰,看到三条腿的香子被钢丝扣套住了脑袋,高高地吊在大树上。
三舅扛回了香子,割下了麝香蛋蛋。舅母捧着麝香蛋蛋,眯缝眼细瞅。三舅做了葱爆香子肉,这是他和舅母时隔好几个月才尝到肉味,那香味令二人大快朵颐。
当晚,舅母突然肚子剧痛,三舅拉架子车把舅母送到了镇卫生院。路上,舅母双腿间鲜血直流,胎儿流产了。医生说,是麝香动了胎气。舅母捶打舅舅:“都是你造的孽呀!”三舅扯着自己的头发,发出了像香子般的惨叫。
三舅砸了猎夹,扔了扣套,再也不进山捕猎了。舅母落下了病根,再没怀孕。
几年后,大山里封山育林,三舅应聘做了护林员,一干就是二十多年。工资虽不高,可三舅喜欢这工作,整天穿梭在山林中,看护林草,看护野物。三舅说,现在“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观念深入山民心中,山民们保护林草,爱护野物。大山的天更蓝了,水更清了,山更绿了,野物更多了。
“呦——”“嗷——”“啾——”窗外黑魆魆的密林中传来野物的叫声,三舅眯眼歪头竖耳。舅母扯三舅的胳膊:“老头子,早点儿睡觉,明早还要早起巡山呢。”
[责任编辑 冬 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