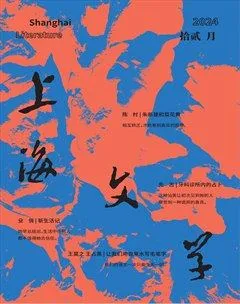让我们用自来水写毛笔字
第一封信:
占黑,记得四年前的一次春游,我们展望写作,你说想尝试言情,也在规划长篇。那时候你的小说宇宙就像被激怒的河豚鱼,从早期六七千字左右的身材变成五六万字的体量,最典型的莫过于《痴子》,后来发表在《上海文学》的《韦驮天》也属于这时期的代表作,对白在这些作品里扮演了更为重要的角色。我本人最近也在经历类似的转变,其结果是很难再回到万字以内短篇小说的赛道,偶尔回看自己起跑时的作品,也会有遗憾之感,仿佛在植物园观赏了一些花蕾,它们挺好的,但可以更美。我很清楚这种审美转变的逻辑,偶尔与“巨鹿路”的朋友说起,有人笑笑答道:“这不蛮好,同样发一篇小说,稿费多拿不少。”有趣的是,最近读到宗仁发老师的一篇文章,他说:“这几年参加《收获》文学排行榜的评审和一些期刊的评奖,集中阅读了刊物上发表的数篇短篇小说,包括平时在我主编的《作家》来稿中也是明显感觉到现在的短篇小说越写越长,动辄一万七八千字,甚至超出两万字,而万字以内的短篇则越来越少见。”看来,这种转变不是你我的个别现象。
莫之
第一封回信:
莫之,说来真巧,在对话之前,我最先想到的也是那次春游。那是二○二○年,上海还在那场风暴外围,植物园里景色正好,因为人们很少出门了。现在回想,当时的展望一件也没实现,言情和长篇就像两张悬浮的大饼,我从来没有真正去够过,也懒得去够了,就让它像个笑话挂在我的头顶好了。回望过去的写作,大概是在写完《小花旦》这个中篇之后,我告别了那些小体量的、街道英雄的习作,但并不清楚接下来想干什么。只是在顺其自然的过程中,发现后面的习作基本都是两万字上下的体量了。长久以来,这也成了某种私人的“甜区”和“舒适区”,我喜欢和习惯这种尺寸,像一部电影,不长不短,既能保证精准,又能送它起飞,对于我自己的精力而言,也刚好在全力消耗和快要耗竭的临界点上。但当我开始尝试写更长的作品时——我再回头看,发现它们各有各的失败之处,包括你提到的《韦驮天》《痴子》,失控的地方太多了。我最近在整理书稿,发现最糟糕的一篇叫《半熟之士》,糟糕得我都心疼那些读过的人。最后改了题目,尽力调整了结构,做了大量删减,让它看起来不至于太臃肿。但失败是再正常不过的了,你说对哇?好快啊,我上一次写小说已经是一年多以前的事了,不知不觉就停下来了。最近读你的《忘不了的你》,也是很长的作品,不过因为时间线拉得长,读下来很顺,也很松,我得学习这样的节奏,不要总是紧绷绷地绷在那里。你写得很好。
占黑
第二封信:
占黑,说起那个闲坐植物园的下午,对我来说也是直面困境。我的小说写作当时陷入某几个主题的循环(音乐里,某段旋律的重复也被称为loop),水准也倒退得厉害,这就像那时静肃在家,所谓的活动与锻炼仅限于家庭空间,你多走几步,就回到了原点。我当时很反感这种loop的状态,试图在小说天地里多闯几步,结果更加喇叭腔,简直荒腔走板。你刚才提到舒适区,我们这些写作者登上舞台,无论龙套绿叶红花,各有舒适区,以前我觉得舒适区的面积要大,现在更在意体积,换言之,舒适区要如何挖得深,可以像以前战备挖的防空洞那样容纳十几支摇滚乐队在上海的地下同时呐喊——你以前玩乐队也有过在杨浦某防空洞排练的体验。挖得深,也可以解释短篇增肥的动机。我不晓得你的小说是怎么生长的,我是很依赖生活经验的,从现实提炼打动我的人物,然后为他们开垦一片土壤,逐渐形成故事。或许我是因为学生时代读烦了话剧式的传统小说,抑或是我在写小说以前有五年的记者生涯,习惯了凝练的笔触,对白这种文体在我的小说里一直缺乏温度,朋友说:“也是因为你的对白写得不好。”我听了不响。你提到《忘不了的你》,这个小说是我真正接纳对白的一个作品,在此之前,有一些对白明显抬头的尝试被我归为展示诚意,属于我有意识要跟它和好。谈判的过程,我着实为对白唱了不少赞歌,譬如对白最容易达成某种活灵活现的诗意,能够用一种捣浆糊的方式为很不龙标的内容消毒。我还说了很多不适合这个场合刊登的赞美诗,总之,对白它被我夸得老脸一红,挥挥手说,好了,好了,我们不要商业互吹啦,莫之,我原谅你了。随后,我正式进入了一种新的写作状态。占黑,你前面提到《小花旦》,过谦地将它之前的短篇称为习作,能谈谈那时期的转变吗?叙事者和小花旦的对话相当精彩。
莫之
第二封回信:
《忘不了的你》里有好的对话,不轻不重,不避让,也不抢风头,作为读者,我应给你这点信心,你和你在写作中所抗拒的对话在此处是和解的。我有个陋习,也可以说是我和我那份“对话”难以和解的地方,那就是我不用引号。可能是潜意识里不想把对话作为单独一类区分出去,一场小小的“去特殊化”运动。
对话是很有意思的,如果把写作看成素描,对话也许是最需要用橡皮涂涂改改的地方。打个比方,它就像公园里老人拿自来水在水泥地上写毛笔字,不适合留下痕迹,要快晒干了才好看,晒干后凭空消失了更好看,你懂的,结结实实的就不容易好看了。尤其是在不太长的篇幅里,让它承担推进情节或暴露信息的责任是很辛苦的。如果把对话可视化,它应该是一团渐渐变大的毛线,一捏又可以变小变扁,而不是一条线的形状,你喜欢饭桌戏的氛围,肯定能get我不太准确的描述。有时候对话的氛围和状态比内容更令人着迷,当然,从写的角度来说,对话的内容也很难拿捏,太实太虚都会导向不自然,一旦不自然,对话的根基直接就倒下了。
《小花旦》里说了什么我记不清了,这几年我有点沉迷于观察和写隔空对话,各种即时通讯工具,社交软件,一个屏幕,一条对话框,一些字幕,千丝万缕的情绪、涵义、氛围,这里面太有花头了,在某些特殊情景下,它们超越了沟通,甚至超越了新闻报道的能量。
占黑
第三封信:
占黑,隔了两天收到你的回信,这感觉如同你所说,我们的对话也许要学沾水在公园的地上写毛笔字,最好是晒干以后再看。其实昨天下午看完电影我是想催稿的,但是戴了渔夫帽的你在影城门口的夕阳下踱来踱去,像宫崎骏电影里的小女孩,对当时正忙着选饭店的大伙说:“那么多人啊,我突然不想去了。”说完你真的开溜了。你看,我在表述这个细节的时候保留了引号。说起来,我似乎要向引号道歉,随着对白在我的小说里不断抬头,它却是快要消失了。我同意你说的,引号有特殊化的强调作用。我想起读初一的时候,荧光笔在上海刚刚走红,我喜欢用黄色的荧光笔在课本上划重点,划太多了,被同桌瞧见,她说,都是重点,那不等于都不是重点嘛。我听了不响。除了这点原因,我把引号从对白的头上摘掉,还有减字数的考虑。这话说起来荒诞,《小说界》你肯定晓得的,改版以来的约稿以一万字为界,偏偏我越写越长,严重越界以后有一种流亡作者的自觉,删掉引号可以减罪。还有分号的故事,你还记得吗,那年冬天你在杭州做新书分享会,我说,占黑,好像你的小说里几乎没有分号。我当时想借助分号,将几组动作合并在一个句子里,试图模拟音乐的同步性。我们听一首贝多芬的室内乐作品,两把小提琴加一把中提琴、一把大提琴,它们合奏之际,那种同时发出不同声音的效果是书面语言无能为力的,汉语在这方面特别明显,英语还可以通过从句叠加从句奋力一战。不过我的这些想法在当时的分享会上并未吐露,在此后的写作里也没有展开。嘿,这封信略长,见笑了,你随意。
莫之
第三封回信:
我想了想,自己在日常的语言运用中也不太注意标点符号,键盘打字什么的一向是空格代替,可能它对我来说真的不重要,退一步说,我们古人大概也是这样想的,哈哈。你说得对,很可惜我们的语言不像《降临》里的七肢桶那样可以不受时间限制,我们的语言一次只能生发一回,要感受到类似音乐的同步与交织,只能靠读的人自行在脑内发挥,毕竟阅读本身就是想象力的一种。
但此时我想到的不是这种同时性,而是流动的过程,它不仅仅是节奏、情绪、速度,也不仅仅是语感,而是更整体的——这口气怎么延续下去,这条河怎么流淌。这种体验在短篇里可能更容易获得,读长的就不由心生敬佩,怎么可以做得这么好,像托妮·莫里森、阿兰达蒂·罗伊,都是令人惊叹的流动。我之前读到一个美国黑人小伙叫亨利·杜马斯,三十出头在哈勒姆街头被白人警察过度执法死的(那是一九六八年),留下的作品不多,他死后很多人都被他的才华征服。他写小说就有一种绝妙的flow,堪称庞麦郎唱的“魔鬼的步伐”,大概和音乐一样,黑人天然就有这种感觉。
占黑
第四封信:
确实,黑人的律动(flow)独步天下,即小说的所谓语感,而同为说唱术语的beat或许可以理解为修辞,某某写的小说,flow和beat俱佳,那意味着此人的语言甚好。我很羡慕那些语言好的作者,这种东西属于天赋,很难修炼,多数时间,我觉得自己顶多算个工匠,我的小说是在不断的校阅中打磨,由此产生棱角与锋芒。记得你曾在播客节目中透露,写小说的时候,你先要通读之前写成的内容,顺着那口气进入状态,我觉得这就好比飞机起飞之前的调整与滑行。我的写作也充满了类似的准备工作,借此也可以解嘲一句,为什么在过去的十余年中,平均每天只能推进几百字,好在去年与对白及时和解,写台词的确会加快小说世界的构建。至于小说这条河怎么流淌,速度与节奏确实太重要了,短篇小说通常叙事密度比较大,这个度很难把握,你在第一封回信里要求自己“不要总是紧绷绷地绷在那里”,那其实也是困扰我已久的问题。小说流速过快,潮水汹涌,会让观众不敢凑近了欣赏,或者说,形成某种类似于咀嚼压缩饼干的口感。以前有朋友说读我的小说像在吃五仁月饼,我想,除了食材选择的差异,密度也是原因之一。这让我想起小津安二郎的电影,他的战后作品,尤其是晚年的彩色影片有不少耐人寻味的空镜头,譬如凝视一个红色水桶,一列火车从他的固定镜头呼啸而过。这种质朴而诗意的视听降速,如果之于小说,最常见的方式莫过于环境描写。占黑,好像环境描写在你的小说里像葱花、姜丝一样切得比较碎,这是否与你更青睐第一人称叙事有关,当“我”的故事讲得正欢,骤起几百字的环境描写其实还挺违和。
莫之
第四封回信:
五仁月饼笑死我了,你朋友的嘴巴蛮毒的。我没怎么留心过自己怎么写环境,但经你提醒,我突然意识到自己平时在阅读中确实容易快速过掉这类信息。比如听《红楼梦》的有声书,听对话的时候觉得都还蛮熟,听到人物穿戴和房间布置则会感到陌生,因为从小每次读到这里就主动加速了。但听书的速度是均匀的,没法略过,倒也新鲜,只是依然对什么样的花纹、什么样的料作没有深究的念头。比如现在很多人观鸟,据说观鸟之后,你就不会再写“一只鸟从天上飞过”这种话了,好歹要精确到是哪种类型的鸟,但像我这种对博物学兴趣不大的人来说,是个鸟就行了。我可能更追求从感官出发的样态,它留在我心目中的印象比它本身的形象重要得多。比起类目,比喻更让我感到自由,感到和世界的连结。
占黑
第五封信:
环境描写还挺折磨人的,我在不同阶段都有这样的感受。作者时期的苦闷是如何写得不那么僵化。读者呢,我小时候和你一样,每当小说出现环境描写就忍不住提速,后来遇到一个电工老法师,在我的初中时代,此人是我父亲的麻将搭子,有一次他们中场休息,老法师抽着香烟问我,怎么会想到去看大仲马的,日本漫画不看啦。我说,不看了,被姆妈看见又要刮三。老法师说,蛮好,这本书好看的。我说,故事相当精彩。老法师说,有几段出海的环境描写非常见功底。我耐心地听他讲解,回头再看那些段落,仍旧缺乏共鸣。占黑,面对文字以及日常生活的诗意,女孩子是不是更早开窍,好像男生就比较迟缓,或者说,更追求生活的传奇性、官能性,比如我在上世纪九十年代的头五年阅读了大量的少年漫画(少年マンガ),主要是一些打打杀杀的题材,我当时也看高桥留美子,属于换换口味,但是到了大学,我被几个室友影响着重温小学时代看过的那些漫画,高桥留美子突然变得和福楼拜一样让人着迷,后来,我几乎每年都会重读李健吾译本的《包法利夫人》,高桥留美子的《相聚一刻》也是如此。我有一本翻破皮的网格版《包法利夫人》,纳博科夫在《文学讲稿》里吐槽各种英译本将“耳垂”译成“耳朵尖”,将“苍蝇顺着玻璃杯壁往上走”译成“往上爬”,李健吾的译本也存在这些问题,周克希的译本更为精准,而且句子像老鹰翱翔那么舒展,不像李健吾的断句比较碎,不过这种小葱切段的旧上海语感很是吸引我。老实讲,我是在《文学讲稿》的帮助下走进了《包法利夫人》里面那些近乎冗长的环境描写,读了纳博科夫分析寒碜帽子、婚宴蛋糕的千层饼主题,我意识到原来环境描写可以是心理描写的外延,如同古典章回小说里的诗、偈子,是作者忍不住要开天眼的一种游戏、表演。占黑,那些研究小说艺术的书籍对你写小说产生过影响吗?
莫之
第五封回信:
你现在连写信也喜欢写对话了,哈哈,你和它的关系肉眼可见地正在变亲密。好几天没回复,很惭愧,脑子里挖不出什么书袋来回应你最后的问题。我现在习惯在睡前顺便想一想信里写什么,结果就睡着了,你试图唤起的话题简直成了我的催眠剂。环境描写嘛,我也没有特地思考过,通常就是一个“乘兴而至,兴尽而归”的过程,顺水推舟,上岸收线,自然就好。或许你不把它定义成环境描写,当成是“眼睛望向别处”(我是说写作的眼睛),有一眼没一眼地望,就会放松很多。这几个回合交流下来,我又有点糊涂了,关于小说是什么,写小说又是什么。我不想讨论“写小说能不能教”这种很大的问题,但写小说肯定要学,漫长的、磕磕碰碰、进进退退的自我学习、自我教育,以及在实践里漫长的自我认可和怀疑的过程。你有什么经验和感受吗?我还能想起最早的时候在淘宝买你自印的书,记得《现代变奏》和《生活的甜蜜》的封面,每本书都有编号,我还记得你说,有一百个人买这本书就很好了。我很高兴我是那一百个人之一。也许那时的我们都更轻松一些。
原谅我的拖拖拉拉。
占黑
第六封信:
没关系的,占黑,就当这间隙是我们对话的中场休息。你提到我自印的长篇《生活的甜蜜》(正规出版易名《安慰喜剧》),我想起里面安插了一个中篇小说,就叫《中场休息》,因为那本书是戏仿舞台剧的结构,中场休息的时候,叙事者可以跟读者说几句不上台面的悄悄话。和你一样,我并不打算讨论“写小说能不能教”,趁着中场休息,我重温了一部分以前很爱看的文论,我现在觉得这些书最大的贡献是为小说的世界培养了许多优秀读者。我在第四封信里提到了工匠,其实,阅读文论就像是小说工匠为自己布置的课外作业。占黑,你读大学以前是否也深陷题海,我迄今忘不了《一课一练》之类的辅导书,做得苦透苦透。谈小说艺术的文论有一个普遍现象,以纳博科夫、昆德拉、詹姆斯·伍德的那些杰作为例,他们埋头传授的是如何识别小说的优点(如同我们看自己的小说),而文学杂志的编辑恰恰相反,他们惯于指出小说的缺点(如同我们看别人的小说)。在我的印象里,小说投稿一旦留用,能从编辑处听到的就主要是喜讯与客套,当编辑愿意像写豆瓣短评那样与作者探讨一番,那么作者收到的多半是退稿意见。据说,每位文学杂志的新人编辑要上的第一堂课即退稿的艺术,以至于与一些相熟的编辑打交道,还是会让我想起三岛由纪夫的小说《假面的告白》。试问,谁没有玻璃心呢,友谊的小船翻起来比翻书还快。但说句实话,作者要进步离不开专业读者的建议。我最近在看某同行的小说,有豆瓣评论如此写道:“书中的两个主要人物经常分不清楚,不知道哪位是男主角哪位是女主角,他们的对话虽然都标注了‘某某说’,显得很繁琐和啰嗦,担心读者分不清是谁说的,然而我却还是很难一下子分清。”真巧,我的读后感也是如此。这说明给角色取太过中性的名字也是有隐患的。占黑,你在第一封回信里提到“最近在整理书稿……做了大量删减”,不知你是否也有类似的体验,许久之后重读自己以前写的东西是最容易看出缺点的。
莫之
第六封回信:
莫之,我正在看书,中途突然想到什么,赶紧打开邮箱写下几句。我突然发现我们正在进行的是一种协作的写作,而我们所经历过的大部分写作,它的快乐,它的孤独,都在于只能由一个人来体会和承受,这大概和写剧本什么的不太一样。你把我的停顿叫中场休息,让我想到了自己在写作中会碰到的停顿,有时我会不断地去读和微调前面的部分,就像反复去捋平一根线,企图让它平到可以继续延伸下去。但也有时,怎么捋都没有用,无论是中止还是硬扛,这都是只有自己知道,而且还没写完,自己心里模模糊糊地,怎么可能跟人讲其中的头绪呢。这样的过程既是困扰,也是魔力,对吧。
回到我看的这本书,作者是个美国人,叫里克·德马里尼斯。以前另一个写作朋友推荐了他的一篇小说,发表在上世纪九十年代的翻译杂志上,我读完后查了查,再无别的中文译作了。这个作者在本国也不算有名,和大多数美国作者一样在大学里教写作,除了厄普代克曾选过他的一篇进年选(就是杂志上那篇),没什么水花了。你提到文论,我就想起曾下载过他的一本讲短篇小说的书,读下来,中规中矩的,一边讲要素,一边引用经典的作品。但这足够厉害了。我虽然当过老师,老实说,哪怕是认真读过、真心喜欢过的书,隔一段时间也就忘了,脑子里能想起的更多是某个阅读的情景,比如外面的鸟在叫之类的,而不是书里的鸟在叫。所以隔一段时间重读,该激动的地方还是会激动,甚至想做笔记的地方都发现之前做过一样的。对自己的小说也是这样,完全抽身出来看,好坏是一目了然的,喜恶也很分明。若是要改,那这件事就没底了,修改是无止境的,内心的标尺也随着不同的时间在变。若非出版的滞后性,我几乎不读自己过去的东西。
关于最近几年的写作,我当然有很多不满意的地方,也在思考自己为什么牛角尖钻得越来越深,比如不喜欢好好叙事,每到一个路口就把桥拆了,弯弯绕绕,变得越来越晦涩,读起来很累,我自己都读得累死了。有人问我,是在自我审查吗?我倾向于否定。可能是在这几年的生活环境里不断向内折的结果,你说我小说里的人变得不明亮了,这是事实,偶尔我也会怀念从前字里行间那种快乐和强健的气息,但失去它们并不是一种退步,我对自己说,这只是一种变化,而变化会一直在发生,只要每一步都是自己诚实地走出来的就好。呼,长舒一口气,说了好多话。
不是常有那种线下活动吗,两个人跷着二郎腿聊着八竿子打不着的天,也许毫无准备,张口就来,也许你聊你的,我聊我的,我不喜欢那样,现在这样挺好的。
占黑
第七封信:
占黑,读了你的长信特别感动,即使此刻夜已深,我仍然想把这封信一气呵成地写完。上周四,我们与几位朋友在静安寺聚餐,也许是喝多了,我说:“占黑,你有没有觉得,你小说里的人物没有以前那么开心了,以前你的人物也在硬扛这个世间的苦难,但是我在你的小说里读到了受难者的快乐与幽默。”我请求你能理解,身为朋友,我当时试图表达一些个人的感受。我很意外,这段没有下文的插曲会被你引入信中,一开始,我发现自己的评论好像有被误读,我着急解释,但是此刻二刷你的回信,又觉得你的概括还是精准的,我说你笔下的人物没有以前那么开心了,即他们变得有点阴郁,那似乎也就是“不明亮”。显然,你对自己的转变是有一整套质量把控的,正如你所说,“内心的标尺也随着不同的时间在变”。不过我提出重读旧作这个话题倒是真的为了更好地自我检视。先说以前,我的习惯是写完一个小说会集中精力修改打磨,从一稿到投稿,间隔不超过一个月。但是这个流程最近有所调整。我把集中修改变为一周一改,打磨的过程中另起炉灶,我在新的写作中沉浸得愈深,重读旧作时的陌生感就愈加强烈,这样更容易发现缺点,不过这都是未经编辑验证的实验室结果。占黑,我们从未聊过这个话题,你小说一稿完成之后到正式投稿,通常需要多少时间?
莫之
第七封回信:
哈哈,你知道的,我不擅长面对面谈论和写作有关的事,吃饭的时候就只吃饭。但我感激你的反馈,也感激我们至今还在互为彼此的读者。其实常常觉得羞愧,如果自己不是正在写作中,似乎很难称得上是“写作者”,也不知道能代表那个真正的“写作者”说点什么。你有类似的体验吗,无论是看待自己还是他人,活人还是死人,难免会产生一种略带割裂的迷惑,诶,这个人就是写出那些文字和作品的人吗?很多时候我都避免去查关于作者的信息,尽量把作品和作者分开来看。但在我参加过的读书活动里,无论是关于新鲜陌生的还是广为人知的作者,大家都会热情地讨论和TA本人有关的事。我当然能理解这种好奇,不过同为作者,我想大部分作者都希望被看到的是作品,而不是别的东西吧。扯远了。
关于修改,这件事当然是没有尽头的。离得近看,就会不断敲打细节,隔一段时间看,可能会看出新问题,想要动一动筋骨,除了极个别成品(就是特殊情境下进行的呕吐式写作),大部分都是“只要你想改,就可以一直改下去”的,也就是永远在“未完成”的状态里。由于个人工作习惯的问题,我不太接受约稿。通常都是进度差不多了再想投稿的事,这也导致我可能会一直延宕在修改的动作里(由于我没有写过长篇,还没体验过“一稿”“二稿”之类的东西)。我的工作习惯是一边写一边改,写完也就暂时完成了,后面就是漫长的敲敲打打。也思考过改变工作方法,只是养成了习惯,尤其是思维上的,改变起来是有难度的。有一阵我想,在电脑出现之前,人们经历手写、打字机写,差别在哪里呢?手写的话,大面积的修改可能就是一遍遍地重写?我只体验过一点点,或许你有什么补充记忆。打字机也是,它更像是被头脑中的一种声音所指挥,不用看前面未完成的句子,而是不断地输入和延伸。没有可视化的前提,思维的进行方式也就不一样了。
占黑
第八封信:
你提到打字机,哈哈,前些年我曾考虑买一台复古打字机键盘,幻想那噼啪的声音能提升写作效率。坦白讲哦,我的任何文本创作都离不开键盘,最早是本世纪初,为一些地下杂志写乐评,后来短暂尝试手写,痛失灵感,所以我不敢轻易换键盘,毕竟连输入法我都在沿用远古的“微软拼音ABC”,很多习惯已经化为手机解锁的指纹。这无疑也是写作者的某种舒适区。你另提到写长篇,不妨借此回归第一封信中对短篇越写越长的讨论。我想讲的只是一种可能性,与文学杂志打交道久了,我感觉中篇的首发空间其实是最小的,长篇的情况,虽然国内能发的期刊很少,但架不住图书市场的胃口大,至于短篇,那机会确实特别多。也许有些小说的格局本不适合写成短篇,只是为了更容易发表而去适应那个环境,正如你在描写美国之行用的那个比喻:“看着身边每个人像油豆腐塞肉那样把自己塞进座椅间的缝隙,我简直不愿跨向我那精心挑选的角落靠窗雅座。”油豆腐塞肉好像不是一篇小说正确的存储方式,就在我默认自己已经退出了短篇跑道的时候,我在清明节扫墓的漫长车程中读到了一组绝妙的短篇,女作者用动物狂欢节来刻画残酷的历史悲剧,给我启发,也许存在一条叙事的小弄堂,我想称之为童话现实主义。我在驶出上海的公交车上与那位女作者发微信说,也许哦,将来我写一个小说,主角是地板、小号、萨克斯,它们可以讲讲主人的故事。我思忖这不就是科幻题材飞跃龙标的传统技能吗,又想起重塑雕像的权利、CarsickCars这些北方乐队编写英文歌词的某些动机。想想还是蛮“扎劲”的。
莫之
第八封回信:
我还记得你很早以前有个小说,里面提到一伙喜欢音乐的人都住一栋楼什么的,那个画面有点梦幻。后来我在上海精卫中心旁边看到一栋居民楼真的叫爱乐大楼,站着笑了好一会儿,又觉得合情合理,小说里的那些人就应该住在600号附近,要么在楼里发疯,要么出来配药,就是现在网上常说的“精神状态超前”。昨天晚上我出去溜达,看到万体馆里平时可以跑步和散步的公共区域都被封了起来,因为张信哲在八万人体育场开演唱会。现在的主办方真的很小气,故意在铁皮围栏之间的缝隙后面再多摆一架围栏,让你一点也看不到,其实就算看得到,也只是个检票口,并没损失什么。而且现在都是实名制,刷身份证入场,外面一个黄牛都没了,冷冷清清的,只有一圈保安。我竟有点失落,靠着围栏听了会儿歌,听完小时候最喜欢的《宝莲灯》主题曲就走了。一路上很多人都坐着听免费的演唱会,我看到一个姐们戴着耳机站着唱歌,里面的每一首她都会,唱得特别好。她那种旁若无人自顾自嗨的样子,让我觉得她就是爱乐大楼里的人。里面唱到《过火》的时候,整条街变成了大型KTV,每个人都在唱,连奶茶店的员工也边做边唱。你见过电视里放网球公开赛吗,每到休息间歇,镜头就切到球场外面的公园,人们坐在草地上看免费的大屏幕转播。其实我们都是在外面听个响、看个热闹的人,谁也不清楚真正的中心是什么,我是说我们和文学的关系,但哪怕是站在铁皮围栏外面也很开心了,站在那里,我们脑子里就会有属于自己的“文学的样子”。
占黑
第九封信:
你刚才描绘合唱《过火》的画面仿佛是一部电影的结尾,我喜欢那个边唱边做奶茶的小工,镜头请停在TA身上,字幕慢慢流淌,让TA做完几杯奶茶。碰巧了,我的大学室友昨天也在看张信哲,同时发视频为我们转播,另一个室友了解完票价说,快下岗了,我还是实惠点,在屋里为申花队加油。下岗已经七年的我不响,静音看申花队,聆听远方的张信哲,中场休息之际打开邮箱,瞧瞧占黑回信了吗。远与近,这可以是一个比喻,回应你说的,我们与文学中心的距离。开心很重要,无论我们身处何方,找准自己的定位,发出独特的声音。我现在的文学观是越来越保守了,我倾向把小说写成一个乐子,里面有滑稽的人物,哭笑不得的故事,让一部分读者先开心起来,至于我想表达什么,还是让读者去猜。猜谜的难度要适中,太难会打击参与,太容易就成了教条。要让谜底成为沾水写在地上的毛笔字,小说发表以后它就看不见了。打键盘至此,我意识到对谈字数即将破万。占黑,属于我们的演唱会势必超时,场地方的负责人会不会哇啦哇啦跑出来拉电闸啊。不过,谁都晓得这是套路,我们的生活被绵密叠加的套路所包裹。此刻,我唱完这首歌,观众礼节性地喊起了encore。我想,是时候把话筒交给你了。
莫之
第九封回信:
莫之,谢谢你为这些邮件内容所做的编辑和整理。和惯常的工作方式一样,我一口气通读完以上的对话,临时决定补充写点什么。往上瞄了一眼,发现这恰好就是你呼唤的encore环节。好的,我返场了,一切是这么顺理成章。每当写作之间的空当以最自然的形态被连接起来,我心里就会很快乐,这是写作中的快乐,就像吸上了一口纯氧。
其实我还有很多事情想问的,比如对百年前上海音乐的资料调查和书写,对千禧年上海地下乐坛的整理和回顾,这都是工作量很大、很费心血的事情。我想,这些努力的过程和结果绝不仅仅会只呈现在你的非虚构作品里,润物细无声,或近或远的以后,它们也将以某种形态悄悄映透在你的小说写作中,只是后者,你无法太过牵挂它们的降临。来日方长,我并不打算在这里问了,还是庞麦郎的那句话,时间、时间会给我答案。
二○一九年年末(现在想来是暴风雨前的宁静,我们对此一无所知),我去育音堂看庞麦郎的演出。他放着自己的伴奏带,却跟不上那里面的节奏,每首歌都出现了不自知的layback,这就导致台下稀稀拉拉的二三十个观众就算想跟他大合唱也跟不上,只能各唱各的。那场面真的太逗了。简单的握手环节之后,他和所有人一样,是背着书包自己坐地铁走的。那时还没有关于他精神失常的报道,自费买票去看演出的观众既不是什么“黑粉”,也不是什么献爱心帮他圆梦。我们就是想看他,想跟他一起唱他的歌。
回到之前提起的那本平平无奇的讲小说手艺的书,作者最先说的是“onlydothisforlove”,尽管知道理想的作品几乎是不可得的,知道自己并不一定能从中获得什么,同时一定要付出很多,没准还会失去很多,这又何妨呢。Doitforlove,notforlive。当然,自己的生活也很重要!愿你过得好,春夏之交,身心愉快。
占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