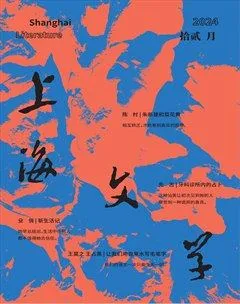隐形人
李清打电话过来:“我要见你,马上。”蒋润说在老地方见,并叮嘱她删除通话记录。
所谓老地方,是他们常去的一家咖啡馆。半落地窗,长线吊灯,混凝土石台上放着蒲团,圆桌带着金属的冰冷质感,二楼有个单独的小房间可以俯瞰吧台。他们通常选在那个小房间里。
时近除夕,咖啡馆内没什么人,外头正下着蒙蒙细雨。在蒋润点完单坐下来的五分钟内,又来了一对情侣。他们很快利用起了整个二楼空间,女人在不同角落辗转腾挪,低眉托腮,或背倚石柱,男人则举着一台胶片相机,不断为她拍照。蒋润观察了片刻,就收回视线。
那些女人也常常希望蒋润为她们拍照,用手机就可以,她们说。蒋润建议她们不要在手机里留下任何令人生疑的东西,虽然他是职业摄影师,有一间不大但粉刷一新的影棚,里头放着背景架、静物台、反光伞、柔光箱等一系列专业设备,但是不,他从不为她们拍照。
“啪”一声,李清将小香包甩到桌面上,坐下来,双手拢住长发往脑后捋了一把,一颗细小水珠从她的羊羔绒外套上滑落。
“你点了什么?”她的手还放在后脑勺,眼睛盯着蒋润的杯子。
“Dirty。我帮你点了桂花拿铁。”
她这才看向他,嘴半张着。
“我忘了你会帮我点了,又多点了一杯,”她说,“对不起,我心太乱了。”
“所以发生什么了?”
李清用指节敲击了两下桌面,目光移到那对情侣身上,此刻他们已经在另一头并排坐下,脑袋紧挨着翻看相机。蒋润注视着李清的脸,她的眼皮轻微浮肿,口红有一小块涂到了嘴唇外。他看得心痒起来,想伸手替她拭净。
“简单来说,就是过不下去了。”
“这听起来可不简单。”他笑起来。
李清调转头与他对视,眼神似有怒意。店员朝他们走来,在桌上放下咖啡杯和纸巾。蒋润目送着店员走远,等待李清酝酿好她想说的话。
“早上他妈送年货过来,说让我补补身子,说着说着又提到了那件事上,话里话外的意思无非是,这全都是我的错。”
蒋润将双肘抵在桌沿上,向李清靠近了些。
“当着我的面说,免疫性复发流产,听起来就是母亲克孩子。”
“他那会儿不在家?”
“他就站在那儿,什么也不说。”
李清瞪大眼,仿佛被什么难以置信的事震惊,想从蒋润这儿得到一个答案。
“你们之前对这件事沟通得多吗?”
“沟通?第一次误诊为宫内感染时,他怀疑我在孕期和别人上床了呢。”她往后靠向椅背,看着他说,“那时候,我们甚至都还没熟起来。”
他和李清曾经同在报业集团为一本刊物供职。当年,他还未出师,跟着一位姓徐的师傅出外景,或棚拍。他负责布置道具,拿遮光板,调仪器参数。李清是编辑,天天拎一个Celine的包上班,公司里的人说她早早就结婚了,老公很有钱,家里的房子、车子都写了她的名字。
“别听他们瞎说。”在集团的年会酒席上,蒋润借众人彼此寒暄暖场的间隙向她求证过,李清反应冷淡。入座后,他们在同一张桌子。蒋润偷眼瞧了她几次,感觉她神思游离。
再后来,他离开杂志单干。起初生意来自同事介绍,渐渐有自己稳定的客源。有一天,一家新上线的生活方式买手店来找他拍产品宣传图,他认出来现场跟片的负责人是他的大学同学刘晓凡。他盯着她微微翘起的上唇,想起他母亲曾经对着一张合影里的她评价道,女孩子人中这么短,以后没福气的。现在,那张嘴在他面前拉成一条弧线。“好巧啊。”刘晓凡说,蒋润随之应和。
结束工作后,他们就近找了一家餐馆吃饭。他得知刘晓凡已经结婚,几乎是一瞬间,他预感到,在言语的浪潮褪去之后,会有别的滩涂显露出来。酒过几巡,话题开始往家庭生活的方向延伸。
“我在厨房忙着备菜,让他出门时顺手把家里堆的那些大小快递箱子拿到车库去,他立刻就不耐烦了,摔门出去,还说我穷气。”
“现在纸价上涨,纸箱攒一攒,能卖不少钱吧。”
“你比他明白。”刘晓凡轻轻看他一眼。
“跟出版社的人合作时,听他们说起过。”
刘晓凡喝了一口酒,从包里掏出烟。
“在我老家,我妈连经炉灰都收集起来,拿去卖。”她说。
“是不是进入家庭生活,这些就变得无师自通?”
通常,蒋润会把空置的快递盒放在门口,每每等他出门时,它们已经消失无踪。他在楼下撞见过那个挨家挨户收走快递盒的老太太,那些快递盒被拆解、压扁成平面,成摞地捆扎在她的自行车后座上。蒋润喜欢保持空间整饬、洁净,无法忍受出现一些秩序之外的东西。有一回,客人在影棚里打翻了奶茶,他让助手继续布光,自己第一时间跑去清理。
“你以后就知道了。男人怪这些事把我们变得乏味,自己又不分出手来帮忙。”
“我不觉得这些事会让一个人变得乏味。”
一个小时后,他们已经在酒店的床上抵足而卧。起初,刘晓凡话多到让蒋润有些不耐烦,他慢慢发现,令他不耐烦的是那些话里的鼓励性质。他告诉她,如果觉得不舒服,就说出来。她说,不,是真的很得劲。她脸上急于申辩的神情不知为何隐隐触痛了他,他选择接纳她的说法。日后,当他和别的有夫之妇上床时,他才意识到,那是她们取悦自己丈夫的手段,背后往往压抑真实的心理感受。
原以为就是一次性的,酒精催动的,没想到之后,刘晓凡主动来找他。同样是吃饭、聊天、上床,这渐渐演变成他们之间交往时的标准配备。蒋润能感觉到,刘晓凡的身体在他面前越来越放松。她闭着眼,在他的加速中将空气变成颤抖的波纹。事后,刘晓凡对蒋润说,出于某种愧疚感,现在丈夫只要提出需求,她就会尽量满足,性生活的频率甚至比之前还高。
刘晓凡坐起来,将下滑的被子拢在膝盖上说:“你知道这个会难过吗?”
蒋润沉默了两秒,“你和你丈夫上床开心吗?”
“好像也谈不上多开心,但至少,不委屈了。”
“别委屈自己就好。”
刘晓凡有了孩子后,他们断了一段时间联系。他倒不担心孩子与自己有什么关系,每次上床之前,他都会先去淋浴,将自己冲洗干净,再戴好套。他知道一些男性身上携带的细菌,会在女性身上变得显性,成为炎症,这远比让对方意外怀孕发生的概率要高得多。
再次收到刘晓凡的消息是在过年前夕。那是一条拜年短信:“新年快乐,早日收获幸福。”那种感觉,就仿佛吃花蛤时,嘴里硌进几颗沙。事实上,假如她一言不发从他的生活中消失,他反而会觉得那是一个更自然的收梢。但刘晓凡也像一张试纸,映现出了他想要的情感关系,没有索求,没有依赖,如同两只咬合着的蜻蜓在一片草叶上短暂地栖息。
“你在想什么?”李清盯着蒋润的脸,猝然一笑,“感觉到压力了?”
“什么压力?”
“你担心我想离婚。”
蒋润笑了笑。“我担心这个干吗?如果你认真考虑了,并且决定离婚,我当然支持。”
“我离婚之后,我们的关系会发生变化吗?”
“你希望发生变化吗?”
“所以问题又回到了我这里。”李清冷冷地说。
蒋润端起咖啡深啜一口,冰凉的液体滑过喉部,像某种镇静剂。
“你还记得我们是怎么熟起来的吗?”他问。
他在问出这个问题那一刻,脑中已经同时浮现出画面:赶工至深夜,他与助手将两人高的巨幅背景纸卷好搬到墙边后,嘱咐对方先走。走出大门,他看到对面楼群的阴影里,一男一女似乎在吵架。男人想拉女人胳膊,被她伸手架开,她别过头,朝空气中吐出一口烟。男人又去拉,这回牢牢箍住了女人的手腕。女人想奋力甩脱,身体呈现出对抗的姿态。“滚开!”变调拔高的声音中藏匿着一丝熟悉,但蒋润问着“需要帮忙吗”靠近他们时,并没有认出那半张脸沉在暗处的女人是谁。
女人定睛看他,一下子松了劲。
“蒋润?”
他微微睁大眼辨认对方。
“我是李清。”她的视线往身旁的男人身上一扫,“这是我老公。”
男人看着蒋润,仿佛他是一个巨大的、等待解答的疑问,直到李清说“我前同事”,才朝他点了点头说:“她喝多了,让你见笑了。”
“他不是你朋友,你不要跟他说话。”李清说,“好久不见。我听说你自己开了个工作室?”
“就在对面,”蒋润回头一指,“全靠前同事们照顾生意了。”
“那我可不好意思了,都没来光顾过。回头有活儿,我来找你啊。”
一种奇怪的预感再次掠过蒋润的脑海。在经过一些其他女人之后,他知道那是一种对情感背面的积垢的嗅觉,但李清似乎是不同的,她的内心好似发生过一次爆破,只留下一些乱石纷陈的挖掘现场。不知为何,看着她的脸,蒋润确信这一点。
在刘晓凡与李清之间,还有过三个女人,持续时间从几个月到半年不等。有一位,是与朋友同席吃饭时认识的,年纪比蒋润大,与丈夫合伙开了一家做LED广告牌的公司,两人已经长时间没有性生活,因此各自在外寻找新鲜刺激。她的体内似乎有个不知餍足的涡旋,将人卷入去向不明的所在。做爱后,她会趁蒋润洗澡的工夫,偷偷在他的后裤兜里塞几张纸币,让他吃点好的。还有一位,家庭主妇,有孩子,每次见他都穿一条雪纺连衣裙。她在床上喜欢玩一些角色扮演的游戏,先是让蒋润掌掴她,伴以言语羞辱,尊严委地后,再寻机一跃而起,化身吞食交配对象的黑寡妇,在摇摆与震颤中篡夺权力。有时,她会突然哭起来,身体变得直僵僵的,蒋润从假死的幻境中脱离,安慰她,感觉自己好像变成了一根绳索,正拖住一个缓慢溺水下沉的人。后来,在聊天过程中,那女人说,为了让孩子有个完整的家庭,我是绝对不会离婚的。倒好像蒋润对她有所求似的。
那晚之后,没过多久,他就收到了李清发来的信息:“我刚参加完活动,就在你的工作室附近,有空一起吃个饭吗?”他赴约了。他们聊了聊前同事的八卦、近年来每况愈下的传媒生态、各自生活中的趣事,开怀处,李清拊掌而笑。蒋润有些错愕,从前他很少看到李清笑,在公司里她也一向寡言,他从李清的笑容里捕捉到一种破碎感,后来,他发觉那是因为她咧嘴笑时,眼角纹丝不动。他忘了在哪儿看到过对一位演员演技的解说,那位演员像某种精密仪器,上半张脸和下半张脸传递的情绪,是分开的。
第二次,刊物下厂,她加班到深夜,问蒋润想不想回前公司看看。办公室内,大半区域已经熄了灯,办公转椅维持着人离开时的朝向,过刊摇摇欲坠地摞放在地板上,一张图钉没订好的杂志小样在蒋润经过时从排墙上无声飘落。
“怀念吗?”李清抱臂走在他身边。
“压力大的时候会怀念这里的安稳,”蒋润指了指地上的过刊,“但那种安稳其实像它们一样。”
“是啊,不过像我这种身无所长的人,也只能等着它倒下来的一天了。”
“那你在工作之外,也是这样吗?”说完这句话,蒋润感觉自己稍稍越界了。
李清停下来,默不作声地盯着他。他被盯得心里发毛,解窘笑了笑,拿起她工位上的一支口红说:“你知道吗?之前我买了支口红送人,对方直接说,你买的什么鬼色号,这是给老阿姨涂的。我突然觉得,女人真的很难懂,连一支口红,学问都这么深。”
“不是女人难懂,是人本身就很难懂。”
乍然间,她把他拉进了样衣间,拨开一件件罩着防尘袋的衣服,推撞入深处。他们吻在了一起。松开彼此时,李清还在喘气。
“现在是不是更难懂了?”她说。
但他们没有上床。第三回,他见完客户,正好在前公司附近,就约李清吃饭。李清回说不饿,想散散步。那天李清穿了一件织金丝绒筒子领连衣裙,衬得她挺秀颀长。他们沿着人行道漫无目的地走着,间或抽烟,前头有个母亲带着一个小女孩,女孩的手上牵着一只镶着彩色小灯泡的气球,气球在夜色中的轮廓被光线勾画出来。
“现在的小孩真好,连气球都比我们那时候的高级。”李清突然促狭一笑,“我们走过去,笑着对她说你好,然后用烟头把气球戳破。”两人渐渐笑得不可自抑。
就这样不知走了多久,聊到街景渐暗,四周幽静,话题慢慢稀微,沉默填满其间的空当,蒋润突然心觉有异,但他说不出异样的是什么。他听着身旁李清高跟鞋在地面上的叩击声,淡淡的小苍兰香水味时隐时显,像念头乱线交错钩织,倏忽间又暗冷不见,他问自己,你想从这段关系中得到什么?这段关系的未来会和之前一样吗?他发觉自己没有答案。
“跟你分享一件事,”李清脚步一顿,在一家已经暗了灯的咖啡店门口的室外落地窗台上坐了下来,“不久之前,有一天晚上我醒来,发现我老公在一边做梦一边挖自己的鼻孔,我亲眼看着他把鼻屎吃进嘴里。那一瞬间,我起了一身鸡皮疙瘩,整个人蜷缩起来,我感到一种恐惧,还有一种……羞耻。”
她回头看着蒋润说:“我为他感到羞耻。”
如今他知道,羞耻感也可以是一种生命力,无论是为他人感到羞耻,还是为自己感到羞耻,羞耻感出现是因为你面前的生活撕开了一道口子,而你突然在某种压力之下,感到无所适从,这种压力,通常与你是个什么样的人有关。在那些关系中,他不止一次问自己,你为什么不感到羞耻?羞耻往往来自于内在的道德焦虑,但他并没有,他不承担什么,他不制造责任,努力把风险降到最低,可这并不意味着他就被道德赦免了,这个世界的法则仍然适用于他,假如他和这些女人的关系曝光,道德不会放过他。然而,和她们在一起时,他从来没有感受到危险,从来没有担心过有一天一切会中止。李清却是不同的,在他们上床后,他已经提前预演结束时的伤感,并觉得他们之间所维系的东西——无论它是什么——随时都能被毁掉。他也被一种无名的感受所包围着:自己似乎凭借对李清的兴趣依稀摸索到了自我更深层的形状。
真正到了床边,他反而很平静,或许是因为早已在想象中体验过这一切。他缓慢而有耐心地掘进、探勘,随后陡然间,用突如其来的激情劫掠她的身体,凿开她,在撞击中感受自己一次又一次地直抵幽深处,他希望那里有一条通道,连接着她的头脑、她的心。
“你今天看起来心神不宁的。”李清站起来关上小房间的门,又推开窗,从包里掏出烟点燃。
蒋润的目光一直追随着她的动作,直到她坐下来,视线又重新聚焦在她脸上,样子看起来就像是等待她把刚才的话再重复一遍。
“为什么要问我们是怎么熟起来的?它暗示了我们的结局?”她说。
“不,我刚刚只是在想,我们的关系,从最开始到现在,发生了多大的变化。”
李清摇摇头:“我不知道,也许吧,也许是发生过很多变化,也许一段关系在经过剧烈的变化后,就会成为我们现在这样,死水一潭。”
他的视线牢牢锁在她的脸上。他感觉从某一刻开始,她就一直在试图激怒他,而他的情绪确实因此起了些波澜。他讨厌这种感觉。
“你想说什么?”
李清吐出一口烟,顿了几秒说:“我想说,虽然我们上过几次床,你听我吐过几次苦水,但事实上,你约等于一个不存在的人,想到这一点,我的生活更加难以忍受了。”
“那你想结束这一切吗?”
有那么一会儿,两人对视着,一言不发,直到李清把烟灭在不锈钢烟灰缸里。她看了看自己的指甲,毫无兴致的样子,又啜了一口咖啡。蒋润看着她吞咽时滚动的喉部,目光上移后,再次与她四目相对。
“所以就是这样了,我们要么假装这段关系不存在,要么结束它,没有别的选项。”李清说。
“我从来没有假装它不存在。”
在说出这句话之前,蒋润已经感觉到,他们的对话始终盘旋在一道空气墙外,而想要让一切对流,决定权在他手中。只是,他不知道该如何使用它。在他意识到它重量的那一刻,这重量刹那间就逾越了他的想象。他一下子被压缩得很小,仿佛杯沿上失速滑落的一颗水滴。
有人敲门。是之前拍照的那对情侣。男生举着相机,脸上扯开一个带着讨好意味的笑容。
“不好意思,打扰两位,”男生举起手中相机示意,“方便借用一下这个空间,帮我女朋友拍两张照片吗?”
李清瞟了那个男生一眼,快速喝了一口咖啡,就拎起小香包越过他们离开了。蒋润朝男生笑了笑,紧随其后出了房间。脑中有个声音在告诉他,不要去追她,让她消失,等待几天、一周、半个月,甚至一个月后,波动的情绪归位,世界恢复成它理应所是的样子。
李清加快脚步,高跟鞋在路面上发出一连串的叩击声。这个街区邻近江边,都是仿欧式建筑,外立面是一色的清水红砖墙,中间区域旷阔。当所有人都在以同一种步速行走时,蒋润感觉到,那种叩击声正在释放出一种压力,贴紧他,他在李清身后保持的距离足以认领它。
这是某种狩猎吗?他想着。一件被他压在记忆底部的事突然撞进脑中。在他重新遇见李清的半个月后,他曾经在一次出外拍摄时见到过李清的丈夫。他们要拍摄的是一家新能源汽车公司的创始人,他随之见到了那家公司事业部的总经理,并认出了他。对方错愕了两秒,拍了拍蒋润的肩侧。收工时,蒋润经过吸烟区,再次见到他,冲他点了点头。他朝蒋润走来,抖了抖烟盒。
“不了,谢谢。”蒋润说。
“兄弟,你对我是不是有些误会?”
“我们就见过一次,哪里谈得上误会。”
男人吐出一口烟,眯着眼睛看他。
“我不是那种会对女人动粗的人,而且,面对李清这种女人,有时候你真的不知道拿她怎么办。”
“你不用跟我说这些,我和李清,我们谈不上熟悉。”
“但你肯定不缺这样的经验吧。处理女人,还有她们那些问题。”
蒋润挑了挑眉,“什么问题?”
“敏感,情绪大起大落,诸如此类的。像李清,她喜欢戏剧化、夸张、极端的东西。有一阵子,她常常当着我的面吞抗抑郁药。我有时觉得,这只是她舞台装置的一部分,符合她想要扮演的角色的审美。”
男人把烟头在脚底碾熄。
“她在朋友面前不会表现出这一面,你可以放心。”他审视着蒋润。
“没什么可不放心的,再见。”
有很长一段时间,蒋润都没有再想起这次短暂的碰面,他觉得一切只是验证了他对李清生活状况的猜想,而那层始终笼罩着她的忧郁、她偶然一现的脆弱与天真、那些婚姻真相的碎片不容分说地截断了该有的怀疑。蓦地,他不确定了。关于李清,他究竟知道些什么?可紧接着,他不相信她这一想法,又带来片刻的负罪感。
他扩大步幅,跟上李清。他们都直视前方,看起来就像两个碰巧并肩步行的人,只是不知将去向何处。
“忘了刚刚说的那些话吧,对你不公平。”李清开口,同时放慢了脚步。
这下子他反而又迟疑起来,“对我来说,只是有些突然。”
“你知道吗?人类的记忆检索方式是习惯从头一直检索到尾,比如要挑一件黑衣服时,假如前三件都是白衣服,第四件是黑色的,人类会确认第五件也是白的,才取出黑的。我觉得人在寻找爱的人时也是这样。只不过,在你确认完之后,往往已经失去找前一个人的机会了。人就是这样——无法控制自己。”
蒋润回头,发现李清在哭,泪珠在脸上画线。在此之前,他从来没见过她哭。骤然间,他伸出手去拉李清的手,扣住她的指节,所有念头一眨眼都被驱逐了。李清没有抗拒,他微微加重力道,仿佛借此就能承受更多。
两人往前走了一段,犹如处于真空状态,意识像被某种光晕蒙蔽着,剩余的部分只能用来指导躯体执行最简单的动作。不远处迎面走来一行人,手上的握感倏地空了。蒋润怔然半晌,扫视一圈,没有从那些人中辨认出任何一张熟悉的面孔,目光最后落回身旁低着头的李清身上。交错而过一段距离后,李清才抬起头来,她凝视前方,眼中没有任何具体的东西。
“怎么了?”他问。
周遭的声浪从某个破开的口子里猛地涌进脑中。他知道,那个属于他的时刻已经过去,在庞杂而混乱的系统里,意义难明的符号各安其位,而他将再度隐形。
何焜,“九○后”青年作家,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作品发表于《天涯》《鲤》等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