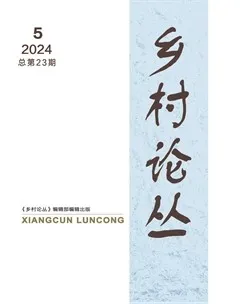优势视角下留守儿童家庭亲子关系分析
摘要:亲子关系的质量对儿童的心理健康、社会适应性和人际交往能力的发展至关重要。当前,关于农村留守儿童家庭的研究大多关注问题层面,无形中忽视了这种特殊家庭模式内含的正向因素。本文依托优势视角理论认识留守儿童家庭亲子关系,不再将视野局限于异地生活、经济困难等外部因素,以理解亲子关系的复杂性。通过寻找正向因素,研究的聚焦点从关注留守儿童心理矛盾转向促进家庭成员积极的情感交流,从关注亲子关系本身的疏离转向亲子之间的整体环境系统,进而充分利用潜在的正向因素建立亲子之间的稳固联系,促使优势迈向正常化,增强家庭成员的幸福感和心理健康。
关键词:优势视角 亲子关系 留守儿童
一、引言
留守儿童群体的出现与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城乡发展不均衡密切相关。1990年代初,随着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深入实施和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大量农村劳动力涌向经济较发达的城市,以寻求更多的就业机会和更高的生活水平。这些流动劳动力主体由农村成年人构成,因工作生活压力和城乡二元体制的限制,除少数农民工会带着子女外出务工外,大部分农民工会将子女留在农村,从而形成了留守儿童这一群体,并随之产生了一系列问题。
根据《2022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2022年全国外出农民工17190万人,其中7061万人跨省流动,10129万人在省内流动,13256万进城农民工年末时在城镇居住。有配偶的外出农民工占67%,即将近七成都已成家,平均年龄42.3岁。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显示,全国有留守儿童的家庭共计占7.013%,留守儿童人数约为751.35万;在这些留守儿童中,农村留守儿童达到604.14万,占比80.58%。
目前,我国学界对留守儿童领域的研究多从问题视角出发,分析不良亲子关系对儿童心理健康、行为习惯及社会适应等方面的影响,较少研究亲子沟通的具体过程和影响机制。传统的问题视角在着眼于发现问题的同时,也会带来一种普遍性忧虑。例如,将留守儿童享受父母带来的物质生活条件改善与失去父母的陪伴对立起来,无形中忽视了留守儿童家庭中存在的正向因素。因此,本文引入优势视角理论,发现并关注留守儿童家庭所拥有的正向因素,包括情感、知识和人际关系等,以正确方式构建健康亲子关系,缓解或解决留守儿童家庭所存在的一些问题。
优势视角理论起源于nvXl4Fq2rfYYkXke3dlQRXFqa9g6tGLpdHovAc2i4sU=20世纪80年代的美国,由心理学家和社会工作者共同提出。优势视角理论可被视为从人类生存问题出发的包含一系列关于健康和潜力的假设和归因的组织化建构(Goldstein,2004),其概念框架是基于对缺陷模式的挑战而建构起来,它的核心概念是围绕发现到的优势和资源而形成的。优势视角理论的内涵包括任何个人和家庭都存在特定优势、抗逆力信念及增权,着眼于寻找和强调问题背后的积极因素和现有资源,包括个人的技能、知识、经验,社会支持网络以及组织的资产和能力。注重培育正面的情感态度、自我效能感和希望,以推动积极变化。优势视角蕴含的英雄主义气质释放了人类的精神力量,质疑了习以为常的传统思想,展现了全新的生存方式(Saleebey,2004)。
近年来,很多国际组织和机构开始将优势视角引入社会服务和政策制定工作中,以促进个体发展和社区建设。研究者们通过实证研究发现,优势视角能够帮助人们更好地应对压力、增强自尊和自信以及提高生活幸福感。同时,优势视角还可以促进个体社会参与能力和社会适应能力的发展。在社会工作中,优势视角被广泛应用于各种服务领域,如家庭、青少年、老年人等相关领域。
二、农村留守儿童家庭亲子关系现状
本文所指的留守儿童,是父母长期离开家庭所在地,从农村流向城市,自身留在农村,且无法得到父母充分照顾和关注的未成年人。留守儿童通常由亲戚、邻居或其他非直系亲属照料或自我照料。据《中国教育统计年鉴2021》的数据显示,2021年,初中阶段留守儿童693万人,小学阶段1011万人,可见留守儿童群体体量庞大。农村劳动力的外流在减少农村公共活动的同时,也降低了村民群体的内聚性,导致留守儿童对家的归属感和对农村的认同度降低(吴重涵,戚务念,2020)。目前,留守儿童在享受物质生活条件改善的同时,父母无法陪伴其左右,这一现状影响了传统的家庭结构和亲子关系。家庭成员的分离可能导致代际关系的弱化,影响家庭稳定性和和谐性,进而对社会基本结构单元产生影响。
(一)情感表达受限
受传统文化的影响,中国人在情感表达方面多采取含蓄内敛的方式,这一影响在农村地区更加深远,导致父母与子女之间的情感表达受限。
很多留守儿童或抱有自己的事情就算跟父母说了也没用,父母无法帮助自己解决困难的想法,或持有不想让父母为自己担心的心态,很少主动与父母交流。父母的缺席使得留守儿童在情感认同、自我价值和安全感上感到缺失。
大多数留守儿童家庭中的父母认为,为子女提供更好的物质条件即是给予子女最直接、最强烈的情感表达。例如,提供生活费、零花钱,以额外开支满足子女心愿,或在过年回家时给子女购买几套新衣服和零食等礼物。家庭物质条件的改善意味着更好的生活质量。客观来说,这为亲子关系的改善创造了更有利的外部条件。当经济条件允许时,父母可能还会选择更频繁地回家或带子女去城市一起生活,增强家庭成员之间的直接联系和情感交流。然而,值得注意的是,物质条件的改善虽然为加强亲子关系提供了可能,但并不能完全替代父母与子女之间直接、长期和持续的情感表达。
(二)教育沟通交流匮乏
亲子间的良好沟通、理解和支持对于子女的成长和发展至关重要。尽管亲密关系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但沟通仍是关系维护的关键。亲子沟通是联结父母和子女情感关系的纽带,更是实现家庭功能的重要方式。依恋理论指出,从婴幼儿时期开始,父母与子女的互动对子女个性的形成和影响将会伴随其一生(巴克斯特,2010)。
大多数留守儿童家庭父母的文化程度相对较低。根据《2022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的数据,在全部农民工中,未上过学的占0.7%,小学文化程度占13.4%,初中文化程度占55.2%,高中文化程度占17.0%,大专及以上占13.7%。加之,异地分离,农民工在子女的学业监督和学习指导上参与度低,无法起到良好辅导作用,留守儿童教育层面的沟通交流缺失。
留守儿童单向接受学校教育,缺乏家庭的学习支持和监督,学校成为留守儿童日常生活和学习的主要依托。学校不仅要承担知识教育职责,通过现代和科学的教学方法提供更加广阔和多元的知识视角,还需要在生活习惯、行为规范等方面对留守儿童进行指导和监督,这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父母传统的或者过时的教育观念对子女思维方式和学习方法的限制。然而,教育资源在城乡之间分配不均衡,农村地区学校实力、资源有限,使得农村留守儿童不能享受与城市儿童相同的教育水平,加剧了留守儿童的教育困境。
(三)亲子互动缺失
社会学习理论的代表者班图拉认为,一个人的大部分社会行为都是通过观察他人、模仿他人而习得的。在儿童的心理和行为形成初期,父母是其最重要的模仿对象,不仅用简单的社会规范增强儿童的心理适应,还通过自身行为对其行为规范产生随机影响(张学浪,2016)。
正常情况下,亲子之间可以通过日常相处来表达看法、交换意见,以此增进亲子之间的了解,共同解决家庭生活中的问题。然而,留守儿童得不到父母长期的关怀、照顾和教育,这使得亲子之间无法通过日常生活互动来加强情感联系(肖莉娜,2022)。同时,在留守儿童家庭中,因为缺少日常的交流沟通,父母无法顺利系统地传授自己的生活经验,帮助子女建立正确的价值标准与行为习惯,留守儿童可能缺乏必要的社交技能和自我表达能力。这种情况在信息时代被进一步放大,使他们更多地依赖电子设备进行交流,而缺乏真实的人际互动,在发展社交技能和处理人际关系方面可能遇到困难,甚至有可能影响他们成年后的社会适应能力,包括建立稳定的人际关系和职业生涯发展。
然而,留守儿童家庭亲子关系问题具有多维性。以问题视角关注留守儿童,可能导致过分集中于困难和缺陷,忽视了留守儿童家庭潜在的正向因素。通过转向优势视角,识别和强调留守儿童家庭、社会等主体中存在的优势,包括家庭经济条件提升、社会支持网络、文化韧性,以及信息技术条件,可以构建一个更加积极和支持性的环境,为缓解或解决留守儿童问题提供新的思路和方向。
三、优势视角理论下的留守儿童家庭亲子关系
McMillen(1999)认为,人们在经历痛苦和危难之后可能伴随着成长,因为曾经面对的困难甚至创伤性事件会导致在此后遇到另外的挑战时,具有更大的信心或者应对逆境能力的提升。从优势视角理论出发,留守儿童家庭不单单存在问题和障碍,其蕴含着可以发掘的优势和机会等正向因素,有助于留守儿童问题的缓解。
(一)未间断且得到强化的情感联系
家庭是以婚姻和血缘关系为基础的最小社会单位,是亲子情感交流的“基地”,亲子关系几乎是幼儿全部情感的依赖所在。依托优势视角理论可以发现,即使留守儿童家庭亲子间异地分离,父母与子女之间的情感感知和利他动机依然高度契合,亲子之间的情感联系也始终没有间断,并在家庭情感共同体中被不断强化。
1.理解父母付出。大多数留守儿童理解父母为了提高家庭的生活质量而长期外出务工所做出的努力和奉献,物质条件的改善也能使留守儿童感受到父母的关爱和努力,增加他们对父母的理解和尊重,认同父母的教导。例如,留守儿童从定期收到的汇款中能够感受到父母的关心和爱,认识到父母外出务工的目的和不易。他们也会努力掌握父母迁移所带来的各种变化,主动调整与父母之间的关系,以适应自身所处的环境(肖莉娜,2022)。留守儿童通常能够形成良好的消费观念,珍惜父母给的生活费,生活节俭,懂得心疼父母。
2.独特的社会支持系统。留守儿童在社会文化的熏陶、亲子关系的感知、学校与社区重要他人的替代中,形成了基于自身视角的亲代在位的认知图式(吴重涵、戚务念,2020)。尽管留守儿童与父母存在物理上的分离,但他们拥有扩展的家庭和社交网络。这些网络中的成员,如祖父母、亲戚、邻居或朋友等,可以提供情感支持、照顾和指导。这种网络为留守儿童提供了额外的关怀和亲密关系,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父母的空缺。以安徽、河南、四川等劳务输出大省的情况为例,农村年轻劳动力几乎全部向外省流动,村里普遍是留守儿童,同辈群体之间差别不大,从而淡化了他们对父母不在身边的消极或错误解读,能够以更为理性的心态看待留守现状。同辈群体在留守儿童的社会化、心理发展和行为塑造方面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提供了学习社交技能的平台。留守儿童通过观察和模仿同龄人的行为,学习如何适应社会,包括言语交流、冲突解决、合作与竞争等。在面对生活压力和挑战时,来自同辈的支持可以减轻压力和不安,增强留守儿童应对生活挑战的能力。
(二)较强的独立意识和责任感
有研究表明,儿童身处困境时具有良好的适应性和抵抗挫折的潜能。当农村留守儿童面对挫折难以寻求父母帮助时,也有可能使其获得成长机会。
1.独立自主意识。优势视角下,无论是个人还是家庭都潜存着正向资源,生活中的疾病和创伤可以是伤害也可以是机遇(王礼刚,张桃香,2022)。帕尔曼认为,一个人有意识去处理自身问题,认清问题与自身的相互依存关系,就是个人的潜在优势。留守儿童由于长期独立生活或被委托照料,逐渐养成了自己处理各类事务和解决问题的习惯,这种自主能力的提高,推动他们成为独立、自信和有责任心的个体。
本文结合对皖北地区农村留守儿童的观察和此前的研究发现,留守儿童具备较强的抗逆力。抗逆力作为优势视角理论的核心,是个人的自我纠正取向,是弯曲而不折断或弯曲之时反弹的能力(Vaillant,1993)。抗逆力被视为基于关系的而非孤身一人的,以抗逆力为聚焦的实践知识创造了一种乐观和希望的情境,认为个人在面临困境时依然能够做出正确的选择,从而推动事情向积极方向发展。因此,依托优势视角理论能够发现,大多数留守儿童在心理、行为方面更加成熟。
2.承担一定家庭责任。留守儿童理解父母在外务工的不易,希望能为父母分担家庭负担。这种意识是留守儿童对父母为家庭所作贡献的肯定,能够更加深刻地意识到家庭的重要性,更加珍惜与父母的沟通和相聚。他们遵从父母嘱咐,在学习上用功,在生活上照顾好弟弟妹妹,做些力所能及的家务或农活。留守儿童作为新时代的青少年,有顺应时代的思想观念和技能知识。例如,精通智能设备的使用,能够运用网络资源自学,等等。在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外流,只剩空巢老人和留守儿童的现实情境下,儿童作为农村中的新生力量,在家庭遇到问题时能够利用网络查找解决方法。从这一层面来说,留守儿童也承担了一定家庭责任。
(三)具备多元文化价值观
留守儿童在农村长大,对当地文化习俗、传统习惯有深入了解和认同,是继承和发扬这些宝贵文化遗产的新生力量。同时,部分留守儿童在约三个多月的寒暑假期间会到父母务工所在城市居住。这使得他们可以获得跨文化交流的经验。在城市居住期间,留守儿童可以体验快节奏的生活方式,接触到不同的人群和文化,交到新朋友,体验与农村不同的生活环境。城乡两种生活经历拓宽了留守儿童的眼界,培养了他们的包容性、开放性和多元思维,形成多元文化价值观,有利于他们更好的适应留守生活。
四、视角转变——改善留守儿童家庭亲子关系的建议
传统研究中的思维惯性是寻找问题,针对问题寻求解决办法。然而,过度关注问题容易降低留守儿童的自信心,产生遇事消极应对、畏难等情绪。因此,可尝试合理运用优势视角理论,发现并利用留守儿童家庭中存在的正向因素,培养留守儿童、父母等主体的积极心态,建立“发现优势―增强信心―解决问题”的良性循环。
(一)正视情感表达
根据此前的研究,与父母保持亲密联系的儿童更有可能表现出积极的情绪和行为,如更高的自尊心、更好的社交技能和更强的自我控制能力。应积极挖掘利用留守儿童家庭存在的正向因素,引导留守儿童正确宣泄内心烦恼,主动大胆的向父母表达爱意和思念,拒绝羞耻心理干扰,增强抗挫折能力。
对进城务工的农村父母也应进行相应引导和教育,强化父母的家庭教育观念及其重要性,让父母学会与孩子沟通、交流以及教育孩子的正确方式。发挥父母对孩子的独特的教育功能,引导孩子健康成长。父母应学会倾听孩子诉求,给予足够关注和支持,如通过定期举行家庭会议,主动增加与子女的沟通次数并提高沟通质量,分享自己的感受,养成开放的情感表达习惯。
还需要注意的是,在优势视角理论框架下,创建良好的家庭关系需要父母与子女共同合作,通过建立信任、互相理解和保持真诚以促进亲密关系的发展。亲子之间应建立平等的伙伴关系,伙伴关系侧重于各方之间的互相支持、合作和认同,而不是其中任何一方具有压倒另一方的优势地位。父母要走进子女的内心,给予信任,尊重子女的需要、差异和边界。“重视儿童的兴趣、年龄技巧和智力发展,鼓励多用积极的诱导,少作消极的批评”(张学浪,2016)。
(二)远距离亲子沟通
有研究显示,在友情、爱情等纯粹关系的发展和维护中,远距离的亲密关系可能比每天都在一起的亲密关系表现出更高的关系质量与奉献精神(Kelmeretal,2013)。
对留守儿童家庭而言,手机等智能设备在亲密关系维持中所发挥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手机作为留守儿童重要的社会支持系统之一,不仅支撑信息交流,更重要的是提供情感支持的重要媒介。根据第52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2023年8月28日发布)的数据,截至2023年6月,我国互联网普及率达76.4%,即时通信、网络视频用户使用率分别达97.1%和96.8%。农村留守儿童普遍拥有智能手机或智能手表。截至2021年6月,我国农村网民规模达2.97亿,农村地区互联网普及率为59.2%,行政村通光纤和4G网络的比例均超过了99%。这为留守儿童家庭远距离沟通提供了条件。
手机可以有效缩短留守儿童与父母的心理距离,亲子之间可以经常进行语音聊天和视频通话,发送语音、图片和视频,分享情绪,寻求慰藉,实现“联系的在场”,手机成了人们“移动的家园”(胡春阳,2012),减少亲子间不能实地近距离沟通的负面影响,将家庭成员紧密联系在一起。同时,在多人聊天、群视频功能的支持下,家庭成员间可以实时“面对面”聊天,营造出欢聚一堂的氛围感,有效降低距离带来的隔阂感和负面影响。此外,父母通过加入子女的班级群,与教师保持良好沟通,能够实时了解子女在学校的表现和学习成绩,督促子女学习。
(三)发展社会支持系统
社区层面,积极利用社区资源,如社区中心、儿童活动中心和文化活动等,让留守儿童参与更多集体活动,增强社交技能和归属感。利用社交平台等技术资源建立支持网络,提供必要物质和情感支持。家庭成员、亲戚、朋友和邻居构成的非正式支持网络是社会支持的基础,发挥重要的情感支持、物质帮助和信息交流功能,能够在留守儿童面对困难时使其感受到关爱并获得帮助。社区应积极引导在家祖父母或其他监护人,传授科学有效的方式方法,为留守儿童提供充足情感支持,包括倾听孩子的想法和感受,鼓励他们表达情绪,积极回应他们的需求,并积极参与孩子的学习和教育过程,监督完成课后作业,与学校老师保持沟通,了解孩子的学习状况和需要。
学校层面,设立专门的留守儿童支持系统。例如,关爱小组、自我成长小组等,由教师和心理咨询师参与其中,利用视频通话、在线咨询平台等技术,为留守儿童提供心理健康支持和咨询服务。这些小组可以定期监测留守儿童的学习进展和心理状态,及时提供必要的帮助。学校可以为留守儿童设置各种线上和线下兴趣小组、技能培训班,在帮助他们发展个人爱好的同时,增强他们的社交技能和团队合作能力。
政府层面,制定并实施专门针对留守儿童的政策,确保他们的教育、健康和安全需求得到满足,支持改善留守儿童的教育和生活。加大对农村地区的教育资源投入,改善留守儿童的教育环境和质量。通过互联网和数字平台提供高质量的教育资源,如在线课程、虚拟教室和教育软件等。这不仅可以帮助农村留守儿童获得与城市儿童同等的学习机会和资源,还可以发展他们的自学能力和问题解决能力。此外,通过税收减免、创业扶持等措施,鼓励留守儿童家庭父母返乡就近就业或创业,从根本上解决留守儿童家庭成员异地分离的问题。
五、结语
本研究依托优势视角理论,通过寻找正向因素的思维取向,打破了问题视角所常描述的“消极”的留守儿童问题的刻板印象,是对问题视角的再平衡,也是对优势视角理论本土化的实践尝试,以期丰富优势视角理论的研究内容,为留守儿童家庭亲子间情感表达、沟通及未来发展向好提供新的可能。
值得注意的是,本文主要将皖北地区农村留守儿童家庭作为研究对象,且当地大多数留守儿童有寒暑假与父母在大城市生活的经历。因此,本文研究结论对全国范围内的留守儿童问题不具有普适意义。未来的研究,或可对始终生活在农村,未曾随父母流动的留守儿童进行研究,或可聚焦于跟踪调查,研究留守儿童在成年后与其父母的相处方式及家庭关系。
参考文献
[1]胡春阳,毛荻秋.看不见的父母与理想化的亲情:农村留守儿童亲子沟通与关系维护研究[J].新闻大学,2019,(06):57-70+123.
[2]Saleebey.优势视角:社会工作实践的新模式[M].上海: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2004.
[3]Dindia,K,and Canary,D. J.Relational Maintenance: Definition and Theoretical Perspectives on Maintaining Relationships[J].Journal of Social and Personal Relationships,1993,(10):163-167.
[4]Crystal Jiang,L,and Hancock,J.T.Absence Makes the Communication Grow Fonder: Geographic Separation,Interpersonal Media and Intimacy in Dating Relationship[J].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2013,63(3):556-577.
[5]陈亮,张丽锦,沈杰.亲子关系对农村留守儿童主观幸福感的影响[J].中国特殊教育,2009,(03):8-12+32.
[6]范志宇,吴岩.亲子关系与农村留守儿童孤独感、抑郁:感恩的中介与调节作用[J].心理发展与教育,2020,36(6):734-742.
[7]吴重涵,戚务念.留守儿童家庭结构中的亲代在位[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20,38(6):86-101.
[8]朱科蓉,李春景,周淑琴.农村“留守子女”学习状况分析与建议[J].教育科学,2018,(04),21-24.
[9]吴霓.农村留守儿童问题调研报告[J].教育研究,2004,(10):15-18+53.
[10]肖莉娜.“爱而不亲”:留守儿童的亲子关系体验与建构[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54(1):108-117.
[11]张学浪.新时期农村留守儿童家庭教育纽带构建:现实困境与破局之策[J].农村经济,2016,(06):124-129.
[12]王礼刚,张桃香.优势视角下社会工作介入农村留守儿童的服务研究——农村留守儿童亲子疏离案例分析[J].现代商贸工业,2022,43(19):231.
[13]何雪松.社会工作理论(第二版)[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
[14]卢婷,陈彦.再识家庭:家庭照料的优势运作与价值审度[J].太原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25(03):37-45.
[15]谭秀芝,张春雷,王欣.积极心理学在农村留守儿童心理品质培养方面的应用[J].教育实践与研究,2024,(21):43-46.
(作者单位:新疆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