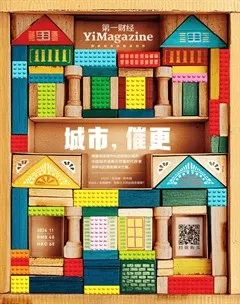城市到底在“更新”什么?

如果说城市是一台长期运转的“超级机器”,那它难免也要面对各种故障和零件老化。针对规划用地变化、建筑物日久失修、生活居住环境亟需改善等需求,政府和城市治理机构在为城市寻找一系列解决方案。这些领域里的各种尝试,人们通常称之为“城市更新”(Urban Renewal)。
城市在更新什么?
“城市更新”这个词最早出现在1949年美国的《住宅法》中,指拆除老城区危房和贫民窟,然后在这块地上建造现代化的高层住宅、商业街区和交通基础设施。
全球各地城市更新主要开始于“二战”之后—从重建被战争摧毁的城市开始。为了应对城市扩张,英国在1946年就出台了《新城法》,成立能够强制征地的国企开发公司,以支持全国76个城市的更新需求。之后的30年里,英国多了32座新城,平均每座城市人口超过5万。政府为此不断修改法律,提高开发项目的最高借贷限额,为新生的城市修改行政体系。这一时期,不止是英国,各个发达国家的政策制定者、建筑师、意见领袖们都富有激情地讨论“什么是理想生活”,拆除他们认为过时的老建筑,兴建大型集合住宅和地标建筑。
1958年,荷兰海牙举办了第一次城市更新研讨会,旨在向美国城市规划师介绍欧洲的战后重建工作。美国的专业人士当时急于借鉴欧洲经验,试图像欧洲人一样,在市中心划出人行步道,而不是为汽车规划道路,为区域和建筑规定更精细的多种用途。
参会者还进一步探讨了城市更新的意义和定义:小到城市居民对自有房屋的修理改造,大到城市基础设施的更新换代,“有关城市改善的建设活动”都可以被看作城市更新。
但根据1965年美国城市规划组织的一份研究报告,当时的城市更新也有局限。1949年至1964年间,美国联邦政府事关城市更新的所有支出中,只有2%用于重新安置当地居民,过半被征收的土地因为资金不足、无人开发中荒置,另一半则被政府低价出售给了私人开发商,在规划上也是种族隔离的作派。
“许多清理区(波士顿西区就是一个例子)之所以被选中,并不是因为那里有最糟糕的贫民窟,而是因为它们是建造豪华住宅的最佳地点—无论城市更新计划是否存在,这些住宅都会被建造。”美国经济学家、政府顾问马丁·安德森(Martin Anderson)在其著作《联邦推土机》中辛辣地批评。
这个观点可能有些过火,但另一位规划学家切斯特·哈特曼(Chester Hartman)刚好研究过波士顿西区的意大利人聚居区—这个地方被城市更新管理局判定为贫民窟,结果表明,项目结束后,71%的白人居民搬到了当地“更优质的住宅”里,但需要支付的租金涨了70%。
1970年代,全球城市更新策略又迎来变化。1970年,美国联邦政府通过了《住房和城市发展法》,更加强调保护社区,提高居民参与度。各国政府整改城市中心的居民区和工业区使得人口外流,居民失去工作机会,老城区空置,于是,再次开发市中心、振兴产业成了政府的新目标。
1980年,英国政府通过《地方政府、规划和土地法》,社会资本自此登上城市更新的舞台。该法案规定,地方政府必须就工程合同公开招标,并建立开发公司,政府和私营企业共同持股。他们的任务说白了只有一项:吸引人们回到城市。
美国学者、城市规划师尤金妮·L·伯奇(Eugenie L. Birch)在2007年的著作《土地政策及其后果》中指出:21世纪,人们对城市的态度发生了重大变化。经过政府和开发公司多年运作,城市重新成为人才和资源的代名词;市中心不再是贫困和犯罪的温床,人们反而盛赞这些地方拥有历史文化遗产和强大的社区。
在中国,从1970年代开始,北京、上海、广州、南京、合肥、苏州、常州等城市,都开展了大规模的旧城改造。“拆迁”这个词,也是伴随一代人的城市时代记忆。

如今,广义上的城市更新涉及城市重建、旧城改造、城市再开发、城市复兴等范畴。它面对的挑战越来越复杂,城市更新的手段也不再局限于建筑物拆改,而是转向采取更多维度的方法。
近200年来,城市更新的背后大多有政府的身影,它们从公共利益出发,主导或发起不同的项目。但传统政府背景的城市更新机构正变得更有综合性。
中国香港的市区重建局就是一个综合了各种城市更新职能的法定机构。它的前身为1988年成立的香港土地发展公司,2001年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立法,市区重建局由此诞生。市区重建局可以与业主谈判,以合理市场价收购其房产,作为法定机构,也有在限制条件下直接征用土地以加快香港市区重建进度的权力。除此之外,市区重建局还要修缮老房子,改善市区环境,推进居民的安置及补偿、重建规划及文物保护等事务。
同一时期,在日本也诞生了类似的组织,名叫“都市再生机构”(以下简称“UR”)。UR是独立行政法人,归日本国土交通省直辖,自负盈亏。UR的前身是“日本住宅公团”,曾负责开发“团地住宅”—类似于中国的公房。2004年它更名为“都市再生机构”,职能也不再是拼命建公寓楼,而是管理名下住宅租赁,并参与各大城市更新项目。由于兼具政府背景和公司两种属性,在复杂的城市更新项目中UR负责统筹各个利益相关方。

现在,更多利益主体期望直接参与街区事务。几乎所有城市更新的决策过程,都涉及到公开听证会、咨询会以及街区活动。“街区也认识到,让私营部门参与街区振兴工作很关键。(在城市更新中)街区发展委员会处于战略地位,这个组织可以争取到当地居民的支持,从而让项目赢得公众的广泛认可。”伯奇写道。
在城市更新这个领域,一个组织或机构可能早已无法推动一个利益关联广泛的综合项目,每个国家、每座城市都面临不同的问题,政府、企业和居民力量等多方之间总是在不断角力。
城市更新,不止是政府的事
城市更新并非政府一方的工作与责任。这类项目常常面临建设时间长、启动资金高的困境,为缓解财政压力,政府会尝试引入市场领域的合作方,另一方面这也是为了将建设规划工作交给更专业的人来做。全球主流的城市更新模式是PPP(Public Private Partnership),即政府与企业等社会资本合作。
PPP最初出现在基础设施建设中,许多早期的铁路系统就是私人公司与政府合作建造的。现代PPP则发源于英国。在1992年,英国政府提出了PPP最具代表性的方法—PFI(Private Finance Initiative),即“私人融资活动”。它指的是利用私人资金和专业知识,在公共设施等的设计、建设、维护管理和运营中,由私营部门主导提供公共服务。此类项目中,政府不再负责公共设施的建筑工程,而是通过长期合同,将建设和运营任务外包给私营部门。
英国伦敦国王十字街区(King’s Cross)城市更新是典型的PPP项目。国家和地方政府、铁路公司、房产开发商合作推动了该地区的城市更新。
国王十字地区曾经是伦敦物资交换的门户,自维多利亚时代开始,它就是英国的重要的工业运输中心。但铁路运输的衰退让这里变得萧条。国王十字车站也位于这个区域,它和圣潘克拉斯站(St. Pancras Station)连接了这里与英国中北部几个重要工业城市。

1996年,国王十字街区迎来了转机。英国政府决定将铁道线“High Speed 1”(HS1)的终点站从伦敦的滑铁卢车站改为圣潘克拉斯车站,使其与英国国内铁路网络“无缝连接”,英国政府也希望此举成为国王十字地区更新的起爆剂。HS1上运行的“欧洲之星”列车,将穿越英法海底隧道,进一步连接伦敦和欧陆地区。
当时,英国政府持有国王十字车站和圣潘克拉斯车站及周边部分地区的土地产权,另一家公司Exel(后被敦豪公司收购)也拥有国王十字区域内大量土地,其他地权由一些小业主分散持有。
中标HS1建设工程的是伦敦和欧陆铁路公司(LCR)。当时LCR是一家私营财团,2009年时它因经营不善被英国政府收购。英国政府向LCR注资数十亿英镑,LCR还获得了HS1沿线地块的开发权以及国王十字街区周边物业的开发权,而LCR需要将街区更新项目的一半净利润返还给政府。随着HS1建设的推进,LCR慢慢从单纯的铁路建设公司转变成了物业开发和资产管理机构。
2001年,LCR委托房产开发商Argent负责区域的整体开发,这两家公司在2008年联合Exel公司共同成立了国王十字中心有限公司(KCCLP)。到2014年时,KCCLP这家公司成了国王十字地区土地的单一所有人,这意味着基础设施建设变得更便利,供热、供电公司不再需要疏通复杂的产权关系。同时,该区域的城市更新有了更多的资金来源,比如KCCLP接受了澳大利亚最大的养老金基金之一AustralianSuper的投资。

KCCLP承担了与各级政府、组织沟通的职责。除了需要从政府拿到开发许可,他们还要与负责遗产保护的组织沟通区域内历史建筑的改造问题,与居民组织沟通以获取当地人的信任。之后,通过“以点带面”策略,KCCLP于2002年吸引了中央圣马丁艺术与设计学院在国王十字地区开设新校区。它所带来的人才又吸引了不少大公司入驻,Google和路易威登就把英国总部搬到了这个区域。
PPP模式让国王十字地区重新焕发了生机。通过政府和开发商的协调,区域内各类主体的利益得到兼顾。在二十多年的城市更新过程中,国王十字街区引入了近2000套新住宅、近10万平方米的零售空间和50万平方米的办公空间。从2010年到2022年,国王十字街区的办公室的平均租金提升了约一倍。
综合问题的开发样板—TOD
交通是城市更新的一大驱动力。“二战”后,随着私家车普及和高速公路网扩展,特别是在美国,不少城市逐渐向郊区扩张,中心呈现衰败趋势。城市的无序蔓延让基础设施服务变得低效,同时浪费了土地资源,也让城市居民更加依赖驾车出 行。
当人们开始反思私家车带来的城市问题,“公共交通引导发展”(Transit-Oriented-Development,TOD)的思想应运而生。在城市规划师彼得·卡尔索普(Peter Calthorpe)看来,TOD理念强调通过高密度、多功能的土地开发策略,建设有效的公共交通系统,减少居民对汽车的依赖。
日本的许多城市长期践行TOD的发展模式。数个铁道线路交叉的枢纽区域是城市问题集中爆发的场所。交通枢纽的建设往往基于“过时”的规划方案,随着城市人口增多,常常出现用地紧张、基础设施老旧等问题。在城市更新的语境下,TOD的模式仍旧发挥着作用:升级车站的同时,推动周边可步行范围的城市更新。日本铁道公司的典型做法是,拆除自己在原有街区所有的旧建筑,引入全国连锁品牌以及自家公司旗下的业态,这样更容易保证收益。
东京涩谷站周边区域的城市更新就遵循TOD模式,地区建设由铁路公司主导。涩谷站于1885年正式开通,随着线路增加,它逐渐成为东京最大的交通枢纽之一—共有4家铁路公司的9条线路在这里交汇,平均每天有超过300万人在这里上下 车。
在涩谷站慢慢发展为交通枢纽的同时,这里也出现了轨道交通、巴士系统换乘动线复杂,以及纵向移动的客流量剧增等问题。车站外,涩谷大十字路口已经成为东京的标志性景观,紧邻大十字路口的八公广场往往人满为患。同时,轨道和高架隔断了城市空间,行人想要穿行车站的东西两侧并不容易。
涩谷站周边区域更新的契机是铁道“地下化”。为了缓解JR山手线的拥挤,日本政府于2001年规划了新地铁线“副都心线”,并且为了与东急东横线实现互通,决定将地上的东横线转移至地下,释放东横线的车站和轨道用地。同时,在涩谷站前区域重新规划空中人行动线和地面巴士枢纽。2005年,政府认定涩谷站周边地区为“都市再生紧急整备地域”,这意味着,行政部门对该地区的容积率限制更加宽松。
开发商在必须动脑筋围绕车站做文章的时候,总能想出一些最大化利用有限空间的办法。东急集团在这轮城市更新中扮演了重要角色。除了改良轨道交通的换乘体验,他们还积极参与不动产开发。
2003年,随着东急东横线“地下化”工程开展,东急集团旗下的综合商业设施东急文化会馆停业了。当时这座8层建筑已经运营了近50年,设施老旧,陷入亏损。9年后,东急文化会馆的原址上建起了一座全新的商业设施—约40层涩谷Hikarie,高楼的地下是东急东横线与东京地下铁的换乘通道,地上建筑涵盖了商业、剧场、办公等各种功能,展现出名副其实的“立体城市”概念。
开业后的18天内,涩谷Hikarie就吸引了220万人拜访。打响这第一炮后,东急集团计划在20年间在涩谷站周边新建SHIBUYA STREAM、Shibuya、Scramble Square、Shibuya Sakura Stage等10个商业设施。
除了东京,中国香港也擅长TOD项目。在TOD项目中,中国香港政府首先以车站建设前的市场价格将站点周边土地的开发权出售给港铁公司(Mass Transit Railway,MTR),港铁再与私人开发商联合开发该地块。当地铁站修建完成后,沿线的地产价值提升,港铁再将部分产权出售,获得的利润通过分红和持股升值的方式还给政府。
TOD常常和其他“人本主义”的城市更新思想一起出现,强调城市的公共空间,激发人的主观能动性。21世纪的城市更新基本以人为主线,比如混合用途开发、公园导向开发、阻止城市衰退的复兴主义、社区参与规划等,各种流派互相影响和促 进。
但和其他理念相比,TOD的成功有很高的门槛,不仅取决于当地是否有足够高效、能够聚集人流的公共交通服务,车站周围设施的初期建设成本投入也很大,需要合理规划、长期维护。在这个背景下,一些更轻量化的做法开始出现。
轻量化的微型更新
在日本,团地改造项目为这类微型更新提供了一些经验。日本的团地类似于中国的公房老小区,是日本在战后为工薪族开发的标准化集体住宅。截至2020年,根据日本政府国土交通省统计,日本全国共有2900个团地住宅小区,其中过半的房龄超过30年,居民也呈现高龄化趋势。这些团地住宅基本没有商业和交通配套,很难打动年轻住户,空置率很高。
曾经负责这些团地开发的独立行政法人日本住宅公团,也就是如今的UR,也由此开启了让团地重生的序幕。原拆原建的做法最为简单直接,但《日本公寓重建法》规定,每个小区必须有8成所有者通过决议,并重估设计、成本、所有权等问题,才能推进重建计划。考虑到UR管理着70多万户团地住宅,这将是一个漫长而难以协调的流程。
UR不得不寻找让这些“存量房”更有价值的解决方案。他们找到了无印良品居住空间部门,朝着年轻人会喜欢的方向重新设计住宅内部装潢。截至2024年10月,双方已经合作改造了68个团地住宅小区,其中91%的小区全部租了出去,3/4的住户年龄在40岁以下。这个合作还会延续到UR管理的团地的公共空间里,无印良品会改造店铺,举办市集和工作坊。
几乎同一时期,一些轻量化的城市议题解决方案也在美国实施。2007年到2013年,时任美国纽约交通局委员珍妮特·萨迪-汗(Janette Sadik-Khan)开启了一连串“抢街”行动。萨迪-汗自称是社会活动家简·雅各布斯理念的继任者,主张保护现有的社区生活和小尺度街道。她认为,通过简单的道路规划—让市中心多出几条步行街,就可以提振街区人气和商业,减少纽约可怕的交通拥堵。
萨迪-汗的任期内没有任何复杂的大工程。只需要几十万美元,让工人带上障碍物、油漆和热塑塑胶,放上露天长椅,就能迅速在街道上设定边界,建成一个“步行广场”。将周末的街道禁车,行人就会自发“占领”路面锻炼身体,孕育各种社区和商业活动。
2009年,纽约交通局下发的交通禁令给时代广场改造开了个头,42至47街区禁止行车,整个时代广场多出了近1万平方米的步行区域。2011年的数据显示,时代广场行人受伤人数、车辆事故和犯罪率都明显下降,底层商铺每平方米租金涨了一倍,跻身全球十大零售商圈。
回到中国视野,成都市玉林东路社区的“巷子里”项目也是个值得讨论的案例,因为它走通了一条鲜有前例的路子:增建从社区党群服务中心一楼延伸出来的新空间,并且因为容纳了咖啡馆、画廊、文化活动场所等,社区活力被重新激活。社区党群书记杨金惠主动向社会公开募集专业人士,找到了一介建筑的创始人张唐,他们一起调研居民需求、艰难筹集款项,落成了“巷子里”。
最初,杨金惠想利用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周边的空地,做一些适宜残障人士的改造,由武侯区残疾人联合会提供启动资金。但在居民会议上,大家拒绝接受建筑外观改造方案,理由是要投入资金,却没有为他们的生活着想。杨金惠意识到,她需要一位分析社区现状、聆听居民需求的“社区规划师”。
张唐的经验起了作用。她不停地找居民聊天、走访调查,一点点调整思路,种种问题随之浮现:社区定位中包含艺术文化,却没有公共艺术空间;许多流动人口是年轻人,但“15分钟步行圈”里没有他们喜爱的小店;一些本地居民找不到合适的交流场所,难以建立对社区的认同感和自豪感。
巷子里开业初期,张唐利用外部客流打响知名度,邀请成都10家独立咖啡店的主理人、艺术家们轮番前来驻场。等客流稳定后再考虑雇用人手。巷子里无需向社区支付租金,收益来自场租和零售分成,但若商业活动和社区活动撞了时间,场地会优先给社区用。这种做法也错开了外来人群和社区居民,使彼此的生活轨迹不受影响。
巷子里获得了2020年公共建筑·空间类的日本优良设计大奖(GOOD DESIGN Award2020),如今已运营4年。这些成果说服了社区继续聘请张唐和一介建筑改造其他场地。谁都没想到,一块可以改建的空地,会牵扯出这样一个完整方案。
但是一个有活力的街区也离不开持续的运营与管理。2020年,日本东京下北泽BONUSTR ACK项目开张,这是个小型商业街,运营公司散步社和土地持有者—私营铁路公司小田急电铁签订了20年协议。散步社创始人有着社会创新媒体和独立书店的运营经验,为了说服有意思的个人小店入驻,这家公司甚至用店家能承受的预估店租倒推建设成本,不停地举办经营经验分享会。等到街区建成开张后,每隔几周,他们都会在街区空地上举办市集,吸引新的访客。凭借在成本控制与街区文化营造平衡点上的创新,这个项目在日本吸引了不少社区运营者与开发商的注意。
同样,在中国,有持续运营能力的机构正成为城市更新参与方看重的重要力量,地产开发商将可以填充进开发项目的运营方式称为“内容”,开始寻找更有性价比的“会做内容”的企划者与运营者。但更多地方政府与机构一方面希望让社区获得更多关注与活力,却又面临缺乏持续运营的人力与资金的局面。
在这种情况下,具备城市规划、项目企划、设计能力、运营管理能力等综合技能的专业社区营造组织陆续出现。在日本,这类机构已有先行者—“都市再生推进法人”就是日本城市更新进程中的一股重要力量。基于日本20 02年颁布的《都市再生特别处置法》,市、町、村级别的行政单位可以指定有能力和经验统筹各个利益方的公益团体或公司为“都市再生推进法人”。在政府机构和私人开发商难以触及的部分公共区域,这些组织会起到补充支援作用。
即便街区“升级”成功,士绅化仍然是一个备受争议的问题。这个说法首次出现于1960年代前后的全球城市贫民窟拆除浪潮之中,指的是城市更新进程中,廉价街区因为设施升级、先进规划理念,在短时间内房价升值。针对士绅化,常见的批评是城市更新造成生活成本上升,让富裕居民挤走了原住民。
从社区团结的美好故事到“急速士绅化”模板,美国纽约的高线公园(High Line Park)只用了10 年。“高线”之名源于一条曼哈顿下西区荒废已久的城市货运铁路高架桥,它途经城中贫困的老工业区。2001年,社区居民拿出改造方案说服政府沿铁路造一个可以深入街区的公园,让社区组织运营。2009年,高线公园和纽约人正式见面,成为城中热门地标,但居民们并未走进去,吹捧它的是富人阶层、游客和在周围上班的人。2016年,高线两侧的房价比东边两个街区高出20%。
围绕高线公园的争议迄今仍在继续,这个故事可能发生在任何一个完成“升级”的街区与城市。有人喜爱那些经过雕琢的生活方式与新的商业机遇,也有人感慨原住民的流失,更有人愤懑,一种以城市更新“副产品”形态展现的社会不公在陆续涌现。
现代城市面临着越来越复杂的综合议题,越来越多组织、机构与个人开始在城市更新决策中拥有一席之地。有人看到了更多新的利益,也有人看到更多新的机会,城市更新的议题也仍在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