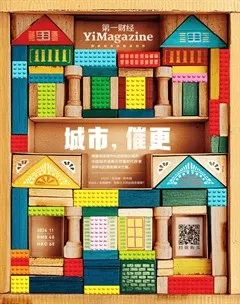黄旺:一个人想得过于透彻,就不可能开启行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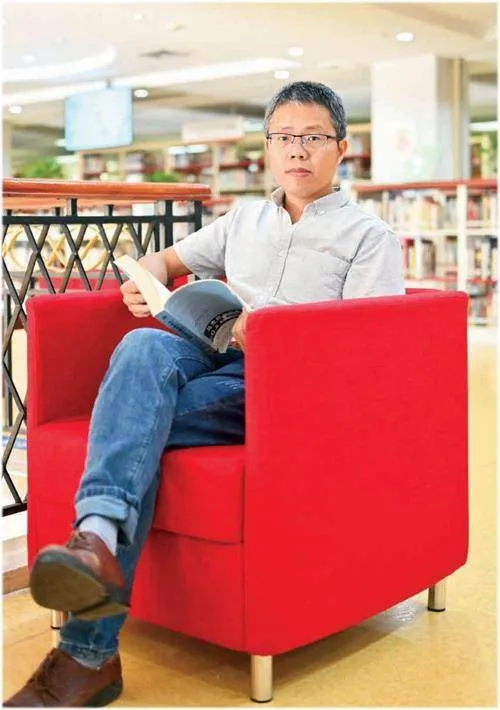
Yi:YiMagazine
H:黄旺
01
Yi:最近有没有遇到什么有趣的观点或者书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H:对于我们这些研究哲学的人来说,其实能够吸引我们注意的新东西并不多。与能研究自然科学这些学科的人不同,他们可能需要紧盯新的进展和前沿,研究哲学更多的是关注一些永恒和古老的问题。因此,最近几十年出版的书籍,尤其是一些二手著作,通常只是作为研究参考。真正打动我们的,还是那些经典著作。
最近让我觉得有意思的书是柄谷行人的书,他有两本书我看了之后觉得很有意思。一本是《力与交换模式》,另一本是讨论康德和马克思的著作《跨越性批判》,探讨世界历史和民族国家等问题。他重新思考的框架非常有意思,对世界的理解和解读也很有启发性。尽管论点有不少漏洞,很多内容也经不起推敲,还是能给到我们一些新的视角,因此我个人还蛮喜欢的。
02
Yi:一个擅长现象学方法的哲学学者在日常生活中会不会有什么不一样?比如,交谈的特性、分析问题和做事的方式等。
H:现象学与其他哲学流派之间的差异并没有那么大。只不过,现象学更强调从事实和现象出发,基于直接感知的事物来做哲学探索,其他的流派可能更多从已有的理论出发。这种方法上的区别并不算特别重要。哲学的思考方式与其他学科的不同在于它以彻底和整体的方式来思考世界。哲学家面对任何问题,首先会问这个现象的前提是什么。很多我们认为理所当然的事物,其实都有潜在的、未被反思的前提,而这些前提可能是成问题的、过时的,甚至需要被超越。所以你会发现跟做哲学的人聊天,他不会被你牵着鼻子走,他们总是会反思和追问你——这个东西怎么来的,凭什么作出这样的判断——总是有一种怀疑的眼光。在分析问题和做事的时候,这种习惯可能会带来更宽广的视野。
03
Yi:如果读者没有接触过现象学,有什么方法能够快速让他们感知到现象学的方法和视角?他们可以如何将“现象学之眼”运用到生活中?
H:理解现象学并不需要接触复杂的哲学术语或专门的理论,关键在于保持对事物本身的敏感性。简单来说,就是不要成为一个唯心主义者,而是做一个真正的唯物主义者。现象学家的理想形象可能可以类比为婴儿,因为他们以全新的眼光看待世界,不会将任何事情看作天经地义,而是从事物本身出发,避免被已有的概念和理论误导。许多人思维僵化,特别是一些老年人,他们往往坚持已有的观念,忽视与之相悖的事实。这种对新事物的无感是与现象学相违背的。现象学有个口号就叫“面向事情本身”。举个例子,我记得我在读本科的时候,那时候是2001年左右,遇到一位北大的文学教授来学校做讲座。讲座是两点半开始,但是那天下午非常炎热,大家都在树荫下等候。到了一点左右,开始有人到门口排队,大家也纷纷跟着排队,最终大家不得不在烈日下暴晒。当时我是有些不满的,如果没有人领头的话,大家原本都可以坐在阴凉的地方等待。这个现象很有趣,但当时我没有进一步反思。很多年后我听到“内卷”这个词,突然意识到其实事情本身早已显现,只是我没有敏感地察觉和理解。
如果你能对一个事物敏感,能够赋予它一种新的形式或者概念去解释,让它呈现出来,那么它就向我们显现了。所以,以现象学的方式看世界就是尽可能地看事情本身的显现,而不是让事情本身在一个既定的框架下显现。就好像,这里有个儿童填色图,大部分人都觉得给它填上色就好了,但你仍然看不到事情本身。“看事情本身”就是把一套已经画好的轮廓否定掉,然后你自己根据现实重新构建一个能更好描摹它的轮廓。这是我认为普通人面对生活时应具备的态度。
04
Yi:书里提到,“朋友圈和短视频的真正意义,恰恰在于它是无意义的!对于我们来说,重要的是不要让注意力空闲下来,关键不在于给我什么东西,只要你给我点东西就好。如同一个强自镇定的人,需要随便什么东西来稳定他惊慌失措的灵魂。”对于很多人而言,更深刻地体验时间的流动性可能有些奢侈,毕竟生活已经让他们自顾不暇,他们只是想从无聊信息中寻找一些慰藉。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H:对,我发现有人会说这本书是不是有精英主义的倾向。在某种意义上,这种说法是对的。大家确实想要打发时间,因为生活已经很苦很累了,然后你让我看那么严肃、那么痛苦的东西。我就想寻求轻松,我想消磨时间,这种需求是很自然的,寻求慰藉也是一种正当需求。
那么问题在于什么呢?马克思有一句话,他说宗教是人民的鸦片。马克思和之前的人批判基督教,认为它是一种虚幻的东西,是人民苦难生活的慰藉。这种对宗教的批判是有意义的,这与我的批判相似,但它也是不够的。我会告诉你,你去寻求短视频,寻求那些没有营养的东西,实际上和以前的人寻求宗教这种鸦片是一样的。生活中充满了不幸和痛苦,我当然需要去找一些安慰和调剂的东西,短视频就起到了类似鸦片的慰藉作用。马克思就说,单纯批判宗教、批判意识形态是没有意义的。同样,批判短视频和那些低质量的电视剧也是无效的。你仅仅批判它们多么没有艺术价值、多么廉价、多么利用人的心理,都没有用。因为如果你不能消除现实的苦难,即使没有这些慰藉,人们依然会去寻找其他形式的慰藉。
因此,这样的工作并不是哲学家在纸面上能够完成的,而是需要行动。必须要去改造和改变现实。现在人们为什么对这些廉价的东西有需求,背后当然有资本等复杂原因,但根本原因就是现实的不幸与问题。就好像小孩子沉迷手机,问题不在于手机本身。批判手机和游戏是没有用的,根本问题在于他们的生活。如果一个孩子的生活完全被无意义的刷题和考试占据,他就需要寻求虚幻的慰藉。
如果不去改造现实,让大家的生活充满意义,这种需求就始终存在。有句话说,思考就是抵抗。但单靠思考来抵抗是无力的,必须通过行动去抵抗。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我指出短视频和流行文化存在的问题,这只是一个前提,并不是最终答案。
05
Yi:从这个问题延伸出来,能看出哲思容易给人带来痛苦,很多人宁愿当“快乐的猪”。你怎么看人应该在哪种程度上保持对自身的觉察?
H:我认为没有绝对的尺度,应该寻找适合自己的方式。只要不走向极端就可以。一个极端是完全没有觉察,浑浑噩噩地活着,就像苏格拉底所说的那样,未经审察的生活不值一过,与动物没有什么区别。另一种极端,比如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地下室手记》中地下室人的形象,过度反思,导致失去行动能力,这也不对。过于清醒或者沉迷反思而没有付诸行动,也是不可行的。
我想说的是,行动总是带有盲目性,所以不要害怕一定程度的盲目性,生活就是要在缺乏充分准备和完整信息的情况下去冒险。正是某种盲目的冲动才能带来创造。如果一个人想得过于透彻,就不可能去做。对自身的过度觉察容易导致哲学上的极端倾向,过于理性主义,但人本能的东西是无限丰富的,超越了个体的理性反思。我们行动中的盲目性并不一定是坏事,不要害怕,要接纳盲目性。
个体的理性反思能力常常是有限的。反之,你的本能和内心声音、盲目的行动,往往是更高层次的理性。比如你站在悬崖边会感到恐惧,这种恐惧是本能,实际上它是比我们的反思更高级的理性。但盲目性有可能不尊重现实,因此在当下的处境中也并不是最好的选择,你需要理性来辅助判断。就好像走玻璃栈道时、站在悬崖边时的恐惧感是本能的,但这种恐惧没有道理,应该用理性去消除。就像康德讲的,“直观无概念则盲,概念无直观则空”。你不能只依赖概念,也不能只依赖直观,二者结合起来是比较好的。
06
Yi:“我有一种可能十分偏执的审美倾向:我喜欢自然而原始的东西,而讨厌人工的整齐划一的东西……”该怎么理解人类对于“整齐划一”的心理需求?欣赏丰富、无序是人的审美天性,还是一种知识的造物?
H:我觉得对整齐划一的心理需求,其实简单来讲就是人寻求安全感和依赖心理。这种整齐划一的美学就像是一个人需要别人安排好他的生活,让别人告诉他这个世界是井井有条的、富有稳定感的、可预测的,这样他才会觉得安心。如果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皇帝或君主,他就会觉得惶惶不安,就像冬天里没有戴帽子一样。他一定要有人管着他,给予他方向,就像把已经嚼好的食物喂给他一样。整齐划一的美学在于别人已经消化了这个世界,并将它呈现出来。这是一种普通人的天性,他们不想承担责任,也不想做智力上的努力,只想获得一种安全感和舒适感,可以看作是人的天性或懒惰的表现。对丰富和无序的欣赏,更多是一种精神的创造。如果这样讲的话,后者可能确实存在一种精英主义的倾向,这些人总是会从无序中创造秩序,而不是等待别人给予他一个贫乏的世界。
07
Yi:你如何理解“时间河流”这一意象?时间的经验会如何影响个体的选择和行动?
H:我们普通人一般都有一种时间河流的形象,好像在慢慢地走向终点且不断流动,但这其实是一个假象。在时间河流中,年轻时我们充满了无限的未来,觉得未来还很远,这时候可以尝试不同的事情。然而,随着逐渐步入中年或老年,我们开始感受到生命在走向一个终点,时间的有限性会带来一种紧迫感。在做任何事情时,这种时间的有限性会影响我们的选择和决断。这就是为什么我说连续性的时间河流是个假象,实际上,真正重要的是那些决定性的瞬间,这些瞬间能够创造永恒。
在关键时刻获得的东西,会在以后的生命中持续发挥作用。大部分的时间其实可以视为生命中的“垃圾时间”,在这些时刻,生活中并没有充实的、有意义的事情f0879ccb3d791c83968323c42c4f259c填充它,因此好像过了,又好像没过,生活显得虚度。所以,我觉得更应该强调的是时间的断裂和突变,而非它的连续性。比如,人们通常会认为长寿是好的,像是活90岁与活80岁相比,时间生命的长度就更长。但实际上,衡量一个人的生命长度,不是看客观的时间长短,而是看它的丰富性。如果一个人的生命中充满了有意义的瞬间,能够创造出更多的永恒时刻,那么他的生命就是有厚度的。生命的经验丰富度决定了生命的质量。有些人可能活得很短,经历却非常丰富;而有些人可能一辈子在自我重复中度过,虽然活得很长,但没有什么意义和价值。
至于什么是有意义的瞬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意义参照系。在这个参照系中,当你觉得当前所做的事情能够在生命经验中持续发挥作用,那就算是有意义的瞬间。比如,你经历过某个事件,这个事件深刻地改变了你,就像历史的转折点一样,能够扭转你生命河流的方向,这样的瞬间有意义的。
08
Yi:我们欲望的是他人的欲望,你怎么看一个人真正想要和应该要的东西是什么?从你的角度来看,什么是良好生活?
H:这个问题可能没有明确的答案。我也不知道自己真正应该要什么或想要什么。追根溯源,你可能会发现你认为自己想要的东西,最终不过是充当了别的东西的工具。这个问题的一个关键点在于,不要让自己仅仅充当别人欲望的填充材料。如果你只是被动地服从别人的意志,那么你的欲望就会被误导,成为他人的工具。这种欲望就是一种错误的欲望。例如,你想要很多钱可能是因为别人想发财,想要你购买他们的东西。这时候,你被牵着鼻子走了,成了别人意志的单纯质料。相反,良好的状态是从自身出发,你需要审视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么。一般来说,内心给出的答案会比外界的尺度更接近真实。如果你被迫按照社会的标准去生活,感到自己的欲望受到压制,那这很可能是一种不恰当的欲望。但即便如此,追问下去,你内心所想的是否真的就是“应该要”的东西?也不一定。因为很多时候人们会将社会标准内化,导致所欲望的仍然是他人的期望。因此,持续审视和反思自己的内心是必要的。严格来说,这个问题并没有固定的答案,也不会有一劳永逸的答案。因为人是一种永远不满足的动物,任何东西都无法完全满足我们的欲望。如果我告诉你什么样的生活才是美好的,你就会成为填充那种生活形式的单纯质料,然后失去自我。每个人必须自己去探索,美好的生活就是按照自己的意愿塑造自己,成为自己想要的样子。
09
Yi:有什么你觉得被高估的人类美 德?
H:孝顺。对这种美德的过度强调带来深厚的父权制色彩,封建社会中,君臣和父子之间是类比的关系,皇帝和百姓、父母与子女之间的权利义务非常清晰,不孝则不忠,为了巩固皇权所以格外地强调父权和子女对父母的义务。这种结构支撑了“家国天下”的观念。我们社会普遍认同的观念是,孩子出生后就对父母负有债务,这种观念让许多人在一生中都感到难以偿还。这种感觉不仅压抑了人的天性,也使得个体难以真正实现独立与自主。我并非说孝道完全没有意义,我认为它更应当是发自内心的爱,而不仅仅是责任和债务。严格来说,父母在生育孩子时,并不是出于对子女无私的爱,因为此时孩子还不存在,而更多是基于自身的考虑—无论是延续生命、寻求陪伴,还是满足社会期望,父母的动机通常是自我中心的。
因此,父母对孩子的责任是巨大的,孩子对父母的责任则相对较小。如果父母不能很好地承担抚养和教育的责任,那么一味地强调孝道其实是一种不公正的道德绑架。
10
Yi:有什么你曾经相信,但是现在深表怀疑的事情?
H:我想了一下,确实有一些东西让我怀疑,但我不确定是否适合分享。我现在觉得,像“客观的真理”或“历史的正义”这样的概念,可能根本不存在。历史是否真正存在绝对的正义是很难讲的,很多不正义是永远得不到伸张的。除非设定一个末日审判,否则历史充满了大量的不正义。
我们从小接受的教育常常告诉我们“正义只会迟到,但不会缺席”,实际上正义的到来充满了偶然性。当我们讨论某个科学上的真理时,比如某个定理—这个真理是由一个人发现的,并以他的名字命名—似乎在历史上占据了一个牢不可破的位置,但实际情况是,这个过程充满了偶然性,可能另一个人也发现了一个类似的理论模型,但因为在学术竞争中他是个无名小卒而被遗忘。在这样的情况下,选择什么样的理论,可能更多是一个政治斗争的结果,而不是单纯的真理与谬误的对抗。
我在思考过程中意识到,我们曾以为的冥冥之中的正义和客观真理,其实并非如此。人类是充满谬误和有限性的动物,历史的偶然性一直存在。许多伟大的天才被历史淹没,而一些小丑似的人物因机缘巧合在历史上占据重要地位。所以我现在觉得,历史正义和客观真理这些概念是需要重新审视的。而学者的使命就是为历史中那些被压迫、被遗忘的、失语的人说话,去纠正历史中的不正义,从而重新讲述一个更多面、更丰富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