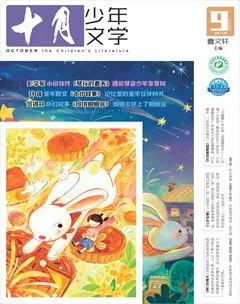七炉故事


七炉是一个茶馆的名字,原本在栖镇旧街。
小时候我经常去七炉茶馆打开水。小镇上的人家是不烧开水的,灶台上备的热水主要用来洗碗。喝开水,一般是让小孩子拎着藤皮暖壶去茶馆的老虎灶上打。
七炉茶馆离我家不远,临街枕河,旁边是西陵桥。坐在茶馆里,但见窗外一片湿润的绿,脚下似有水声,俯身一看,乌篷船吱吱呀呀地从窗下撑过去了。茶馆的店堂不大,拢共摆了七八张桌子,每天清晨都坐得满满的。这个店没有什么招牌,门前连个幌子都没有,但是茶客都叫它七炉茶馆。说是七炉,其实并没有七个炉子,进门可见一个极大的老虎灶,灶面上有几口汤罐,还有一个积锅(在大锅里接上一个木桶,形似蒸笼,用来囤积开水)。老虎灶不烧煤,烧的是糠壳,烧火的阿亨一畚箕砻糠倒进灶口,火势忽地一下蹿上来,轰轰作响,像老虎吼叫,汤罐里的水立马咕嘟地就沸腾开了。小孩子来打开水是不收现钱的,收茶筹子—三寸长的小竹片,烙有“七炉茶馆贰分”的火印,一支茶筹子可打一壶开水,这是茶馆预先卖出去的。
栖镇讲究吃早茶,天一亮,老茶客们起了床,两眼还是昏的,两脚已经习惯地走进茶馆,找到固定的茶座,各人用的茶壶杯盏也是固定的。喝的茶叶都很便宜,七分钱一小包的青茶或者苦丁茶,好一点儿的红茶也不过九分钱,更讲究的茶叶如瓜片、肉桂则是茶客自己带来的。七炉茶馆用的是旧街鹿井里的水,这口井里有泉眼,水质清而滑,用以泡茶,色香味俱发。一盏浓茶浇下去,早到的茶客咳嗽一声,人才算真正醒过来。
比起陶然楼、如意、小桃园这几家茶馆,七炉是比较小的,在店里张罗的只有一两个人。茶馆当家的是三娘娘(我们那里把开小店铺的都叫作当家的),三娘娘虽说当家,却不怎么管事,除了早晚最忙的钟点,她到茶馆里周旋一下,日常的大小事务—烧老虎灶、卖茶筹子、跑堂、挑水,都是堂倌阿亨在打理。一般说来,堂倌大多是嘴巴利索、八面玲珑的,就像样板戏《沙家浜》里的唱词:“垒起七星灶,铜壶煮三江,摆开八仙桌,招待十六方,来的都是客,全凭嘴一张。”不过这阿亨却是个例外,他的嘴巴看上去有点儿倔,一个方下巴,地包天,干什么都像是咬着牙齿在攒劲。有一回我在茶馆门口拍蜻蜓玩(夏天欲雨的午后,河边总有一大群蜻蜓飞舞),一不小心把一个蜻蜓拍进了他挑的水桶里,他气得把一桶水都泼在街上,咬着牙嘟嘟囔囔,险些要骂出来。不过,他也不方便骂人,因为他跟我的外婆是本家亲戚,按辈分,还应该喊我一声舅舅。他当然不会这么客气,只喊我刺毛(小毛虫的意思,他管满街的男孩子都喊刺毛),我们背地里叫他弯扁担。他挑水的扁担是弯的。
虽说不喜欢弯扁担,小学毕业前,我还是天天往七炉茶馆跑,除了打开水,主要是听评书,或者听茶客们闲侃、讲故事。
江南的茶馆大多会兼营书场。茶市既罢,将桌椅稍加调整,空出的地方摆一张围了枣红帷幕的桌子,就是书场了。门口再挂一面水牌,上写“特请维扬吴宝应先生开讲《隋唐英雄传》,是月初五日起风雨无阻”。书场分为下午场和夜场,七炉茶馆只开夜场。开场前,茶馆里头乱哄哄的,有小贩们提着篮子叫卖瓜子荸荠,有老人在极响地吸水烟,还有猫狗在桌子底下钻来钻去。一群半大的男孩子围在书案边,盯着案上的醒木和一把折扇,仿佛看见这扇子在吴宝应的手里,一会儿是秦香莲递上的状纸,一会儿是关公胯下的赤兔马,一会儿又是李元霸的金锤,端的是呼风唤雨,变化无穷。很快,跑堂的上来给先生的盖碗里倒上茶水,拍一下醒木,“开书哉!开书哉!”于是小贩们收起生意,书台上的小孩也被轰了出来。
听书,是要收费的。三娘娘坐在门口的矮凳上,脚边放一个针线篮子,想听书的往篮子里放一角钱,她笑一笑,放人进去,继续挽着毛线团,不耽误手里的活计。未成年的孩子听书半价,五分钱就够了。我则是连五分钱都不用掏,只需要装作找阿开写功课的样子,问:“三娘娘,阿开在不在?”
三娘娘挪开针线篮子,“在,进去吧!”
阿开是三娘娘家的小孩,比我大两岁,跟我在一个班上,经常一起趴在茶桌上写作业。夜里,他总是在茶馆里忙活。我径直走到老虎灶后边,看见阿开在打瞌睡,橘红的灶火映着他翘起的鼻头,鼻头上有三粒亮亮的汗珠—他的鼻子爱出汗,并且总是三粒。我拍醒他,他揉揉眼睛,把小板凳让给我坐,拎起灶台上的铜壶,去书台那边续茶水,突然回过头来,对着我指一指第二张桌子,画了一个圈。
我晃晃两个指头,表示马上过来。
这是我们的对话方式。他的意思是左侧第二张桌子要加一个茶盅,让我帮忙送过来,记得在茶盅里搁一个橄榄。阿开习惯于用手说话,据说两三岁的时候他发过一次高烧,嗓子就哑了。不过他的耳朵还算灵敏,能在课堂上正常听讲,甚至能听出知了在哪根枝丫上叫—夏天,我们经常去粘树上的知了。他捉知了可比我们厉害多了,有两回我看见他扛着竹竿刚走到梧桐树下,一树的知了突然就安静下来。
跟阿开在一起玩,既省钱,还能听到一些逸闻趣事,对我是一种懵懵懂懂的文学启蒙。常在七炉说评书的先生有两位,一个是柳醒民,另一个是吴宝应。这两位都是扬州人,风格截然相反,人们常说“柳书一段情,吴书一股劲”。 柳先生擅长说《聊斋》、《西厢》和《再生缘》,故事里多的是才子佳人,啼笑姻缘。他是个沉静的人,在书台上噱弹唱演,讲究草蛇灰线伏脉千里,下了台一拱手,转身就走,白天几乎见不到他。吴宝应好酒也好动,他会讲《隋唐》、《水浒》、《包公案》以及《杨家将》,讲得最多的是《武松打虎》。很多年以后我还在小说里写过这个人:“评书里说三碗不过冈,吴宝应是三碗才开讲,喝酒是打虎的前奏,虎打得痛不痛快,要看酒喝得痛不痛快。吴宝应眉眼迷迷糊糊的,睡不醒,酒一下肚,醒木一拍,武松的江湖胆、英雄气立马全醒过来,活该老虎要倒霉了,那一顿拳脚大开大合,荡气回肠……”
这个人在我的童年时代是真实存在的,他常年在外行走江湖,见闻多,三教九流,风水八卦,以及《搜神记》《子不语》之类的志怪小说他都知晓一二,在茶馆里讲起各种见闻,跟说评书一样,起承转合,抑扬顿挫,绘声绘色。他往茶桌上一坐,旁边围的都是人。
一天,我去七炉打开水,看见吴宝应正与茶客们摆弄一个茶壶,小小的一把紫砂,荸荠色,形状也有点儿像个荸荠。吴宝应说这里头有个典故,跟《长生殿》里的杨贵妃有关,传说杨贵妃爱吃荔枝,还爱喝南方的马蹄爽(荸荠的汁水),唐明皇就命宫廷造办处特制一对荸荠壶,专门盛放马蹄爽。工匠们发了愁,哪里去找能烧紫红器皿的泥料呢?恰巧造办处总管身边有个伶俐的小书童,名叫供春,他发现金沙寺里一个老和尚会做紫色陶器,用的什么泥料老和尚却秘不外传。和尚制壶后常在大缸里洗手,这供春心思灵巧,就用缸底沉淀的细泥烧制出了这对荸荠茶壶,成为名满天下的供春壶。
如今且不说这壶,就是喝茶的杯子也大有来历—吴宝应又拿起一个精致的小茶盅,递到大家眼前转了一圈,杯口略有残缺处,镶了两朵银制的梅花,另有四个字:陌上花开。说这也是唐代的东西,是西湖边的名伎苏小小留下来的,相传苏小小与宰相之子阮郁一见钟情,分别之时曾以此杯饮酒饯行,一时伤心将杯子摔破,阮郁为了安慰苏小小,将杯口用梅花镶补好,并约定来年陌上花开之日,便是两人重聚之时。
事情说得有鼻子有眼,茶客们听得啧啧称奇。吴宝应又说,大凡非常之物混迹于市井,必得有非常之人才能识得,若不是他吴宝应,这两样东西至今还埋没在陈观年的铺子里。陈观年是无锡开古玩铺子的,跟吴宝应是老熟人。几个老茶客小心地借这荸荠壶泡了一壶茶,闭目细品,愈发觉得滋味不同以往,便争着替吴宝应把茶钱付了。
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也一直认为吴宝应是非常之人,身边随手一摸就是宝贝,长大之后读过书,才知道这些故事是吴宝应在信口胡吹,或者说是即兴创作,因为供春壶最早造于明代,至于那个杯子上的字句,出自五代时期吴越王钱俶写给妻子的信“陌上花开,可缓缓归矣”,跟苏小小扯不上关系,况且苏小小也不是唐代人。
这把荸荠壶后来让阿开摔破了。吴宝应很喜欢逗小哑巴开心,教他做柳笛,从河边折一根三寸长的柳条,捋掉柳叶,把树皮从枝条上拧下来,像一个空笛管,末端捏扁,刮薄,含在嘴里,就能吹出清脆的笛音。一根小小的笛管,他能吹出《小放牛》《四季歌》《边疆的泉水》等一大串曲子。他还教了阿开几手茶艺功夫,说阿亨续茶只会“三点头”,左手掀起壶盖,右手的铜吊子一抬,点个三下,开水就灌满茶壶,最多做到滴水不漏,跟扬州茶馆的茶艺师比起来,那就是小巫见大巫。人家有名的茶艺师傅续水用长嘴铜壶,续水犹如苏秦背剑,又如高山流水,讲究一个翩若惊鸿,矫若游龙……吴宝应说得热闹,到底应该如何背剑,他用扇子比画两下,其中门道也不甚了了。偏偏抵不过阿开的好奇心,悄悄地折了一根柳枝,插在铜吊子上冒充长嘴壶,抽空在茶馆里练习了好久。这天,他特地给吴宝应表演了一下,手提铜吊子,一翻身,哐当!搁在桌边的那把荸荠壶应声落地,碎成八瓣。
三娘娘连声地叫哦哟哟不得了,生怕吴宝应发作。吴宝应倒也不心疼,大方地摆摆手,只让阿开去街对面的四时春面馆,给他叫了一碗三鲜面。
不久吴宝应回了扬州,给我们讲故事的主要是张汤罐了。
七炉茶馆和包百味酱菜店中间有一个小人书摊子,靠墙放着几排窄窄的旧木橱,还有几把零乱的小竹凳,木橱里排满了巴掌大的小人书,花花绿绿的,煞是撩人。小人书也叫连环画,可看可租,在摊边看一分钱一本,租回家看三分钱一本,看书的有大人也有小孩,以孩子居多—这大概就是小人书得名的缘由。小人书会讲故事,评书、电影和民间传说里的故事,书里应有尽有,比方说吴宝应讲的《隋唐》《杨家将》都是成套的连环画。
摆书摊的老头就是张汤罐。这老头七十多了,长得瘦巴巴的,弓着腰,像一条老丝瓜。他总是套一件夹袄(夏天也穿),戴一副发黄的老花镜,身上散发出一股药罐子的味道。别看他一副病恹恹的样子,眼睛却尖得很,哪个看书想混赖(比如两个家伙看完了手里的书,偷偷交换,这样看两本只付一分钱),哪个往怀里揣书,一切小动作都逃不出他的掌握。有一阵子,我、毛豆还有小明眼馋小人书又没有钱,就想出一个派代表的办法,轮流凑一两个钢镚镚,派一个人去摊子边看书,看完了再把故事传达给大家。传达的故事毕竟没有原版的好看,毛豆灵机一动,瞅见画得好看的页面打算撕下来,拿回来给我们分享,谁知刚动手就被张汤罐逮住,差点儿把耳朵拧掉了。
不过,张汤罐跟阿开的关系还不错,他有一个大罐头瓶,阿开每天给他送两瓶子免费的茶水。夏天的午后,看书的人少,张汤罐有时也挪步到七炉这边来坐坐,戴上老花镜,补破损的小人书,该缝的缝,该粘的粘,缺页的地方,他裁一张大小相同的纸,拈起细小的毛笔,重新补画上去。我和阿开好奇地凑上去看,他补的是《十五贯》,这本小人书我看过,是一个古代清官破案的故事,缺的这一页是苏州知府况钟假扮算命先生,在城隍庙测字,智逮真凶娄阿鼠。但见张汤罐随手勾了几下,纸上渐渐地有门有墙,有了城隍庙,接着娄阿鼠的嘴脸开始浮现出来,活灵活现,跟书里的人物差不多—嘿,想不到这老头儿还有这么一手!比我们学校里教美术的章大桥厉害多了,章大桥用炭粉画的人像,一个个笑起来都是歪嘴巴。
接下来越画越细,帘幕、案台上的香烛还有人物衣服上的花纹,要慢慢填充,张汤罐的手开始打颤,他摇摇头,把笔搁下了。我趁机翻着补好的小人书看,阿开却拿起笔,学着张汤罐的样子描书上的图画。老头儿看了没吭声,还点了点头。
这以后,张汤罐时常送几本小人书给我们看,说先看故事,再看人像和布景,看熟了可以照着描。我美滋滋地看了几次便宜书,发现他每回拿来的书都是同一个人画的,比方说《李自成》、《郑和下西洋》和《渔岛怒潮》,作者是丁世弼,而《翠微亭》和《暴风骤雨》都是施大畏画的。我用半透明的竹纸蒙在书上,依葫芦画瓢,描完一页先给张汤罐看。老头儿说不对,画小人书要定好焦点,先勾出人像,再把纸面划分为四个区域,从左到右依次着笔,画面才有层次,不至于一塌糊涂。
过了大半年,我把书摊上成套的《三国演义》、《儒林外史》和《岳飞传》都看完了(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全套六十本的《三国演义》我尤其喜欢,后来自己攒钱买了一套),故事记得很熟,画小人书的水平却没有多少长进。
相比之下,阿开的进步很快,他是学什么像什么,渐渐地能够给张汤罐打下手,两人面对面趴在茶桌上,老头儿画张果老,阿开画旁边的毛驴,老头儿画山,阿开画山上的亭子。张汤罐很满意,兴头来了也跟我们讲讲连环画的掌故。他说自己四十多年前曾在上海画过连环画,那还是旧社会,画小人书都是师傅带徒弟,而且是流水作业,先由师傅“拗壳子”(画人物),再由助手“着布景”(配景),学徒“着花头”(填衣物纹饰),最后是编故事的写口白,如此周转,一幅图画就完成了,学徒们就从这周转里学到了本事。
他还说不要小看画小人书的,行行出状元,京剧有四大名旦,画小人书的也有,像赵宏本、陈光镒、沈曼云、钱笑呆就是画小人书的四大名旦—钱笑呆有咬笔头的习惯,画完半本书,出门吓人一跳,牙齿全是黑的!这事他亲眼见过。他还见过海派美术名家程十髮,程先生也画过小人书。他有两本程十髮画的《画皮》和《野猪林》,用油纸包着,轻易不给人看。
这些故事我听得津津有味,阿开不管,他只顾低头画猫,鼻头上三粒汗珠闪闪发亮。他喜欢施大畏和贺友直画的小人书,贺友直笔下的布景经常是乱糟糟的,乱得生动而有趣,猫卧在桌子底下会打着哈欠挠痒痒。
张汤罐叹了一口气,摸摸阿开的脑袋,可惜了,要不是个哑巴,将来没准能考上美术学校,凭一支笔换饭吃。
小学毕业之后,阿开没有读初中,在茶馆里记账,做堂倌。他还是喜欢画画,在老虎灶的墙边画了一幅张果老骑驴唱道情,褐色的线条加点点滴滴,像是蘸了酱油用刷子抹上去的,细看,人物袍袖飞扬,形象朴拙,毛驴只用重彩点出一头四蹄,腿脚简约得像草棍,很像施大畏的风格。
有一年五月,我还吃过七炉茶馆做的槐花饼,这种点心的原料采自树上新鲜的槐花,用糖腌制起来,再以油面做皮,裹上槐花,拍进一个木雕的圆形模具,出炉的槐花饼热烘烘的,入口甘甜,沁出春的气息。饼皮上有个闭着一只眼大笑的娃娃头,格外可爱。
制饼的模具,大概也是阿开刻的,我认得他的手笔。
又过了一些年,我离开了栖镇。那时,七炉茶馆已经歇业,街边的小人书摊也消失了。
时光荏苒,如白驹过隙,到了2010年,我去锦溪旅游,遇见一个在柳树下吹笛子的中年人,曲调是《小放牛》,他吹得很入神,鼻头上有三粒汗珠,依稀是七炉茶馆里的阿开的模样。
我忍不住上前拍拍他的肩,他放下笛子,问:“有什么事?”
没事。我抱歉地朝他笑笑,快步走开,忽然觉得眼里有一点儿涩,也许是秋风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