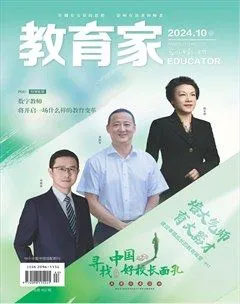科技伦理教育如何“入心”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强调,“深化科技评价体系改革,加强科技伦理治理,严肃整治学术不端行为”。科技伦理是指在科学研究和技术开发等科技活动中,科技工作者及其共同体需要遵循的价值理念和行为规范,是促进科技向善、增进人类福祉、推动科技事业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目前我国很多高校已开设不同形式和内容的科技伦理课程,主要面向理工科专业学生讲授科技伦理知识和道德规范,一些相关教材和案例集相继出版。与此同时,有关科研管理部门针对在职人员的科技伦理职业培训和专题宣讲也纷纷开展。这意味着,科技伦理教育如何“入脑”的问题已经基本解决。接下来,要进一步解决的是如何“入心”的问题,这可能会面临更大挑战,需要认真加以探索。
科技伦理教育“入心”的标准
科技伦理教育需要贯彻“知行合一”的原则,只有“内化于心”,才能“外化于行”。中国自古以来就有主张“心之官则思”的文化传统,至今人们仍然习惯讲“用心”思维和做事。然而现在人们对“心”的理解和运用往往约定俗成、心领神会,缺少专门反思。人们现在讲的“动脑”,主要指运用逻辑分析、规则意识和工具理性;而“用心”则是指一种整体性的、注重有机联系、强调直观体验的思维活动,具有知情意相贯通的特征。当思考真正“入心”的时候,来自外界的知识和信息一定会引发人们内心深处整体性的状态变化,发现自身与外部事物之间的更多有机联系,增强切身体验的深度和广度,由此形成明显的情感反应和明确意向,然后才有可能指引自己的行动,产生“知行合一”的效果。
在教学活动中,可以从以下方面考查是否产生了“入心”的效果,而这种效果对于学生未来在工作岗位上践行科技伦理原则和道德规范将有着重要影响。
其一,学生能否根据学到的科技伦理知识和典型案例,主动发现现实生活中存在的新的典型案例,并从利益相关者角度提出自己的思考和见解,指出这些事件中哪些人在什么问题的处理上违背了工程伦理原则和职业道德规范。由于这些新案例刚刚被报道,尚未形成科技伦理方面现成的标准答案,所以需要学生自己“用心”去思考,否则就不可能提出较为深刻的见解。
其二,学生能否反思自己以往在涉及有关科技伦理问题上的模糊认识甚至错误行为,意识到这些问题的学术道德属性并自觉改正。这些往往属于学生的隐私行为,如果自己不讲出来,别人可能并不了解。能够对这些事情深入反思需要真正“动心”,才能触及其内心深处的价值观和伦理意识,并使其发生改变。
其三,学生能否在面对复杂的科技伦理难题时学会道德推理和论证,明确意识到在哪些场合需要体现出社会责任感,并最终做出合理的道德决策。学生通过讨论提出种种解决方案,设身处地思考相关的利益冲突和行为责任,逐渐引发内心深处的观念转变,才能提出积极、稳妥、周全的对策。
让科技伦理教育“入心”的举措
在教育方式上,要改变只是在课堂上单向传授知识、宣讲科技道德规范的模式,使学生们意识到科技伦理课程与专业科技知识课程有明显区别。科技伦理课程的教学内容应该适应知情意相贯通的要求,力求生动活泼、声情并茂、富有启发性。现在的科技伦理教材包含不少典型案例分析、二维码形式的音像资料、思考与讨论题等内容,有助于创造知情意相贯通的环境。但是,教师在讲授时不能仅停留在让学生了解书本内容的层面上,而要让这些内容“活”起来,创造师生互动的氛围,一起讨论和交流对这些内容的体验,包括对相关知识的理解、情感反应和意向变化。此外,还要不断引入新的案例分析、音像资料和论题,最好是能引起强烈情感共鸣的,或者有相关科技人员亲身参与的重大事件。可以设想,如果一位讲授化工科技伦理的教师曾亲身进入过重大事故现场参与处置危险化工产品,他再来讲工程伦理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形;当青藏高原科考人员在恶劣环境下一点一滴搜集原始数据后,再来讲科研伦理和学术道德,肯定会对学生产生强烈的感染力和震撼力,他们的道德情感就更容易生成,并不断加深。
在教学方法上,应该通过多种渠道增强学生的整体认知能力和体验效果,使知情意相贯通有流畅的途径。课堂上的知识讲授无论怎样生动活泼,引发的整体认知、情感共鸣和意向转变也仅是初步的,缺乏真正身临其境的感受。我国的科技伦理教育有必要借鉴西方“田野哲学”的研究和教学方式,尽可能为学生们创造参与现实情境的机会,比如到工科实验室、生产车间、施工现场了解工程伦理的现实问题,到环境污染处理的现场了解环境伦理的现实问题,通过回顾处理学术不端事件的全过程了解科研活动的实际伦理问题,等等。如果始终限于在课堂上讲授科技伦理知识,走不到课堂之外,想达到“入心”效果是很难的。提出“价值敏感性设计”(value sensitive design)的美国华盛顿大学教授巴特亚·弗里德曼就特别强调,道德教育需要道德情感的支撑。从“知行合一”角度培育学生道德情感,需要使学生学会设身处地地思考和感受具体的道德情境,通过了解品德高尚的科学家和工程技术人员的先进事迹,从内心深处领会道德情感的力量。这也就意味着需要从科技伦理教育的角度,不断发现和宣传具有强大感染力的科技界道德楷模的事迹,使学生学习有榜样、行为有参照。
在考核标准上,科技伦理教育的“入心”效果应该是分层次、分阶段的。在学校教育阶段,如果学生能够根据学到的科技伦理知识和典型案例,总结出现实生活中新的典型案例,并进行准确分析;能够深刻反思自己以往在科技伦理方面的模糊认识和错误行为,并给出纠正措施;能够对复杂的科技伦理难题及时进行道德推理和论证,做出正确的道德决策,就可以认定产生了一定的“入心”效果。学生毕业之后,如果能够在科研、生产、工程实践中切实履行科技伦理原则和道德规范,体现出明显的伦理意识和社会责任感,才可以说充分达到了“入心”的效果。如果某一高校里的某一门科技伦理课程能够使学生普遍在“入心”的层次上有所收获,特别是他们毕业后在科技伦理实践中进步显著,才可以说是实现了科技伦理教育“入心”的目标。
为了保证科技伦理教育产生“入心”的效果,还需要在师资培训、教学管理、教育评估等方面做必要的配套改革。当前,在科技伦理教育的教师队伍中,具有哲学专业背景的教师往往缺少科学技术与工程专业实践的亲身体验,而具有理工科专业背景的教师往往不大熟悉知情意相贯通的认知规律和文化氛围,两者的密切配合才能够实现科技伦理教育“入心”的目标。因而,在科技伦理教育师资培训中,需要这两类教师交流合作经验、配合模式和具体途径。
在科技伦理教育管理和评估中,有必要给予“入心”这一要求更多的重视,鼓励教师总结这方面的经验和体会,创造更多交流机会,普遍提升科技伦理课程的社会效益。实际上,能够防范重大技术风险、化解重大工程事故的根本因素,往往取决于关键技术岗位上少数人的道德敏感性和社会责任感,要保证这一因素发挥作用,科技伦理教育必须“入心”。如果这样来看“入心”的价值,那么在教育管理和教育评价中赋予科技伦理教育更高的权重、给予更多的支持,无论从社会生活的健康发展还是教育事业的使命来看,都是极为必要的。
科技伦理教育的“入心”要求,体现了科技伦理教育的中国文化特色,对世界上其他国家的科技伦理教育也具有重要的启示性作用。西方发达国家的科技伦理教育在培养学生的伦理意识和社会责任感方面有明显成效,涌现出了一些坚持科技伦理原则和道德规范的典型案例,对我国的科技伦理教育有着重要的启发和借鉴意义。同时,很多国家也出现了不少违背学术道德、科研伦理、技术伦理、工程伦理、环境伦理的典型案例,表明其科技伦理教育中还存在一定问题,包括忽视整体性、有机性、体验性等弱点。通过分析这些案例有助于他们更深入地理解科技伦理教育“入心”的价值。关于科技伦理教育“入心”的研究,还有很多具体问题值得深入探索,需要科技伦理学界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共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