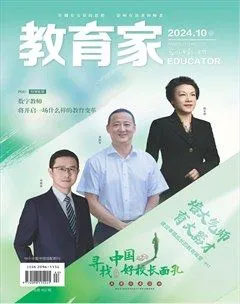构建教育大模型要创新驱动而非盲目扩张

随着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的迅速演进,全球掀起了大模型构建的热潮,我国多所高校也纷纷参与其中。例如,清华大学联合企业研发了GLM系列基础大模型,并成立了人工智能研究院基础模型研究中心,积极推动了大模型技术在教育、医疗、金融等领域的应用。其他高校也计划或正在研发具备自身特色的教育大模型。这一浪潮不仅推动了技术创新,也培养了相关领域的人工智能人才。然而,教育大模型的构建有其特殊性,需综合考虑教育规律与技术成本,避免盲目发展。
构建教育大模型的必要性
在当前的人工智能时代,大模型的研发主要集中在通用领域,国内外陆续出现了GPT-4和GLM-4等通用基础大模型。通用基础大模型具备强大的泛化能力,能够理解和生成多模态信息,并在多个领域和任务之间实现迁移与应用。
然而,尽管其具备一定的跨领域适应能力,通用基础大模型仍无法完全替代教育大模型。教育领域有其独特的复杂场景,要求深入捕捉学习者的认知过程和教学互动的细节,强调个性化教学并符合教育教学规律,且涉及伦理与价值观的传递。此外,通用基础大模型也难以完全满足教育数据的隐私保护与合规性等方面的要求。相比之下,教育大模型能够针对这些特殊需求进行构建,提供更精准的个性化支持和更深入的教学分析,确保符合教育规律和要求。因此,尽管通用大模型能力日益增强,在教育领域仍需构建教育大模型以实现更佳效果。
具体而言,教育大模型需要收集并整合通用领域与教育领域的多模态数据,这些数据包括但不限于课堂音视频、作业与试卷、慕课内容、论坛讨论以及教学理论和学科知识,这些多模态数据是构建教育大模型的信息来源。在此基础上,再通过不同模态数据与特定模型框架的结合,采用自监督学习等方式进行预训练,从而形成教育大模型。与传统模型相比,该模型能够更深入地理解教学资源、教学对象和教学过程这三个核心要素。教育大模型的核心能力包括理解教育资源的属性、关联与语义信息,识别教学对象的行为、语言与意图,并解析教学过程中各类互动、活动和目标。最终,教育大模型能够为教学平台和系统提供自动生成教学资源的能力,为线上线下学习者提供个性化学习支持和互动体验,同时为教师和教育管理者提供教学设计和决策支持。通过这些方式构建出教育大模型,可以更好地服务于不同学段和教育场景,显著提升教学质量和学习效果,并支撑多类教育智能化服务和系统。
构建教育大模型需要大量技术与成本
构建教育大模型的过程可分为几个关键步骤,每一步都涉及不同的技术要求和资源投入。首先,是数据收集与处理,这是构建大模型的基础环节,涉及大量教育数据。这些数据来源广泛,数据的质量和有效性对模型的构建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其次,需要选择合适的深度学习模型架构,并通过堆叠大量神经网络层来提升模型的表示能力和泛化能力。在训练过程中,需要大量数据进行迭代优化,持续调整模型参数以最小化损失函数。最后,在模型训练完成后,还需对其进行不断调整与优化,包括采用更先进的优化算法和改进网络结构与参数,以确保模型在不同教育场景中的适用性。
而构建教育大模型的成本首先体现在其庞大的计算资源需求上。深度神经网络的训练需要高性能的GPU或TPU集群,训练硬件的购置费用惊人,且运行和维护成本也非常高。例如,大规模训练大模型的计算集群在运行过程中耗电量巨大,完成一次基础模型训练的电费往往高达几十万元人民币甚至更多。其次,存储资源开销巨大,教育大模型需处理和存储海量的多模态教育数据,包括训练数据、模型参数及中间结果,对存储系统的容量和读写速度提出了极高要求。再次,人力成本同样占据了相当大的比例,构建大模型需要由数据科学家、机器学习工程师和教育领域专家组成专业团队,团队的薪酬、培训及协作成本不菲。最后,持续优化也是一项长期成本投入,涵盖算法改进、模型调整、性能监控和问题解决等多个方面。这些都需要持续的人力和物力投入,才能确保所构建的大模型能够在教育领域落地应用并达到预期效果。
构建教育大模型需科学规划和引导
统筹规划与多方协同相结合。构建教育大模型是一项复杂的系统性工程,涉及高昂的软硬件成本和庞大的人力投入。因此,需要在国家层面进行统筹规划,科学合理地推进教育大模型的构建。教育与科技管理部门在这一过程中不仅扮演着引领和规范的角色,还肩负着政策制定、资源配置和监督落实的责任,以确保教育大模型的构建与国家的教育方针、发展战略及实际需求紧密结合。这一规划过程需要深入分析不同教育阶段的特点和需求,例如基础教育侧重于知识的普及与基础技能的培养,职业教育注重技能实训与就业导向,而高等教育则着重于科研创新和专业人才培养。因此,可以分别构建满足不同教育层次需求的教育大模型,但应避免在数量和规模上的盲目扩张,以防资源浪费和低效重复建设。
在构建教育大模型的过程中,需鼓励高校与企业协同推进。高校拥有丰富的教育资源和科研能力,可以参与教育大模型的基础研究、技术开发和人才培养,并为模型开发提供理论支持。企业则可以借助其资本和技术优势,推动大模型的研发进程、产品化和市场化。通过技术创新,企业还能进一步利用高校的科研成果,优化和升级教育大模型的功能,满足市场需求。此外,教育大模型的构建需考虑教育的多样性和地域性,应鼓励地方政府、一线学校及社会各界共同参与,形成多方协同、共建共享的格局。例如,不同地区可以提供其典型的教育场景数据和教育服务需求,在构建教育大模型的基础上,进行适当微调和优化,从而确保其能够服务于不同地区和不同特点的教育对象。
数据安全与伦理规范建设相结合。教育大模型的构建需要大量教育数据,因此在数据确权和脱敏的基础上,需要建立基础教育领域的数据资源开放共享机制,以提供可靠、真实和准确的教育数据,打通教育数据使用的“堵点”。同时,严格规范教育数据的采集、存储和使用,保护学校和教师的数字资产,并强化“知情——同意”原则,以保障师生的隐私和信息安全。此外,教育大模型依赖无标注数据进行自监督学习,其训练过程中难以避免产生数据偏见、知识产权纠纷和计算准确性等问题。因此,在应用于教育时,必须从公平性和可解释性等方面进行风险评估,并确保模型输出内容的科学性和准确性,以避免价值观偏差。
另外,基于教育大模型的人工智能产品可以为教学提供辅助,应明确其在教育中的应用边界,制定相应的规则、标准和责任,确保合法合规、伦理有序。例如,教师或教育管理者应监管模型的使用,特别是在人机协同和智能教学辅助中,要明确功能限定,避免模型影响学生的独立思考和认知能力。同样需要注意的是,教育大模型的构建是一个长期且复杂的过程,需要持续进行跟踪研究和评估,以确保其在实际教育教学应用中能够切实提高教育质量和效率。
充分利用现有大模型推动教学与科研。目前,国内外开源的通用领域和跨领域的大模型逐步增多,并展现出其在多任务上的强大泛化能力,尤其在多模态复杂信息的理解和推理上取得了显著进展。因此,应该鼓励国内高校科研团队通过下游任务的适配与微调等方式,充分利用现有的大模型来解决实际问题而非从零开始构建。例如,国内高校可以结合自身学科的特点和科研需求,对现有大模型进行低成本的微调,进而构建适合特定专业(如法律、医疗、公共管理等)的技术解决方案和科研服务。通过这种方式,国内高校可以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充分利用前沿人工智能技术提升其教学与科研工作的智能化水平,满足相关学科甚至跨学科的实际需求,提升教学与科研的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