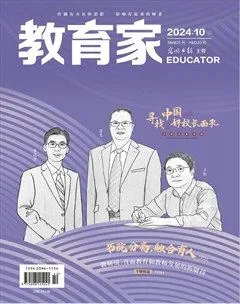外部赋能,领航教研员专业成长


每一位教育者的专业成长均离不开外部的支持与助力,教研员群体自然也不例外。针对教研员专业成长道路上遇到的各类挑战,本刊编辑部邀请相关领域专家,共同探讨如何为教研员的专业成长提供有效支持。
罗生全:一是大量事务性工作挤占专职教研时间。作为教育管理的“中层地带”,教研员“对下”需服务中小学校及教师,“对上”要服务教委、教体局、教育局等教育行政部门,“横向”需配合考试院、评估院等部门的工作。基于行政身份与专业职能的双重嵌套,教研员需承担大量非本职性的工作,成为教育行政部门的“机动部队”,如负责起草相关通知文件及领导讲话稿、承办教育展演活动、被借调完成各项工作等,难以静心开展教学研究。
二是混同教师职业晋升机制导致专业成长动力不足。当前,我国尚未建立专门的教研员准入、晋升、发展及退出机制。教研员在职业晋升通道上面临着诸多限制。例如,在职称评聘方面,教研员的各项条件往往参照教师标准执行,这导致与同等条件的教师相比,教研员在各方面的待遇上普遍一般,容易打击他们的工作积极性。若教研员缺乏明确的专业发展规划,则很容易迷失职业发展方向,甚至可能产生职业倦怠感,丧失工作热情和创新精神。
三是缺乏专业定位,产生自我价值认同危机。当前,我国大多数教研员主要从中小学优秀教师及骨干教师中选聘而来,从教师到“教师的教师”,从教学到教学研究、指导、服务与管理,教研员面临着角色转换、职能调整等适应性问题。不少教研员对自我角色职能认知模糊,对自我价值的认同产生怀疑,认为个人教学实践不如一线教师、教育科研不如高校教师、教材研究不如学科专家,同时囿于理论水平,无法将已积累的优质教学经验转化为教研理论反哺教学实践。
陈大伟:的确,专职教研员也有差异,不少教研员的专业素养和实践成效是很不错的,以下的讨论主要针对素养不高、校长和一线教师满意度不高的专职教研员。
2006年7月19日的《教育时报·课改导刊》曾经登载了一位乡村小学教师的“一次教研活动经历”,文中这样写道——
我仍然有几分自信,更加迫切地希望教研员能进行一些点评,要知道专业引领、专家的评价对教师的帮助最大。
教研员终于开口了。“这节课学生自己分析课文的时间太长了,应该让学生充分地去读,在读中发现问题,然后共同思考和解决一个个问题。”“让学生把一个个知识点找出来,然后引导学生去体会知识点。”“知识点仍要偏重的。”“对课文词语的理解一定要解决好。”“学生发现问题、讨论问题时该制止要制止,该引导要引导。”“让学生当老师,这不行,学生怎么能当老师?怎么能说把学生培养成老师呢?怎能让学生站在老师的角度去提问题呢?不能!”
听着教研员的发言,我的头发蒙,我在笔记本上写道:“难道我失败了?我怎么觉得他是个‘落伍者’?”我的心情越来越沉重,难过、压抑,一阵阵袭来。我仅存的一点点自信被教研员打垮了!我自己坚信的“教学理念”——教师是引导者、帮助者,要重视学生的学习主动性,要与学生平等对话,不能光让学生掌握知识,还要让学生体验求知的过程、掌握求知的方法……全被击了个粉碎。
我们能感到,这位教研员的点评和表达方式,伤了一线教师的心。从这种意义上来说,这位教研员需要提升专业素养、改善工作方式。
一个人的经验是和他的经历紧密相关的,就像坐井观天的“青蛙”,它的生活环境和生活经历形成了经验,决定了它看到的“天”。教研员的哪些经历和经验有可能成为其专业成长路上的“绊脚石”呢?我以为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
其一,大多数的教研员来源于一线优秀教师。这里的“优秀”主要表现为教学业务能力较强、教学成绩突出,也可以说,有不少是应试教育的佼佼者。这样的经历可能让教研员迷之自信,意识不到自己在先进教育理念方面存在欠缺。就像井里的“青蛙”,对“小鸟”所说的“天大得很”不大容易听得进去。当经验成了包袱,就容易失去改变和专业成长的动力。缺乏动力的另一个原因是,专职教研员往往承担着一个区域某个学科教育教学质量的责任,担心变来变去影响教育教学质量,还不如稳妥一些、保守一些。
其二,专职教研员不仅要有课堂教学的高超能力和专业素养,还要有组织教师学习和研究所需要的教师研究、教师影响等方面的高水平素养。如果工作中不理解教师的心理和实际,缺乏与教师沟通交流的设计和实施能力,其结果往往就会南辕北辙,在上述案例中,我们能够清晰地看到这样的问题。因此,教研员要花时间做教师研究、教师专业发展研究。
其三,专职的学科教研员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和决定了所在区域某一学科教师在专业上的发展机会与发展可能,区域内的学科教师不敢不尊重、不能不奉承。处于这样的环境中,教研员很容易自以为是,以“专家”自居,于是对一线教师指手画脚。对这样的教研员,一线教师可能表面奉承,私下难免不满和腹诽。我认为,越把自己当专家的教研员,别人越不认同你是专家;越是愿意和一线教师平等交流、相互学习的教研员,越容易成为专家,也更能赢得一线教师的尊重和信赖。所以,还是别轻易把自己当专家。
《教育家》:部分基层教研员反馈,针对教研员的专业培训非常少,以至他们在教研工作中成长受限。教研员需要什么样的专业培训?如何为他们构建一套专业的成长体系?
陈大伟:与一线教师比较,教研员应该是水平更高、专业能力更强的一支团队;对于这样的团队,更需要的不是培训,而是引导学习或组织研修。诚然,教育行政管理部门、上级教研机构应该建构教研员专业成长的支持体系,但教研员不能仅奢望依靠一套完整、外在的专业成长体系来提升自己,更应该主动争取学习机会,在实践中研修、在合作中研修、在共同做项目中研修,这是教研员专业成长的主要路径。
在2003年新课程的国家级小学语文骨干教师(参与者大部分是教研员)培训班上,我分享过一线教师对一些教师教育的批评:“授课教研员在用不重视参与者主体作用发挥的方式告诉学习者,在课堂教学中要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是没有实践经验的培训者在教中小学教师如何实施课堂教学变革。”我认为教研员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有两个。
其一,要求教师研究学生、以学论教,教研员就需要研究教师,发挥教师在教师研修和专业发展中的主体作用。教研员要把对教师的研究、教师学习和发展的研究、教师指导和影响的研究作为专业成长的主要课题,补上这样的短板。
其二,要丰富实践经验、提升实践指导能力。就现在的课堂教学研讨,我认为多是“上课教师深处水深火热之中,其他教师和教研员都在隔岸观火”,要避免隔岸观火,则需教研员亲身体验。我在四川省绵阳市涪城区教师进修学校工作期间,和团队共同提倡并实践了“四环节”教师研修方式,即以4课时研修为单元,第一环节是一线教师上一节课,第二环节是学科教研员上同一堂课的“同课异构”,第三环节是参与教师研讨课堂教学,第四环节是教研员就相关主题做专题讲座,这种与一线教师“同在共行”的交流方式,不仅有助于促进教研员的实践能力提升,而且拉近了和一线教师的关系,赢得了他们的信赖和尊重。
此外,教研员的专业成长还有“急用先学”的特点,比如新的课程方案、新的教材出来之后,为适应新的时代变革要求,教研员就要先学、先知、先会,从而较好地发挥学科引领作用,落实相应变革措施。
罗生全:专业培训是促进教研员专业成长的重要外在手段。当前,针对教研员开展的专业培训普遍较少,甚至没有,导致教研员的专业发展主要依赖于系统内部的自我驱动和个人自主学习,总体反映出业界对教研员的长期忽视。对于教研员而言,他们当前亟需系统化、科学化、专业指向明确且常态化的专业培训,为个人教科研工作奠定扎实基础。为促进基础教育教学质量的提升,我们应该走出教研员专业培养盲区,为其构建一套科学系统的成长体系。
第一,做好教研员专业发展规划,明晰专业成长方向。各地教育行政部门要重视教研员专业培训,划拨教研员培训专项经费,予以政策和经费的倾向性支持,建立专门的教研员专业发展体系,并将其作为重点工作加以落实,特别是要加紧制定和发布教研员专业发展标准,围绕专业知识、课程建设、教学指导、科学研究、组织领导和专业品质六个方面,细化教研员专业发展内容,为其提供方向引领。
第二,完善教研员选入退出机制,确保教研队伍流动化。为解决新教研员补充、在职教研员发展与老教研员退出的一体化问题,有必要构建公平、科学的教研员准入机制,着重提高门槛、规范准入程序,丰富考试、考核、考查等选拔方式,尤其注重教育理念、专业能力和专业品质等方面的考核;建立在职教研员流动、退出预警机制,增强教研员专业发展风险和失业风险防范意识;建立稳定有序的教研员退出机制,制定教研员退出条件和标准,实行任期制、辞职制,让教研员“自愿出”“自然出”,并通过返聘、续聘、顾问、成果表达等方式传递教研精神。
第三,优化教研员绩效考核任用标准,激发专业发展后劲。为完善教研员专业发展评价体系,发挥以评价促发展、以评促学等功能,有必要依照教研员专业发展标准制定教研员绩效考核、晋升、任用等方面的基本条件和细则,强化教研组织氛围支持,通过物质奖励、精神奖励等方式提升教研员的自我效能感。
《教育家》:在数字化转型的浪潮中,教研员作为“教师的教师”首先需要积极适应这一变革,以便更好地引领和指导教师开展相关实践,但在实践中,部分教研员难以较好地适应新技术的融入。对此,您有哪些建议?
罗生全:基于数字化转型大背景,作为一线教师“领头羊”的教研员亟须破解教研数字化变革的问题,有必要从以下两方面着手。
一方面,增强数字化和数字化应用意识。数字化和数字化应用意识直接影响着教研方向以及技术变革教研的广度与深度。教研员要率先认识新技术、适应新技术、利用新技术,清楚地认识到数字化转型不仅是工具的更新,还是教研思维、教研方式等方面的变革,需聚焦学生核心素养的培育,建立生成式的数字教研观。
另一方面,不断提高数字化教研能力。教研员要依托线上、线下学习资源,拓展学习空间,主动学习使用各种教育技术工具,利用新技术创新教研工作的方式方法,提高信息检索、加工、整合数字化教研资源的能力。同时,通过行动研究、课例研究、案例研究等帮助一线教师解决教育教学中遇到的技术问题,深化教学、研究与个人专业发展的融合。
陈大伟:我认为,数字化转型学习也是一个“用中学”的问题。英国纽卡斯尔大学教授苏伽特·米特拉在印度做过“墙中洞”的儿童教学实验,结果显示:孩子们可以用“自组织”的方式学会电脑的使用。这是技术学习和运用的一个经典实验,揭示了新工具、新技术学习的有效途径。教研员的新技术学习也可以而且应该通过“自组织”的方式实现,把教研员抛在数字化的环境中,让他们去感受、去体验、去运用,形成数字化转型的学习动力。
关键在于,教研员要意识到数字化转型是时代趋势,运用新技术做教师教育、教育研究和教学管理是教研员应具备的基本功。第一,教研员要跳出原有的“井”,看一看数字化转型带来的新的“天”。第二,要建立一批教师运用新方法的先行团队和实验团队,形成引导的力量和榜样的示范。第三,要有便捷的技术支持团队,能够及时提供使用上的指导,帮助解决使用中出现的问题。第四,开展新技术运用方法的研讨交流展示活动,做相关的研究和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