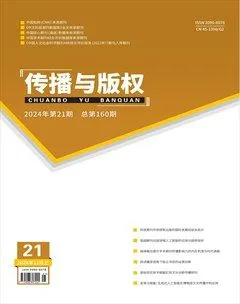高校图书馆读书会深阅读引导实践
[摘要]文章以闽江学院图书馆知行读书会为例,阐述深阅读和读书会的相关概念及高校读书会类型,对知行读书会深阅读引导活动的发展概况、组织形式和活动流程进行系统梳理,从阅读文本、阅读习惯、阅读动力和阅读环境四个方面分析知行读书会深阅读引导方式,为高校图书馆开展深阅读活动提供实践经验。
[关键词]高校图书馆;读书会;深阅读
自2014年起,“全民阅读”已连续11年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2020年10月,中央宣传部印发的《关于促进全民阅读工作的意见》指出,阅读是获取知识、增长智慧的重要方式,是传承文明、提高国民素质的重要途径,深入推进全民阅读,对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促进社会进步具有重要意义[1]。2022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向首届全民阅读大会致贺信,希望全社会都参与到阅读中来,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在此背景下,高校图书馆积极开展形式多样的阅读推广活动,对提高大学生阅读兴趣起到重要作用。在数字时代,碎片化和消遣式等浅阅读现象,在一定程度上容易导致大学生存在阅读专注度不足、文本理解能力降低、批判性思维缺乏、学术视野受限等问题,不利于培育大学生的人文素养和精神内涵。如何引导大学生形成深阅读行为和习惯,成为高校图书馆在开展阅读推广活动时亟须解决的重要课题。基于此,文章论述闽江学院图书馆知行读书会的实践案例,并对其深阅读引导方式进行分类总结,为后续相关理论研究和实际工作提供参考。
一、相关概念
(一)深阅读
目前,学界尚未对深阅读做出明确规范的概念化定义,具有代表性的概念界定有以下几个。周亚将深阅读解释为读者从具有较m7pt4FZvrVwmIa73xJrWfw==大知识信息含量和较高系统性的书面语言和符号中获得丰富意义的社会行为、实践活动和心理过程,且在这个过程中,阅读主体大脑参与度很高,对阅读语言和符号的熟悉、理解与掌握达到较高的程度[2]。吴健认为,深阅读指读者在原有知识经验的基础上,主动地理解和内化阅读内容,批判性和启发性地重构知识,开拓新的意义领域,实现迁移和创新的活动过程,并主动自觉地选择阅读策略,而深阅读的核心价值取向和最终目标是实现创新[3]。李桂华基于生成认知理论,将深阅读定义为读者这一具有心智能力的有机体在适宜的情境下与阅读对象相遇,产生积极的阅读态度和行为动力,进而发展而来的高参与度的阅读行为[4]。综上所述,深阅读的基本特征是阅读主体的深度参与,包括认知、行为、情感等多方面的高参与度,体现在读者对阅读内容的理解、思考、评价和感悟达到较高程度。
(二)读书会
读书会在不同地区有不同的名称,国外将其称为读书俱乐部(Reading Club)、阅读小组(Reading Group)、学习圈(Study Circle)等,国内则有读书会、书友会、读书沙龙、阅读小组等名称。学界使用范围最广泛的读书会的定义源自瑞典官方发布的《成人教育公告》(Adult Education Proclamation),即一群人根据事先确定的目标或主题,共同进行有组织、有方法、有计划的学习[5]。此外,国内学者在研究中对读书会的概念界定亦提出不同解释。赵彦梅等认为,读书会是人们对书籍进行阅读与讨论的非正式组织[6]。吴惠茹提出,读书会即一群人针对某个主题或相关问题有组织地共同探讨研究的定期团体聚会[7]。赵俊玲则将读书会理解为以阅读交流为中心的民间组织[8]。段梅等认为,读书会指一群爱书者们定期聚集在一起,看书、共享、交流、探究自己读书心得的活动,通过参与者对相同文字的阅读与讨论以及对新知识的吸收,激发新的思考,进而扩大学习空间[9]。文章以高校图书馆读书会为研究对象,将读书会界定为一群志同道合的读书爱好者定期聚集的阅读组织,且读书会以读书交流、心得分享、观点探讨为主要活动形式,旨在引导读书爱好者通过参与活动,开阔视野,启发思辨,促进成长。
(三)高校读书会类型
第一,按照内容性质划分。学科型读书会指围绕相对固定的专业领域或学科主题定期开展研读活动的读书会,由院系教师发起,在教师的组织和指导下,参与者共读专著、论文、报告等学术文献及延伸作品,探讨专业学科问题,以提升自身的学术能力和科研水平,如北京大学“知识产权沙龙读书会”、中国政法大学“法理学专业读书会”、湖南中医药大学“科研小组师生读书会”[10]等。兴趣型读书会指对阅读题材和活动主题拥有共同兴趣爱好的爱好者组成的读者组织,以促进理解与启发思想为目标,定期举行共读、交流、讨论等阅读活动,如东南大学“善渊读书会”、南阳师范学院“绿茵读书会”、天津财经大学“思扬读书会”[11]等,目前较大部分高校读书会属于这一类型。
第二,按照组建方式划分。一是高校图书馆组建。高校图书馆具备充足的文献资源,能够提供研讨室、报告厅等场地空间,在组建读书会及开展阅读推广活动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和丰富的实践经验,由其组建的读书会面向全校招募,不限制学科与专业,成员覆盖面较广,影响力较大,可持续性较强,如:贵州大学图书馆读书会从1994年成立至今已延续31年;南阳师范学院“绿茵读书会”从1990年成立至今已延续35年。二是院系组建。一般由院系教师在读书会中担任核心角色,成员限定于院系的学生,由于成员具有相似的学科背景,其阅读主题一般与特定的专业领域相关,该类读书会的发展依赖于核心人物,可持续性较弱,如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读书会、中国人民大学“兰台读书会”等。三是学生自发组建。该类读书会主动性较强,活动形式较自由,但是容易面临经验缺乏、任务繁重、资金不足及核心成员断层等困境,如华中农业大学“湖畔读书会”、华东政法大学
读书会等。
第三,按照活动形式划分。一是线上读书会,即依托网络信息技术,借助QQ、微信、微博等开展阅读活动的读者组织或团体,其活动不受空间制约,组织方式较为灵活自由,如黑龙江中医药大学“有声读书会”[12]、重庆大学图书馆“悦读会”[13]等。二是线下读书会,指在实际的物理空间中组织和举办读书会活动,目前大多数高校读书会以线下形式为主开展阅读交流活动,辅之以新媒体平台进行成员招募、通知发布和宣传推广[14]。
二、闽江学院图书馆知行读书会深阅读引导活动
(一)发展概况
闽江学院新华都商学院于2015年由学生发起并组织“破茧读书会·经典阅读训练营”,该阅读训练营以“深度阅读,格物致知”为理念,以“阅读,让思考成为一种习惯”为目标,召集对经典著作有相近趣向的阅读群体,通过对阅读方法的进阶训练,锻炼成员深度阅读、慎思明辨、表达沟通的能力。活动期间,成员完成了对杜威《民主主义与教育》、弗洛姆《爱的艺术》等经典著作的共同阅读与交流探讨,并面向全校举办阅读成果分享会,取得了良好的反响。2016年,闽江学院图书馆在“破茧读书会·经典阅读训练营”的基础上成立知行读书会,以“学思知行”为宗旨,以培养深阅读习惯与能力为目标,为大学生搭建以书会友、见贤思齐、分享交流、思想共鸣的平台。其活动以学年(当年10月至次年5月)为时间单位,至今已连续开展9期,读书小组也从最初的8个发展至单期20多个,其中单期参与人数近200人,成员遍布全校各个院系,有多个读书小组坚持阅读数年,形成稳定的阅读圈。目前,知行读书会已成为闽江学院图书馆阅读推广核心品牌项目。
(二)组织形式
第一,规章制订。闽江学院图书馆负责组织与管理知行读书会,制订相关实施办法,对阅读范围、活动频次、研读方式、成果记录等进行明确规定,使活动各个环节有章可循,并为知行读书会提供文献资源、活动场地、网络空间等各项支持,以保障知行读书会的有序运行。第二,成员规模。为了保障阅读讨论效果,闽江学院图书馆将知行读书会成员人数限定为5—10人,使成员人数固定,规模适宜,便于活动的有效开展。第三,书目选择。闽江学院图书馆参考中国图书馆学会阅读推广委员会推荐的大学生校园阅读书目、文津图书奖获奖图书和豆瓣排行榜等列出推荐书单,倡导深入阅读经典著作,尊重成员的阅读自由与个性化需求,由读书小组自行商议决定阅读书目。例如,《红楼梦》已被7个读书小组选为阅读书目,《活着》《百年孤独》《霍乱时期的爱情》等经典著作,均被多个读书小组选择阅读。
(三)活动流程
第一,书友征集。活动开始时间为当年10月,由召集人征集有共同阅读兴趣和需求的成员组成读书小组,提交申请表,包括读书小组名称、成员信息、成立目的、阅读书目、阅读计划、预期成果等内容,在审核通过后由闽江学院图书馆根据读书小组人数统一购买阅读书籍,并对新加入的成员进行培训,使他们对知行读书会的宗旨、理念、发展历程、组织方式、管理制度等形成初步认识,以增强成员的认同感与归属感。其中读书小组可延续名称,具体表现在坚持阅读的读书小组。
第二,阅读交流。活动持续时间为当年11月至次年5月,由读书小组按照计划进行深入阅读与交流探讨,闽江学院图书馆负责知行读书会日常事务的跟进指导和资源配合,协助读书小组制订阅读目标,包括宏观规划、阶段任务和实现路径等,切实引导读书小组完善交流方式、提升阅读质量、增强精读效果。该阶段主要分为自学、讨论、总结三个组成部分,读书小组成员可以根据进度安排先行自学,提出在阅读过程中的疑问与思考,自学部分提倡不仅“看书”,更要“品书”。再根据成员反馈结果,读书小组确定每次读书讨论会的主题,或一个或多个主题,由成员提前准备好相关资料,在现场围绕主题展开观点探讨与思维延伸,以相互启发和促进阅读理解,读书讨论会的时间和地点则以成员方便为原则,集中讨论次数不少于6次,其中线下讨论不得少于3次,讨论部分提倡不仅“品书”,更要“论书”。值得注意的是,知行读书会召集人一般充当读书讨论会主持人,以把控节奏和引导讨论,保证成员客观理性交流,交流的主体则是读书小组所有成员。知行读书会鼓励创新,尊重个性,支持多元的表达方式,引导成员通过读书笔记、思维导图、PPT、漫画、辩论、情景再现、影视赏析、作者其他作品对比、相关作品延伸阅读等方式对书中架构、人物关系、作者观点、创作背景、文风特色、主题思想等进行梳理、解读、思考、分享与交流,并在每次读书讨论会结束后撰写、提交活动记录表,包括时间、地点、参与成员、主持人、记录员、阅读章节、讨论主题、活动流程、现场照片等内容,还在文末附上成员对此次讨论主题的读书心得,于学年计划完成后以小组为单位提交成果总结报告,从而锻炼成员的表达能力与写作能力,总结部分提倡不仅“论书”,更要“思书”[15]。
第三,评估反馈。活动评估时间为次年5月,在每期活动结束后,闽江学院图书馆知行读书会根据读书小组的创意表现、计划执行、阶段心得、总结报告、阅读方法、活动形式、影响力等日常表现评选出20%的优秀读书小组和优秀成员,并颁发阅读基金作为奖励。闽江学院图书馆知行读书会制订明确的考核评估与激励制度,公开补助、表彰等奖励标准的具体细则,其中补助奖励包括书籍费、影印费、活动经费、召集人的工时费等,表彰奖励包括设置各类奖项、颁发荣誉证书、成果发表与展示、优秀成果分享会等。闽江学院图书馆知行读书会通过物质激励与精神激励并举,鼓励学生积极主动参与和认真持续开展读书活动,为读书活动的有序开展提供充足的助力。
第四,成果展示。活动分为阶段成果展示和优秀成果展示,展示内容包括读书心得、成果报告、活动过程、讨论记录、阅读计划、读书方法、阅读感悟与成长等。闽江学院图书馆在官方网站主页设置知行读书会专栏,整合校内所有读书小组信息,为读书小组提供信息发布、成果发表、经验交流的平台,并通过微信公众号、视频号、公开讲读会、优秀成果分享会、优秀成果汇编等方式进行阅读推广宣传。例如,阅读《红楼梦》的读书小组从书中出现的186种美食切入,组织成员亲手烹饪,举办红楼珍馐品鉴会,并和汉服社及戏曲社合作,开展《红楼梦》相关服饰形制知识讲座、汉服走秀和红楼梦戏曲活动,获得热烈反响,扩大了知行读书会的知名度与影响力。
三、闽江学院图书馆知行读书会深阅读引导方式
(一)从阅读文本引导
文本作为阅读的对象,是深阅读行为产生的基本物质条件,不同文本引发不同的深阅读可能性。彭佳提出,在阅读关系中,文本是处于中心地位的,正是文本自身的多义性使它具备创新功能,能够促进新的意义产生[16]。卡尔认为,读者在深阅读过程中会不断将自己代入文本,与文本中的观点和人物进行互动,从而达到自我审视与自我成长的目的[17]。阅读文本是引导深阅读行为的重要条件,是影响深阅读效果的关键因素,因此,闽江学院图书馆知行读书会在文本的选择上注重可读性和启发性,其中:可读性指文本的审美价值,内容是否具有吸引力,是否能够激发成员的阅读兴趣;启发性指文本的知识价值,是否具有内涵和深度,是否经得住研读和审视,是否能激发成员产生新的洞见与领悟,甚至迸发顿悟的灵感[18]。闽江学院图书馆知行读书会根据中国国家图书奖、文津图书奖、鲁迅文学奖、茅盾文学奖等,为读书小组推荐相关阅读书单,尊重成员在阅读书目上的自主选择权,积极发挥自身的价值导向作用,促进成员提升阅读品位。
(二)从阅读习惯引导
第一,阅读频率。文本只有在一定时间长度内被连续阅读,并延伸为一种心理过程,才能使读者获得对其系列意义的把握,才能为读者的判断、认知和评价提供最丰富的可能性[19]。闽江学院图书馆知行读书会要求读书小组提前制订阅读计划,并定期举办读书讨论会,集中讨论次数不少于6次,其中线下讨论不得少于3次,以保证读书讨论会阅读频率的延续性和稳定性。
第二,阅读注意。深度阅读过程不仅需要读者以投入时间为条件,更加需要读者注意力的充分集中和凝聚,引导读者去对抗在感官信号之间转移注意力的人类本能,开启心无旁骛的静谧空间,去建立连接,做出推论,催生思想[16]。闽江学院图书馆知行读书会要求成员在阅读过程中提出疑问与思考,并为读书讨论会主题准备相关资料与发言内容,调动注意力进行深入阅读,领悟作者的观点,深化自身的理解,重新运用语言表达或其他表现形式输出洞见和感悟,形成读书心得报告,在沉浸式的阅读中培养自身踏实钻研的阅读习惯。
第三,阅读思维。阅读思维指读者在阅读过程中的思维活动,是读者在熟知阅读文本的基础上运用自身的知识储备和心智能力,理解、感知、评价阅读文本的心理过程。闽江学院图书馆知行读书会要求成员在读书讨论会时围绕具体话题展开观点交流与探讨,从准备过程中的思考与判断到分享阶段的输出与反馈,培养自身的批判性思维与逻辑思维能力,践行深阅读,从而获得优质的阅读体验,建立积极的阅读态度,掌握科学的阅读方法,提高与文本对话的能力,完善自身的知识结构。
(三)从阅读动力引导
第一,自我成长。闽江学院图书馆知行读书会在读书讨论会中要求成员对书中架构、人物关系、创作背景、文风特色、作者观点、主题思想等进行梳理、解读、分享与交流,在观点碰撞的过程中取长补短,多闻阙疑,博采众长,学习新知识,激发新思考,走出因个人视野、思维、见识等方面不足而造成的偏见和局限,以获取信息,拓宽视野,互相启发,丰富生活。此外,其还要求成员撰写读书心得与成果报告,亦有助于提升成员的表达能力与写作能力。
第二,社会认同。闽江学院图书馆知行读书会不仅要求成员在读书讨论会中切磋学识、分享观点,还要求成员在图书馆官方网站、微信公众号、公开讲读会、优秀成果分享会上面向全校输出见解与感悟。通过自我展示,成员有效激发内在动力,提高自身的参与度,从而促进知行读书会的可持续发展。
第三,社交需求。明代顾炎武在《与友人书》中引用《礼记·学记》并加以补充:“独学无友,则孤陋而难成。久处一方,则习染而不自觉。”日本明治大学教授斋藤孝在书中提及:“人们在交谈时,如果双方读过同一本书,拥有共同的阅读体验,那么交谈中便能引用书中话语,从而使交谈更加开心,更有深度和广度,而读书会正好能够人为地实现这个过程。”[20]二者都论述了寻觅书友、交流见解的重要性,从人际传播角度强调了读书会的意义。闽江学院图书馆知行读书会搭建以书会友、见贤思齐的平台,让成员能够从中结交志同道合的同好,在交流中获得思想共鸣、文化认同和精神升华,增强归属感与满足感,体验阅读的乐趣并享受其中。
(四)从阅读环境引导
第一,阅读氛围。不同于以讲座形式为主的读书会,话语权由专家学者等核心角色主导,读者只能在互动环节中提问,缺少各抒己见的话语空间。闽江学院图书馆知行读书会旨在为成员创造平等交流的环境,让每个成员作为交流的主体,都有发言与讨论的权利,注重成员间的互动关系,强调自由开放、尊重个体、独立思考、包容多元、倾听异见、理性沟通的对话风气,使成员在独特的见解中产生自我认同感,在书友的鼓励中获得社会归属感,在平等自由的良性氛围中丰富交互体验,提高阅读兴趣,强化阅读意愿,拓展思维广度与深度。
第二,他律作用。一方面,规则制约。闽江学院图书馆知行读书会对活动频次、阶段任务、心得报告、成果记录等进行明确规定,对个体形成外在约束,以他律促自律,约束成员的阅读行为。另一方面,群体效应。闽江学院图书馆知行读书会作为一个团体组织,发挥群体作用,影响个体的心理和行为,形成趋同效应和从众效应,使成员向优秀的榜样学习,自我鞭策,主动思考,深入阅读,输出更精彩的见解与感悟,在无形中形成阅读激励。
四、结语
目前,大多数研究将高校图书馆读书会的发展困境归结于政策资金扶持、各方协同合作、馆员专业素养、组织管理经验、推广宣传形式等方面问题,并就此提出有针对性的改进策略。文章认为,对一个自愿参与的组织来说,外部支持与政策环境等客观条件固然重要,但成员的主观能动性才是影响和阻碍高校图书馆读书会可持续发展的核心。闽江学院图书馆知行读书会要根据实际情况调整活动周期,从学年制转向学期制,以激发成员持续参与的热情,并从个人价值和社会价值方面发挥作用,深入挖掘自身在个人成长和社会贡献上的多元价值,如促进自我认同与实现、满足社交回馈与情感需求、强化社会归属感与责任感等,从而增强成员的内在驱动力,吸引并留住成员,进一步提高成员的参与度,探索深阅读服务模式的创新路径,为后续研究和实践工作提供探索方向。在数字时代,高校图书馆读书会要主动拥抱挑战,通过持续创新阅读推广策略和活动形式,精准对接并满足大学生群体日益多元化的阅读需求,积极引导大学生踏上深阅读的探索之旅,享受深度思考与知识内化的乐趣,从而构建和完善层级分明的阅读服务体系,打造独具特色的阅读活动品牌,成为校园推动文化传承与创新、践行文化育人使命的重要阵地。
[参考文献]
[1]中宣部印发《关于促进全民阅读工作的意见》深入推进全民阅读[EB/OL].(2020-10-22)[2024-09-11].https://www.gov.cn/xinwen/2020-10/22/content_5553414.htm.
[2]周亚.“浅阅读”概念界定及相关辨析[J].图书馆杂志,2013(08):18-22.
[3]吴健.大学生数字化深阅读研究[D].徐州:江苏师范大学,2017.
[4]李桂华.深阅读:概念构建与路径探索[J].中国图书馆学报,2017(06):50-62.
[5]周田田.美国读书会发展历史探究[J].图书情报研究,2015(03):27-31.
[6]赵彦梅.公共图书馆开展读书会活动的探讨:以南京图书馆陶风读书会为例[J].图书馆研究,2013(01):79-81.
[7]吴惠茹.阅读推广视角下的高校图书馆读书会实践研究[J].图书与情报,2014(06):76-81.
[8]赵俊玲.国内外读书会研究现状及展望[J].图书情报研究,2015(03):15-21.
[9]段梅,曹炳霞,韩叶.读书会的发展与阅读推广组织方式[J].图书情报工作,2015(20):29-33.
[10]郑玥,田瑶,陈丽.浅谈中医药院校科研团队管理经验:以湖南中医药大学“科研小组师生读书会”为例[J].教育教学论坛,2017(45):14-15.
[11]刘宝明,王南.高校图书馆读书会的创办、管理与实践:以天财思扬读书会为例[J].高校图书馆工作,2015(03):31-33.
[12]周乔木,李昂,许永程.基于自主学习的大学生线上知识社群构建的难点与对策:以新冠疫情期间“有声读书会”的实践为例[J].大众标准化,2020(20):145-147.
[13]谷诗卉,杨新涯,许天才.读书会网络化服务模式与实践研究:以重庆大学图书馆“悦读会”系统为例[J].图书情报工作,2017(05):73-78.
[14]陈哲彦,徐雁.分众阅读理论下借力读书会的高校图书馆阅读推广探析[J].图书馆理论与实践,2022(03):92-97.
[15]刘心红.大学图书馆阅读推广理论与实践探索[M].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2022.
[16]彭佳.另一种文本中心:回应尤里·洛特曼的文本观[J].符号与传媒,2011(02):188-193.
[17]卡尔.浅薄:互联网如何毒化了我们的大脑[M].刘纯毅,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0.
[18]吴靖.浅浏览时代的文明忧思[J].书屋,2012(09):4-8.
[19]丁宁.接受之维[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9.
[20]斋藤孝.阅读的力量[M].武继平,译.厦门:鹭江出版社,2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