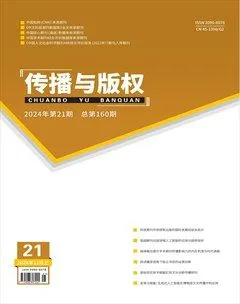民俗题材纪录片媒介景观与文化内涵的构建
[摘要]纪录片是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展现中国形象的重要手段。当下,民俗题材纪录片借助技术手段,以创新性的艺术手法真实再现民俗事象,增强观众对社会文化的认同。民俗题材纪录片采取多维叙事和情景再现手法,深情讲述民俗文化的璀璨历史,展示土地、百姓和民俗间的紧密关系,从历史、空间、情感、现实等方面呈现民俗历史渊源、地域特色和现代嬗变,构建了独特的媒介景观,实现了民俗文化的活态化传承与发展。
[关键词]民俗题材纪录片;《声命》;媒介景观;文化内涵
作为一种范围宽泛的文化事象,民俗在传承中不断发展,指导着民众的日常生活。民俗是人类智慧的结晶,对形成社会共识、文化习惯和增强民族共通感有重要作用。近些年来,民俗题材类纪录片层出不穷,如《民俗中国》《舌尖上的中国》《我的记忆我的年》《寻找手艺》等掀起一波热潮。中国纪录片正由重“量”走向重“质”,纪录片栏目样态正在被重塑,“纪实+”类型更加多样[1]。民俗题材纪录片能突破时空局限,再现民俗传统,立体化表现民俗现场,通过创新传播形式,在“原汁原味”的民俗事象中让观众体味市井百态。例如:纪录片《声命》以6集篇幅描绘陕北民歌的诞生、发展、复兴、创新过程,用6个完整独立的民歌故事,展现陕北风土人情和地域景观。数字时代,民俗题材纪录片借助相关技术构建媒介景观,对民俗的原生内容进行再创作,以提升民俗文化的传播力,并力图透视民俗特质,深入挖掘并弘扬其蕴含的中国文化精神。
一、民俗题材纪录片的媒介景观
民俗题材纪录片能有效传播民俗文化,提升民俗文化的价值。近些年来,民俗题材纪录片构建的媒介景观极大地强化了创作内容的剧情化色彩,将民俗融入民众的日常生活,通过故事化的叙述展现民俗的前世今生。例如:《声命》以时间为经,以故事为纬,用故事推动历史、用语言传颂民歌,在历史时空的交错叙事中,真实鲜活地呈现了陕北历史实貌和精神之魂。在复原民俗场景中,民俗题材纪录片以最自然的乡土地貌和极富特色的世俗人家表现历史进程中的民俗文化,引发了全社会对民俗文化的广泛关注。
(一)技术赋能:虚拟影像再现文化景观
民俗题材纪录片通常以民俗文化为创作主体,以时间为轴,借助影像表达内容,旨在展现民俗文化的创作过程和文化魅力,如《中华民俗大观》《民俗中国》《非遗里的中国》《留住手艺》等全面总结民俗文化,呈现民俗的发展历程。与传统叙述式纪录片有所区别,《声命》的主创人员在创作之初便提出“越是传统的题材,越要运用非传统的手法,以剧情化为主,访谈、资料、解说相结合”的拍摄思路。《声命》以时间顺序纵向展开叙述,横向穿插独立故事,内涵丰富,脉络清晰。纪录片《声命》通过《黄土地的呼吸》《走西口的长路》《兰花花的绝唱》《东方红的号角》《西北风的席卷》《信天游的回归》6集短片,讲述民歌的发展史,覆盖中华上下五千年的文明史。“影像介入历史,成为‘历史的使者’、描述者和还原者,其影像的意义在于这一影像对历史事件的见证与当代阐述。”[2]
民俗题材纪录片基于传统影视艺术的特性,展示了特定的文化生态、民众的生产生活百态。例如,《声命》第二集《走西口的长路》展现了陕北人以往“女人挖苦菜,男人走口外”的生活方式。《声命》通过白描式的叙事场景转换以及男主人视点的游移,展现了一系列具有中原和口外特色的文化生态,如吆喝订缸的小贩、打竹板的说书先生等,呈现当时陕北地方小城的繁华热闹、人情冷暖以及在此特定情境下而形成的多变的艺术形态,从而将走西口那段历史中的陕北人对家乡的思念、路上的劳苦奔波等都一一再现,以细腻生动的第一人摄影手法深描走西口的历史文化景观。
《声命》的主创人员采用实景拍摄,一路辗转米脂、清涧、神木等地,在故事讲述中呈现陕北景观:黄土地的特写、黄土高原的全景展现、四季变换中的窑洞等。虚构化的故事讲述使人沉浸其中,构建远去的历史记忆,唤起人们内心对陕北土地更深沉的爱。《声命》还邀请各方专家如陕北民歌专家王克文、狄马和音乐家赵季平、冯健雪,以及著名编剧芦苇等人,专家严谨的点评、“他属”年代的回忆,展现了当代陕北人对陕北这片土地历史和文化的理解、热爱和追寻。《声命》将戏剧化和纪实性、历史和现在相融合,在塑造陕北人物的过程中展现民歌文化的辉煌。
(二)场景嵌入:民俗事象重构仪式化生活
民俗是民众生产生活的“活化石”,民俗题材纪录片再现民俗景观和百姓生活,最根本的目的就是通过地域化的叙事材料,将根植于故乡文化的民生变迁逐层讲述给观众,并再现社会历史,力图映照当代中国大众的生存境遇[3]。例如,纪录片《中国新年》呈现中国人在春节期间置办年货、举办庙会、祈福等一系列富有中国特色的节日习俗,来构建中国人隆重热闹的节日仪式化景观。《声命》通过建构现实与影像中陕北文化的互文,于陕北民歌历史中勾勒鲜活的生命图景,在纷繁人世间道尽悲欢离合,从土地到劳动、从劳动到歌唱,将普通者的呐喊浓缩在光影之中。
作为民众的一种生活方式,民俗给予民众最真切、直接的体验,使民众在这种体验中感受生活和生命的意义。以乡土为空间载体的民俗事象,永远是与那片土地的民众相联系的,陕北人的生存状态都是在黄土高原上或高亢或婉转的陕北民歌中体现的。如第一集《黄土地的呼吸》中,男女隔坡对唱情歌、新窑筑好的合龙口仪式、敲锣打鼓的迎亲队伍,以及宴请宾客的敬酒曲等生活仪式,生动展现了陕北的内在魅力。詹姆斯·凯瑞认为传播仪式并非讯息在空中的扩散,而是在时间上体现出对一个社会的维系和延续[4]。陕北腰鼓、信天游、秧歌等一系列充满生命力的陕北文艺,以及打夯、拉磨、碾场的劳作场面和腰带、头巾、夹袄、束腿裤等具有地域特色的装束,共同构筑了不因时代更迭而改变的乡情文化。《声命》通过最具地域化的叙事内容,呈现了陕北民俗景观在数千年历史中的变迁,旨在全面展现其整体艺术风格,强调陕北文化的多元与共生,同时彰显陕北人的自由与包容。在这个过程中,《声命》借助影像营造的虚构空间弥合已消逝的历史空间,进而表达“变”与“不变”的文化内涵,在时空流动中展现人物的命运。
(三)视点融入:民间叙事联结历史人文
纪录片《舌尖上的中国》《我在中国过大年》《中国春节:全球最大的盛会》《晥美风味》等常以平民化的叙事视角呈现民俗文化,凭借具有亲和力的内容让观众产生共鸣。与口述式表达不同,纪录片《声命》通过情景化再现展现了陕北历史的演变,也揭示了熟人社会下的陕北人和陕北文化。陕北民歌源自民众,《声命》以民间视角展现百姓生活,全片通过当地演员的动情演绎,深入展现了乡土文化积淀下的陕北人风土人情,焦点落在大时代中的小村庄和小家庭,描绘了村庄里的男女老少,在此,人文厚蕴与原生自然交融,爱恨情仇与悲欢离合交织,从而向我们展示了一幅写意自然、形简意远的陕北画卷。
《声命》在宏大的历史叙事中,通过讲述小人物的故事,将普通百姓的儿女情长与悲欢离合与历史变迁相联系,在特定的宏观历史场景中呈现人物的生活状态和情感关系。如第四集《东方红的号角》呈现了《东方红》的创作者李有源的成长经历,讲述了他如何创作出这首响彻全国乃至全世界的歌曲。1936年,中国工农红军经过两万五千里长征成功抵达陕北,陕北人民感受到幸福的日子终于来临,一大批感激、歌颂共产党的红歌应运而生。《声命》在宏观层面概述历史事件,通过讲述民歌历史映射百姓生活,将民间视点贯穿始终。《声命》通过讲述历史故事,展现普通人的生活困顿与命运波折,引发现代人对先人的关怀与追忆,以及对现实生活的珍惜与感恩。这种对情感的生活化的描述,让现代人在关怀自身生存环境的同时,传承陕北特有的群体精神、人文理想和文化风骨。
二、民俗题材纪录片的文化内涵
民俗题材纪录片借助“流动的影像”凸显民俗发展过程,阐释民俗文化内涵,实现民俗文化的传播。随着数字化技术的迅猛发展,民俗题材纪录片呈现更加丰富的表现形态。这也加剧了民俗文化从乡村到都市、从线下到线上、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变,其传播主体、形式的多样化以及商业化的操作让更多人感受到了民俗文化的魅力和劳动人民的生活智慧。
(一)创新传播形式,建构文化认同
近些年来,基于“影视民俗”的艺术特性,民俗题材纪录片内容以现场纪实为主,以后期解说和现场采访为主要语言的呈现方式,将民俗纪实与虚拟现实相结合,采用蒙太奇式镜头呈现地方风采。例如:《中国新年》主要采用内视角和外视角结合的叙述方式,通过主持人的第一人称叙述,增强了作品的趣味性。《传承》通过讲故事的方式娓娓道来各民俗文化如马头琴、高跷捕鱼、皮鼓等的传承发展。民俗题材纪录片《声命》勾勒陕北民歌的发展史,展现民众生活,传达民俗文化,对陕北民俗和人民的赞叹都聚焦在人物的行为和语言中。
当然,《声命》的主创人员也表明“我们不能对本土文化妄自尊大,抱残守缺”,“陕北民歌的兴盛,固然与它自身的艺术魅力有关,但也不可否认与政治推力有关,对它的爱一定要有节制,懂得自省的爱才显得更深沉”。《声命》在展示陕北民歌的内在与外在魅力时,也对其未来发展表达了担忧,特别是在当今全球化和新媒介快速发展的背景下,作为传统文化的陕北民歌如何在保持“原汁原味”特质的同时,追赶潮流?事实上,这种对传统文化的忧患意识经由纪录片向民众发出警醒,是通过回溯过去的自我形象和生存经验,并能不断自我调整,以此解决现实情境中的认同危机,进而保持自我发展的延续性[5]。
民俗题材纪录片对数字化手段的应用,如AR技术、全息投影等,能够实现现实与虚拟的融合,使得民俗文化得以“活下来”“火起来”。例如:《新丝绸之路》运用影视特效让消逝的文化得以“复活”;B站的非遗微纪录片《海派百工》在5分钟内展现了多种非遗项目,通过上海手工艺传承人的讲述并采用“面塑+定格动画”等形式使非遗更加生动,同时,“点赞、投币、一键三连、弹幕评论”等互动方式也增强了观众的参与感。这种新颖直观的内容形式和表达,为观众呈现了一场传统文化的盛宴,同时构建了现代人对传统文化的认同。
(二)揭示民俗特质,回归民间精神
民俗题材纪录片通过展示民间生活,透视民间生存状态,使更多人感受到普通民众的情感,体验独特的历史意蕴与生活文化。民间视角的历史再现不仅体现了创作者自发的民间意识,还隐藏着创作者对百姓的生活状况的关切。例如:民俗纪录片《湘西》以6集篇幅讲述传统社会中湘西人的生活方式,展示了城市与乡村、长辈与晚辈、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冲突与调和,如年少离家的儿子常因观念不同与久居深山的篾匠父亲争吵不断。影片不仅展现了手艺人从不断探索到追求精湛的过程,还将他们简单但却深厚的父子亲情展现得淋漓尽致。这种日常生活的叙事似乎在证实民间文化和民间启蒙精神:利用艺术来调和理想的冲突、照映现实生活,将个人命运与社会变迁相联系。例如,《声命》中呈现的陕北民歌类型多样,陕北北路高亢粗犷的爬山调、漫瀚调、山曲、二人台等,陕北南路委婉凄切的信天游、小调、道情等,催生了一系列诸如《推炒面》《走西口》《一对对丢下个单爪爪》等经典民歌,久唱不衰。《声命》通过将陕北民歌与其他民俗文化融合,在故事化的演绎中展现了陕北人的热情。
同时,《声命》以小人物视角呈现民间生态环境,以民间场景彰显民俗精神。《声命》以女性为核心叙事主体,凸显女性在礼教束缚中对爱情的追寻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体现了陕北人的率真和大胆。在第一集《黄土地的呼吸》中,《声命》讲述女子巧儿和男子二娃突破父母阻碍相亲相爱的甜蜜爱情故事。影片将故事人物的表情、动作刻画得极其细致,咄咄逼人的巧儿父亲与家庭中软弱的母亲和敢于冲破“门第”观念追求幸福的巧儿形成强烈的戏剧冲突。同样,在第三集《兰花花的绝唱》中,《声命》以兰花花为叙事主体,通过融合民间传说,勾勒出她与红军宣传队班长相识、相知、相恋与别离的故事。特定时代情境下的民间叙事立场体现创作者强烈的价值取向,这一系列的戏剧冲突强化了民间伦理关系,分离、团圆式的传统叙事结构也体现了民众心理,以及立体化的民间人物形象和民间文化象征符号体现了质朴真实的民间精神,并与时代精神相连结,表征着自由化的人生理想和文化价值。
(三)讲好中国故事,涵养家国情怀
纪录片的核心为记录,如《舌尖上的中国》《风味人间》《湘西》《第三极》等摆脱了以往“局外人”的身份,将虚拟与纪实相结合,以全知视角讲述民间文化的历史,使得民众对中国的文化意蕴乃至民族特质有更清晰的了解。在现代化的时代语境下,《传承》以动人的故事展现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遗产,表征中国人浓厚的乡思意蕴。《行走的歌谣》透过现代青年群体中流行的《无锡景》《探清水河》等民间小调,展现中国近代历史、城镇乡村的巨变,以及小人物的喜怒哀乐,力图揭示民歌发展的全过程,凸显历史的厚度,在努力挖掘传统文化内涵的同时,更为处于现代社会中的人们谱写一首民族赞歌。《声命》依托具体历史语境,讲述了在苦难中成长的陕北人,通过捶打自己的生命骨架,不断成长,以抵抗身心内外的困境与危机,支撑着一代代陕北人以昂扬的姿态和精神状态生存与发展。尤其是处于现代文化转型期的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新一代的陕北人更急于寻找陕北文化的“根”,继承陕北先人优良的文化传统,在陕北人的故事和陕北民歌中不断成长、奋进。
中国故事语境充分体现了中华文化“平等、参与、和谐、共享”的精神,《声命》在对这种文化精神的追忆和询唤中,带领观众沉浸式感受生命真谛,实现个人和群体、本国文化和国际文化的交流。如《声命》第五集《西北风的席卷》透过影像资料和角色演绎展现20世纪80年代陕北一个偏僻的农村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发生的变化:必备的老三件、农场放映的电影、进入农家的电视机、稀有的轿车以及流行的港台文化,都如潮水般涌向了百姓的生活。这种对文化的寻根和唤醒极具情景化,由小及大、由内到外、由古道今,一一述说改革开放中陕北和中国的新变化。在这开放和多变的局势中,《声命》凸显了陕北人的自由与自信,讲述了陕北民歌以一阵强有力的“西北风”正影响全国,陕北文化中的“寻根文学”“西部电影”也将获得新的生命力,而这也从侧面展现了人们对家园的留恋和热爱。
三、结语
民俗事象因时而变,缘事而发,在承载中国传统文化、彰显民众审美趣味的同时,也借助数字媒介实现普及与增强受众认同。民俗题材纪录片《声命》在继承传统纪录片艺术特征的基础上,通过呈现原生态和富有地域特色的陕北景观,以剧情化故事展现陕北人独特的精神特质。民俗题材纪录片以其特有的地域色彩和艺术品位,展现了民间民俗文化从农村走向城市、从山野走上舞台、从现实走向网络空间,正是源于中国人对家园乡土和社会文化的留恋与关切,才会创造出一个个具有自身和时代特色的文化瑰丽。数字化时代,民俗题材纪录片在叙事内容、叙事视角和叙事方式上实现了新的突破,借助数字影像全景展现民俗之美,沉浸、互动式的表达也大受欢迎。在民间视角和中国宏大历史背景下,民俗题材纪录片的创作者应深入挖掘民俗文化的内涵,更好地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构建文化认同。
[参考文献]
[1]路斐斐.中国纪录片:从重“量”转向重“质”[N].文艺报,2019-05-08(004).
[2]肖平.历史影像的“意义阐述”[J].中国电视,2006(01):21-25.
[3]魏嵘.地域景观中的文化乡愁:大陆新民谣叙事性研究[J].兰州学刊,2016(11):134-141.
[4]凯瑞.作为文化的传播[M].丁未,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5.
[5]赵静蓉.怀旧:永恒的文化乡愁[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