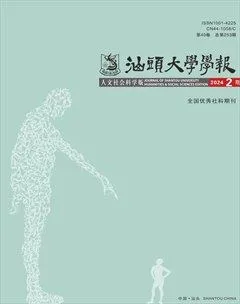“塑造”信任:互联网对信任形成的三重路径的影响
摘 要:信任对社会经济目标实现和个人生活有重要意义,与信息的获取和判断有密切关联。已有研究重视到新媒体对信任的影响以及传播者特征对信任的意义,本文在信任形成的不同路径的框架之下,分析互联网以其技术特征和关系结构在其间发挥的作用。互联网的影响体现在三个方面:认知路径上,是信息对信任过程而言的从可用性转向可塑性;情感路径上,是信任依托的关系稳定性上增加了关系的实现性特质;制度路径上,是信息主体被规制形式的边界由清晰变得杂糅。研究使得互联网环境下围绕信息的信任特征更加凸显,正是以上三个路径的变化综合体现了网民面对的信任环境。
关键词:网络传播;信任;认知路径;情感路径;制度路径
中图分类号:G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4225(2024)02-0070-10
引 言
信任是我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是社会合作的必要基础。人们为实现或优化共同目标,需要基本的社会信任作为条件,它是与道德、公民精神相关的使经济体正常运作的必要元素[1]。信任过程发生在已知、未知和不可知的交叉点上[2],对于个人来说,是重要的心理事件。信任的发展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尽管在讨论其发展的路径上学界存在不同观点,但对其与信息的获取、加工和判断有着密切联系这一点上,是有共识的。
将信任过程视为信息获得、加工和判断的过程,对我们理解互联网时代的信任极具启发意义。这是由于信息的生产和传播是互联网上的重要过程,正是处于不断更新中的信息使得网络空间充满生机活力。互联网不仅是人们获取信息的途径,也是重要的生存空间和生存方式,互联网的海量信息量、互联网的人机互动、生人社会人际互动、以间接的非面对面互动的特性,凸显了信任的信息加工的过程性特征。网络用户针对亲身经历或旁观目睹的网络主体互动,轻信、误信或者不信的情形,由此重构或修补了对社会现实的理解。联系到当前社会治理领域对网络舆论尤其是信息耐受力的关注,社会创新对网络所展现的可能性的关注,都离不开信任过程这一议题,因为信任在网络空间的生长为社会治理和社会创新提供了必要条件和展现了网络特征。研究在信任发展的不同路径的框架之下,分析互联网以其技术特征和关系结构与网络信任之间相互建构的过程,特别是它们在信任过程中发挥的作用,从而展现网络环境中的信任建立的特有面貌。
一、信息传播与信任发展路径的
相关研究
传播学研究有关注信息来源的可信度的传统,即具有何种特征的传播者传播的信息能够产生广泛影响的问题受到重视[3]。大众传媒被发现在形成当代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形成共识的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这主要指的是,人们信任媒体传递的信息,媒体扮演建构世界观的角色,而这些信息也因为可以被政治或商业利益利用而遭到批判。伴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网络传播的可信度也备受关注。研究主要关注,相比面对面沟通,互联网对人际交往、信息获取以及在线交易等过程中的信任形成的影响,以及探索互联网环境中建立信任的条件。此外,信任研究也逐渐与政治极化、公共领域的分裂以及“后真相”传播等问题联系起来[4]。可见,互联网作为沟通方式、信息环境以及制度环境的特征在研究中受到关注。
翟学伟把信任分为基于人的“表现性信任”和基于事的“实情性信任”,前者包括个人的表现和人的组织方式[5],例如关注传播者、关注官方与非官方媒体接触产生的差异影响[6]便是从“表现性信任”出发的研究。而网络信息传播带来的则是“实情性信任”的发达,人们对信息的判断摆脱了权威,而只关心发生了什么事,评论或反响如何,事况是否真实等[5]。这与信息能够脱离其具身化在场的生产者,被不断地复制、加工、传播有关。因而,在网络环境下确定信息可信度不仅需要评估信息来源,也要评估信息本身[3]。网络信息信任也不再处于诸如关系信任、制度信任等的遮掩之下,带有更多的技术环境影响之下的色彩。
追溯围绕信任的研究,可以发现信任被理解为一种预期,一种对未来发生结果的信念,因而信任研究在强调风险和不确定性作为发展信任的基本前提条件上是一致的[7],不过着眼于信任发展的过程时,研究观点表现出多样化。但是,已有研究多在新媒体带来的信任问题的整体框架之下论述[8],并未从信任形成的不同路径去探讨网络环境中的信息生产和传播对信任的影响。
信任发展的不同路径具体表现为理性选择、情感影响和制度影响[9]。理性选择路径认为,人们决定是否付出信任主要基于认知过程。人们根据观察到的特征或过去的行为对他人进行评估[9],信任与否的主要问题也在于如何获得有关潜在收益、损失和成功概率估计的所需信息,通过计算达到效用最大化和损失最小化[10]。情感影响的路径认为,情感是信任的重要维度,情感成分由参与关系互动的人之间的情感纽带构成,正是信任的情感成分使得信任者向被信任者敞开心扉[11]。而且,影响信任的认知维度也与相互的熟悉程度以及伴随的积极情感密切相关。信任发展的制度路径强调正式和非正式制度的作用,信任是不同制度之下的产物。马克思·韦伯把信任分为特殊信任和普遍信任,前者基于血缘、亲戚、朋友、家族社区等私人关系,并以习俗、传统、道理伦理等非正式制度为保障;后者基于信仰共同体,以信用契约或法律准则为基础和保证[12]。法律通过建立避免机会主义行为的激励机制来促进信任的形成,非正式制度则通过声誉惩罚发挥作用[13]。
着眼于不同的路径理论在主观层面、主体间层面和结构层面上影响信任的形成与发展,使得信任的形成与发展具有一定的综合性[14]。但它并未脱离以往关于信任研究的积累,即首先信任是一种预期,即通过认知评估去衡量这一预期的胜算;其次,信任具有情感特征,与信念相联系;第三,针对信任这种连接现状与未知之间的“危险的一跳”,做出制度安排,以减少错信的代价,强化守信的规范和法律惩戒。这一理论的优势在于对信任过程分析的细化,特别是结合网络环境中的信息生产和传播对信任的影响作用的分析,可以从三个不同路径入手,把握住网络环境信任问题的特点。
二、信息可塑性:互联网对信任
形成的认知路径的影响
从信任形成的理性选择路径来看,信任与否与信息的可用性密切相关。互联网对信任形成的认知路径的影响在于对信息环境和信息呈现方式的作用,使得信息的可塑性增强。
(一)网络信息生产、传播与呈现方式的影响
1. 网络信息生产和传播过程的影响
网络信息生产和传播的主体自由度更高。生产和传播信息并广泛影响他人的权力以去中心化的方式,由传统的专家、意见领袖以及媒体组织扩展至普通个体。多方主体积极参与带来的信息创造和流动使互联网充满生机活力,其分配和占有方式有助于改善信息不对称的问题。但与此同时,网络用户发布信息的自由度更高,不仅发布信息的过程不会受到如专业新闻生产者的组织过滤,而且对信息的注意义务也远低于新闻媒体。所见“事实”与观点意见被各种主体表述,泥沙俱下,因而需要网民仔细辨识。虚假专业知识和社会新闻是网络平台主要的不实信息类型[15],这两类信息的报道对传播主体的专业知识、逻辑性、洞察能力要求较高,传播主体的伦理价值观的建设也尤为必要,这些能力和素养恰是普通个体恰缺乏的。
网络信息生产和传播的过程性增强。信息生产和传播的过程由固定时点转向全天候无间断,真相被逐步生产和揭露的特点更加强化,网络信息快速完善、更新,也更容易以不完整和“过时”的面貌呈现。人们的注意力被热点牵引,顾不得追问最终结果,部分热议的网络事件甚至没有最终定论或者没有合理解释[16]。对网民而言,他们在碎片化时间里介入信息环境,如盲人摸象般打捞“事实”并形成认知,由此形成片面或错误的判断基础。
2. 网络信息聚合式呈现的影响
首先,网络信息跨平台传播、聚合式呈现,在强调“信息价值”的逻辑下,网络信息生产者对来自专业新闻媒体和自媒体的信息加以组合或再创作,进而进入平台个性化推荐机制。然而,这种整合信息资源的过程弱化甚至忽略了信息源的身份和原始语境,原始信息的表述被有意或无意改造之后加以呈现。例如2020年10月,闪电新闻客户端在以《钟南山院士:初步发现复方板蓝根对新冠病毒有效》为题的报道中提示,该新闻原标题为《钟南山院士:初步发现复方板蓝根可体外抑制新冠病毒》,但由何处转载而来,闪电新闻并未标示。就围绕复方板蓝根的争议,钟南山事后强调,“在实验室有抗新冠病毒作用,这离体内有效还很远”,虽然对比标题变化,能够发现可能的断章取义,但信息源的缺失仍然使得网民理解信息缺少了一项依据。
其次,网络聚合也将所有信息置于相同可访问水平,使各种来源和类型的信息(例如专业新闻媒体和自媒体信息,新闻报道和软文广告)似乎值得平等考虑,产生“平层效应”[17]。在认知判断过程中,不同类型信息源可能的立场和倾向差异被遮蔽,导致网民容易把广告信息中的商品或服务误认为是新闻报道,是一种客观、中立的呈现。2016年7月,原国家工商总局颁布《互联网广告管理暂行办法》,回应此前热议的“魏则西事件”,明确将“推销商品或服务的付费搜索”定性为商业广告,并要求显著标明“广告”,方便用户获知信息类型,以避免因新闻“背书”而产生误解。2023年8月,市场监管总局公布《互联网广告可识别性执法指南(公开征求意见稿)》要求“在新闻资讯、互联网视听内容等互联网信息内容流中发布的信息流广告应当显著标明‘广告’”,也是基于相同考量。
再次,网络信息生产者通过超链接结构或嵌入相关新闻,或添加背景资料,丰富自身传播的信息量,使不同的信息线索发生交互。但超链接结构让接收者在不同网站间跳转,在不同时空中穿梭意味着信息传播的上下文缺失,意味着在叙事上可能的混乱。可以说,网络超链接在整合碎片化信息的同时,也将信息接受者的注意力引至别处,带来感知觉、注意、记忆等方面的问题,表现出缺乏概括知识的意识和能力,难以辨别有用信息,记忆和提取信息困难等状况[18]。
总之,网络信息生产和传播的过程参与性增强,全时性、过程性凸显,并以聚合式呈现。网络信息可塑性增强的同时,也影响到信息的真实性、清晰度和准确性,对人们的认知判断构成挑战。
(二)网络情境下的信息符号呈现特征的影响
在互联网应用的早期,由计算机中介的沟通对非语言线索做了较多过滤,对认知判断和信任形成而言意味着与发言者相关的背景信息的缺失。并且,互联网早期还被认为是任务导向型工具,适合传递简单信息,不适合承载情绪情感[19]。如今,网络信息的多模态特征增强,能够为用户创造丰富的视觉体验,也是展现个人情绪和社会情绪互动的重要载体,成为影响网民认知过程的重要特征。
1. 视觉图像为传播符号的影响
文字是抽象符号,接触文字信息时,人们需要从中提取语义,依靠想象重建事件。相比之下,视觉图像是对社会环境中的物件和事件的直观展现,并且配合文字信息呈现时,视觉图像为事物形象提供指引,还为叙事提供证据[20]。视觉图像具有更强的感染力,人们通常也不会对图像信息的真实性报以过多的质疑,而且当以图像形式对虚假信息加以反驳时,其被操纵的可能性也容易被忽视,所谓“有图有真相”。
然而,随着图像编辑软件的广泛应用,图像与视频处理变得越发容易,人们对图像进行修饰、编辑,甚至不乏有意地误导性呈现。Hameleers等人的研究即发现,参与研究的被试认为以多模态呈现的虚假信息比仅文字呈现的虚假信息更可信,他们归纳了四种歪曲现实、传递虚假信息的方式:将真实的视觉信息与误导性文本结合(去情境化);剪裁视觉效果,以目标导向的方式突出某些方面(重新组织);操纵图像来呈现不同的现实(视觉篡改);同时操纵图像和文字来制作内容(多模态篡改)[21]。2022年2月,标题为“一名乌克兰父亲在上战场与俄军作战前与女儿挥泪诀别”的视频在社交平台广为关注,但视频真相却是来自乌克兰东部地区的父亲准备将女儿送往俄罗斯,然后与毁坏家园的乌克兰军队作战。[22]这则虚假新闻利用的便是视频图像的感染力,以多模态呈现的去情景化的信息给网民带来了识别难题,需要较高的信息素养方能应对。
2. 倾向性的情绪和意见为传播内容的影响
情绪互动是网络互动的重要内容,网络环境中个人信念与情感行动的逻辑相较于事实和证据的影响增大。网民会接受强烈刺激性的信息,对含有情绪感受的网络信息更加感兴趣,而且能否通过互动得到自己需要的情感慰藉也是个人衡量其网络交流活动是否成功主要标志[23]。甚至,新闻业也正转变为一个基于情感的市场,网民更倾向于去接触并传播与其先前信仰一致或相悖的信息。新闻信息中蕴含的情感要素能否切中网民痛点、引发共鸣,是其影响力的关键。
网络信息接触也激发起含有集体兴奋的网络意识或网络情绪,受到刻板印象与群体认同的影响,表现出明显的倾向性。多起网络直播间野性消费事件背后,是网民对主体身份特征的共情。不少网络舆情事件始发于当事人或相关人爆料,通过带有个人主观视角的表露、叙述吸引其他网民关注。2021年8月,阿里巴巴公司女员工周某自述遭遇职场性侵,被迫出差、强行被灌酒、醉酒被猥亵、向公司申诉多天得不到回应等问题引发热议,并释放出诸多负面情绪。虽然在公安机关的调查中周某被迫出差和强行被灌酒均不属实[24],但陪酒文化、职场性骚扰以及员工维权难确实是企业负面舆情的重要议题[25]。可见,围绕情绪的互动更容易脱离具体的事实,网民以倾向性观点为核心进行意见输出、树立二元对立的话语框架。更有甚者,在“某大学女生诬蔑偷拍”事件中,性别对立在与其他不同事件联系捆绑中加剧[26],在“大妈地铁怒怼cosplay女孩穿着暴露”事件中,商业炒作利用、刻意制造从而强化代际群体矛盾[27],进而影响他人的认知判断。
此外,在算法影响之下,社交机器人也是倾向性情绪和意见在网络空间扩散的助推器。社交机器人为互联网贡献了很大一部分信息量,编程通过模拟人类行为和自主创建内容与人类交互,但很难将其与人类自然生产的信息相区别[28]。也就是说,信息传播因社交机器人的出现更加容易被操纵,却不易被用户所察觉,而且在算法模型的辅助之下,它们更加表现出信息生产者通过向网民提供符合其观点、信念与期望的内容来吸引网民注意力的能力,从而调动网民情感行动。
从网络情境下传播的信息符号来看,处理和编辑图像的实践是一直是互联网创造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今深度合成的技术也已应用于专业视听内容制作领域。视觉合成媒体的构成元素间的关系错综复杂,无论是出于逼近真实还是臆造现象的目的,都制造了认知难题。另外,网络信息传播者通过利用或煽动网民情绪,发挥其在网络中的动员能力,通过制造虚假共识影响公共话语,作用于网民信任,这是有别于需要经过具体信息收集、逻辑判断的认知过程。
三、关系实现性:互联网对信任
形成的情感路径的影响
在情感因素影响信任形成的路径中,人际关系的稳定性以及与之相随的熟悉感有着重要作用。因此,互联网对信任形成的情感路径的影响在于对人际沟通过程的维系或改造。
(一)互联网维系人际沟通的情感基础
尽管人际互动由互联网中介,呈现出不同于受时间和空间限制的面对面交往的面貌,但网络社交以及电子商务中的部分设计仍在倾向于建立熟人社区、培养熟人关系,旨在继续发挥情感因素在信任建立过程中的作用。
在网络社交中,不少社交网站以人口统计学特征、社会身份特征帮助个人确立群体归属,例如保研论坛以城市、大学或专业划分板块,为关系聚合和沟通互动创造便利条件;社交网站也通过用户的主动性和个性化推荐形成人际联结,通过交往信息的圈层化增进内部相似性,例如网民参与MBTI性格测试,通过积极的自我类别化来获得相似的情感体验,在群体成员间实现意义的互换。又如豆瓣用户拥有共同的名字“豆友”或“豆子”,微博超话社区围绕特定内容对象出现的群体昵称,宛如现实中的村落或社区标识,成为维系用户信息与精神交往的纽带[29]。网络社群也让大众传播时代的媒体读者或观众以可见的形式出现,专职人员通过持续的优质内容服务和活动激励,强化了社群用户与媒体的连结,这些忠实的用户对媒体而言有更多的信任,是媒体品牌化过程中的重要支撑。
在电子商务活动中,品牌忠诚度是经营者关注的重要维度,能够为其带来复购和推荐的销售增长。信任性指标能够衡量在线品牌忠诚度,体现着对产品质量、性能、商家服务等方面可靠性的坚持[30]。经营者通过表明拥有可追溯的交易记录、拥有长时间的经营历史来表露自己,通过提供优惠价格、提供售后反馈或鼓励用户忠诚等方式表明自身与用户建立持续的互动关系的意图和偏好[31]。对于互联网建立的虚拟性和开放性人际交往来说,网络经营者通过增强对用户而言的关系熟悉和环境熟悉程度,以接近现实场景中通过长期人际交往培养的情感联结,激发用户发展信任的可能性。
情感是人们应对不完备信息和不确定性的方案,人们在对被信任者行为动机和能力的感知和归因中,充满了情感的影响。信任涉及对信任对象的认知熟悉程度,熟悉不仅意味着可以捕获更多的信息有利于综合分析,熟悉也伴随着积极情感,尤其是过去良好的交往经历让人们对建立信任关系更加乐观[13]。网络为人们创造了匿名生存的条件,挑战着由先赋性的地缘、亲缘维系的熟悉感,以及从持续互动中获得的积极情感,但信任建立的情感路径在新的情景下被应用,使得关系连结相对牢固。
(二)互联网改造人际沟通的情感基础
信任发展的情感路径依赖于人际互动过程建立的情感基础,而这一基础在网络环境下有所变化。互联网影响人际沟通的情感基础进而对信任发展产生的促进或限制性影响,在已有研究中存在不一致。例如Rockmann与Northcraft在一项关于社会困境中的合作与背叛的研究中发现,与面对面相比,由计算机中介的沟通中参与者认知信任和情感信任水平都处于较低水平,欺骗的可能性却更高[32]。这是由于网络互动缺乏面对面交流中的手势、眼神和面部表情等方面的身体暗示,人们需要在缺乏情感基础以及行为线索的情况下,基于有限信息对他人作出判断。
但不同的是,Walther的社会信息处理理论认为,人们倾向于根据自己的愿望,乐观地去填补信息空白,在网络环境下表现出比在面对面时更高的亲和力[33]。并且,个人在视觉匿名和以文本为主要方式沟通的情况下,也会更加主动地向陌生人进行信息表露、展现自己。鉴于自我表露对亲密关系的发展有着重要意义,Joinson认为,网络沟通比面对面交流更容易发展高水平的信任[34]。
相关研究虽然观点相异,但均关注到网络对人际沟通的情感因素及信任建立的影响。相比与现实情境中的人际互动,互联网方便脱离具身化的个体间的交流,也创造了便于个体进行自我呈现和印象管理的各种条件。从信息接受的角度看,网络沟通使得可供用户处理的人际沟通的情感线索缺失;从信息生产的角度看是激发用户参与人际沟通的积极性,以及对他人作出情感表达的可能性,在二者共同的作用下从基于信息判断到给予或收获信任的弹性增强。更有甚者,拥有多重身份“超级个体”,围绕海量频出的互联网内容,短暂而迅速地聚集又退去,创造了一个流动的交流世界,形成“衣帽间共同体”、“狂欢节式”的共同体[35]。例如“搭子”式社交在年轻人群体中流行,垂直细分的、流动的“搭子”关系展现了人们对陪伴的需求和对边界的极力维系,与稳定亲密关系的羁绊与可能的情感消耗形成对比。人们借助网络追逐、接纳着更多样的可能性,由此建立的互动关系便具有较强的流动性,不稳定、也更加易变[29],因而加大了实现以熟知为基础、深化情感连接的互动的难度,人际合作建立特别是持久维系的不确定性增大。
总之,网络中依靠对他人的情感熟识以及可靠性判断决定是否交付信任路径的不再有保障。网络行动者维持时间嵌入性和社会嵌入性的努力或因流动性强的“超级个体”的存在而效果降低。也正是信息信任与人际信任的错位,使得基于判断信息建立信任的过程实质得到凸显。网络互动与其说是高水平信任或信任无法建立的极端,不如说充满了相互的博弈。在这种情况下,信任关系的发展表现出了较强的实现性和反思性,有别于轻信或全不信。
四、规制杂糅化:互联网对信任
形成的制度路径的影响
信任发展的制度影响重在区分不同制度类型的规范方式及适用,并且身处其间的主体对制度规范有所感知,以便顺利行事,同时也存在个人因信任发展的方式与外在的制度规范不一致而陷入信任困境的情况。网络环境囊括了多层次的可能成为信任对象的主体,包括互联网基础设施、网络服务平台、网络信息内容生产者、网络商业与社区服务提供者,网络环境中影响网民信任的既包括正式制度,也有非正式制度的作用。但是无论是了解网络硬件机器还是软件程序的运行,进一步识别其间的规范,对大多数网民来说,网络环境下主体的多样性使得在其间发展信任成为一项复杂的工程,是网民“技术黑洞”与持有的认知理念的综合产物。
(一)法律规制的未知地带
互联网能够以极快的速度传递信息并产生广泛的影响力,但病毒、特洛伊木马、蠕虫、间谍软件等对网络技术系统的可靠性、信息传输的安全性构成重大威胁。各个国家或地区的管理部门保障互联网设施及其运行安全,也对互联网数据传输与内容传播的安全性作出规制。这些来自外部的管理通常以不同位阶层次的法律法规实现,保护互联网实践的同时,也整治打击网络违法行为,保护国家安全。
虽然互联网无国界,但是互联网行动者有明确的国籍、文化和信仰,受到其国家法律的约束和保护。在全球互联主体的背后存在着不同的正式制度,这增加了主体相互间事先明确行动预期的难度。因此,参与网络活动面对互联网基础设施,涉及到人们对保护或监管网络的组织机构的信任。对于网络行动者,不论是网民个人还是法人、非法人的组织,在参与网络活动过程中信任形成或调适的过程,是对法律法规规制之下形成的网络秩序的反应,信任的对象指向社会法律法规及其制定者和执行者。考虑到网络空间互动涉及多个国家或地区,网络交易的管辖权和适用的法律对信任的形成和发展意味着与意识形态存在交织,特别是对于跨国运营的平台主体和信息传播主体而言。《经济学人》在《谁在害怕Tiktok?》的报道中提及,各国政府担心“用户的数据可能会落入不当的控制之中,或者用户观看的内容可能被中国左右”[36],以至于采取封禁命令。可见,对跨国互联网企业特别是其所属监管机构的不信任成为影响使用者网络信息接触和设施应用的关键门槛。与现实环境下制度影响信任发展的路径相比,网络的无边界凸显了契约或法律监管适用的范围,以及监管主体之间可能存在的矛盾。
另外,“代码”广泛却潜在的影响是互联网环境下独特的制度性角色。除传统的专家系统,搜索引擎或各种智能内容生成方式也为人们提供建议。但对拥有强大影响力的平台主体秉持技术中立或者处于技术黑洞的网民来说,并未意识到网络空间“代码即法律”的逻辑。结果是其一,忽略了平台以自身利益出发作出的信息过滤。实际上许多互联网“基础设施”例如谷歌、苹果、脸书等商业巨头,对互联网的控制和影响力不亚于,甚至大于绝大多数政府机构。相比向社会公开的法律规制,互联网企业的商业决策或技术设计变化,对网民或其他市场主体的影响更大且潜在进行[37]。其二,跨国互联网企业与个别政府合作,潜在的对用户进行监控,损害用户或他国政府的权利。例如,2021年由丹麦广播公司公布的美国通过丹麦的互联网电缆监听他国高级政要的“邓哈默行动”报告[38]。2023年5月,中国外交部就制定“全球数字契约”向联合国提交《中国关于全球数字治理有关问题的立场》,提议尊重各国对数据的安全管理权,而且提议信息技术和产品服务供应企业不得非法获取用户数据、控制或操纵用户系统和设备[39]。在具体实践中,无论哪种情况,用户尤其是普通网民个体对影响其互联网行动的制度框架不甚明晰,认知可能的威胁并非易事,从而无法采取准确的行动逻辑。
在信任形成的制度路径之下,以法律为代表的正式制度可被预见,可以帮助个体与虽不属于同一社区但同受制于该正式制度的他人就预先定义的问题范围进行交易,也可对人们可能采取的策略产生明确的事前预期[40]。互联网的技术特质和结构属性,产生了具有拼贴画效应的时空场景,基于固定空间所形成的制度规约在网络空间中面临冲击[41]。法律规制在网络空间的未知地带对于信任主体而言,是由技术系统以及活动主体归属的复杂性带来的。
(二)互惠与竞争的内在价值冲突
除正式制度的规约,网络空间的互动也受到非正式制度的影响。非正式制度是分散的、不成文的规则,它允许人们就范围更广泛的问题建立关系,能够适应不可预见的事件[40]。非正式制度在小群体范围内形成信任关系有较强的适应性,互联网扩大了关系交往的范围,不仅凝聚了具有受到多样文化传统和价值理念影响个体、使之频繁互动,而且网络空间中也存在着内在价值有别的非正式制度。
良善有序的网络空间是网民发展信任的优质环境。互联网有着协同共建、共享互利的性质,也发展了诸多互惠的实践。在网络商业活动中,用户信任他人意见、根据他人反馈的情况做出判断,是基于其他商品或服务使用者的诚实意见的假定。依据Sundaram等人的研究,消费者传播正面和负面口碑的动机,都包含利他主义[42]。在网络社交媒体上,专业新闻机构在新闻生产中引入参与、互动的理念,通过发起共享目标,激发民众参与公共生活的动力和兴趣。例如,加拿大Postmedia媒体公司曾向网民发布数据收集令,采用众筹的方式在社交媒体获取了来自不同省份的600余万条数据,创建可搜索的捐赠数据库并向民众免费开放,方便人们了解政治性捐赠资金的去向。[43]社交媒体上的网络募捐、网络援助、网络运动等实践也屡见不鲜。在应急情况下,基于第三方的公益慈善平台或者网民自制的在线简易互助文档,都体现了互联网共享需求、引导资源流向的作用,也体现着普通网民间或特定群体内的信任关系。此外,网络服务的提供者也利用非正式制度之下信任建立的逻辑,主动为网民提供对自身有利的声誉线索。另一方面,违背互利共享价值的行为主体通常会受到来自网民的声誉惩罚,这正是非正式制度发挥作用的方式[13]。
但是网络空间中不同主体的诉求可能相互矛盾,特别是盈利性主体从网络资源中获取利益,会危及网民对网络知识经验共享互惠价值观的信任。网络商家提供者利用平台确立的评价体系,出现虚假评价或虚假交易的情况,以期在竞争中取得优势。这种情况日益严重,成为超乎许多人意识的普遍问题。基于亚马逊平台的一项研究发现,虚假评论确实有助于提高产品卖家的网络店铺评级和销售量,并且购买评论的卖家通常不是知名品牌,而是那些较小的、鲜为人知的商家通过虚假评论获利[44]。如此获利方式侵蚀商家的道德,损害网民利益,降低人们对网络交易的信任水平。另外,通过不良方式的竞争不仅存在于卖家之间,而且存在于平台之间。例如美团平台曾通过调整其后台参数降低跨平台商户的曝光率,逼迫商户使用其独家服务,对商户以及竞争性平台都产生不利影响。2021年8月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禁止网络不正当竞争行为规定(征求意见稿)》,规定经营者不得采取返现、红包、卡券等方式足以诱导用户作出指定评价、点赞、转发、定向投票等互动行为[45]。尽管市场监管部门注意对违规商家行为加以规范,但部分网民以好评换红包或折扣、与商家互惠的心理使得监管效果难成,表现出网络空间中非正式制度的张力,使得网民可以依据的形成信任的事前预期更加不明确。
结 语
互联网作用于信息生产与获取,使之快速传播和广泛扩散,也作用于围绕信息互动的关系连结,无论是相比面对面沟通抑或传统媒体时代都有所不同。尽管人们也将计算机视为一个社会行动者,但其保密性、可访问、可控制等能力的背后是受到不同制度和非制度因素影响主体。研究不仅使得互联网环境下围绕信息的信任特征更加凸显,而且通过不同的路径呈现出网络影响信任形成的多个维度。
在认知路径之下,是信息对信任过程而言的从可用性到可塑性的变化,其中包括生产传播过程以及信息符号的呈现,这是网络传播创造力和感染力的体现,同时也意味着信息在准确性和清晰度上存在着被质疑的空间。在情感路径之下,是信任依托的关系稳定性增加了关系的实现性特质,一方面培养熟悉感的网络设置让网民方便嵌入到关系互动中,另一方面关系流动使得基于信息判断到给予或收获信任的弹性增强。在制度路径之下,是信息主体被规制形式的边界由清晰到杂糅的变化,包括正式制度性作用的碰撞,也包括内在价值有别的非正式制度逻辑的互动。即使在网络已普及应用的情况下,无论是表层的信息呈现,还是潜层的技术运行保障和信息主体关系,对网民来说都存在不确定的风险,正是以上三个路径的变化综合体现了网民面对的信任环境。
参考文献:
[1]HIRSCHMAN A O. Against parsimony: Three easy ways of complicating some categories of economic discourse[J]. Bulletin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Arts and Sciences, 1984, 37(8): 11-28.
[2]SELIGMAN A B. The problem of trust[M].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0: 318.
[3]METZGER M J, FLANAGIN A J. Credibility and trust of information in online environments: The use of cognitive heuristics[J]. Journal of Pragmatics, 2013, 59: 210-220.
[4]FLEW T, JIANG Y. Trust and communication: Looking back, looking forward[J]. Global Perspectives, 2021, 2(1): 25395.
[5]翟学伟.中国人的社会信任——关系向度上的考察[M].北京:商务印书馆,2022:324,337-341.
[6]王辉,金兼斌.媒介接触与主观幸福感——以政治信任为中介变量的实证研究[J].新闻大学,2019(7):1-15.
[7]CHESHIRE C. Online trust, trustworthiness, or assurance?[J]. Daedalus, 2011, 140(4): 49-58.
[8]谢金文,王健美.社会信任的多学科研究及其影响[J].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12):63-73.
[9]TAMILINA L. A brief overview of approaches to defining social trust[EB/OL].(2018)[2022-11-13]. https://mpra.ub.
uni-muenchen.de/96510/2/MPRA_paper_96510.pdf
[10]葛忠明.信任研究中的理性主义分析范式——兼谈公共非营利合作关系中的信任问题[J].东岳论丛,2015(7):19-23.
[11]LEWIS J D, WEIGERT A. Trust as a social reality[J]. Social Forces, 1985, 63(4): 967-985.
[12]唐琪,唐兴霖.信任结构变迁的逻辑——基于社会变迁的视角[J].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13(2):39-45.
[13]NOOTEBOOM B. Social capital, institutions and trust[J]. Review of Social Economy, 2007, 65(1): 29-53.
[14]MURPHY J T. Building trust in economic space[J]. 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 2006, 30(4): 427-450.
[15]界面新闻.抖音强力“打假”:处理319万条不实信息,处置效率提升232%[EB/OL].(2022-8-17)[2023-
3-10]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413945470531
98318&wfr=spider&for=pc.
[16]曾凡斌,程小妹.十八大以来网络事件的分类、诱因、表现与结局[J].广州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9(1):74-86.
[17]BURBULES N C. Rhetorics of the web: Hyperreading and critical literacy[M]//SNYDER I. Page to Screen: Taking
Literacy into the Electronic Era. London: Routledge, 2003: 102-122.
[18]张克永,李宇佳,杨雪.网络碎片化学习中的认知障碍问题研究[J].现代教育技术,2015(2):88-92.
[19]RICE R E, LOVE G. Electronic emotion: Socioemotional content in a computer mediated communication network[J]. Communication Research, 1987, 14: 85-108.
[20]MESSARIS P, ABRAHAM L. The role of images in framing news stories[M]//Reese S D, Gandy O H, Grant A E. Framing public life. New Jersey: Erlbaum, 2001: 215-226.
[21]HAMELEERS M, POWELL T E, MEER V D, et al. A picture paint a thousand lies? The effects and mechanisms of multimodal disinformation and rebuttals disseminated via social media[J].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2020, 37(2): 281-301.
[22]澎湃新闻.俄乌战火纷飞,小心被这些假消息混淆视听[EB/OL].(2022-2-26)[2023-3-25].https://m.thepaper.
cn/newsDetail_forward_16872756.
[23]白淑英.网络互动中人际信任概念辨析[J].学术交流,2004(12):119-122.
[24]广州日报.警方通报阿里女员工事件情况:嫌疑人涉嫌强制猥亵罪[EB/OL].(2021-8-16)[2023-4-2].https://
gzdaily.dayoo.com/pc/html/2021-08/16/content_875_765
829.htm.
[25]澎湃新闻.阿里价值观滑铁卢:职场中的性别霸凌和绩效暴力[EB/OL].(2021-8-12)[2023-4-10].https://m.
thepaper.cn/wifiKey_detail.jsp?contid=13997951&from=
wifiKey#.
[26]凤凰周刊.川大女生事件,一场被“流量密码”反噬的网暴[EB/OL].(2023-6-13)[2024-5-20].https://mp.weixin.
qq.com/s/jfVYY7_UXI9tPiln3XxEGA.
[27]观察者网.反转?!大妈怒骂cosplay女孩,竟是商业炒作?[EB/OL].(2017-8-12)[2024-5-19].https://mp.weixin.
qq.com/s/HsJI9HTuS_siCUPFgMlV1w.
[28]Pew Research Center. Bots in the Twittersphere[EB/OL].[2023-4-13].https://www.pewresearch.org/internet/wp-
content/uploads/sites/9/2018/04/PI_2018.04.09_Twitter-
Bots_FINAL.pdf.
[29]陈梓鑫,闫玉荣.流动的现代性视角下社交媒体用户的身份认同建构——基于侠客岛微信群组互动的考察[J].中国社会心理学评论,2022(2):225-243.
[30]鲍林.在线品牌忠诚度的测量指标体系研究[J].江苏商论,2010(7):122-123.
[31]RIEGELSBERGER J, SASSE M A, MCCARTHY J D. Trust in mediated interactions[M]//JOINSON A, MCKENNA K Y A, POSTMES T, et al. Oxford handbook of internet psycholog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53-70.
[32]ROCKMANN K W, NORTHCRAFT G B. To be or not to be trusted: The influence of media richness on defection and deception[J].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and Human Decision Processes, 2008, 107(2): 106-122.
[33]WALTHER J B.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 Impersonal, interpersonal, and hyper personal interaction[J]. Communication Research, 1996, 23(1): 3-44.
[34]JOINSON A N. Self-disclosure in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 The role of self-awareness and visual anonymity[J].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2001, 31: 177-192.
[35]齐格蒙特·鲍曼.流动的现代性[M].欧阳景根,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325-326.
[36]The Economist. Who’s afraid of TikTok?[EB/OL].[2022-
7-7].https://www.economist.com/leaders/2022/07/07/whos-
afraid-of-tiktok.
[37]左亦鲁.超越“街角发言者”:表达权的边缘与中心[M].北京:社科文献出版社,2022:207.
[38]央视新闻.美国窃听欧洲盟友,丹麦何以成为帮凶[EB/OL].(2021-6-7)[2023-5-3].http://m.news.cctv.com/
2021/06/06/ARTIK5eOWdSbrus1YwI9n4pp210606.shtml.
[39]外交部.中国关于全球数字治理有关问题的立场(就制定“全球数字契约”向联合国提交的意见)[EB/OL].(2023-4-30)[2023-5-15].https://www.mfa.gov.cn/web/
wjb_673085/zzjg_673183/jks_674633/zclc_674645/qt_67
4659/202305/t20230525_11083602.shtml.
[40]FARRELL, H. Trust and political economy: Institutions and the sources of Interfirm cooperation[J].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2005, 38(5): 459-483.
[41]姜楠,闫玉荣. 场域转换与文化反哺:青年群体与变迁社会的信息互动[J].当代青年研究,2020(2):39-45.
[42]SUNDARAM D S, MITRA K, WEBSTER C. Word-of-Mouth
Communications: A Motivational Analysis[J]. Advances in consumer research, 1998, 1: 527-531.
[43]Postmedia. Political Donations Database allows Canadians to Follow the Money[EB/OL].(2018-3-20)[2023-5-15].
https://www.postmedia.com.
[44]HE S, HOLLENBECK B, PROSERPIO D. The market for fake reviews[J]. Marketing Science, 2022, 41(5): 896-921.
[45]法治日报.距离好评返现绝迹还有多远[EB/OL].(2021-
11-23)[2023-5-8].http://epaper.legaldaily.com.cn/fzrb/
content/20211123/Page06TB.htm.
Building trust: the impact of three-folded paths of trust formation by the Internet
YAN Yu-rong1, CHEN Zi-xin2
(1.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Northwest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Xi'an, Shaanxi 710122;
2. Institute of Media and International Culture,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Zhejiang 310022)
Abstract: Trus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the realization of social and economic goals and individual life and is strongly linked to information acquisition and information judgment. Existing literature emphasizes the impact of new media on trust and significance of disseminator characteristics on trust, studying the role of the Internet with its technical features and relation structure under different path frameworks formed by trust. The impact of the Internet on trust is reflected in three aspects: On cognitive path, the impact of information on the trust process is from the usability to the deformability; On emotional path, relation stability relied by trust is added by relation realization; On institutional path, the boundary regulated by information bodies is from clearness to mixture. This study highlights the importance of information to trust formation in digital world. The changes in the above three paths comprehensively reflect the environment of trust netizens live in.
Key words: Internet communication, trust, cognitive path, emotional path, institutional path
收稿日期:2023-12-17
作者简介:闫玉荣,女,山西晋中人,西北政法大学新闻传播学院讲师,博士后研究员。
陈梓鑫,女,河南驻马店人,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传播所在读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