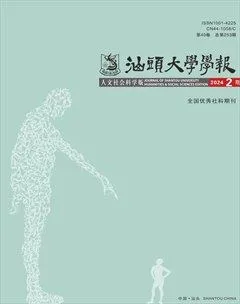万世学者之正鹄
摘 要: 《御选唐宋文醇》是由乾隆帝御选的古文选本,引导、规范了乾隆朝的古文选本方向。乾隆帝在《御选唐宋文醇》中肯定韩愈、赞扬韩愈、维护韩愈,将韩愈作为儒家道统的典范,将韩文作为“醇文”的正面典型,为士人树立了学习的典范。《文醇》选入的岭南韩文,在肯定韩文艺术成就的同时,赞扬了韩愈为官岭南的政绩,肯定了韩愈对人民的教化作用。乾隆帝对于岭南韩文的批评也显示了对于边疆治理的政治思考。
关键词:《御选唐宋文醇》;韩愈;古文选本;岭南;批评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4225(2024)02-0021-08
《御选唐宋文醇》初刊于乾隆三年,所有的选编工作都是在乾隆帝弘历的指挥下进行的,其编选目的在于纠偏和垂范。《文醇》是在储欣《唐宋十大家全集录》的基础之上进行的重选本和增选本。乾隆帝认为储欣编选《唐宋十大家全集录》“识未衷、见未当”,与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钞》无大差别,并未能改变其“便于举业”的基本倾向。《文醇》更新了编选理念,对《全集录》进行了纠偏,强调宗经重道,不再强调“举业”。乾隆帝编选《御选唐宋文醇》,“用以昭示艺林,洵足为万世学者之正鹄矣”[1]。《御选唐宋文醇》与文风建设[2]、官方思想[3]、文化体制[4]、文化政策[5]的关系,以及《御选唐宋文醇》的古文观[6],已有相关研究成果。但对《文醇》中作家地位的高下,《文醇》批评话语权力对作家地位的建构等相关问题目前没有深入讨论,本文选取《文醇》中的韩愈进行研究,论述《文醇》中韩文典范地位的形成过程,并指出岭南韩文的特殊文化含义。韩愈作为十家之首,“夫文自昌黎起八代之衰,为其去排偶苶弱之习,而返之于先秦两汉之遗法”是《文醇》批评的重点,乾隆帝对韩愈的批评,起着引导“操觚之士向方”、纠正“为文之矩矱”的重要作用。
一、《文醇》对韩文的选评情况
《御选唐宋文醇》①共五十八卷,选文474篇。卷一至卷十为韩愈文章,共选入99篇。韩愈文卷数占全书17.24%,韩愈文篇数占全书20.89%,列于十家首位。《文醇》所收韩愈文文体种类也最为丰富,共有十五种之多,分别是杂著24篇、书14篇、启1篇、序19篇、记4篇、议1篇、状2篇、表2篇、实录1篇、祭文8篇、哀辞1篇、碑6篇、碑铭3篇、墓志铭10篇、杂文3篇。九十九篇入选文章中,选入篇数最多的是杂著、序、书、墓志铭四类,共六十七篇,已超过总数的五分之三。杂著、序、书、墓志铭也正是韩愈古文的菁华所在。《文醇》中的韩愈文章,篇篇皆有评点,其中乾隆帝本人御评就有49篇,可见乾隆帝对韩愈文章的重视。乾隆帝在为《御选唐宋文醇》作序时就说到:“昌黎韩愈,生周汉之后几五百年,远绍古人立言之轨,则其文可谓有序而能达者。”[7]序可见乾隆帝对韩愈文章十分推重。在《文醇》中,无论是位次,还是卷数、篇数,甚至是文体种类、评点,韩文都是重中之重。
《文醇》的评论体系分为三个层级:第一层是“圣祖仁皇帝御评”,“用黄书恭载篇首”,“以昭异代儒臣千古之至荣。”[7]凡例一第二层是“皇上御评则朱书篇后。”[1]第三层是“至古今人评跋,及诗文论说,于文有所发明者,亦别色附录于后。”[1]参照具体评点,康熙帝御评为黄色,位于文章开头;乾隆帝御评为红色,位于文章结尾处;他家评点为蓝色,又排在乾隆御评之后。至于勾画圈点,《文醇》用连圈“。。。。。。。”于文章关窍佳句之处进行标注,以连点“、、、、、、”点名文章脉络,以“—”界划文意。《文醇》对文章的评论均采取总评的形式,没有文中夹评。《文醇》所收韩文,篇篇有点、篇篇有评。其中康熙帝御评有17条,占韩文总数的17%;乾隆帝御评49条,占韩文总数49%;他家评论50条,占韩文总数50%。
需要说明的是,《文醇》中的朱评(乾隆帝)虽然是评论重点,但黄评(康熙帝)和蓝评(他家)同样不可忽视。黄评和蓝评是朱评的重要补充。从侧重点上来讲,黄评(康熙帝)评论笔法,朱评(乾隆帝)强调重道宗经,蓝评(他家)主要是文献考证。黄、朱、蓝三种评点三位一体,分别从文章、道德功业以及文献考证的角度进行评论,对韩愈文章进行了全方位、立体化的分析,全面揭示了韩愈及其文章的价值。
二、《文醇》中韩文的三方评论
《文醇》中存在康熙帝、乾隆帝及其他评论家三个评点主体,三个主体对韩文的评点各有侧重。鲁迅有言:“选本可以借古文的文章,寓自己的意见。”[8]同理,选入《文醇》的另外两种评论文字实际上也是经过乾隆帝拣择的,与乾隆帝自身御评相互映衬,共同构成了《文醇》的批评话语体系。
在黄、红、蓝三类评论文字中,黄评(康熙帝御评)简洁明快,具有即兴评点的特点。在评论内容上,黄评(康熙帝御评)也更偏向于文风、用笔、词句等具体事项。如康熙御评《师说》:提一“道”字为主,识解最高,而用笔尤极其古峭[7]卷一;《答刘正夫书》:于朴茂中独见风骨[7]卷四;《答吕毉山人书》:谈兵事文,英气勃发。西汉晁错、赵充国每以此擅长,斯文近之[7]卷四;《魏博节度观察使沂国公先庙碑铭》:叙文简质,铭词古奥。古奥处可及,简质处不可及[7]卷九。由黄评可知,康熙帝更欣赏韩文的文笔、文风、结构、气韵、法度、境界等文章要素,对于韩文,康熙帝是从比较纯粹的文章学角度来评判的,要言不烦,简洁精当。
《文醇》中的黄评(康熙帝御评)位于文章篇首眉批处,是批评总纲。在批评形式上,朱评(乾隆帝御评)、尤其是蓝评(他家评论)是配合黄评(康熙帝御评)展开的。首先来看乾隆帝御评(朱评)。乾隆帝御评对于康熙帝御评的配合表现在:一、乾隆帝评点了康熙帝所不及的篇目。如朱评《爱直赠李君房别》:纡徐委折,以扶友于直,善辞哉[7]卷二;《上巳日燕太学听弹琴诗序》:文、意固两具之[7]卷四;《为裴相公让官表》:文实能写度心曲。碧血荧荧,光出楮墨,而辞气浑浩流转,足为千古表笺法式[7]卷六。上述篇目,均是黄评(康熙帝御评)所不及的文字。对于康熙帝御评韩文的缺略之处,乾隆帝进行了自己的补充。康、乾两代帝王对于韩愈文章文风笔法的肯定,奠定了《文醇》中韩文古文正宗的地位。二、乾隆御评对于康熙御评所未涉及的内容批评进行了详细补充和阐发。对于同一篇文章,黄评和朱评的批评重点完全不同。相较于康熙御评,乾隆御评更详细,也更注重对韩文的阐发和引申。如《争臣论》,康熙帝御评仅为有“一解一难,开阖有法”八个大字,乾隆帝御评则字数过千。在上千字的御评之中,乾隆帝首先引用并驳斥了欧阳修对于阳城的批评,认为“修之为此言,以警当时突梯脂韦,自托于阳城,待事后谏之徒也。然所以訾城者,得无未察其心欤?”[7]卷二乾隆帝认为阳城身为言官绝少进谏(七年之中仅进谏二次)并非尸位素餐,而是仔细考量唐德宗朝政治生态之后的谨慎做法。乾隆帝对于欧阳修评论阳城“岂无一事可言,而需七年邪”的反问提出了批评,认为“城为谏议七年,德宗失政虽多,安有更急于此二事(廷论陆贽、沮延龄作相)者?”乾隆帝认为欧阳修对于阳城的批评是“诚未论其世也”的缘故,在否定欧阳修观点的基础上,乾隆帝对阳城做了翻案文章,一改欧阳修对于阳城的否定基调而对阳城肯定到“唐之不亡于德宗之手,孰非城之力哉?”进而推原韩愈作《争臣论》的本意:“迨顺宗初年,城已死,愈为《实录》,其中特立传者三人,陆贽、阳城、张万福,详书其谏德宗事。是愈于其时,已晓然有以知城之心”。乾隆帝主张以公正客观的态度评价阳城:“后人又何必伸愈而绌城哉?”在此基础上乾隆帝又扩展到对于“退之为史官不敢褒贬而柳子厚作书以责之”之类“子厚之责退之亦犹退之之责阳城”的如何评价历史人物的话题,认为“泥迹而求未有不大谬”,对待历史人物应该采取谨慎严肃的态度,不能妄下论断。乾隆帝认为“退之之不敢以孔子自任而不为史也,亦犹阳城之不敢以伊、周自任而不妄谏也”,均是严谨处事的表现,进而对韩愈本篇《争臣论》的写作做了最终判断:“退之达作《争臣论》时,犹未若为史官时之明达也”,认为文中韩愈对于阳城的责难有偏颇之处。但若抛开事实,仅就态度而言“退之责谏臣,子厚责史官,砥砺臣节,而羞素餐之徒,岂非直、谅、多闻古之益友哉?”最后乾隆帝给出了阅读韩愈《争臣论》时的正确态度:“尚友古人者,胥当三复其言,不必索瑕求瘢,好为虐古之论也。”由乾隆帝御评《争臣论》一则可以看出,乾隆帝力图在考辨史实的基础之上还原历史人物的本来面目,进而推原韩文的写作情景及写作态度,强调要以客观严谨的态度阅读韩文、以严肃认真的态度对待历史人物。借由《争臣论》评点可以看出,乾隆御评与康熙御评存在相当大的差别。康熙御评是即兴的、印象式的,偏重于评价韩文笔法;乾隆御评是严肃的、系统的,强调知人论世,更注重韩文的内容及读法。乾隆御评重视文章的阅读理解,康熙御评注重文章的文笔写作,朱评是对黄评的补充,也是对黄评的进一步深入。
其次,他家批评(蓝评)也是对黄评(康熙帝御评)和朱评(乾隆帝御评)的重要补充。《文醇》中的蓝评是古今人评跋及诗文论说,“皆取其于文有所发明者”[7]凡例四,既是对两代帝王御评的重要补充,也是对韩文的进一步阐释。通计蓝评涉及52家,唐3家、宋27家、元1家、明16家、清5家,所收宋、明两代评论最多,这也从侧面反映了《文醇》主要吸收了宋明评点家对于韩文的评论。在前人对韩文的接受、评点及经典化的基础之上,康、乾二帝(尤其是乾隆帝)的意见对前人意见的吸收、批驳和升华是值得注意的。
《文醇》中韩文的蓝评(他家评论)对于黄评和朱评的补充表现在:一、篇目上的补充。对于康乾二帝未予置评的韩文,他家评论(蓝评)起着补足的效果。如《杂说一》就采取了康熙朝李光地的评论:“此条寄托至深,取类至广。精而言之,则如道义之生,气德行之,发为事业文章,皆是也。大而言之,则如君臣之遇合、朋友之应求,圣人之风兴起于百世之下,皆是也。”[7]卷一《读荀》《读鹖冠子》《获麟解》等同样如此。二、蓝评与黄评的互相补充。康熙帝御评(黄评)主要是从文章鉴赏的角度,对韩文文笔、文风、结构、气韵、法度、境界等进行表彰和揭示。而《文醇》所选入的他家评论(蓝评)主要是从韩文的写作背景及写作目的方面对韩文创作进行揭示和补充。如对于《师说》,黄评(康熙帝御评)道:“提一‘道’字为主,识解最高,而用笔尤极其古峭”,是从见识和笔法方面来讲的。而蓝评(他家评论)则采用了洪迈的说法。洪迈将与韩愈《师说》相关文本进行了补充说明,并对韩愈“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的本意进行了辨析,得出了韩愈“非好为人师者也”的结论。同样地,对于《守戒》康熙帝御评肯定的是文章的格局和气韵;而朱熹评论讲述的是《守戒》的创作原因及后续结果。康熙御评(黄评)和他家评论(蓝评)一直接、一间接,黄评引导读者欣赏韩文的见解、结构和笔法,蓝评还原韩文的具体写作情境,两种评点文字相互配合,将韩文的阅读引向深入。三、蓝评与朱评的相互配合。不同于康熙帝对韩文提纲挈领式的评点,《文醇》中乾隆帝的朱评可谓洋洋洒洒,有些朱评字数几与韩文原篇相埒。从乾隆帝对其祖父康熙帝推重的角度来讲,朱评和蓝评都是对于黄评的补充。但实际上,朱评才是《文醇》评点的主体,内容上较黄评和蓝评细致得多。乾隆帝御评韩文时最突出的特点在于独到的见解和论断,这与他家评论(蓝评)补充写作背景、考辨创作意图的客观评价有显著的差异。如对于《伯夷颂》,蓝评仅仅引用了王安石对于伯夷事迹的推论,而乾隆帝朱评则在蓝评的基础上深入了一层,对于王安石的观点进行了进一步的批评。乾隆帝首先肯定了王安石对于伯夷事迹的考证:“王安石谓伯夷、叔齐扣马而谏、采薇而食、饿死首阳诸事,皆无有者。据《孟子》以驳《史记》,亦具有见。”接着引用了朱熹对王安石观点的看法:“荆公之论,与此《颂》正相反。学者审之。”进而对朱熹的言论进行了进一步的思考:“朱子之言,或为引而不发,或为疑事毋质,皆未可知。”最后乾隆帝表明了自己的论断,在前人观点的基础上,乾隆帝引申出了对君子“求同存异”的深入看法,伯夷降周这一历史争议事件也成为圣人知行合一的典型教材。乾隆帝敢于下判断并且勇于下判断,蓝评位处朱评之前,从形式上讲是朱评的重要补充,但从内容上讲,朱评则是对蓝评的深入阐发。
最后,在韩文评点的篇目上乾隆帝御评具有避熟趋新的特点。乾隆帝尽量避开名篇熟篇,不与黄评、蓝评重复评论。从数据上来讲,乾隆帝御评韩文49篇,与康熙帝御评(黄评)重复的仅《争臣论》《送郑尚书序》《送水陆运使韩侍御归所治序》《魏博节度观察使沂国公先庙碑铭》4篇;与他家评论(蓝评)重复的仅《伯夷颂》1篇。从具体篇目上来说,乾隆帝对于韩文名篇不直接评论,而是通过对黄评和蓝评的择选间接地加以评价。如韩文名篇《获麟解》《进学解》《师说》《送孟东野序》《禘袷议》《论佛骨表》《祭十二郎文》《平淮西碑》《南海神庙碑》《柳子厚墓志铭》《鳄鱼文》《送穷文》《毛颖传》等,乾隆帝均不加评论,体现了乾隆御评对韩文名篇的有意回避。这一点从乾隆帝对《答李翱书》和《与李翱书》的处理中可以明显看出来。《答李翱书》是一篇书信体的论说文,韩愈在文中叙述了自己学习古文的三个阶段,并且提出了著名的“气盛言宜”的主张。《与李翱书》纯是朋友间的书信,信中韩愈向李翱诉说自己暂不能回京的苦衷。《答李翱书》的重要性毋庸赘言,就连康熙帝都评价道:“好学深思,读书养气,昌黎一生得力,略尽此篇。”[7]卷三然而就是这样一篇重要的文章,乾隆帝却不加评论,反而却对《与李翱书》有详细阐述。乾隆帝选评《与李翱书》的着眼点在于:“录此,与后《上张仆射书》并读,知昌黎虽困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至于如此,而曾不以纤毫非义屈,益以见其平日所云实之美恶、其发不掩者,诚笃论也。”对于韩愈在信中对于箪食瓢饮的抱怨,乾隆帝认为韩愈是“出于一时困苦之怀”的牢骚,“其言不可为典要”。读者对待韩愈此文的正确态度应该是“师其意,勿师其辞;匪特不得以昌黎言疑颜子,亦不得以昌黎言疑昌黎也。”[7]卷三乾隆帝在此坚持了“知人论世”和“不以辞害意”的严谨批评态度,发明了《与李翱书》的内在价值。
三、《文醇》对韩文典范的建构
《御选唐宋文醇》对韩愈文章十分推重,其对韩愈文章的称许表现为肯定韩愈、赞扬韩愈以及维护韩愈三个方面。乾隆帝肯定、赞扬、维护韩文的过程也是《文醇》中韩文典范地位确立的过程。
首先,乾隆帝肯定韩文的思想价值,强调韩文的社会意义。第一,充分肯定韩愈对于社会问题的看法,发掘韩文的社会性意义。在评《原毁》时,乾隆帝说到:“(韩愈)既穷其情状,又抉其本原,如大禹铸鼎,使民知神奸。其于天下后世,所以诏告而警戒者,深矣。”[7]卷一在乾隆帝看来,《原毁》不仅仅是一篇文字,而是警世之文。韩愈对毁谤的阐发和论证,对于社会治理有重要的参考意义。对于《杂说四》(即《马说》),乾隆帝将其总结为“知人”问题,认为“诚能知人,将治天下如运之掌矣”。人才与国家的关系如此密切,然而“人固不易知,知人固不易易”。乾隆帝十分肯定韩愈此文的社会意义,认为“三复斯文,慄然冰渊,惄如调饥。”[7]卷一乾隆帝选录韩愈《圬者王承福传》与《太学生何蕃传》认为王传记言、何传记事,王传所写“其言有足警鄙夫之事君,明天之不假易,而民生之不可以媮,不可以无传”[7]卷二,何传“爰于卒章,告万世以立言之意”,韩愈所强调的“凡贫贱之士必有待然后能有所立”[7]卷二才是士人立身处世的准则。在评价《赠张童子序》时乾隆帝也说:“务力于学,以成其人,毋使斯世目为尤物焉可也。”[7]卷四强调的也是人才的自我修养问题。对于韩愈的碑版之文,乾隆帝则注重阐发其表彰忠孝、劝诫世人的内在意蕴。韩愈《袁氏先庙碑》,乾隆帝直接指出韩愈意在表孝而非扬忠:“(袁)滋盖谨愿之士,不能达大道忘身为国。故韩碑著其孝,不言其忠。”[7]卷八对于韩愈《魏博节度观察使沂国公先庙碑铭》,乾隆帝认为“(田)弘正父子祖孙三世,皦然泥而不滓,竭其股肱之力,加之以忠贞,不济则以死继之。以垂光于青史,良不愧昌黎‘世忠孝’一语也。”[7]卷九对于《唐故相权公墓碑》,乾隆帝认为“昌黎为推其(权德舆)父皋贞孝之贻,一篇之中三致意焉。其劝善之意,微哉!”[7]卷九对于《考功员外卢君墓铭》,乾隆帝云“‘四夔’者,名士标榜陋习,非其实也。昌黎此文,隐而显矣”[7]卷九,认为韩愈此文意在讽刺互相标榜的陋习。第二,肯定韩愈对于国家治理问题的看法,认为韩文对于国家治理具有重要的警示作用。韩愈创作《对禹问》对传贤与传子这一政治权利交接的关键问题进行了论述,认为从人事来谈论尧、舜传贤与禹传子均为明智之举。乾隆帝认为韩愈对于传贤与传子的制度性考察“实能补孟子之所未言”[7]卷一。乾隆帝指出《上宰相书》“固是昌黎少作,然说《诗》义极湛深,其道先王兴贤育才之意甚明切。宰相而能如是,可谓举职矣”[7]卷九,从中可以体会人才选举的重要性,对于科举和教育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通过韩愈《赠崔复州序》,乾隆帝读出了治国之道:“欲为君尽君道,欲为臣尽臣道,当于此等文字,反覆循环,推类以尽其余,庶几赤子得养于其父母乎!”[7]卷四在此韩文具有了政治教材的色彩。《石鼎联句诗序》则是“盖深晓世人以弥明非神仙,而神仙之说诚荒唐也”[7]卷五,是对成仙求仙的讥刺。观《蓝田县丞厅壁记》“唐时州县之治可知也”[7]卷六,可做历史政治的参考。碑记体的《衢州徐偃王庙碑》,也可以从政治历史角度加以阐发:“昌黎述此,盖以唐德既衰,泽不下逮,藩镇不臣,往往呕咻兵民、规窃土地,死则子弟自代而请命于朝,托以兵民。安己之政,有若天与人归者然。故昌黎举偃王之不忍斗其民,弃国走死,以全臣节,以国易仁、为笑于顽;而其后世子孙,硕大蕃衍,经越数千年,而庙祀如始祔之时……所以警动怵詟之者,旨深哉!”[7]卷八韩愈在《殿中少监马君墓志》“不乐其生,而发《诗》人‘尚寐无讹’之叹”,在乾隆帝看来也“岂专为马氏言哉”[7]卷九,也可以以文观政。
其次,赞扬韩愈本人的道德品行及其对于道统文统的建设。乾隆帝对韩愈本身的道德品行非常推崇,在评论韩文时不时会出现赞扬韩愈的句子。如读韩愈《五箴》评价道“坦坦荡荡,而非有所恐惧疑惑而动其心也。君子之心,本如是欤!”[7]卷二读《后汉三贤赞》则认为韩愈“其行事亦骎骎相似,故赞之以明己意也”,文是余事,“唯别有意在言外”[7]卷二。《与崔群书》赞叹道:“昌黎之言,截断先后,专责现今之合天与否,诚达于天道笃行君子也。”[7]卷三除德行之外,乾隆帝更赞扬韩愈对于文统道统所做的贡献。在评价《杂说三》时,乾隆帝说“(韩愈)述孟子‘几希’之旨,开濂洛关闽之先”[7]卷一,突出了韩愈“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的先驱作用。评《读仪礼》时又云:“此韩愈所以读《仪礼》而谓‘今无所用’,顾犹有爱于圣人之制度者也。欲本三代之遗意,以为天下国家必衷之于忠,以求天理民彝之自然,期忠得而渐具其质,或庶几焉。”[7]卷一关注的是韩愈对儒学礼仪制度的维护和继承。《答尉迟生书》云:“昌黎未尝言《易》,而深得乎《易》之义。其云‘实之美恶,其发也不掩’,可为探本穷源矣。”[7]卷三《与冯宿论文书》云:“昌黎之于文,于此实深喻之;深喻之,则艺也进乎道矣”[7]卷四,强调韩愈文道合一。在《答吕毉山人书》中,乾隆帝更直接将韩愈作为儒家道统承上启下的关键人物:“唐承晋魏之后,六经晦塞。昌黎思扫其榛芜,务张而明之,旁搜远绍,孤而无邻,故每以颜子得圣人为依归,则箪瓢自乐为易易,深悲己之不得所依归也。……设与程、朱生同时,则其所造诣,必更有进。……若其裁山人之狂简,竭益友之直谅,声出金石。胸罗羲娥,又磊落而英多哉!”[7]卷四评《太原王公神道碑铭》时则点明韩愈对于文统的接续:“数语曲尽历来人文凋敝、六经榛塞之故矣。……昌黎揭之,以激励后学,所谓‘吏部文章日月光’欤!”[7]卷九
最后,对于韩文存在争议及误读的地方,乾隆皇帝仔细进行辨明,并且对韩愈进行坚决维护。如程颐认为韩愈《读墨子》“孔墨相用之说为甚不可”,以墨学混淆了儒学。朱熹也认为“学者必知孟子‘归斯受之’之意,然后识公读《墨》之旨”。客观上韩愈对于儒墨的态度比较含混,所以存在误读的情况。乾隆帝认为韩愈与孟子对待儒、墨的态度并不相悖,极力维护韩愈:“盖韩愈之意,悯后世经生,家各务售其师之说,而不求诸心,不衷于理,距杨墨于门墙之外,而为杨墨于门墙之中。外犹恃其中之存,中则无复外之迹象,其为害也,更有甚焉。是以著说以矫之,岂果贤墨而与孟子相剌谬哉!”并进一步说到:“况夫墨为孔用,则其墨亦孔;孔为墨用,则是孔非墨。”[7]卷一与其说这是韩愈《读墨子》的观点,不如说是乾隆帝的观点,从中可以看出乾隆帝对于韩愈观点的补充和维护。乾隆帝强调韩愈不违孟子的说法不止此一处,还可以从《与卫中行书》的评论中看到。对于韩愈在《与卫中行书》所表达的穷通祸福观念,石大任认为:“韩愈谓贵与贱、祸与福存乎天。”乾隆帝认为石氏是误读了韩愈文章,对此乾隆帝批评道:“斯言也,不特未达昌黎之旨,盖亦未达孟子之旨也。”乾隆帝进而维护韩愈:“昌黎谓‘穷通之来不接吾心’,岂不约而易行哉?安在其为与孟子剌谬也!”对于韩愈与孟子观点不甚相合之处,乾隆帝也辩解到:“诚以昌黎之心,行孟子之言,左盾而右矛,各得其用也。”对于借孟子攻击韩愈的做法,乾隆帝进行了严肃的批评:“乃必以孟子之矛,刺昌黎之盾,夫矛之设,岂为刺己之盾而然哉?”[7]卷三同样的观点在评论《与李翱书》时再次出现:“匪特不得以昌黎言疑颜子,亦不得以昌黎言疑昌黎也。”[7]卷三在乾隆帝的批评语境中,韩愈是与孟子、颜渊等儒学宗师同等的人物,其权威性不容置疑。在评论《争臣论》时,乾隆帝对韩愈的维护有进一步的表现。林少颖对《争臣论》中韩愈责阳城的行为评论到:“退之讥阳城,固善矣;及退之为史官,不敢褒贬,而柳子厚作书以责之。子厚之责退之,亦犹退之之责阳城。”林氏将韩、柳二人责人的行为进行类比,认为性质相同,实是较为客观的看法。乾隆帝则认为林氏“目见泰山,不见眉睫……以此绌阳城,并绌韩愈,则更为好议论之过也。”在乾隆帝看来林氏将韩柳二人进行类比,会消解韩愈的权威。乾隆帝说:“退之之不敢以孔子自任而不为史也,亦犹阳城之不敢以伊、周自任而不妄谏也,可轻议之哉?”进而认为“柳子厚之学,不可与退之絜也,明矣。”[7]卷二韩、柳二人同样性质的责难行为,在乾隆帝这里却有高下之分。乾隆帝肯定韩愈责阳城,却否定柳宗元责韩愈,认为柳宗元对韩愈的责难是苛责、妄责,甚至认为柳宗元之学不如韩愈,其吊诡之处隐藏的是对韩愈的偏爱、维护和推崇。
四、《文醇》中韩文的岭南批评
“唐室重内轻外,匪特轻外也,其遐方边徼,朝士得罪者,乃之官焉。”[7]卷四《御选唐宋文醇》中所选录的岭南韩文包括送友文和贬谪文两部分。《送友人之岭南》表达的是韩愈对岭南的想象,自身遭贬后韩愈的文章创作则是其为官岭南的事功和体会,具有文教南行的客观效果。
对于岭南韩文中的送友文,乾隆帝十分重视。在评点韩文的基础之上,发表了一系列关于岭南治理的观点。《送窦从事序》的写作背景是“窦平为广州从事,盖人情所不释然者,故昌黎文以开之。”乾隆帝对于唐时的岭南偏见评论到:“地莫非王土,民莫非赤子,其远于京师,君、相耳目之所难及,则俾牧斯民、抚斯土者,宜较近地有加;意必忠信慈惠、才行卓荦,世所共仰之人,乃宜居之。而以为罪臣责逐之所,何其倒置也!”[7]卷四在乾隆帝看来,岭南因为地理遥远,监管不便,选择官员时更需谨慎认真,选取德行兼备之人。在对唐代岭南任官制度进行批评的同时,也暗含了对现今岭南选官制度的思考。除直接评论外,乾隆帝特在《送窦从事序》文中“是以人之之南海者,若东西州焉”下加密圈(。。。。。。),侧面上显示了对岭南疆域的重视。韩愈在《送郑尚书序》中谈到:“若岭南帅得其人,则一边尽治,不相寇盗贼杀,无风鱼之灾、水旱疠毒之患;外国之货日至,珠香象犀玳瑁奇物,溢于中国,不可胜用。故选帅常重于他镇,非有文武威风,知大体、可畏信者,则不幸往往有事”,强调地方官吏任用与岭南治理之间的关系,甚得乾隆帝之心,对此乾隆帝特意圈出文中“(郑权)家属百人,无数亩之宅,僦屋以居,可谓贵而能贫,为仁者不富之效也”,意在强调郑权之德行。至于韩愈文中所写对岭南的暴力镇压“至纷不可治,乃草薙而禽狝之,尽根株痛断乃止”,乾隆帝认为大为不可。乾隆帝首先考证用兵远疆的历史源头,认为“其用兵之见于经者,虞舜、殷武而已。舜以三旬。殷武以三年。《诗》颂殷武,而《易》称其惫,不无微辞。”一旦对远疆地区兴师征伐,则旷日持久,难以收功。“然亦止是楚地耳,非此序所称岭南五管之远也”,现今岭南相较于商周时期的楚地更远得多。“自汉以降,多用兵于蛮夷,然终莫或得志,孰曾‘尽根株痛断之’哉?就使能‘草薙而禽狝之’,无俾遗种,于帝王御世之道,又乌乎可?”乾隆帝认为“昌黎原未尝以为真可草薙禽狝也”,岭南之人“好则人,民吾同胞,同胞可悉剸以刃哉?”在论证分析之后,乾隆帝强调“读者毋误会昌黎之意,以为‘真有尽根株痛断之’一说也。”[7]卷五
对于岭南贬谪文,乾隆帝一方面看中韩愈的坚守和修养,另一方面则重视其对岭南的教化。《答窦秀才书》作于贞元二十年(804),此时韩愈因为言事之罪,黜为阳山令,因而在文中自述为“远宰蛮县,愁忧无聊,瘴疠侵加,惴惴焉无以冀朝夕。”然而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韩愈仍不忘为君子,并与朋友互相激励:“虽使古之君子,积道藏德,遁其光而不曜,胶其口而不传者,遇足下之请恳恳。犹将倒廪倾困,罗列而进也;若愈之愚不肖,又安敢有爱于左右哉!顾足下之能,足以自奋。愈之所有,如前所陈,是以临事愧耻,而不敢答也。钱财不足以贿左右之匱急,文章不足以发足下之事业。稇载而往,垂橐而归,足下亮之而已。”[7]卷三
韩愈《送区册序》[7]卷五对于岭南才俊区生十分欣赏,乾隆帝则更关注文中“庄周云‘逃空虚者,闻人足音跫然而喜矣’,况如斯人者,岂易得哉”一句,将区生作为难得的人才加以重视,体现了对岭南文教的关心。《燕喜亭记》[7]卷六是韩愈为阳山令时所作。乾隆帝欣赏《记》文“智者乐水,仁者乐山。弘中之德,与其所好,可谓协矣”,强调德好一致,注重德行修养。《祭郴州李使君文》[7]卷七为韩愈祭奠故人李伯康而作。韩愈贞元十九年贬为阳山令,过郴州,识李伯康。贞元二十一年又待命于郴州,二人生平契分,皆具此文。《笔墨间录》云:“祭李郴州文,尤雄奇。”乾隆帝重视如下文句:“美夫君之为政,不挠志于谗构。……幸窃赌其始终,敢不明白而蔽覆”,仍然是坚持和修养。贞元十九年冬,韩愈与张署俱自御史贬为南方县令,永贞元年又同为江陵府僚属。对于《祭河南张员外文》[7]卷七中所叙韩张二人交往情形,乾隆帝朱笔密点“岁弊寒凶,雪虐风饕;颠于马下,我泗君咷……我预在此,与君俱膺;猛兽果信,恶祷而凭?”最终落脚到“屡以正免,身伸事蹇;竟死不升,孰劝为善”一句,乾隆帝对韩愈此文的肯定在于对其朋友德行的表彰,这也侧面表现了对韩愈德行的肯定。
从内容上讲,《文醇》收录韩愈岭南教化文两篇。《南海神庙碑》圣祖御评为:“典重高华,足以润色太平、铺张盛事。后幅拓开一步,文境倍觉宽舒。”张英也言:“结撰闳钜,波澜壮阔,词藻瑰丽,雅足与题相配。”乾隆帝重视“治人以明,事神以诚;内外单尽,不为表襮”“册有皇帝名,乃上所自署”,其文曰“嗣天子某,谨遣官某敬祭。其恭且严如是,敢有不承!”“公又固往,不懈益虔,岁仍大和,耋艾歌咏”“刑德并流,方地数千里,不识盗贼;山行海宿,不择处所。事神治人,其可谓备至耳矣”[7]卷八这些文字,间接地体现了韩文对于太平盛世的襄赞与教化。《鳄鱼文》借《朱子考异》之言表达了韩愈对岭南民生教化的重要作用:“潮人叹曰‘昔韩公谕鳄而听,今公戮鳄而惧。所为虽异,其使异物丑类革化而利人,一也。吾潮间三百年而得二公,幸矣!’”[7]卷十乾隆帝特别圈出《鳄鱼文》中两段文字:“刺史虽驽弱,亦安肯为鳄鱼低首下心,……鳄鱼有知,其听刺史言”“七日不能,是终不肯徙也,……夫傲天子之命吏,不听其言,不徙以避之,与冥顽不灵而为民物害者,皆可杀。”这两段文字正展现了韩愈为民做主、为民除害的勤政爱民的形象。乾隆帝拈出这两段文字表达了对韩愈在岭南行教化的肯定和重视。
从对于岭南韩文的评点中,可以看出其中投射的乾隆帝政治观念。韩文中的岭南是边疆地区的代表,乾隆帝重视边疆、强调对边疆进行文治教化而非武力征服,讲求官员自身的素质,注重对边疆施行儒家仁政。乾隆帝以韩愈为儒家道统表率,以韩文为儒家文统典范。在《文醇》的语境下,文教结合、人文合一成为韩愈的精神内核,韩愈也被确立为“为万世学者之正鹄。”
余 论
乾隆帝在《御选唐宋文醇》将韩愈树立为士人学习的楷模。乾隆帝通过选文、圈点及三方评论等多种手段,以肯定、赞扬和维护的态度,对韩愈的文章和德行进行了充分肯定,并对韩愈的岭南事迹做了表彰。在乾隆帝看来,韩文是“万世学者之正鹄”。韩愈作为唐宋大家之首,是文统和道统的重要表率。
《御选唐宋文醇》甫经刊刻,便通行全国,产生了巨大影响。据《清实录》记载:乾隆五年十一月“广西巡抚方显,以奉到恩颁圣祖仁皇帝《避暑山庄法帖》《御选唐宋文醇》及屡荷垂询微疾,具折谢恩”[9];乾隆六年五月“礼部议准、陕西学政陈其凝疏请颁发《渊鉴斋古文》《唐宋文醇》于陕甘二省刊刻广布学宫,从之”[10];乾隆十三年二月祭孔时“赐衍圣公博士等宴。并赐衍圣公孔昭焕御制日知荟说、及经、史、《唐宋文醇》各一部”[11];在乾隆三十七年四月乾隆帝甚至用《御选唐宋文醇》策试天下贡士:“近代茅坤,裒唐宋为八家之选,存古文法度。本朝储欣,益以李翱、孙樵,搜罗较备。曾令儒臣订定《唐宋文醇》,付梓以行。于《文粹》《文鉴》或不至大相迳庭乎?夫治道期于励精,史书贵乎传信,广屯仓以充军实,观人文以验化成,尔多士讲明有年,其悉意正辞,条具以对,朕将亲览焉”[12]。可以看到,无论是颁发地方、刊布学宫,还是赐书衍圣、以之策士,《御选唐宋文醇》都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御选唐宋文醇》甚至流传到了海疆之上,成为台湾士生之学习范文本:“凡御纂诸书,颁发直省,依式镘板流传,并分给各学,存贮尊经阁,俾士子咸资诵习。书坊贾肆,题行刊印者,听其颁行各省者:圣祖仁皇帝……;高宗纯皇帝……御选唐宋文醇、诗醇、钦定四书文……令各督抚购买,给与有尊经阁之府、州县,交学官收贮,以资诸生诵读。学官时率诸生与之讲贯,令其熟习,学政考试经解,于御纂诸经中,摘取先儒异同之处发问,令生童等条对。”[13]从中我们可以看到《文醇》的传播轨迹:借着御选的地位,官方将《文醇》作为教科书颁布全国学校,教习全国士生,并且不禁私刻,借助民间资本的力量进行最大限度的传播。自乾隆三年《文醇》初刊以来,直至光绪二十一年此书仍在重刻,可见其在清代中后期的广泛影响。
《文醇》的广泛传播也将乾隆帝所代表的官方文章批评和作家批评观念推广到全国,《文醇》中的韩愈和韩文作为“万事学者之正鹄”的古文典范,起着“昭示艺林”的重要作用。《御选唐宋文醇》的刊刻也是韩文批评和韩文接受史上典型案例,反映了政治对于古文批评的介入和影响。
参考文献:
[1]弘历撰.御选唐宋文醇[M]//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447册.中国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2005:120.
[2]孟伟.清代敕修文章选本及其对文风建设的意义[J].社会科学家,2005(6):28-31.
[3]陆德海.从御选文章看康、乾官方文章思想的转变[J].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4):84-92.
[4]王红.明清文化体制与文学关系研究[M].成都:巴蜀书社,2010:501-520.
[5]叶高树.清朝前期的文化政策[M].中国台北:稻香出版社,2002:324.
[6]杜玮哲,马茂军.论《御选唐宋文醇》的古文观[J].安康学院学报,2022,34(1):49-55.
[7]弘历.御选唐宋文醇[M].清乾隆三年武英殿四色套印本.
[8]鲁迅.集外集[M]//鲁迅全集:第七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136.
[9]乾隆五年十一月丙申条[M]//高宗纯皇帝实录:清实录第十册.卷一百三十一.北京:中华书局,1985:918.
[10]乾隆六年五月丙子条[M]//高宗纯皇帝实录:清实录第十册.卷一百四十二.北京:中华书局,1985:1048.
03ef9c67f45bb47964838739b0d95b7a34046099b851ce4113a5990163a662a6[11]乾隆十三年二月戊寅条[M]//高宗纯皇帝实录:清实录第一三册.卷三○九.北京:中华书局,1986:52.
[12]乾隆三十七年四月丙戌条[M]//高宗纯皇帝实录:清实录第二○册.卷九○七.北京:中华书局,1986:134.
[13]台湾私法人事编[M]//台湾文献史料丛刊:第九辑.中国台北:大通书局,2000:125.
收稿日期:2024-01-10
作者简介:张 凯,男,河南安阳人,文学博士,华南师范大学博士后、特聘副研究员。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历代古文选本整理及研究”(17ZDA247)
①《御选唐宋文醇》四库全书本诸家评论并无颜色区分,各家评论容易相混。本文以清乾隆三年武英殿四色套印本为基本,酌以四库全书本为补充。
Eternal Model for Scholars
---On Han Yu in Imperial Tang Song Wen Chun by Emperor Qianlong
ZHANG Kai
(School of Literature, South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Guangzhou, Guangdong 510006)
Abstract: Imperial Tang Song Wen Chun was the official ancient literature anthology selected by Emperor Qianlong himself, guiding and standardizing the direction of the ancient literature anthologies in Qianlong period. In Imperial Tang Song Wen Chun, Emperor Qianlong identified with Han Yu, praised Han Yu and protected Han Yu’s image, taking him as a model of Confucian ethics and his articles as a positive model of Chun Wen, which set up a model for scholars to learn. Han Yu’s articles about Lingnan selected in Imperial Tang Song Wen Chun, while affirming the artistic achievement of Han Yu’s articles, praised Han Yu’s political achievement in Lingnan and his civilization among the people. Emperor Qianlong’s criticism of Han Yu’s articles about Lingnan also shows his political thinking on frontier governance.
Key words: Imperial Tang Song Wen Chun; Han Yu; Anthology of ancient literature; Lingnan; criticis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