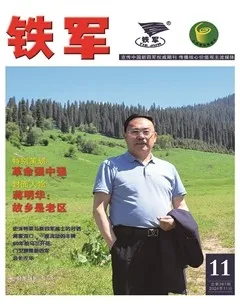《新四军军歌》诞生始末
嘹亮的军歌,不仅凝聚着军魂与军威,也总会让人回想那些激情燃烧的岁月。1939年,由陈毅等集体作词、何士德作曲的《新四军军歌》,成了一首伴随着新四军征战沙场、传遍大江南北的经典歌曲。这首雄壮的军歌,既道出了新四军名称的由来,也展示了新四军的战斗历程、伟大创举和卓越贡献。历经85个春秋,《新四军军歌》依然传递着勇于斗争、敢于胜利的精神力量,激励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军人顽强拼搏、砥砺奋进。
以新四军历史创作军歌
1939年2月,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共中央南方局书记周恩来到皖南泾县云岭新四军军部,传达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精神,研究确定了新四军“向北发展,向东作战,巩固现在阵地”的战略方针。2月24日,新四军军部召开大会,各支队领导集聚云岭。会议开始前,作曲家何士德演唱了歌曲《歌八百壮士》,随即陈毅也在大家的欢呼声中,用法语演唱了《马赛曲》。会后,陈毅很有感触地说,新四军应该像八路军那样,有一支雄壮的军歌,让全军唱起来,以统一思想认识,激励斗志。
创作新四军军歌的提议,得到了与会者的一致同意。随后会议决定,由新四军副军长项英主持创作新四军军歌。项英当即表示:“一首高水平军歌的作用可大了,相当于为新四军编写了一本教科书,可大大提高我军的战斗力,这一点我自己有亲身体验。当年,中央苏区第一方面军取得第三次反‘围剿’胜利后,方面军总政治部即向所属部队发出通知学唱《三期革命战争胜利歌》。当敌人发起第四次‘围剿’时,我们一方面军各部队无论在战前动员,还是在行军途中都高唱《三期革命战争胜利歌》,这既提高了部队的士气,也更加坚定了红军的必胜信念。创作军歌的工作很迫切,前方忙于作战,我们军部人才济济,就在军部征集歌词,然后配曲。现在大家都很忙,我的意见还是各司其职,军歌的创作由袁国平主任来抓。国平作词是行家,抓军歌的创作是最合适的。”
接着,项英就创作军歌提出要求:“第一,应宣传我军的光荣历史和优良传统;第二,要明确我军的宗旨和目标;第三,军歌应该是进军的号角,能催人奋进、勇往直前。只有这样,才是一首好的军歌。”随即,袁国平表示:“创作军歌是政治部分内的事,作为政治部主任责无旁贷。但我对三年游击战争的情况了解不多,还请各位指导。”陈毅立即说道:“我正在写一首叙事新诗,待完成后可供你参考。”项英则说:“我给中央的三年游击战争的报告,你也可以看看。”
经战火洗礼诞生的军歌
1939年3月底,陈毅用白话诗体完成了一首长诗,取名《十年》。随即,袁国平责成朱镜我和时任《抗敌报》副主编的马宁着手在《十年》的基础上修改歌词。很快,他们将长诗改为“光荣的北伐行列中,曾记着我们的威名。我们继承着革命者受难的精神,在南国的罗霄山,锻炼成为钢铁的孤军……风雪饥寒,穷山野营,磨炼我们艰苦奋斗的精神……我们在大江南北,向敌后进军,南京城外遍布抗战的旗旌……前进,前进,我们是铁的新四军。高举新中国的旗帜前进!”作为军歌歌词的初稿送达军部后,项英立即召集军长叶挺、军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军部秘书长李一氓、军部宣传部部长朱镜我等人进行集体讨论,大家认为应突出东进抗战和向敌后发展的思想。随后,在采纳大家意见做了进一步修改后,项英又把歌词发给大家征求意见。
陈毅收到歌词稿后不久,就在给军部的信中写道:歌词很好,表示赞同并建议将“光荣北伐武昌城下镌刻着我们的姓名”中的“镌刻”改成“血染”。最终,政治部采纳了陈毅的意见。
军歌歌词定稿后,即交由教导总队队长、作曲家何士德谱曲。袁国平还特意向何士德详细讲述了皖南的战略环境、新四军的发展方针,强调谱曲时要加强战斗气势。何士德在谱出第一稿后,请教导总队文化队试唱。袁国平和朱镜我听了后认为,第一稿曲调流畅,好听,朗朗上口,可是战斗的劲头不足。
随即,袁国平又对何士德说:“新四军军歌的曲调应高昂雄伟,要有一往无前的进军气魄。”按这个要求,很快何士德写出了第二稿。这一稿没有马上递交审查,而是先在文化队内部试唱,并听取队员的反映。大家认为这一改好多了,雄壮、高昂,节奏鲜明;但不足之处,是新四军指战员大都出身工农,学唱难度较大。于是,何士德再一次作了大幅度修改。第三稿完成后,曲调更加雄壮有力、鼓舞人心,曲与词的结合也比较完美。特别是结尾处,连续三个“东进,东进!我们是铁的新四军!”曲调既有层次,又一次比一次高亢雄健,不仅把全曲推向了高潮,也更加充满了艺术感染力和号召力。
流传中外的《新四军军歌》
1939年7月1日中午,在云岭附近的新村文化队礼堂,何士德指挥军部文化队的歌咏队试唱新四军军歌。项英、袁国平、周子昆、李一氓、朱镜我、黄诚等人出席。当试唱结束后,项英十分高兴地说道:“你们唱得好,唱出了新四军的光荣传统,唱出了新四军的英雄形象。”大家十分赞同,并认为军歌的歌曲很有气魄,表现出了新四军坚决东进抗敌和进军敌后的精神。此时,袁国平当即代表新四军政治部郑重宣布:“通过!”并正式定名为《新四军军歌》。
正当大家沉浸在欢庆之时,日军12架飞机窜到了云岭、中村一带的上空,狂轰滥炸。当地老百姓和部队都有伤亡,文化队的同志也立刻分散隐蔽。警报解除后,项英愤怒地说:“日寇今天的轰炸,对中国人民又欠下一笔血债。我们要用各种战斗来回击敌人,大家要到部队去教唱军歌,用革命的歌声激励士气,打击敌人。”接着,袁国平在讲话中说道:“《新四军军歌》在战斗的血火中诞生了,大家要学好教好。要用歌声鼓舞指战员,向敌人讨还血债……”在项英、袁国平的一番义愤填膺的讲话以后,大家带着满腔怒火和对日本侵略者的刻骨仇恨,再次高唱《新四军军歌》。
1939年8月,陈毅从前线回来时,军部召开盛大联欢晚会。何士德指挥全体指战员高唱《新四军军歌》,唱得整齐、雄壮,使大家精神振奋。当何士德走下台时,陈毅微笑着让他坐在自己身边,一同观看文化队及战地服务团的演出。其间,陈毅幽默地对何士德说:“我是在前方打仗,可是你现在却是在指挥着我们全军作战啰!哈哈哈……”接着,陈毅又说道:“我们有了一首雄壮的军歌了。最后一句‘东进,东进!我们是铁的新四军!’重复了两次,一次比一次高昂,有气魄,意志坚定,这很好!正是我写这个歌词时想强调的地方。”
10月11日,新四军军部在《抗敌报》上刊登了学唱《新四军军歌》的命令及歌谱,要求全体指战员在最短期内唱诵娴熟,“使人人深切了解军歌意义,以军歌之精神为全军之精神,并贯彻此精神于我军战斗中、工作中、日常生活中去。”当时,在皖南采访的美国著名女作家、记者艾格尼丝·史沫特莱,被指战员们学唱军歌的热烈气氛所感染,她在听了袁国平的介绍后,称《新四军军歌》为“时代的强音”,并提笔将歌词译成了英文,传到了国外。德国记者汉斯·希伯也写道:“我在这里听到一支非常流行的歌曲,其中唱道:‘东进,东进,我们是铁的新四军!’在敌后的长江下游流域,没有再比这句响亮的歌词更受欢迎的了。”
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确立《义勇军进行曲》为代国歌后,在上海的中国唱片公司接到了录制国歌唱片的任务。10月1日,中国唱片公司赶制的10张特别唱片运达北京,A面标注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B面标注为《新四军军歌》。由此可见,《新四军军歌》在当时人民心中的地位和影响力之大。
歌曲是有声的精神,精神是无声的歌曲。一首红色旋律跨越时空,贯通着人民军队的精神血脉,汇聚成共产党人和人民军队的精神史诗。85年过去了,这首诞生在抗战烽火中的《新四军军歌》,不仅传颂着永不磨灭的战斗精神,也始终闪耀着时代光芒,不断激励我们从胜利走向更大的胜利。
(作者系南京市委老干部局副局长、市委离退休干部工委专职副书记)
(责任编辑孙月红)